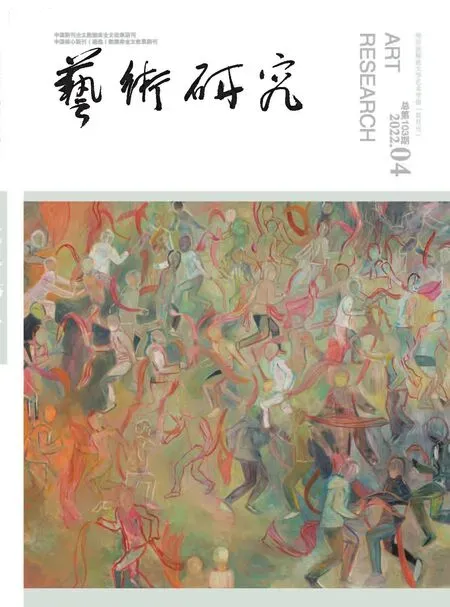“一帶一路”域內旅行記憶遺產及其文化價值
哈爾濱師范大學/王繼慶
記憶遺產這一術語源自《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世界記憶遺產又稱世界記憶、世界記憶工程或世界檔案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文獻保護項目,旨在搶救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中國政府層面也有受到保護的記憶遺產項目選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本文依據這樣的含義來借用記憶遺產術語:它一方面是外在的記憶載體,主要是珍稀文獻,包括古版本及其再生版本、大眾版本;另一方面它是有內在指向性的,即文獻記載的歷史記憶內容,體現出它流傳給后世的地方性知識。本文所說的旅行記憶遺產是指記錄行旅專題的珍稀文獻及其承載的歷史記憶,這里并不特別強調古版本保存方面的瀕危性,其古版本未必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或《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還需注意的是,從功能上看旅游的涵義側重于旅行加娛樂、休閑、教育,旅游多為現代使用的概念,而旅行則是近代之前適用的概念。
一、絲綢之路、“一帶一路”與遺產地旅游
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第1卷中提出“絲綢之路”術語。他還用過大路、主干道、絲綢商路等指代這條東西方交通線路。唐曉峰認為李希霍芬把中國《漢書》、西方古代的馬里努斯和托勒密所描述的中西交通線落實在了現代地圖上。日本學者三杉隆敏研究古代中外陶瓷貿易路線,則較早使用了海上絲綢之路這個專有名詞。他在1968年發表著作《探索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倡議相繼提出。“一帶一路”區域旅游是指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在沿線國家之間開展的旅游,特別是指與絲綢之路遺產有關的旅游。絲綢之路是一個復雜的時空系統。絲綢之路在歷史上和民族遷徙、宗教、貿易、文化藝術有很多淵源。
絲綢之路是學習歐亞文明史的遺產資源。從“整體史”看絲綢之路,其交流、融合、借鑒最多的是貿易和宗教等方面。旅行則反映了社會生活史的一個專題側面。從旅游業發展來看,旅游合作是“一帶一路”合作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參與方不斷擴大。如何增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識和互信,也是旅游研究者應該考慮的問題。人們有必要探索穩定發展“一帶一路”旅游的方法,了解“一帶一路”相關旅游資源的當代價值,以及讓客源國游客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和歷史敘事。
2014年6月22日,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項目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又一例跨國合作而成功申遺的項目,漢長安城遺址、大雁塔、小雁塔等33處絲綢之路遺址點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當年京杭大運河亦入選世界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的中國部分位于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其全段是世界上最長的文化遺產路線。這些世界遺產地為中外游客開展“一帶一路”旅游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2015至2017年中國連續推出“美麗中國·絲綢之路旅游年”,擴大了絲路旅游的國際影響力。
二、東亞及西域旅行記憶遺產梳理
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把歷史區分為長、中、短三個時段,長時段是指一百年乃至幾個世紀的時間段。制約歷史發展的長時段因素包括地理、氣候、生態環境、文化傳統等。中時段研究對象主要是社會經濟結構,而短時段研究對象是事件和個人。旅行記憶遺產總體上反映了所涉區域的歷史文脈,因而具有長時段特征。古代絲綢之路反映了歐亞文明的多元性。從公元前4千年到公元前2千年上古時期,存在從西亞到蒙古草原的青銅之路,屬于早期歐亞物質文明交流產物。而絲綢之路的形成與中國出產絲綢、茶葉、瓷器等貨品,銷售到西亞、東南亞、南亞和歐洲等地有密切關系。東亞各地之間以及東亞和西域之間的行旅由來已久,諸多種類的旅行書寫給后世留下大量長時段疊加短時段的旅行記憶遺產,本文擇其有時代特色者,按從古到今的年代順序梳理如下。
(一)8世紀佛教遠播朝鮮半島
旅行史文獻為絲綢之路歷史敘事提供了史料。例如,中華書局出版《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從1961年出第一種,到1996年為止有10種和中亞歷史地理有關,其中如玄奘、辯機原著《大唐西域記校注》,還有高僧義凈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等。在玄奘大師之前,法顯在公元5世紀就已經西行到西域,并著作《佛國記》。
公元8世紀佛教在亞洲流行傳播,絲綢之路上除了有商人之外就是追求佛法的各國僧侶。新羅佛學家慧超就是其中一位著名旅行家。“依敦煌殘卷所記,慧超系由中原出發沿陸路絲綢之路進入古印度,……進入中天竺,再經舍衛國……,然后經南天竺、西天竺,再進入北天竺諸國,最后歷罽賓、波斯、蔥嶺、疏勒、龜茲等地,于唐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冬返回中國。”新羅佛學家、旅行家慧超著作《往五天竺國傳》,記錄了公元8世紀印度和西亞等地的歷史地理。
從長時段看,絲綢之路與朝鮮半島和日本的聯系較多體現在佛教東傳。唐朝鑒真大師六次東渡日本,唐代中國向朝鮮半島傳播了佛學,后來高麗王朝佛教出現興盛。而更早年代,從公元前2世紀起佛教傳入新疆,也傳入了阿富汗東部。佛教經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國。唐朝禮佛取經的玄奘大師,走的是經過新疆吐魯番的絲綢之路。與玄奘同時代西行取經的還有義凈,而慧超也歷盡千辛萬難到達了印度和西亞。古代旅行中有的旅人受到追求財富目的驅動,也有的旅行者是為了傳播或學習宗教。絲綢之路是商業貿易的路線,也是文明交匯和宗教文化傳播路線。
(二)從崔溥旅行看朝鮮半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聯系
《崔溥漂海錄》表明韓國在歷史上和絲綢之路的某種關聯性。唐宋元時期,中國經由海洋路線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葉等商品遠銷海外。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持續到15世紀,即1405年到1433年鄭和七次下西洋大旅行和沿海貿易活動。鄭和船隊到達了東南亞、印度、斯里蘭卡、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海岸。
崔溥是李朝官員,所處時代距今500多年以前,那時中國為明代、朝鮮半島為李氏朝鮮王朝、日本為戰國時代。鄭和大規模航行停頓了半個世紀之后,崔溥一行人1488年農歷正月從濟州島出發后,遇暴風雨海難而被迫登陸中國臺州附近。他們從寧波地區,到達杭州,經過京杭大運河到北京,最后從山海關經過沈陽,過了鴨綠江而返回朝鮮半島。
《崔溥漂海錄》記錄了4個半月的行程和見聞。盡管崔溥旅行是一次偶然發生的事件,但他們渡過了浙東運河、京杭運河,這就和海上絲綢之路發生了聯系。正如藏彝走廊溝通了北方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后者從成都出發經過云南進入南亞、東南亞的路線,也是明清時期茶馬貿易活躍的地方,茶馬古道的一部分),浙東運河、京杭運河則連接了海上絲綢之路和中國北方地區。
2016年3月,中國中央電視臺《國寶檔案》節目播出電視紀錄片《絲路傳奇崔溥漂海錄》。2016年11月則由浙江省博物館與韓國國立濟州博物館共同籌備了展覽《漂海聞見—15世紀朝鮮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韓國學者樸元熇通過勘校、文本解讀,揭示了作為行紀文獻的崔溥漂海錄從古版本到大眾讀本的流傳過程,以及這份記憶遺產的特殊性和珍貴性。這份遺產展現了崔溥的文人特質、旅行事跡的離奇性。它是一份對朝鮮國王的匯報材料,其中有些內容補充了中國運河修鑿史記錄。古代京杭運河是連接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紐帶。
樸元熇在著述中提到異鄉體驗一一重走崔溥的路、故地重訪。記錄這個旅行體驗,這種歷時性記錄是記憶遺產流傳的重要途徑。時間流逝,世間文物的變化記錄會引起當代讀者對舊文本的閱讀興趣,而且是對“一帶一路”文化傳統的回顧和反思。
《崔溥漂海錄》作為有500多年歷史的記憶遺產,是經由文獻保留和研究傳承下來的,學術研究起到閱讀推廣作用。中國和韓國的飄海錄研究實踐的側重點有一些差別,但都對歷史記憶的形成有一定影響;而且,從學術研究到古道追記,再到電視專題片和展覽,有利于個人記憶向社會記憶轉化,影視化成為新媒體傳播和利用這類記憶遺產的方法,它會影響到學術旅游和文化旅游活動。現代傳媒手段復現歷史記憶或有視角上的局限,人們應注意到相關文物有毀失的情況。電視片《崔溥漂海錄》側重展示海上絲綢之路,啟發了寧波等地的旅游線路可發掘京杭運河等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聯性。
從《崔溥漂海錄》看絲綢之路記憶遺產的形成、流傳和利用問題,對于研究當今“一帶一路”旅游資源的現代價值有很大啟發。“一帶一路”是有歷史傳承的,有文化上的一些共同認識作為基礎。這個例子也說明,韓國與中國遼東地區之間古老的運輸通道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對開展“一帶一路”遺產地旅游有研究價值。
(三)李希霍芬的鳳凰城記憶遺產
由于戰亂、氣候變化、城鎮湮沒等原因,加之海上航線開辟,北方絲綢之路的大部分在晚唐到清代幾乎被阻斷或很少利用。20世紀初建成通車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會使人聯想到,那里就是對古代北方絲綢之路的某種繼承或替代。從14世紀到19世紀末,遼東半島的中朝之間交通路線仍然是暢通的。明朝、清朝都派遣使節出使朝鮮。明清時期來中國的朝鮮使團成員把他們在中國的見聞著錄成書,被統稱為《燕行錄》。鳳凰城是一個重要的中朝交通節點。而且遼東半島乃至朝鮮半島都是蠶絲的產區。近代絲綢工業從中國的四川和江南地區擴大到東北。
1869年5月李希霍芬坐船從煙臺航行到了營口,之后到達丹東附近的鳳凰城,李希霍芬寫道,那里在3月、5月和9月有朝鮮人可以三次過來和中國人交易商品。他提到,“我來的時候正趕上交易日”,即1869年6月9日至10日。他對所遇見的朝鮮人整潔而禮貌的印象,包括外貌和裝束都予以贊揚。朝鮮人在這里交易的商品除了牛皮以外,“他們還賣一種質量很好的紙張,很厚,還有鉛、海參和絲綢”。而且“他們的絲綢都是野蠶產的,但是比遼東出產的質量要好。”
這些記錄說明丹東附近在19世紀中葉與朝鮮保持商品貿易,當時朝鮮出產牛皮、絲綢和紙張在邊境貿易時帶到中國出售。遼東地區扮演了那個時代如同絲綢之路一樣的角色。現在丹東是中國游客赴朝鮮旅游的重要口岸,昔日的遼東之路正成為旅游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
(四)斐士的中亞旅行記憶遺產
斐士先生(Emil Fischer)是出生于奧地利的旅行家,曾經長期在天津工作,活躍在民國時期商界和教育界。他在一次演講中介紹了乘坐飛機到甘肅省城蘭州的旅程,斐士文獻對于認識近、現代北方絲綢之路的具體情況大有裨益。1935年11月19日斐士在天津文學會作演講,并配有幻燈片,第二天即11月20日,演講報告發表于《京津泰晤士報》英文版,以下為其演講的開篇:
“首先感謝大家的厚愛,讓我講一講最近在中國遙遠西北地區的旅行。說到遙遠的西北,那意味著我四十年在華旅行達到了一個高潮,由于中國的政治形勢,對于以前沒去過的那幾個省城來說,去那里旅行的重要性便提升起來;例如,以前沒有機會到訪寧夏府。寧夏坐落黃河岸邊,對面是鄂爾多斯,處于甘肅省城蘭州和綏遠的半道上,蘭州是北平-包頭鐵路經過的城市,京包線穿過中國及內蒙古的邊疆。寧夏的地毯工業十分有名,早在天津成為中國工業領軍城市之前就廣為人知。
沿途有在六盤山隘口照的照片,六盤山海拔2942米,點綴著無比靚麗的山間湖泊,如同嵌入山里的大鍋,山巒環抱著蘭州府,山間谷地的北端,黃河西去的河床十分開闊,顯然在這里旅行會十分艱難。為了便利交通和旅行,現在已修建了公路。1907至1909年建成的蘭州跨黃河鋼橋是個現代化的進步,便利了來往于新疆和蒙古的幾千個商隊,也方便了穆斯林經亞洲內陸腹地,到麥加進行朝拜。”
可見,由于鐵路等交通線路的形成,蘭州、西寧成為北方絲綢之路旅行的重要交通節點。旅行家斐士還十多次經過西伯利亞大鐵路到達歐洲,途中記錄了土西鐵路及附近工業,這是斐士西文文獻與中亞交通經濟相關的記憶遺產。值得注意的是,西文文獻舊稱中亞地區為“土耳其斯坦”,因而土西鐵路全名為“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它是連接西伯利亞鐵路和中亞地區的鐵路線。
三、回應新的絲綢之路
法國學者魯保羅基于西域文明史視角探討西域當代問題時,提出是否會有一條新的絲綢之路的疑問。
“一帶一路”有關的記憶遺產可以回應這個提問,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匯的時空體系,從旅行記憶遺產角度闡釋絲綢之路的豐富內涵有利于理解其時空多樣性、歷史連續性,以及了解歐亞交通網絡在不同時代的人文特征。《崔溥漂海錄》表明,中國東北是連接陸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關聯地帶。京杭運河、萬里茶道等遺產資源具有當代價值,在發展文化旅游時,傳播基于旅行記憶遺產的“一帶一路”歷史知識將為擴大人文交流和促進民心相通起到積極作用。
絲綢之路遺產資源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應先行傳播“北方絲綢之路”文化,從文旅融合、旅游區域合作層面為“一帶一路”倡議擴大人文交流合作范圍。中國東北在共建中蒙俄經濟走廊、擴大圖們江旅游合作過程中應積極推進萬里茶道遺產地旅游。中國東北一直存在與“一帶一路”的歷史關聯性。西北地區則是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地帶,在推廣北方絲綢之路遺產旅游方面有獨特資源優勢。總之,邊疆省份應重視北方絲綢之路遺產旅游,力爭早日籌建與北方絲綢之路相關的客源市場。
①唐曉峰.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M],讀書,2018(3).
②陳淑霞.慧超行紀所見絲路沿線宗教狀況考析[J],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
③斯蒂芬·戈斯,彼得·斯特恩斯,蘇圣捷 譯.世界歷史上的前近代旅行[M],商務印書館,2015.
④樸元熇.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M],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
⑤李希霍芬,蒂森 選編,李巖、王彥會 譯.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 上冊[M],商務印書館,2016.
⑥筆者譯自斐士著《沿新開通隴海線進行的甘肅和青海之旅—從海岸邊到西域》,《京津泰晤士報》英文版1935年11月20日
⑦魯保羅,耿昇譯.西域文明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