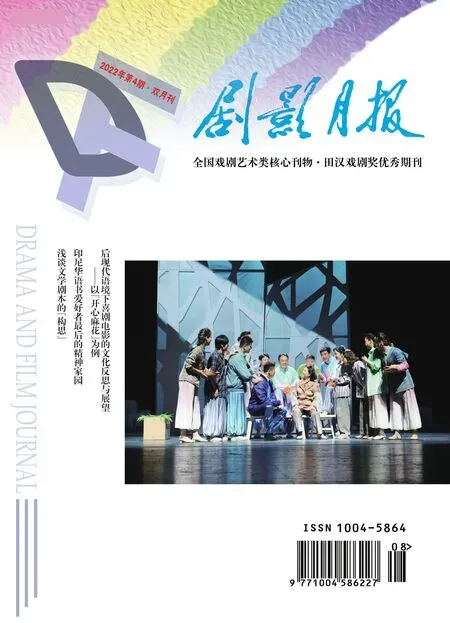對當下我國聲樂表演藝術審美體現的思考
■魏佳
聲樂表演藝術通過將原本書面結構化的音樂作品以演唱者二度創作的形式轉化為流動的音響結構存在,這不僅是二度創作過程中對聲樂作品核心結構的展現,更是演唱者在探索聲樂藝術過程中演唱者對聲樂作品所持的特有審美觀。將歌詞結構與音響結構有機結合,使原來的聲樂作品煥然一新,并且在實踐演唱環節中,從聽眾欣賞、演唱者二度創作的實際過程中,體現聲樂表演的審美功能。在聲樂表演的二度創作中,演唱者以主導的意念為統領來表達情感,對聲樂作品的構造進行解讀。這種以主觀為驅動的二度創作聲樂活動,都在我們研究審美體現的范圍之列。二度創作首要達到的兩項基本要求:一是盡最大化地還原作品,詮釋作品原意;二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將原書本上結構化的音樂作品活靈活現地轉化為流動的音響作品。為達到這兩點要求,不僅需要考驗演唱者掌握的技藝水平包括語音、音節、語義、形與神,而且涉及演唱者對情感處理的把控和舞臺上的心理調節能力。為抓住作品的形與神,演唱者不僅要領會音樂作品的思想內涵、傳達出客觀事物的精神風貌,最重要的是在表演過程中,基于作品本意的前提下,展現演唱者的審美情感。
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美的聲腔要求一直都是“依字行腔”、“字正腔圓”。因此在實際演唱中,演唱者需要充分依據字音、地方戲劇特色,調動人聲嗓音的手段表達出準確的思想感情,美化語言藝術。以湖北民族歌劇《洪湖赤衛隊》為例,自1958年首排至今,已多次改編和創作。1958 年版的《洪湖赤衛隊》,韓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在演唱時采用湖北特色的咬字發音方式,在歌曲《洪湖水浪打浪》中,歌詞“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水”發音為“sui”,“啊”發音為“na”;歌詞“太陽一出閃呀么閃金光啊”,“出”發音為“cu”;歌詞“共產黨的恩情比那東海深”,“深”發音為“sen”。在歌曲《沒有眼淚,沒有悲傷》中,歌詞“喝的是湖中水”,“喝”發音為“huo”;歌詞“韓英我加入了共產黨”,“入”發音為“yu”。韓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在發聲的方法上深受民歌、傳統戲曲唱法的影響。從審美角度來看,王玉珍行腔樸實自然,貼近湖北方言的韻味,能夠走入人民群眾的內心。在聲音的位置上,王玉珍從頭至尾使用了頭腔共鳴,位置靠前,使得聲音更加明亮,具有穿透性。在咬字處理方面,王玉珍對字音有著嚴格的把控,吐字清晰洪亮,收尾干凈,特別的是,為了增加當地的民族特色,王玉珍在咬字時采用了湖北特色的發音方式,并融合了傳統戲曲的韻味,表現出了強烈的湖北風味。正是王玉珍結合當地傳統語音特色,較口語化的處理,切身去體驗當地人的生活環境,使得人民群眾在欣賞作品的過程中,能夠理解人物心境,融入于情節中,產生直接的心靈觸碰,帶來精神深處的共鳴。對比國家大劇院復排版本的歌劇《洪湖赤衛隊》,韓英的扮演者吳娜在保留傳統戲曲特點外,在歌唱語言上改為普通話,利于新時代的觀眾在欣賞歌劇的同時,更好地理解作品。從審美角度來看,與日常生活相適配的普通話更易于新時代觀眾欣賞作品、面對面地與舞臺交流。這種“二度創作”即表演者對歌詞語言方式的藝術處理,加強了觀眾對歌曲情感的理解,讓觀眾感同身受。從兩部民族歌劇的反響來看,1958年版的《洪湖赤衛隊》讓觀眾更加記憶猶新,反響強烈。一部優秀的民族歌劇作品,最重要的是表現其民族性,聲腔的表達是作品獨特的魅力。依照詞的咬字、吐字習慣進而對音調產生影響,采用地方特色的行腔,抓住作品的形與神,這種地方戲劇特色正是中國民族色彩的體現。用這種語言表達方式講述“中國故事”極大地釋放了我國民族歌劇的審美功能,以音樂展現多元的文化符號。
在聲樂表演過程中,歌唱者是在遵循原曲作者“一度創作”的基礎上,根據自身主觀想法上進行“二度創作”,也就是對聲樂作品的再創作。這種以主觀意念為導向的再創造,我們把它稱為“實”。此外,音樂作品這一客體事物通過傳導媒介傳入聽眾的耳朵,喚起聽眾的審美注意力,產生一種對音樂主觀的審美體驗與感受,這種審美活動是復雜的、多變的。于聽眾而言,在欣賞音樂作品過程中,所喚起的審美心理活動與表演者再創作的心理路程具有極大的差異性。這種虛無的音樂審美欣賞過程,我們又把它稱為“虛”。首先,我們在“二度創作”中發現了表演者的審美思想價值。歌唱者的“二度創作”是在把握尊重原作的基礎上發揮創造,歌唱者們需要了解作品背景、思想內涵,對作品的內容進行準確的闡釋,掌握作品的風格基調。在完成以上嚴密的研究后,根據歌唱者成熟的表演能力進行再創造,在聲樂作品中加入自己的獨到見解、新穎的形體表演動作、聲音音色及舞臺風格。
由舒楠作曲的《燈火里的中國》,作者明言創作這首歌曲的初衷旨在歌頌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展現人民燈火般燦爛的臉龐。作為春晚的必選節目,幕后幾位參與創作者們采用了一男一女的對唱形式。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品選用兩位不同唱法的音樂家,一位是通俗唱法,另外一位是民歌唱法。演唱過程中,歌唱家張也沿用淳樸的民歌唱法演唱,與周深空靈的通俗演唱手法相融合,以舒緩、細膩、溫暖又不失有力為基調,在歌曲結尾的吟唱中,雙聲部的演唱時二人分工明確,張也負責低聲部,夯實歌曲柔美悠揚的基調,緊接周深一連串的高音,將歌曲的氣氛烘托到了高點。寬闊的音域體現音樂作品的大氣磅礴,與作品的主題即對祖國的美好祝福以及對未來的欣然向往相呼應。在舞臺美術上,舞蹈演員身著發光的燈籠服飾,與歌唱者們一同在舞臺上升起,背景選用XR(擴展現實)技術,真實還原城市夜幕下的街市景色,打造了一個極具科技感又貼近生活的舞臺。為了作品的整體效果,在綜合創造中也包含了形體美,男女歌唱演員在演唱中全程面帶微笑,時不時地四目對視,以一種無聲的語言塑造著和諧、溫情的氣氛。挺拔的身姿、舉手投足間的優雅,給人以美感,展現了風度儀表美。演員的形體美也同樣對舞臺表演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燈火里的中國》以出彩的演出迅速引發學唱熱潮,有聽眾聽完歌曲后,腦海展現了鮮活的畫面,寫道“仿佛看到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來的飛速進步,從一個個燃油燈的小村落到城市里的萬家燈火。”有的聽眾在閉眼欣賞作品時,腦海中浮現“萬家燈火,家家團圓的溫馨畫面。”除了一般審美感知、聯想與情感體驗等共性因素外,不同聽眾的欣賞水平、習慣、趣味、聯想等也會產生不同的審美效果。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聲樂表演藝術也在不斷演變與發展。聲樂表演藝術不僅是人類杰出的創造,更是反映人類精神生活的載體,不僅在聲樂表演的活動中體現聲樂的審美功能與價值,甚至體現了人類對情感表達的積極和自我創造。聲樂表演藝術所代表的“文化”,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而發展,是一切聲樂活動與實踐的總和,且具有廣泛的聽眾類型,結合不同的審美需求、審美情趣、所處的社會條件,產生了不同類型的聲樂審美主體。比如,原始社會聲樂藝術的誕生是為了滿足人類生命存在,是為獲取生活資料而進行的各種勞動活動的聲樂藝術;嬰幼兒由于年紀尚小沒有音樂感知力,但他們能夠在有節奏的拍撫和輕聲細語的哼唱中安然入睡,即滿足了生理與心理的平衡。而當下不少藝術工作者們通過復排民族歌劇來銘記人民經久不衰的民族精神,歌頌祖國偉大復興的新局面,其間對歌劇創造性的改編則展現了人們新時代下的審美變化。
如今,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們擁有便利的渠道去欣賞音樂,人們可以通過互聯網隨時隨地欣賞聲樂藝術,可以走入大劇院、音樂廳、演播廳等場所近距離地欣賞聲樂表演藝術。世界各地的聲樂大獎賽也遍地開花,聲樂表演藝術越來越受到大家的喜愛。大眾在觀賞聲樂表演時也受到聲樂文化審美導向的影響,所以對于聲樂文化創作者們來說,為大眾審美樹立正確的審美觀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就要求表演者在創作過程中的首要原則是必須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進行創造,不能偏離詞曲創作者的創作意圖,真實地再現創作者要表達的思想內容,秉持真實性與創造性相結合的原則,同時還要注重表演技巧和音樂作品的藝術表現、正確的演唱方法,提高審美能力,從而促進我國聲樂表演藝術的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