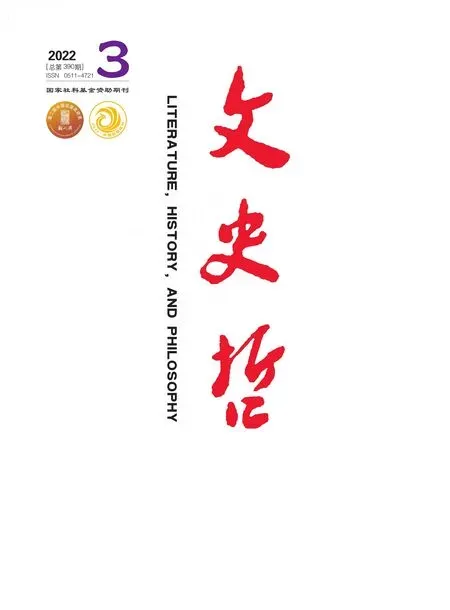儒家的現代化轉型和新時代中國的理論構建
姚 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0)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說:“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在習近平總書記回信一周年之際,我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談一下如何實現儒家的現代化轉型,并由此構建中國新理論的問題。
歷史上任何留存到今天的理論都是對當時主流歷史進程的回應。今天我們談儒家的現代化轉型,首先是要回應當代中國發生的最為顯著的歷史進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引領中國實現了經濟上的巨大飛躍,并將在未來三十年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做到的?這是當代所有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關心的終極問題。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國學者做出了許多努力,試圖總結中國成功的經驗并形成新的經濟發展、制度轉型、社會變革和政治轉型的理論,為我們理解中國、為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然而,這些理論很少直接涉及黨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更很少將黨的實踐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去發展新的國家治理理論。另一方面,官方理論滯后于黨的實踐,無法準確描述改革開放時期黨的成功實踐。這些都是中國面對世界有理說不出的關鍵性原因。
一、從反傳統到禮敬傳統
之所以無法產生新的理論,是因為我們要么被國內的舊理論所束縛,要么被西方的理論所束縛。舊理論還是關于革命的理論,已經不適合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現實;西方的理論是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總結,其中包含很多由西方經驗形成的成見,也不適合當代中國的現實。要形成屬于當代中國自己的理論,就必須跳出上述兩種理論的束縛。在擺脫現有理論的條條框框之后,我們就會發現,黨在改革開放之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黨對中國優秀傳統的回歸。
在哲學層面,黨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傳統。中國務實主義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在認識論層面不承認永恒的真理,二是在實踐層面以結果為導向,手段服務于目的。這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延伸。孔子不信鬼神,對學問和人生采取經驗主義的態度,“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禮記·中庸》)。世間沒有永恒的真理,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實踐是結果導向的,實踐的手段要服務于目的。仁是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但在不同的場合,仁和不同的實踐結合在一起。“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剛、毅、木、訥近仁”,等等。仁是最高理想,但實現這個理想的手段視情景而不同。就如“貓論”一樣,目的比手段更重要。務實主義讓黨擺脫了以往的教條式實踐,開啟了改革的大門;務實主義也讓改革者放棄畢其功于一役的震蕩療法,采取小步快跑的漸進道路,讓中國的改革走得比蘇東國家更平穩、更有效。
在政治領域,黨回歸中國選賢任能的傳統,從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干部四化”起,不斷完善干部選拔制度,使之成為中國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選賢任能的基礎是儒家的人性論和對個人修養的追求。不同于西方單一的人性觀,儒家認為人性是多樣的、流變的和可塑的。孔子盡管認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但相信“中人可教”;孟子相信每個人都有善端,“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荀子盡管認為人性惡,但相信通過“化性起偽”(《荀子·性惡》),人仍然可以成為圣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個人修養的最佳順序和最高境界。儒家對個人修養的關注與墨家對賢能的強調相結合,就形成西漢以降中國官僚帝制的一個重要元素——選賢任能。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實踐在國家治理方面對世界的一大貢獻,在今天西式民主向著民粹主義退化的當口,這個貢獻顯得尤其重要。
在經濟領域,黨放棄了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采取混合所有制下的市場經濟,分配原則也從按勞分配轉變為按要素分配。過去,我們常把這些轉變說成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殊不知,中國早在北宋就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市場,那時的中國和后來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差距,只在于沒有產生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現代技術。搞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的回歸,而按要素分配與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賢能主義完全一致。獎勵先進、懲罰懶惰、淘汰落后,既是市場原則,也是中國賢能主義的原則。
在社會領域,黨鼓勵傳統文化的回歸,傳統節日得到恢復,國學熱、國風熱此起彼伏。賢能主義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且也體現在社會領域,能力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推動力。社會分層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可以為一個社會保持活力提供重要動力,怕的是分層的固化。放眼世界和中國歷史,社會分層的固化和能力作為進入特定階層的憑據之間是相互排斥的。一個以能力為導向的社會不容易形成階層固化,而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一定不會欣賞能力。現今中國社會的賢能主義雖然有走過頭的地方(特別是在基礎教育和高中教育領域),但總體而言為中國社會注入了活力,是中國對發達國家保持追趕態勢的重要動力。
黨的實踐已經超越了理論工作者的步伐,如何將黨的實踐轉化為新的理論,是擺在當代中國學人面前的重任之一。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回到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中去,從那里開始新理論的構建。
二、儒家的現代化轉型
從儒家思想出發構建新的理論,首先就遇到對待儒家的態度問題。社會上的儒學熱,很大程度上是把儒家當作修身養性的學說來講,而不涉及儒家政治哲學的一面。學術刊物發表的多數關于儒家的論文,則是把儒家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而不考慮儒家的現代意義。學界也存在復興儒家政治哲學的努力,但其中也問題多多。多數理論停留在對儒家理想原型的構建之中,而沒有與現實相勾連;多數研究也沒有回應啟蒙運動以來的世界主流價值;在方法論上,多數研究沒有采取當代哲學的分析方法,從而沒有改變“儒家沒有邏輯”的偏見。許多人的一個顧慮是,儒家已經被定性為替專制辯護的政治哲學,今天談儒家的復興因而有重新為專制辯護的嫌疑。這個顧慮來自兩個認識誤區。
一個誤區是對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誤解。“專制”是描述中國古代社會時出現最為頻繁的名詞,但秦統一之后的中國,不能以“專制”來簡單概括。如錢穆早已指出的,秦的統一實現了“化家為國”,即國家不再是國王一家的私產,而是屬于天下的公產。自漢到宋的國家治理不是皇帝一人獨大,而是存在皇權與相權以及后者所領導的政府之間的分權;到宋代,士大夫更是形成了以天下為己任的風氣,而御史的彈劾和監督權也達到頂峰。如福山所指出的,西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接近現代意義的強政府國家,比西方提前了2000年。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秦之后的中國不應被簡單地稱為專制社會(更不應該被稱為封建社會,因為秦已經結束了封建社會),而應該被稱為“官僚帝制”,即皇帝與群臣共治的制度。皇帝代表治統,但由宰相和他們領導的政府實施治理權,這種理性安排是中國古代實現強大國家的原因。
歷史地看,官僚帝制是中國的偉大發明。西方出現過雅典這樣的民主城邦,但這種城邦只適合小型社會;況且,希臘半島上那么多的城邦,也只有雅典實行過民主制度。西方也出現過羅馬共和國,但它最終被帝制所取代。自一萬年前進入農耕文明以來,人類文明社會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都采取了君主帝制,而像中國古代社會這樣理性的官僚帝制,是寥若晨星的存在。我們的先人不僅發明了一種近于現代的治理模式,而且為這個模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學,這就是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經過他改造的儒家學說。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說,以天作為皇權合法性的來源;同時,他也強調皇帝作為天子所應盡的責任,以孟子“民為貴”的思想約束皇權。我們不能因為中國的官僚帝制延續了2000年就怪罪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回到董仲舒的時代,天人感應說為西漢以及此后一千年的長治久安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政治哲學。社會和學界之所以長期把儒家和“專制”聯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明清政治的影響。然而,南宋之后中國政治走向衰退,總體而言是一個文明盛極而衰的結果,具體的導火索則是北方蠻族的入侵。儒家不應該為此負責。儒家在宋明時期的轉型,與其說是導致中國政治走向衰落的原因,毋寧說是儒家為適應中華文明進入停滯期而進行的調整。
另一個誤區是把儒家看作一成不變的、過時的東西,沒有看到儒家學說中能夠與現代價值相勾連的元素。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評價孔子的所有思想,是不公平的。在孔子生活的時代,孔子的思想超越了當時的主流觀念,即便是與同時代的希臘先賢相比,也并不落后。如阿瑪蒂亞·森所指出的,與比孔子晚出生100多年的柏拉圖相比,孔子并不更加相信君主的權力。在孔子之后的2000多年里,儒家被多次改造,在經歷宋明理學的改造之后,更是遁入內心,不僅失去了事功的能力,而且也的確成為皇權的附庸。這正是我們要回到先秦儒家那里的原因所在。軸心時代的每一位先哲都至少參透了人的問題的一個面向,而儒家對人性的看法比任何軸心時代的思想家都更客觀、更全面。儒家關于人性具有多樣性、流變性和可塑性的觀點,與當代心理學和靈長目動物學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自霍布斯以降,西方的政治學說都建立在“人是自利的”這一個對人性的單一假設之上,由此產生的政府(國家)被想象為原子化的公民之間的一個均衡契約。沿著這一思想,西方建構起精巧的國家治理模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模式日益顯露出來頹勢,西方許多國家被原子化的民粹主義裹挾,有滑入不可治理性的危險。儒家的客觀人性論具有極大的現代意義,為我們構建與自由主義民主不同的現代政治哲學打開了大門。
在西方文明興起的歷史中,曾經有過重新發現雅典的過程。我們今天也要重新發現先秦儒家,用現代哲學的方法發掘經典儒家思想的當代意義,并建構新的理論。就新的政治哲學而言,沿著儒家多樣的、流變的和可塑的人性走下去,我們就可以得到與自由主義民主很不同的國家治理模式:每個人都具備成圣成賢的潛能,但由于努力程度的不同,每個人達到的成圣成賢的高度也不同,政治安排因此應該獎勵較高成就的人。據此,選賢任能應該成為具有憲法地位的制度。如此構建的治理模式排斥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但并不拒絕自由主義的個人價值和個人自決原則。儒家相信每個人具備相同的潛能,把個人修養作為君子的一個重要品格,同時也肯定個人通過努力而取得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尊重個人價值。在人際關系方面,儒家秉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核心的中庸態度,因而為社會個體進行自我決策留出了自由的空間。儒家拒絕自由主義抽象的平等,接受建立在賢能基礎之上的比例平等。這可能會讓多數人認為,儒家不支持平等。但是,因為相信每個人具備同樣的潛能,儒家不會拒絕旨在鼓勵每個人發揮其潛能的平等措施,如教育的平等供給。事實上,這樣的平等取向在現實中比抽象的平等更加可取。在政治領域,它防止了對平等的濫用,是民粹主義的一副高效解毒劑;在分配領域,它拒絕福利國家,而把注意力放在提高民眾收入和其他基本能力上面,因而更可能實現可持續的共同富裕。
三、結 語
過去兩千年里,中華文明經歷了兩次外來文明的大沖擊,一次是佛教,一次是西方文化。我們花費了一千年才把佛教完整地吸收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信仰,而且改變了中國人的哲學,宋明理學就是在對佛教的回應過程中產生的。我們現在還在第二次文化沖擊之中。自1840年打開國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如對佛教的吸收一樣,我們必須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發展出來的價值吸納進我們自己的文化之中。西方文化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其力度遠大于佛教的沖擊,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花費比吸收佛教更長的時間去吸收西方文化;當代人比古代人具備更多的歷史自覺。吸收西方文化不意味著被動地去接受,否則就會像日本那樣,在經濟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在文化和哲學領域仍然是兩張皮,不能產生新的理論。用一個比喻來講,我們的態度應該是:用中國自己的思想資源為筐,有選擇地去盛西方的文化價值,打造一只全新的美麗花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