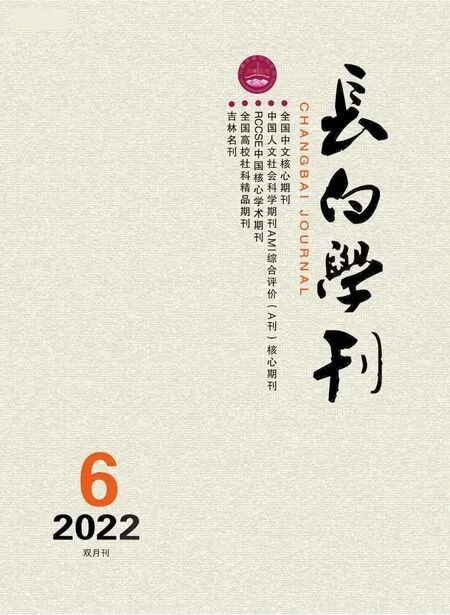民族聚居特困區減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機制探索
王曙光,杞 迪
(1.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1)
一、引言:民族聚居特困區域的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民族聚居特困區是我國扶貧攻堅的重點和難點,其中“三區”和“三州”更是重點中的重點、難點中的難點①“三區”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田地區、阿克蘇地區、喀什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和四省藏區(青海玉樹、四川阿壩、甘肅甘南、云南迪慶);“三州”是指甘肅的臨夏州、四川的涼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三區”和“三州”都是民族聚居特困區,其發展長期受到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歷史條件的諸多約束,貧困發生率普遍在20%左右。[1]256,257涼山彝族自治州(簡稱“涼山州”)是比較典型的集中連片深度貧困區和民族聚居特困區,涼山州的反貧困斗爭是中國反貧困事業中最為艱苦卓絕的組成部分之一。涼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川滇交界處,全州幅員6.0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533.11萬,境內有彝、漢、藏、回、蒙等14個世居民族,其中彝族占54.16%,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脫貧攻堅戰前夕,全州17個縣(市)中有11個縣為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深度貧困縣,全州貧困村有2072個,其中貧困發生率在20%以上的有1350個、50%—80%的383個、80%以上的71個②數據來源:涼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網《五年脫貧大事記》,http://www.lsz.gov.cn/ztzl/rdzt/tpgjzt/tpyw/202106/t20210623_1944934.html。。“十三五”期間,涼山州政府和人民頂著“貧困中的貧困”的帽子迎難而上,通過系統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勝利。4個貧困縣在2019年脫貧摘帽,7個貧困縣在2020年脫貧摘帽,全州累計退減貧105.2萬人,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較“十二五”末增長2.8倍③數據來源:涼山州政府工作報告(2021年),http://www.lsz.gov.cn/xxgk/zfgzbg/202104/t20210401_1868626.html。,徹底擺脫了絕對貧困,創造了涼山發展史上的奇跡,在全球減貧史上亦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表1 十三五期間涼山州各縣(市)脫貧情況
當前,涼山已經徹底擺脫絕對貧困。在這一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上,深入總結涼山州的扶貧攻堅經驗模式,具有特殊的理論價值和政策價值,對于中國乃至全球反貧困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同時,涼山的相對貧困程度還很嚴重,反貧困斗爭遠遠沒有結束,如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如何在已有偉大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減少相對貧困、提高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如何將脫貧攻堅與未來的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是涼山州面臨的緊迫問題,也是決定未來涼山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當前輿論界流行著一種聲音,認為現在脫貧攻堅階段已經過去,“貧困”或者“扶貧”的討論是“過去時”了,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且有害的。如果說涼山州消除絕對貧困的“脫貧攻堅戰”是一場偉大的“殲滅戰”,那么涼山州相對貧困的緩解和鄉村的全面振興,則將是一場更為艱苦也更為復雜的“持久戰”,必須通過系統性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創新,才能實現這樣一個愿景。本文的探討包含兩方面:一方面,通過對阻礙涼山州發展的“三要因”分析框架的構建,深刻分析涼山州在區域發展、個體行為(文化)、公共行為(公共產品供給)等方面存在的內在問題,為下一步涼山州減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構建“產業—教育—生態—文化—社會”五位一體的發展框架,為涼山州未來發展找到準確的著力點。
二、從“區域發展-個體行為-公共行為”的“三要因”分析框架看阻礙涼山州發展的因素
涼山州的貧困問題屬于典型的族群型貧困,是制度供給不足、區域發展障礙、可行能力不足等類型貧困的綜合體,同時又受到民族文化習俗和歷史發展階段的深刻影響。[2]涼山州歷史上長期處于奴隸社會,社會發展滯后,同時偏遠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經濟和產業形態、不健全的社會保障等因素都同其長期貧困高度相關。在將這些不同維度的致貧因素納入考慮后,本文嘗試針對涼山州提出“三要因”分析框架,以期能夠厘清涼山州發展滯后的關鍵機理。所謂“三要因”,包括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資源稟賦約束下的區域發展障礙,兩個“重要原因”,即部分落后歷史文化所導致的貧困人群的“貧困行為”以及社會公共服務和制度供給嚴重不足,前者屬于個體行為視角的分析,后者則涉及公共行為視角的分析。
(一)根本原因:資源稟賦約束下的區域發展障礙
盡管經濟發展與貧困減少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但對于尚處于發展中國家階段的中國來說,經濟發展無疑是貧困減少的重要解釋因素。[3]相對應的,發展落后則是中國許多“老少邊窮”地區長期貧困高發的根本原因。涼山州最主要的區位特征是地處我國西南腹地而域內山高谷深。在這樣的先決條件下,涼山州的產業結構長期處于農業以傳統農業為主、工業十分依賴原礦石開采和初加工,第三產業受交通嚴重掣肘的狀態,十分缺乏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強力引擎,域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涼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北抵大渡河,南至金沙江,西連橫斷山脈,東臨四川盆地。全州轄區90%以上都是山地、高原地形,域內海拔最高處與最低處相對高差達5653米。這樣的區位條件下產生的第一個不利因素就是交通通達性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涼山州基本沒有公路,僅西昌到小廟機場有幾公里可通車。直到今天,同州外、省外大部分地區相比,涼山州的交通仍然處于路網稀、質量差,勉強能滿足人民出行需要的狀態。地處偏遠、山高谷深、交通閉塞基本奠定了過去涼山州經濟發展的基調,使得涼山州很大程度上被“隔”在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之外。農業上,小農經濟下的傳統農業在涼山州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盡管域內特色農業資源豐富,但缺乏“走出去”的物流體系和外部市場,使豐裕的特色農業資源難以實現市場價值,更因資金和農業技術人才的匱乏而難以實現傳統農業的現代化轉型,農業生產效率極為低下。工業上,涼山州工業直至1950年解放時才實現了從零到有的突破,工業基礎薄弱、開發無力加之地域封閉,工業發展遭受很大困難。改革開放后涼山州的工業發展有了較為顯著的進步,但規模以上工業產業主要產品結構仍然單一,主要為原礦石和礦產品,處于價值鏈的底端,附加值低。第三產業方面,盡管州內生態旅游資源、民族文化資源豐富,但同樣因為地處偏僻而交通不便,文化旅游產業的發育長期滯后,與該地區璀璨的民族文化遺產不相匹配。尤其是州府西昌以外的其他地區,閉塞程度更高,經濟基礎薄弱,服務業配套設施落后,對當地群眾的收入提升難以有較大貢獻。
(二)個體行為視角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因素導致的“精神貧困”
關于貧困人口行為的研究是貧困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學術界很早就提出行為是導致貧困的直接機制[4],貧困人口的行為會對政府扶貧政策的效果產生較大影響[5]。具體來講,一些貧困源自于貧困人口做出不利于提高個人生產力或者是增大個人風險的行為,例如生育過多后代、單身生育、接受教育意愿低等。而貧困人口做出該類行為則常與所接受的文化有關。[6]涼山州作為我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最后走出奴隸制的地區,歷史上遺留下的部分落后文化長久影響著域內人民,成為部分人群選擇吸毒、輕視教育、過分懶散等行為的誘因,最終導致這些人群收入水平下降。當然,貧困和這些落后文化因素是相互影響的,個體行為影響到貧困,而貧困反過來強化了個體行為,最終形成一種“貧困——個體行為”長期的惡性循環。
截至2020年,涼山州戶籍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占57.56%,其中彝族占54.16%,涼山州的貧困問題很大一部分是彝族的貧困問題。[7]彝族特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塑造了涼山州經濟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使得涼山州擁有別具一格的彝鄉特色。一方面,彝族特有的生活習俗、節慶、服飾、手工藝品、舞蹈等民族文化,是我國多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價值;但另一方面,歷史上當地落后的社會制度和部分落后的社會文化也成為涼山州長期貧困的根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奴隸制生產方式仍在涼山彝族地區占主導地位,涼山州的社會發展形態嚴重滯后于國內其他地區。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涼山地區進行民主改革,涼山州從奴隸社會一步跨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政治制度的“一步跨千年”卻不等于社會各方面的“一步跨千年”,毒品問題就是典例。歷史上,涼山州鴉片泛濫,存在大量種植和出售鴉片的現象,吸食鴉片被視為奴隸主貴族的特有待遇,是富貴的象征。在這種落后文化的影響下,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涼山彝族對毒品仍然保持著極度錯誤的傳統心理認識,彝族聚居區仍然普遍存在提供毒品以招待貴客的現象[8],涼山州毒品犯罪呈現普遍高發態勢。以2018年為例,涼山兩級法院一審受理毒品刑事案件916件1426人,審結853件1180人,占全州刑事案件的25.99%①數據來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網《依據指導意見從嚴懲處助力涼山脫貧攻堅》,https://www.sc.gov.cn/10462/12771/2019/4/25/7b232de666ac439bb0e1a1c6d7e036c2.shtml。。同時,與毒品相伴的艾滋病問題、涉黑問題也在涼山州泛濫,“黑”“毒”“艾”嚴重影響涼山州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毒致病、毒病致貧、毒病致孤”成為涼山州脫貧攻堅過程的重要難題。
“黑”“毒”“艾”之外,“精神貧困”現象的產生也受到了涼山州過去落后的社會制度和部分落后社會文化的影響。早期,從奴隸制社會中解放出來的許多彝族同胞并沒有接受過現代教育,他們對外界的高速發展知之甚少,仍然保持著落后的生活習慣。早婚早育現象普遍,一個家庭往往子女眾多但并不重視孩子的教育,最終導致了貧困的代際傳播。隨著涼山州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扶貧政策的推進,許多涼山州人民的“脫貧意識”逐漸覺醒,但仍有部分人觀念落后,習慣于“等靠要”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缺乏依靠自身脫貧的志向和行動。在涼山州的脫貧攻堅戰中,對個體行為的深刻理解是施行正確的扶貧策略的重要前提,否則扶貧效果就要打折扣。即使在脫貧攻堅戰結束之后,改變這種落后的文化意識也是實現涼山州未來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和先決條件。
(三)公共行為視角的重要原因之二:社會公共服務和制度供給長期嚴重不足
宏觀上存在資源稟賦約束和區域發展障礙,微觀上部分個體受落后歷史文化影響易誘發致貧行為,這兩點導致涼山州的反貧困存在“先天不足”,需要通過持續的公共服務和制度供給來彌補。但在脫貧攻堅前夕,涼山州在農村基礎公共設施、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等公共服務和制度供給方面存在嚴重不足,無法扭轉上述提出的“先天不足”現象,成為貧困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道路、住房、飲水、用電等農村基礎設施方面,涼山州一些地處偏遠、生態環境惡劣的村落存在住危房、用電無法滿足日常生活需要、飲水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沒有硬化路的情況。曾經在網絡上廣受關注的“懸崖村”昭覺縣支爾莫鄉阿土列爾村就是缺乏基本道路公共設施的典例。曾經這個逼仄的山村進出全憑12段218級藤梯,攀爬落差達800米的山崖②數據來源:涼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網《涼山“懸崖村”村民下山記》,http://www.lsz.gov.cn/hdjl/hygq/shrd/202005/t20200521_1602821.html。。在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服務方面,過去涼山州社會福利院、城市養老和敬老院、救助站、殯儀館等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數量少、質量低。2015年,涼山州鄉鎮(街道)、社區(村)就業社保服務機構標準化率僅為13.05%,社會保障卡持卡人口覆蓋率僅為51%。③數據來源:《涼山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第一章第一節發展基礎-專欄1。醫療水平落后,迄今涼山州全域僅有四家三甲醫院,均位于西昌市內④分別為涼山州第一人民醫院、涼山州第二人民醫院、涼山州中西醫結合醫院和西昌市人民醫院。數據源自涼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網,http://www.lsz.gov.cn/zwfw/jcfw/ylfw/yyml_41184/202108/t20210823_1989326.html。,州內其他縣市人民遇到大病、罕見病往往選擇到西昌市甚至成都市治病,花費巨大。在教育方面,涼山州教育基礎薄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全州15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為14.03%,遠遠高于全國同期人口文盲率4.08%⑤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六號);涼山州統計局-涼山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五號)。。基礎設施差、師資力量匱乏更是曾經涼山州教育供給缺乏的直接體現。2014年,涼山學前三年毛入園率50.73%,僅有3所公辦村級幼兒園。[9]在金融服務方面,全州存在金融業發展不平衡、種類少、規模小、金融體系不健全等諸多問題。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制約,涼山州大面積鄉村地區長期處于金融基礎設施薄弱、金融服務缺位的狀態,農村貧困地區金融服務的主力軍僅有郵政儲蓄銀行以及四川銀行等少數幾家金融機構。[10]以郵政儲蓄銀行為例,截至2020年底,在涼山州下轄的17個縣(市)288個鄉鎮中,郵政儲蓄銀行共有營業網點122個,覆蓋率僅達42%,超過半數鄉鎮存在金融服務缺位現象。而四川銀行在涼山州境內則只有43個網點,其中還有半數以上(25個)位于涼山州首府西昌市域內。融資上,全州直接融資占比小,以間接融資為主要融資方式,同時銀行業資金外流的“系統性負投資”現象長期存在:2020年底,全州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1241.16億元,各項存款余額2688.01億元,存貸比例約為2.17,顯著高于四川省該年存貸比1.30①數據來源:涼山州數據源自《涼山州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四川省數據計算自《四川省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三、突破發展瓶頸,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涼山州模式探究
(一)發展特色產業,突破資源稟賦約束和區域發展瓶頸
區域發展障礙是涼山州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因此,找到能夠帶動涼山州經濟發展的強力引擎就是解決當地貧困問題的根本之策。涼山州的脫貧智慧在于充分利用當地特色資源來培育壯大特色產業,用特色產業發展來為扶貧事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真正朝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方向穩步邁進。
高山深谷是過去阻礙涼山經濟發展的重要區位因素,卻也是涼山州各類特色農業資源的搖籃。化不利為有利,涼山州依托當地特色農業資源,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起一批極具涼山特色的產業,用產業扶貧撐起了涼山州脫貧攻堅的“半壁江山”。2016—2020年,全州累計投入61.49億元實施扶貧產業項目2037個,40.24萬貧困人口依靠產業脫貧,占2016—2020年全州脫貧總人口的48.13%。②數據來源:涼山州“十四五”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初稿),http://www.lsz.gov.cn/xxgk/ghjh/zxghs/202109/t20210926_2020098.html。“十三五”期間,州政府推出并踐行“制規劃增投入、狠抓主體培育、突出利益聯結、強化技術幫扶、堅持市場導向”的產業扶貧理念。美姑縣洛俄依甘鄉阿卓瓦烏村是該理念指導下涼山州產業扶貧的一個縮影。阿卓瓦烏村村民原大都以種植玉米、土豆、蕎麥等傳統農作物謀生。后來,政府充分考慮當地日照、陽光、氣候等自然條件,為阿卓瓦烏村制定了發展葡萄種植業的科學規劃,并助力該村建立農村合作社,邀請專家為農戶進行葡萄種植技術培訓。在此背景下,阿卓瓦烏村葡萄基地以“政府+公司+合作社+農戶”的合作方式建立起來,當地農民通過流轉土地取得土地流轉金、進入園區務工獲得工資、按照股份比例分紅等多種方式分享整個葡萄種植產業的增值收益。葡萄基地帶動了該鄉256戶891人脫貧③資料來源:涼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網《美姑阿卓瓦烏村:葡萄成了致富的“新引擎”》《“美姑甜”大棚生態葡萄基地 葡萄產業“甜”美姑》,http://www.lsz.gov.cn/jrls/gzdt/xsdt/201910/t20191014_1278981.html,http://www.lsz.gov.cn/jrls/gzdt/xsdt/202009/t20200901_1681876.html。,未來更是有通過建立農家樂、發展鄉村旅游、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方式進一步增收的可能。
上述涼山州產業發展模式可以進一步總結為政府主導下的特色農業產業從無到現代化,并將利益通過農村集體經濟這種機制普惠地分享至當地貧困戶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從特色產業選品到龍頭企業的引進、生產合作社的建立,從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培訓到最終產品通過“以購代捐”、政府推介等渠道流通至市場的整個流程,政府起了關鍵作用。而未來要實現各類特色農業產業的持續性發展,使當地農民從中持續獲取收益,需要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要警惕龍頭企業發現“政策紅利”削減后就撤出、特色農業項目抵抗滯銷、價格走低等市場風險的能力低、特色農業產品銷路過于依賴政府等情況。從長遠性、市場化的角度為特色農業產業的發展進行謀劃,關注產業發展中配套設施和服務的提供(如引進農業保險),真正盤活特色產業發展鏈條中的各要素。

表2 “十三五”期間涼山州產業脫貧理念與實踐
(二)加大以教育為核心的公共產品制度供給,徹底擺脫落后文化意識
教育是改變落后文化、掃除社會陋習的治本之策。發展教育對于扶貧工作不僅具有提高人力資本效率的直接作用,更具有“開民智而啟新風”、塑造更符合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社會風尚的間接作用。如果說產業扶貧有力消除了物質上的貧困,那么發展教育就是消除精神上貧困的有力保障。只解決物質上的貧困,精神上的貧困最終還將反映到物質上的貧困中來,使扶貧事業無法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對于涼山州這樣全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存在一些落后社會歷史文化的地區,教育扶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涼山州人民政府充分認識到了扶智對于扶貧的獨特意義,以抓牢基礎教育和健全教育資助體系為兩個主抓手,大力投入到了教育扶貧中去。這兩項措施最大限度上保證了廣大涼山州人民能夠接受到適當的教育,具備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生活的基本素質;能夠從娃娃抓起逐步清除過去文化糟粕影響下形成的社會陋俗;能夠“開民智、啟新風”,提振貧困人口脫貧積極性和主動性。
抓牢基礎教育方面,涼山州展開了一村一幼、“學前學會普通話”等專項活動,并堅決貫徹國家控輟保學政策。2018年,“學前學會普通話”政策開始推進,以“聽懂、會說、敢說、會用”為目標,力爭實現幼教點具有正常學習能力的3—6歲學前兒童(含7歲未接受義務教育兒童)能夠使用國家通用語言進行溝通交流,縮小其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后同從小說漢語的學生的差異。同時,涼山州全方位建立控輟保學工作保障體系,堅持依法控輟、行政控輟、扶貧控輟、質量控輟、情感控輟,以“不落下一個學生”的態度精準把握學生失輟學原因,有針對性勸返。最終,涼山州基礎教育取得了很大提升。第七次人口普查時,涼山州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6.41年提高至7.41年,文盲率由14.03%下降為10.80%。①數據來自涼山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五號),http://tjj.lsz.gov.cn/sjfb/lstjgb/202106/t20210602_1924589.html。建立教育資助體系方面,涼山州致力于建立“縱向貫通、橫向聯通、集獎助貸勤免補多位一體,覆蓋學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力保脫貧攻堅路上沒有一個學生被落下,力爭阻斷貧困和失學之間的代際惡性循環;教育資助政策不僅惠及學生,還以資助職業技能培訓的方式惠及農牧民。

表3 涼山州脫貧攻堅期的主要教育資助政策
上述模式下,涼山州基礎教育公平得以保證。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標準化、現代化的教育不等于同外界完全一致的模式化教育。作為少數民族聚居區,涼山州的教育應該有能夠反映當地民族特色、滿足少數民族同胞精神文化需要的部分。彝文教學、彝族文化科普和傳承等內容也應該通過課堂或其他校園活動的形式在中小學校教育中得到重視。
(三)實行易地搬遷,走出“貧困陷阱”,實現生態保護與人類發展的雙贏
對于位于高寒深山、土地貧瘠、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易地搬遷具有阻斷效應,能夠阻斷人類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惡性循環鏈條。[11]通過易地搬遷的形式,政府能夠更加集中高效地為部分貧困人口提供住房、用水、用電、道路等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真正為部分生存條件惡劣的貧困人口筑起更為長久的基本生活屏障。涼山州的高山深谷中,存在一些“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的小山村,當地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還處在較為落后原始階段,往往是扶貧工作中難啃的“硬骨頭”。涼山州積極推進易地搬遷工作,幫助該部分貧困人口以搬新家的方式解決其長期發展問題。
涼山州全州易地扶貧搬遷安置住房7萬余套、搬遷人口35.32萬人①數據來源:涼山州人民政府網《涼山易地移民搬遷:住上好房子過上好日子》http://www.lsz.gov.cn/xxgk/zdlyxxgk/zfbz/202106/t20210623_1944800.html。,是四川易地扶貧搬遷攻堅戰主戰場。以昭覺縣為例,該縣縣城集中安置點是四川省規模最大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安置了來自全縣28個鄉92個邊遠山村的3900余戶居民,總安置人數超過18000人②四川省人民政府網《全省規模最大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啟動搬遷入住1.8萬昭覺貧困老鄉搬新家》https://www.sc.gov.cn/10462/12771/2020/5/11/d854ff0713494d9db1063c1879856267.shtml。。安置點內配備文體等基本配套設施和幼兒園。除可以享受安置點內的基本公共服務,許多從邊遠鄉村遷入的貧困人口還將更加便捷地享受縣城的教育、醫療等資源,行路難、吃水難、用電難、通信難、上學難、就醫難等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生存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同時,涼山州十分重視易地搬遷戶的后續發展問題和融入問題。在搬遷戶后續發展方面,涼山州出臺了《促進涼山州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就業增收十條措施》,通過有組織勞務輸出、建設產業園區、“扶貧車間”、“扶貧基地”創造就近就業崗位,鼓勵群眾開展生活性服務業創業等多種方式解決搬遷戶的收入問題。在搬遷戶融入方面,州內一些安置點通過因地制宜配套生活菜地、提供“日間照料中心”等服務項目使暫時無法適應新生活的老人真正融入安置點。另外,除了做好遷入區的工作,涼山州未來還應該關注遷出區的生態恢復工作,避免“一搬了之”的情況,在充分利用易地搬遷工作的機會同時抓好當地生態文明建設。未來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大對于群眾就業的支持力度,使搬遷出來的群眾能夠就地解決就業、就地提高家庭收入、就地實現社會保障,為未來涼山州低收入人群的可持續發展奠定產業和就業基礎。
(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實現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活化
八百里涼山,民族文化璀璨無比。保存最為完整的彝族文化形態、瀘沽湖畔的摩梭風情文化、長征時“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的紅色文化……這些歷史文化遺產都在涼山州的崇山峻嶺之間迸發出無窮活力。其中,包含彝族語言、彝族文字與文學、彝族服飾、彝族傳統工藝美術、彝族節慶、彝族傳統音樂舞蹈、彝族信仰與祭祀、彝族傳統民俗等眾多組成部分的彝族文化是涼山州最為獨特的文化資源,具有寶貴的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和產業價值。截至第五批中國非遺名錄,涼山州共有20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中15項與彝族息息相關。脫貧攻堅期間,涼山州重視彝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并積極探索活化“文化”以帶動脫貧,有了“非遺+扶貧”的有益嘗試,形成以下的涼山模式:
1.區分不同文化特質,采取差異化保護和發展措施
涼山州的彝族文化是一整套內涵豐富的文化,它反映了古往今來彝族同胞生產生活的不同方面。在嘗試保護和挖掘彝族文化資源時,涼山州沒有將其簡單籠統地對待,而是科學識別了彝族文化中不同組成部分的特質,有區別地加以保護和發展。以火把節和口弦兩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例。火把節起源于彝族先民對火的原始崇拜和對自然的戰勝,是涼山彝族眾多傳統節日習俗中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最具濃郁民族特色的節日。作為節慶民俗類文化,在外來文化和現代文化不斷涌入涼山州的情況下,火把節展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涼山州在以保護為主的前提下,圍繞火把節進行旅游規劃,在有序傳承的基礎上進行產業化發展,每年吸引大量游客,為當地許多群眾帶來了可觀的旅游收入。2019年火把節假日期間,涼山州共接待游客390.69萬人次,同比增長3%,實現旅游收入18.87億元,同比增長23.01%。③數據來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網《燃情狂歡、活態傳承、文旅融合,涼山火把節“吸睛”也“吸金”》,https://www.sc.gov.cn/10462/12771/2019/8/8/50b6969ae79248248da9d05c1ab58ed3.shtml。彝族口弦則是彝族民間樂器中最普及最獨特的傳統樂器。彝族口弦音樂更因可以模仿彝語聲調曲折而成為彝族同胞表達情感的方式。作為傳統音樂類的文化,口弦在近年存在式微的情況。甘洛縣全國人大代表潘成英曾擔憂地表示,在大涼山喜歡口弦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而且經常學不了多久就外出打工,更談不上技藝精通。因此,對于口弦,涼山州政府的重點工作落在搶救性保護上。布拖縣文化館定期邀請口弦制作匠人或演奏師開展培訓班;昭覺縣文化館面對中小學生開展了彝族“口弦”免費教學工作,致力于使口弦文化在當地得以保存和發展。這些民族藝術形式也可以通過各種演出、節慶和其他市場化機制來實現其傳承和發展。
2.激發各類主體動能,擴大文化產業發展的惠及面
對于適宜產業化的文化,其產業化離不開政府、文化傳承人、各類市場主體的多方努力。為使適合產業化的文化“活”起來,政府應該發揮頂層設計和底部支撐的作用,為文化產業化指明正確的方向、提供制度化的支持,充分調動非遺傳承人和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讓文化本身釋放其獨特的魅力。越西縣樂青地鄉瓦曲村就是充分發揮彝族銀飾制作技藝手工匠人的作用,實現非遺傳承和脫貧“兩不誤”的典例。2016年,瓦曲村的第一書記找到同村的銀飾手工匠人曲目阿且,請他教村里的貧困戶做銀飾。后來,瓦曲村探索出“支部+農戶+貧困戶+合作社”的模式,成立銀飾加工專業合作社,為該村的脫貧致富助力很大。2019年3月,瓦曲彝族非遺手工銀飾傳統工藝工坊被授予國家級“非遺扶貧工坊”。截至2020年,瓦曲村360戶村民中有200戶從事銀飾加工,每戶年收入均達5萬元以上。①數據來源:涼山州人民政府網《非遺助力脫貧攻堅為涼山脫貧攻堅增一抹亮色》,http://www.lsz.gov.cn/xxgk/zdlyxxgk/ggwhty/202012/t20201221_1787241.html。
3.保護尊重和創新發展傳統文化,開拓具備市場價值的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化是對文化的“活化”,是使文化通過產業化的形式在當地人民的生產生活中不斷出現而得以保存的一種方式。而產業化的成功與否與市場高度相關,要想使民族文化產品獲得廣闊的外部市場,創新必不可少。文化產業的創新必須建立在保護文化內核不變的基礎上,可以體現在產品設計、商業模式、營銷手段等產業鏈各環節中,最終目的是通過創新使得文化產品能夠為市場所了解和喜愛。唯品會駐四川涼山傳統工藝工作站的建立就是涼山州借助“互聯網+”的新興業態,將非遺傳統工藝項目推向市場帶動當地貧困人口脫貧的典例。該工作站由唯品會提供創意設計幫助和推廣銷售平臺,再通過工作站下若干非遺扶貧工坊為貧困群眾提供非遺技藝指導和產品訂單。以唯品會為橋梁,將非遺項目與市場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非遺+扶貧”的模式下,要理順文化和扶貧的關系。利用“非遺”文化資源進行扶貧不是把民族文化簡單地作為商品去發展,而是對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活化。扶貧與文化之間良性的互動關系既體現在扶貧后少數民族同胞更有機會在物質生活富足的前提下發展文化,又體現在文化本身可以成為少數民族同胞脫貧的獨特資源,實現“借扶貧重拾文化”和“用文化助力扶貧”的良性互動。要想發揮好這種良性互動關系,就不能忘了保護民族特色文化的本心,在文化產業化和對文化的創新過程中就一定要謹慎對待、尊重文化核心內涵。同時,我們還應在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活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文化遺產的產業化、市場化和文化扶貧過程中,注重其組織形態的革新,大力推廣新的民族文化產業化的組織形式,鼓勵少數民族村落建立有規模的手工藝術合作社、文旅產業合作社,從而提高文化扶貧的組織化程度和集約化程度,有效提升其市場競爭力,提高其市場回報。[12]
四、未來民族聚居特困區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的“五位一體”框架
近年來,民族特困區脫貧和鄉村振興的成功實踐總結起來包含三個層面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一是在產業層面,要突破長期影響當地經濟和產業發展的約束條件,有效綜合利用域內各種產業資源,并運用創新型的體制機制實現產業的市場價值,尤其是通過發展專業合作社和農村集體經濟實現貧困人口的普惠式收入提升和整體脫貧;二是在文化和教育層面,通過“扶貧+扶智”的有效機制,提升當地民族群眾的可行能力,并通過文化教育實現移風易俗,改變當地某些個體中存在的落后文化意識觀念,從而在文化觀念和精神上實現貧困人群的現代化轉變,同時充分挖掘當地的優秀民族文化以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實現民族文化遺產的活化;三是通過易地搬遷,在改善生態環境、保護綠水青山的同時,徹底改變貧困人群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條件,從而徹底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實踐證明,這是一種極為有效的、典型的“經濟產業+文化教育+生態保護”發展路徑,對未來民族特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應作為長期發展戰略持久堅持,不斷深化。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涼山州“十三五”期間取得的偉大成就,但反貧困斗爭不是一勞永逸的。當前,我國民族聚居特困區的絕對貧困已經消除,但是緩解相對貧困的工作還相當繁重,民族聚居特困區相對貧窮落后、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基本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產業扶貧、教育扶貧、易地搬遷、文化扶貧的事業需要朝著做強產業、做好教育、搬過來住得下的方向穩步邁進,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文化建設和制度供給也尚需不斷健全。
當前,那些閉塞的民族聚居特困區正在逐漸消失,未來民族聚居特困區的開放程度將不斷提高,將更加深度地參與到全國的經濟發展循環中去。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聚居特困區更需要深耕自身比較優勢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找準定位,更需要走出一條具有區域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以適應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從高原生態種植業、特色經濟水果、特色養殖業等特色農業,到“風電”“水電”等綠色低碳優勢工業,再到依托當地特色民族文化資源的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盤活民族聚居特困區獨特的要素稟賦是產業發展的關鍵。在此過程中,需要激發廣大民族聚居特困區各族人民的主人翁意識,發展壯大特色產業,保護傳承民族聚居特困區的獨特文化,創建與現代接軌卻不脫離民族本色的大美鄉村。另外,在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轉變的過程中,民族聚居特困區還要注重內生性機制建設,從而降低低收入人群對外生力量的依賴,發揮其積極主動的創新精神;同時,還要通過社會網絡的重建,通過貧困人群的組織化,尤其是要通過完善鄉村治理,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積極推動合作社建設,大力支持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從而使民族聚居特困區的反貧困工作向可持續的縱深推進,構建強大有效的社會網絡[13],把民族聚居特困區真正建設成為鄉村振興的模范地區。
綜上,民族聚居特困區未來要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與可持續發展,應構建一個“產業—教育—生態—文化—社會”五位一體的發展框架:在產業方面,通過發揮資源稟賦方面的比較優勢,發展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地方特色的農業產業和工業產業,提升產業的附加值;在教育方面,大力提升當地人民的教育水平,通過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打造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在生態方面,在以往大規模易地搬遷的基礎上,進一步恢復搬遷區生態環境,并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適度發展生態產業,發揮生態保護的經濟效益;在文化方面,繼續提煉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和優化民族文化產業的商業運作機制,使民族文化遺產在保護的前提下實現內生性發展;在社會層面,通過構建現代化鄉村治理體系,打造堅強有力的社會網絡體系,提高傳統民族社區的治理能力和凝聚力。我們相信,通過這樣一個五位一體的發展模式,民族聚居特困區未來一定會實現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迎來一個民族發展的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