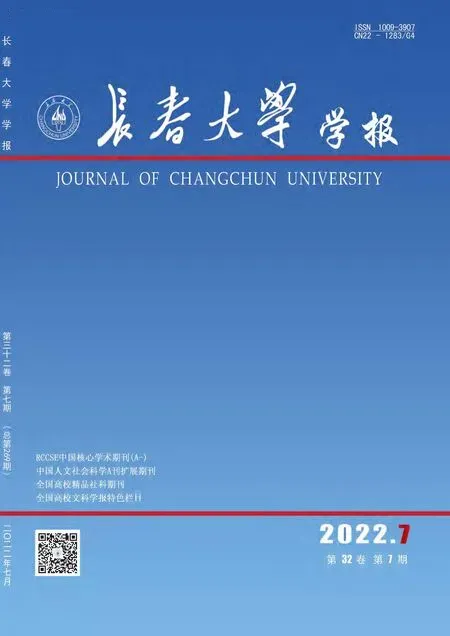共同體視域下的家園書寫比較研究
——以《饑餓的路》與《生死疲勞》為例
吳曉梅,許宗瑞,2
(1.安徽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合肥 230036;2.上海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上海 201620)
本·奧克瑞(Ben Okri,1959—)的長篇小說《饑餓的路》(TheFamishedRoad,1991)與莫言(1955—)的作品《生死疲勞》(2006)在創作風格上均濫觴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這一源頭分流至非洲和中國,結合各自民族中豐富的傳統文化,觀照社會現實,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非洲魔幻現實主義和中國幻覺現實主義。盡管兩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同“源”不同“流”,兩位作者身處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然而,他們面對自己的國家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問題和挑戰時,不約而同地將故鄉作為小說的創作背景和國家的縮影,家園書寫成為他們作品的共同主題,凝結著他們對傳統“共同體”的理性思考。《饑餓的路》與《生死疲勞》聚焦普通民眾,通過他們的生活變化反映社會變遷,傳遞出構建理想家園的強烈渴望。因此,研究作品中的家園書寫主題,可以探究兩條不同的“流”如何經由相異的國度重新匯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共同憧憬和探索理想的共同體。
一、同“源”不同“流”的“共同體沖動”
奧克瑞是尼日利亞第三代英語作家,繼圖圖奧拉(Amos Tutuola,1920—1997)、阿契貝(Chinua Achebe,1930—2013)與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之后,在西方國家和中國產生了重要影響。《饑餓的路》是其重要代表作,曾榮獲1991年英國最具權威的文學獎——布克獎,受到讀者與評論界的一致好評,被公認為非洲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典型作品。對此,美國文學評論家亨利·劉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曾在1992年6月28日《紐約時報書評》上發表的《生者與未生者》一文中指出:“奧克瑞在創作技巧上表現出了與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相似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卻將小說的主題、結構完美地融入了傳統的約魯巴神話中。”[1]我國當代實力派作家邱華棟認為,“《饑餓的路》是一部具有尼日利亞本土文化傳統風格的魔幻之書”,“既借鑒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又挪用了非洲傳統的神話傳說”[2]。在尼日利亞的約魯巴文化中,“阿彼庫”(Abiku)是幽靈王國的幽靈兒童,需要遵守幽靈之王的規定,輪流投胎于人間。這些幽靈兒童為了早日逃離人間疾苦,約定在投胎之后不久便夭折,重返幽靈王國相聚,頻繁往返于生死界。《饑餓的路》中的主人公阿扎羅是一個“阿彼庫”,因為厭倦了生死循環的狀態,且不忍傷害慈愛的父母,決定背棄誓約留在人間,由此開始了充滿抗爭與苦難的生存之旅。奧克瑞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非洲傳統文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呈現了尼日利亞特殊時期的現實家園。
莫言是享譽世界的中國作家,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他于200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是其幻覺現實主義代表作之一。對于莫言的創作風格,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瑞典學院院士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教授曾指出,“我不否認莫言的寫作確實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但莫言的‘幻覺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主要是從中國古老的敘事藝術當中來的”,“將虛幻的與現實的結合起來是莫言自己的創造,因為將中國的傳統敘事藝術與現代的現實主義結合起來是他自己的創造”[3]。《生死疲勞》講述了山東高密東北鄉西門屯地主西門鬧被槍斃后分別轉生為驢、牛、豬、狗、猴和大頭嬰兒藍千歲的故事,時間跨度從中國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土地承包制、市場經濟直至千禧之年。小說借助幻覺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結合佛教中的“六道”輪回和苦難救贖思想,展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家園畫卷。
《饑餓的路》與《生死疲勞》兩部作品雖然采用了獨特的創作手法,但都植根于現實主義,描寫本國社會、政治、文化、歷史等現實情況,關注時代變遷與人的生存狀態。誠如有學者所言:“在書寫人在重大變動下的生存方面,文學從未缺席,也無法缺席,這既是文學關注人的命運的天然本性,也是文學對時代社會肩負的重要使命。”[4]家園書寫之所以成為兩部小說共同的主題,正是源于文學作品所肩負的特殊使命以及文學家們的“共同體沖動”,“即憧憬未來的美好社會,一種超越親緣和地域的、有機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體形式”[5]。由此可見,兩部作品緣何在分“流”之后,可以重新聚合在一起。這種“共同體沖動”正是構建理想共同體的內在動力,促進我們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探索與追尋。
二、真實性的家園再現
《饑餓的路》與《生死疲勞》兩部作品主要反映了歷史轉型時期兩個國家面臨的現實問題、機遇和挑戰。《饑餓的路》講述了尼日利亞于1960年獨立前后面臨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和社會秩序等的重建與探索。多年的殖民歷史致使國家羸弱、民生凋敝,現實的家園不免讓人心憂。《生死疲勞》的故事從1950年展開,描寫飽受苦難的國家和人民在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真實地再現了特殊時期的社會現狀。相似的歷史背景使得兩位作家都選擇了苦難敘事的寫作手法,以此勾勒出真實的家園景象。
(一)艱難的生存狀態
奧克瑞在《饑餓的路》中通過描寫苦難呈現現實家園。饑餓和貧困是苦難的外在表征,始終穿插于作品中,正如奧克瑞本人所言:“苦難是這本書的突出特征之一,人們經受的苦難各不相同。”[6]2000年,莫言在斯坦福大學發表《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的演講,肯定了饑餓在其文學作品創作中的重要地位。《生死疲勞》對于饑餓與苦難的描寫同樣具有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饑餓的路》的主人公阿扎羅一家所在的貧民窟是尼日利亞整個國家的縮影,貧民窟居民是國家苦難大眾的典型代表。阿扎羅父母雖然努力工作,卻始終在貧困線上掙扎,饑餓更是生活常態。奧克瑞在小說開篇寫道:“起先是一條河。河變成了路。路向四面八方延伸,連通了整個世界。因為曾經是河,路一直沒能擺脫饑餓。”[7]1另外,在阿扎羅降生儀式上,幽靈之王對他說:“你將帶去無窮無盡的煩惱。你要走過許許多多的路,才能找到你的命運之河。”[7]6顯然,饑餓的“路”隱喻整個國家的生存現狀,“河”象征人的命運。如同路上會有艱難險阻、河流會有暗流涌動一樣,人們的生存之路與命運之河總是充滿各種磨難。奧克瑞在整體概述之余還通過阿扎羅的視角細致描寫了人們的生存狀態:
他們在鹽袋、水泥袋、木薯粉袋那無可理喻的重壓下打著趔趄。重負擠壓著他們的腦袋、壓迫著他們的脖子,他們臉上的青筋暴突到了快要炸裂的程度。他們的表情如此扭曲,看上去已經不成人樣。我眼看著他們在重負下扭彎了身體,眼看著他們跑動時兩膝向內彎曲,汗水似泡沫一樣從身上淌下。[7]156
莫言在《生死疲勞》中則通過地主西門鬧投胎轉生為西門驢的視角反映出貧苦的社會現實。在中國1959年至1961年大饑荒時期,西門驢描述了自己被饑民殘殺的場景:
……但隨之而來的大饑饉,使人變成了兇殘的野獸。他們吃光了樹皮、草根后,便一群餓狼般地沖進了西門家的大院子。……我感到腦門正中受到了突然一擊,靈魂出竅,懸在空中,看著人們刀砍斧剁,把一頭驢的尸體肢解成無數碎塊。[8]88
對于人類的苦難生存狀態,哲學家們往往會探討其根源所在,叔本華早已對此作出解釋:“痛苦之為痛苦是生命上本質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9]由此可知,兩部作品為何對苦難敘事情有獨鐘。
(二)惡劣的生存環境
兩部作品均從不同角度描述了自然環境受到的人為破壞和摧殘。《饑餓的路》通過阿扎羅視角反映出森林散發出受傷、被掠奪的氣息——“我們經過一棵被砍倒的樹,紅色的液體從砍剩的樹墩上流下,就像一個巨人慘遭殺害,鮮血流個不停。”[7]18《生死疲勞》中亦有類似描寫:“這片樹林子,沒被砍掉當了煉鋼鐵的燃料真是奇跡。完全是因為這林子里有一顆古柏,砍一斧,嘩嘩地流出血來。”[8]140值得注意的是,兩位作家均將樹木擬人化,樹木流血隱喻自然遭到摧殘。樹木同樣具有生命,但往往被人們忽視,現代工業文明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卻悄然破壞了人們本應珍視的生態環境。
物理空間的家亦是家園書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理想之家與現實之家始終密不可分,因此,兩部作品均對現實住宅進行了細致描寫。《饑餓的路》中阿扎羅的家在連日暴雨侵蝕下變得異常破敗——“夜間,雨水從屋頂縫隙漏了進來……我們只得不時把床從房間的一角挪到另一角。情況越來越糟,房間里到處都在漏水。”[7]330《生死疲勞》中同樣描寫了以藍臉父子為代表的底層勞動人民的住宅——他們家只有一間屋子,里面有一個鍋灶和土炕,屋外是牛棚[8]103。
在自然環境與現實之家之外,人們共同組成的社會也是家園書寫不可或缺的內容,關乎人們對于美好家園和理想共同體的建構。奧克瑞在《饑餓的路》中真實再現了尚不成熟的政黨體制帶來的影響。在與窮人黨競選時,富人黨向民眾發放免費奶粉以換取更多選票,甚至還向人群拋撒錢幣,引起民眾哄搶,造成流血傷亡事件。然而,免費奶粉卻是有毒的,再次引發民眾暴動,產生騷亂。莫言在《生死疲勞》中也對當時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批判。“文革”時期,紅衛兵活動頻繁,高音喇叭震落了空中飛翔的大雁,造成人們爭搶。在物質匱乏的時代,大雁肉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莫言通過西門牛的口吻說道:“我聽到了那些嘈雜的、凄厲的、狂喜的聲音,我嗅到了那些血腥的、酸臭的氣味,我感受到了寒冷的氣流和灼熱的氣浪,我聯想到了傳說中的戰爭。”[8]134兩部作品通過描寫政治體制混亂真實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環境。
通過分析兩部作品中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存環境可以看出,苦難敘事是家園書寫的重要手法,可以真實再現家園情景,傳遞出建構美好家園的訴求。尼日利亞約魯巴文化中的生死循環和中國佛教文化中的“六道”輪回,都將苦難視作獲得幸福的必經過程。阿扎羅和西門鬧的每一次重生都伴隨著對未來家園的無限憧憬,然而只有歷經現實生活的各種艱難,理性探索未來之路,才能到達想象中的理想共同體。
三、現實與幻象中的家園追尋與建構
文學家描寫苦難、批判現實的主要目的在于超越苦難、尋求出路。文學作品建構的是此岸世界,卻又探索此岸世界之外的更高的彼岸世界,“在彼岸世界以外,每一個迷途的漫游者都已經找到期待已久的家園;每個漸行漸弱的孤獨之聲都被一個聆聽它的歌隊所期待,被引向和諧,并因此成為和諧本身”[10]。《饑餓的路》與《生死疲勞》都做出了這樣的努力。在《生死疲勞》中,莫言通過驢、牛、豬、狗、猴、人的視角呈現客觀的外部世界,同時又通過“幻覺”方式展現人和動物的內部世界,使得“作家建構的‘象’與‘意’在收放自如中走向嚴肅的主題”[11]。在《饑餓的路》中,奧克瑞通過阿扎羅的獨特身份,將現實世界與幽靈世界串聯在一起,以魔幻手法來寫實,因為“對于奧克瑞來說,幽靈世界并非只是想象的產物,它是比日常生活更為真實的世界”[12]。由此可見,兩部小說既立足現實,又高于現實,通過將“魔”“幻”與現實相結合,完成小說的意義建構,深化作品的思想內涵。通過比較研究兩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可以進一步挖掘出追尋和建構理想家園這一主題含義。
(一)理想家園的追尋者:阿扎羅與西門鬧
在《饑餓的路》中,阿扎羅再一次降臨人世后決定留在人間,背棄與幽靈伙伴的誓約,不再返回幽靈世界。因為幽靈世界再美好,也只能短暫停留,仍需遵從幽靈之王的命令,反復投生于人世。幽靈世界的美好是虛幻的,幽靈兒童終究是無根的漂泊者。阿扎羅選擇留在人間,反映出對精神家園的渴望,希冀找到真正的心靈歸屬。面對艱難的現實生活,阿扎羅從未退縮。無論是幽靈伙伴嘗試將他拉回幽靈世界,還是各種層出不窮的妖魔鬼怪試圖將他帶離人間,他都因為自己的毅力和家人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化險為夷,返回自己眷戀的家園。顯然,在阿扎羅身上,奧克瑞賦予更多自己的思考與期待。尼日利亞國家如同阿扎羅一樣,生存之路充滿痛苦,遭受各種外力威脅,但是,每一次的苦難經歷都是一種成長,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強,向往美好家園的決心毫不動搖。
莫言在《生死疲勞》中塑造的西門鬧這一角色同樣值得深思。西門鬧被槍斃后,始終想著再次轉世為人,回到戀戀不舍的人間故土。他投胎為西門驢后,與母驢花花的柔情繾綣反映出對“家”的渴望。他投胎為西門牛后,因為忠于主人藍臉,拒絕為人民公社耕地而被燒死,卻在最后一刻用信念支撐自己,倒在主人藍臉的土地里。土地是家園的象征。西門牛的悲壯之死表達出它對于精神家園的熱愛和向往。之后,他投胎為豬十六,夜晚逃出豬場后,看到了這樣的情景:“這月亮同樣是胖大豐滿,剛冒出水面時顏色血紅,仿佛從宇宙的陰道中分娩出來的赤子,哇哇地啼哭著,流淌著血水……。”[8]316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月亮象征著人們的精神家園、靈魂的棲息地。此處莫言意在表達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我們的家園終將渡過難關,迎來嶄新的明天。可見,莫言通過豬十六的視角傳遞出人們對于美好家園的向往。當西門鬧再次轉生為狗和猴時,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為讀者打開了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和農村的新世界。最后,西門鬧轉世為人,誕生于新千年,故稱大頭嬰兒藍千歲。新千年的鐘聲宣告過去苦難的終結。西門鬧的“六道”輪回之苦終會結束,飽嘗艱辛終將完成靈魂救贖,可以擁有嶄新的明天。莫言通過西門鬧的輪回經歷使他與整個國家的命運聯系起來。新中國自成立之后經歷了重重磨難,遇到了種種挑戰與機遇,然而,所有的艱難歷程都會煥發新的生機,每一次的新生都伴隨著追尋理想家園的美好愿景。
(二)理想家園的建構者:阿扎羅父親與西門屯居民
在阿扎羅和西門鬧身上體現的是對于美好家園的向往與追尋,而阿扎羅父親和以藍臉為代表的西門屯居民則是以實際行動構建理想家園。在《饑餓的路》中,阿扎羅父親每一次與對手抗爭都隱含著對現實家園的理性思考和對理想家園的積極探索。在窮人黨與富人黨競選中,他堅決擁護窮人黨,揭露富人黨的虛偽、貪婪,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真正民主制度的向往。當言語無法支撐他的夢想時,他化身拳擊手“黑虎”,與象征西方文化中腐朽勢力的“美洲黃虎”和“黑豹”較量,并終于贏得勝利。這象征著他擺脫西方文化藩籬,對自由的渴望和對本土文化的堅守。他最后意識到窮人黨本質上與富人黨無異時,決定做政治家,尋找盟友,組建自己的小軍隊,努力構建理想家園。在此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我們的路必須打開。一條打開的路永遠不會饑餓。奇異的時光就要到來”;“我們必須用新的目光打量實際。我們必須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審視我們自己”;“我們的饑餓可以改變世界,使它變得更美、更好”[7]528-529。阿扎羅父親這一人物形象集中體現了對于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理性態度,對于民主、自由、和諧的美好家園的積極探索與建構。
莫言在《生死疲勞》中亦不乏通過人物形象反映建構理想家園的努力,藍臉便是典型人物之一。他是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唯一單干戶,始終堅守自己的一畝六分地。藍臉的行為正反映出對家園的希冀和建構。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土地仍是家園之根,正如他的碑文上寫的“一切來自土地的都將回歸土地”[8]509。與藍臉對土地的執著不同,洪泰岳作為西門屯的老村長、合作社社長和黨支部書記,固執己見,拒絕變化,固守本土文化的一切東西。改革開放后,西門金龍認同西方文化,對西門屯進行開發和變革,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使得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侵入人們的精神世界。洪泰岳最后選擇與西門金龍同歸于盡這一情節,正反映出人們對待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態度。本土文化中一切舊的、不合時宜的因素應當拋棄,西方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也須擯棄。這些筑夢者通過努力迎來了新千年鐘聲,敲響了未來家園之門。
通過比較分析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可知,家園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還應具有人類文化和精神歸屬的內涵。理想家園的追尋與探索不僅為了擺脫現實苦難和時代變遷帶來的壓力,更需要把握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促進民族覺醒與文化建構,激發人們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探索與思考。
四、結語
《饑餓的路》與《生死疲勞》雖然在創作手法上同“源”不同“流”,但是并非就此流散而去。他們通過相似的家園書寫主題再次交匯,共同探索與建構未來的美好家園。奧克瑞與莫言的作品通過書寫家園探討人的生存與意義,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體現出眾多文學家的集體意識,即文學的人文關懷與時代精神。這種集體意識超越了國家、民族、文化與種族的界限,折射出整個人類對于理想共同體的美好愿景和共同需求。自20世紀以來,中國和以尼日利亞為代表的非洲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現實家園和傳統“共同體”在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持續沖擊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建構理想共同體需要堅守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同時應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理性地對待他民族文化,使其相互融合又各自綻放光芒。唯有如此,才能早日實現中國夢與非洲夢,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