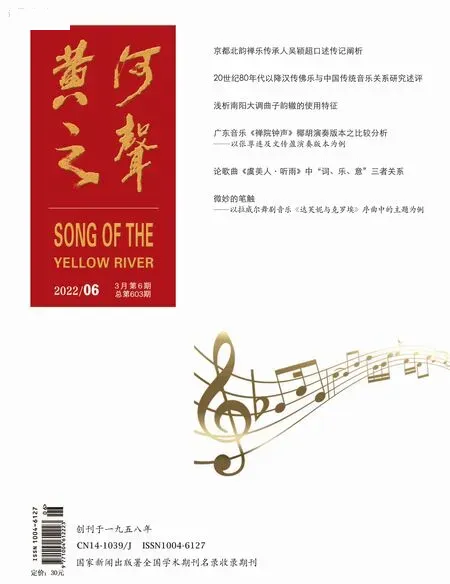聶耳女性歌曲的藝術內涵與演唱分析
——以《鐵蹄下的歌女》《梅娘曲》為例
劉 莎
引 言
藝術歌曲是西方室內樂性質的一種聲樂體裁,是對歐洲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盛行的抒情歌曲的通稱。大約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后傳入我國,受到廣大的音樂創作者的喜愛,一時掀起藝術歌曲的創作熱潮,中國藝術歌曲從此展開屬于自己的歷史。聶耳一生共創作了11首女性藝術歌曲,幾乎占它所有作品的三分之一,是當代中國藝術歌曲不可或缺的瑰寶。他的作品大多都是以社會底層備受壓迫的中國婦女以及新一代知識女性為描述對象。在他的筆下,這些女性都具有著鮮明的性格,在她們的身上都體現著中華民族優良的品質,以及面對外敵入侵時強烈的愛國熱情以及團結一致共同抗敵的革命熱情。
在聶耳去世至今,文藝界有眾多的學者對聶耳女性藝術歌曲的創作以及歌曲中的人文精神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和無限的歌頌與贊美。
一、聶耳女性歌曲的藝術內涵
(一)時代的吶喊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瀕臨亡國的境地,眾多文學家、音樂家拿起手中的筆,用自己的作品表達對毫無秩序充滿不公的社會的憤恨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聶耳的女性歌曲反映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生活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他的作品逐漸走向民族化、大眾化,成為當時通俗歌曲的主流。聶耳其女性歌曲充滿革命性與時代性,反映了時代的呼聲、勞動者的吶喊,是新時代革命女性之歌,向世人表達出沖破黑暗走向曙光的堅強不屈的力量,成為時代的吶喊。
(二)婦女思想的覺醒
聶耳是近代中國首個用歌曲塑造勞動婦女的作曲家,聶耳用生動描繪的手筆來刻畫細膩、婉轉的女性內心心理運動與豐富、起伏的情感表達,使歌曲中的女性有血有肉,其筆下的女性都是革命斗爭時代凄慘、無助、反抗、覺醒的新時代無產階級女性。她們是被社會所欺壓、蹂躪,但她們不放蕩、不魅惑。她們被壓迫到深淵的,但她們仍仰望星空,不絕望、不壓抑。她們沒有堅強的外在武器,但仍然敢于斗爭,不畏強敵,用內心的反抗熱情投身于革命。在20世紀初的中國聶耳用他具有強烈號召力與感染力的女性歌曲喚醒社會廣大的勞動婦女敢于革命、勇于革命的斗爭思想。
(三)作曲手法的大膽創新
由于聶耳無產階級的革命生活,構成了聶耳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他不僅反映大眾的真實生活,又能表達出大眾對美好未來的寄托。聶耳的女性歌曲數量雖不多,但是與大眾生活密不可分,他將藝術性與現實性完美的結合。其外聶耳在女性歌曲的曲式方面做了大膽的嘗試,他將西方的作曲手法與故鄉民間音樂相融合,流暢的旋律中夾雜著民族的獨特風格,使聶耳的歌曲簡單易唱,親切歡快,又具有濃郁的民族風味。成為新的民族風格。
二、《鐵蹄下的歌女》、《梅娘曲》的演唱分析
(一)《鐵蹄下的歌女》的演唱分析
冼星海曾說:“他的作品能夠反映中國群眾的需要,為千百萬群眾所接受與傳誦。”聶耳的作品不論是女性藝術歌曲還是其他的群眾歌曲,都是從現實生活出發,他的作品來自生活又高于生活。《鐵蹄下的歌女》是聶耳于1953年為電影《風雨兒女》所作的插曲,表達了一名生活在舊社會的漂泊歌女被社會壓迫所發出的絕望吶喊以及心中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因為聶耳明月歌舞劇社工作時,常在生活中仔細觀察社會底層女性凄涼的生活,對女性的生活及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更能真實的用音樂詮釋生活。歌中用極其簡練的音樂素材,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弱女子不平的吶喊和在她們備受摧殘的心靈深處躍動的愛國熱情。整個作品籠罩著強烈的戲劇性和悲劇性,讓歌曲爆發出悲傷、深沉的悲劇力量,是我國近代抒情歌曲的典范之作。
這部作品是4//4拍,歌曲西方曲式與中國五聲音階相結合,曲式屬于不帶再現的單三部。此歌不長,富有戲劇性,抒情性的旋律與朗誦性的旋律隨著感情的發展交替出現,可稱為一首非常出色的詠嘆調。掌握好氣息的深沉、連貫,語氣、語調和情緒的變化,音色、速度和強弱的處理,以及附點、裝飾音的正確,是唱好本曲的關鍵。歌曲由柔和抒情的小調開始,渲染了一種凄涼、悲痛的氛圍。第一段前面連續4小節氣息悠長的旋律,表達出歌女四處流浪的悲慘生活現狀,后面則緊接著節奏十分急迫、激烈,以及具有吟唱性質的旋律,與前面形成對比,情感進一步爆發,敘事性的表達歌女內心對社會不公的質問與控訴。歌曲從弱拍起,主要為突出前兩句歌詞中的“到處”二字,以表現歌女所遭受到的各種苦難經歷,表達了歌女對黑暗社會的強烈的憤恨之情以及無可奈何的滿腔愁緒,同時“我們到處”的“處”字的裝飾音,不能輕輕地帶過去,即不能滑也不能溜,小音符也要當作音符來唱,要占拍子,小音符要給重音,要清晰明確,要符合中國字的念法。在演唱中,要注意“不知道國家將亡”的“不知道”的節奏是前十六。第四句“為什么被人當作商女”中的“為什么”要強力度,重音演唱,突出對社會不公的控訴。第二段旋律則是一字對一音的組合起伏的旋律與非規整節奏加上極具口語化的歌詞,抒發對女主人公對舊社會不公與壓迫的憤懣、控訴。弱起則增加旋律與節奏的波動性,更加突出歌詞中的重點,整個一段都是訴說歌女不幸的經歷,因此整段在演唱力度上都要減弱,并且在演唱“為了饑寒交迫”與“我們到處哀歌”時,情緒與語氣都要呈現出逐漸漸弱的趨勢,“我們到處哀歌”要以哭訴的語調緩緩唱出,與前一句形成統一。“我們”二字的前休止符宛如一個柔弱女子在訴說自己內心的凄苦與不平而發自內心的痛苦所導致的哽咽與停頓,“嘗盡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遠的漂泊”,字里行間都是字血聲淚,因此在演唱時力度要有所起伏,從漸強后轉漸弱,從而塑造了四處漂泊備受壓迫的歌女形象。二三段之間的間奏,呈現出強的音樂表現力,預示著全曲高潮的來臨,在間奏期間,演唱者需調整情緒,以情帶聲詮釋全曲的高潮。第三段,旋律整體呈波浪型起伏,語調、歌詞、情感與節奏聯系得更加緊密,節奏拉長,演唱速度也明顯加快,曲調也變為明朗的大調,顯示出急促、緊迫與憤慨的音樂情緒,“誰甘心做人的奴隸”,“誰愿意讓鄉土淪喪”這兩句通過節奏與歌詞的完美配合使全曲情感完全爆發,達到了全曲的高潮,演唱這兩句時要帶有反問的語氣演唱,同時要用重音演唱。“可憐是鐵蹄下的歌女”演唱情緒由控訴轉哀怨,因此演唱力度要減弱,演唱語氣也要轉為哭訴,全曲最后一句“被鞭打得遍體鱗傷”是全曲情緒的最低點,同時也是情感最豐富的一句,其中包含了歌女的憤懣之情、對現實生活的無奈之情,以及熱愛家國的愛國情懷卻生活低微等多種情緒,因此演唱時要弱中帶有力量,最后長音“傷”要著重強調。
總之,這首歌的演唱要注意情感的把握與表達,首先要了解這首歌的創作背景,更加深刻的了解歌曲的思想內涵,從而更好的以聲傳情,讓聽眾也能感受到歌曲沉痛、凄慘但又頑強的抵抗,心懷希望。其次也要注意節奏的準確與弱起的表達,這樣歌詞,語境更能完美的結合。最后,還要把歌曲譜面上的力度、速度記號要表現出來,這樣歌曲才有對比,而對比則產生美。聶耳通過運用不同的音樂手法,完美的詮釋了歌曲的藝術內涵。這首作品是聶耳女性歌曲的代表作之一,時至今日仍具有催人淚下的悲劇力量,流傳之處,無人不贊。
(二)《梅娘曲》的演唱分析
1935年1月31日,由田漢創作的多幕劇《回春之曲》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次公演。話劇描寫了“九·一八”事變之后,一批南洋愛國青年華僑為救亡圖存,千里共赴國難,回國參加抗戰的感人故事。《梅娘曲》是聶耳于1935年為田漢的話劇《回春之曲》所作的插曲。這部話劇以愛國為核心,圍繞這南洋的愛國青年華僑的人生故事展開。其中包括轟轟轟烈烈的愛情以及反帝反日,不為舊社會屈服的熱血奮斗。《梅娘曲》出現在《回春之曲》的第三幕,主人公梅娘是一位出生于南洋商人家庭的女學生,他的戀人高維漢歸國投身抗戰后,在戰爭中受傷而臥榻病床,不幸因傷失去記憶。梅娘不顧家人的反對和阻止,毅然決然的從南洋,卻又看著心上人清醒后便失去了記憶,內心百感交集,為喚起他的回憶,在病床前深情而又悲傷的唱出了這首歌曲。《梅娘曲》首唱者是著名影星王人美。話劇《回春之曲》公演后在全社會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梅娘曲》也隨之在國內和海外僑胞中廣為傳唱,凄婉動人的歌聲中有海外兒女對愛情的堅貞不渝,更有廣大華僑對祖國的深深熱愛。聶耳并沒有到過南洋,在樂曲創作中,他根據劇情的需要,用簡樸的手法將人物內心復雜的思想感情一步步、層次分明地作了細致的刻畫,讓音樂語言和歌詞配合得非常緊密。
《梅娘曲》這首歌是分節歌的形式,共三段。音樂具有宣敘調特點,語言與音樂密不可分,緊密連接,給人一種說唱的體驗,情感與旋律不分你我。整首歌曲中的歌詞先以回憶往日的甜蜜來反襯現在的痛苦,其次是為當時沒能追隨愛人而深感悔恨與內疚,最后因為追求愛而拋棄一切卻沒有任何結構而感到痛苦。全曲中不斷重復歌詞“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每一次重復都不斷強調不要忘了那些過往,與目前高維漢失憶的處境形成鮮明的對比,過去的幸福更加突出現實的殘酷。第一句“哥哥,你別忘了我呀!”弱起節奏與前八分休止符的停頓,使歌詞與語氣緊密結合,簡單的幾個字,包含了心疼、苦楚、憤怒、不甘等情緒,因此在演唱時需準確把控弱起與休止符的節奏型,從而準確的表達出歌曲的情感,同時在演唱“哥哥”這兩個詞時要唱出語境感。第二句“我是你親愛的梅娘!”每次重復時譜面都出現了漸強記號與mf的力度記號,因此在演唱時要情感與力度都要有所提升,同時著重強調“梅娘”二字。歌曲第一段與第二段用回憶的口吻來展開音樂的發展,第一段描繪她們當時快樂的時光,因此在演唱時要稍微輕快些,在演唱第一段最后“我們在,遙遠的”時要準確唱出三連音的節奏型。在演唱第二段回憶部分時情緒要轉為低沉與悔恨,演唱“我是那樣的惆悵”時,要準確唱好附點節奏,演唱出惆悵的語氣。最后一段,述說了自己與家人的不合,以及自己對封建社會的壓迫所產生的痛苦、迷茫與抵抗,表達了社會新女性的思想崛起。這一段是全曲的高潮,也是悲傷情緒最濃烈的時候,連續的“但是,但是”半小節的休止符,生動的描繪出哽咽的梅娘形象,“你已經不認得我了”更是表達出一種對生活折磨的無奈與妥協,大大的增加了歌曲的悲劇性,更加有現實意義。因此在演唱時,要把重音十六分節奏型正確詮釋出來。
總之,這首歌旋律樸素簡單,音域起伏不大,在視唱方面并不難,主要是歌曲的情感表達,要想象自己就是歌曲中的“梅娘”體會歌曲濃厚的情感,充分的理解歌詞的含義,以訴說的形式演唱整曲。第一段是回顧美好的時光,情緒應是柔和,甜蜜又夾雜這無奈。第二段是回憶梅娘并未跟隨高維漢一起回國,此刻的情緒則是后悔與惆悵。最后一段,男主人公徹底的忘記了梅娘,情緒便是無限的遺憾與意味悠長的傷感,演唱時這三段不同的情緒要表達到位。這首歌首演之后,許多東南亞華僑受此曲的感召,紛紛回國為抗日救亡行動奉獻出自己的力量。眾多著名歌手廣泛傳唱,成為評價甚高的流行曲傳頌至今。
結 語
聶耳雖然已經長逝于世,但他的藝術卻永傳不朽。他用他那慰藉人們心靈的筆桿子譜寫出一段又一段的世紀長歌;他用他那熾熱的愛國熱情謳歌著人民與祖國的曠世奇戀;他用他那血肉之軀奉獻于山川大地。他是時代的象征、革命的楷模、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將他的一生都交給了藝術和祖國。他的作品意義深遠,情感真摯、樸素,富有藝術氣息與民族特色,內容豐富,以現實為源泉,又高于現實,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角落。他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藝術畫廊中的瑰寶,也是世界藝術史中的一顆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