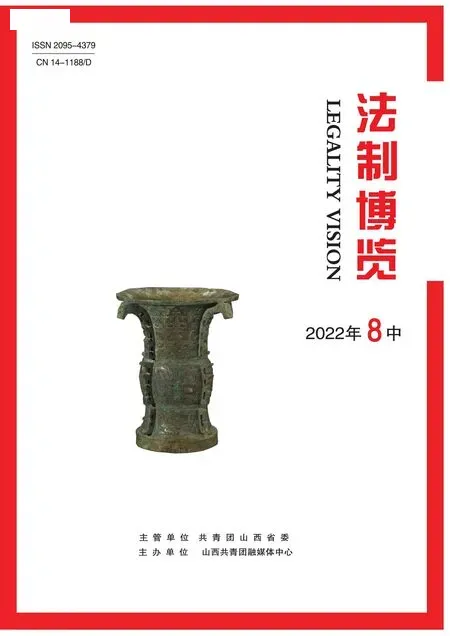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背景下關于無人駕駛汽車交通事故侵權責任研究
王 琦
鄭州經貿學院,河南 鄭州 451191
一、無人駕駛汽車相關理論
(一)無人駕駛汽車的界定
無人駕駛汽車即通過智能駕駛系統來駕駛的汽車,無人駕駛汽車中對人類駕駛員的需要較低,甚至沒有。智能駕駛系統主要由信息搜集系統和信息處理系統來實現,即汽車通過車載攝像、雷達和GPS進行圖像和距離數據信息收集,由信息處理系統對接收到的數據信息進行處理,而后處理結果與操作硬件相結合完成汽車安全運行的全部操作,以此代替駕駛人的思維和操作達到汽車的獨立自主運行,做到“無人”駕駛。
(二)無人駕駛汽車的分類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美國汽車工程師學會以無人駕駛汽車的自動化程度為標準分別對無人駕駛汽車進行了分類(以下分別簡稱“管理局標準”“學會標準”)。“管理局標準”將無人駕駛汽車分為五級,而“學會標準”則將其分為六級,兩種標準關于無人駕駛汽車的前四級分類并無不同,區別在于“管理局標準”在無人駕駛汽車實現有條件自動化(智能駕駛系統完成大部分汽車操作,駕駛人充當安全員角色)后,未再對自動化的程度進一步所做區分;“學會標準”則對更高層次自動化的無人駕駛汽車進行劃分,即高度自動駕駛和完全自動駕駛。但相對于“管理局標準”,管見以為“學會標準”更為合理,原因在于,其將無人駕駛汽車的自動化程度作了進一步的細化。自動化程度不同的無人駕駛汽車對駕駛人的依賴性不同,發生交通事后,所依據的法律規范亦有所差異,因此,有必要對自動化程度在有條件自動化及以上的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的侵權責任進行探討。
(三)無人駕駛汽車的法律地位
無人駕駛汽車將駕駛人從汽車操作者的身份中解放出來,通過科技手段減少汽車駕駛過程中的失誤操作,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關于無人駕駛汽車的法律地位,學說存在爭議。[1]支持無人駕駛汽車有民事主體資格的認為無人駕駛汽車本身擁有人格,可以享有權利,主要學說有電子人格說、代理說、有限人格說等,電子人格說將無人駕駛汽車的人格擬制為法人的一種,由法人承擔侵權責任;代理說、有限人格說將無人駕駛汽車的法律地位界定為人與物之間,是一種有限的人格。否定無人駕駛汽車有民事主體資格的認為無人駕駛汽車僅僅是人類制造出來的輔助工具,通過算法等方式,傳遞相關信息。管見以為,民事主體的標志在于其可以對外作出獨立的意思表示,承擔民事責任。而無人駕駛汽車無意思表達能力,屬于物。
二、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責任承擔主體的確定
自動化程度越高的無人駕駛汽車,駕駛人的作用越小,甚至會出現不需要駕駛人的情況,如果發生交通事故,責任承擔責任主體如何確定有必要明確。管見以為在確定責任承擔主體時可以將以下民事主體納入其中。
(一)智能駕駛系統設計者
智能駕駛系統設計者在設計之初應當保證其系統面臨復雜多變和突發狀況時,能夠準確無誤地運行,保障消費者人身安全。若無人駕駛汽車因運行錯誤導致交通事故時,該智能駕駛系統應當被認定有缺陷或功能障礙,智能駕駛系統的設計者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二)無人駕駛汽車生產者
依據現行法律規范,無人駕駛汽車生產者適用嚴格責任,即若因無人駕駛汽車存在缺陷導致交通事故發生,無論其生產者在生產的過程中是否存在過錯,其應當在缺陷范圍內對交通事故的受害者進行賠償。生產者若有法定抗辯事由,則可依據《產品質量法》的相關規定作出抗辯以免責。
(三)無人駕駛汽車銷售者
依據我國《產品質量法》的規定,若銷售者銷售的無人駕駛汽車存在質量問題,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銷售者在其過錯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在有明確的證據證明生產者生產的無人駕駛汽車無質量問題、使用人操作規范、無第三人故意破壞的情況下,銷售者若無證據證明其售出無人駕駛汽車前無過錯,其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其二,在無人駕駛汽車存在質量缺陷時,銷售者若無法提供缺陷汽車的生產者和上游銷售者,則認為其未盡到檢驗無人駕駛汽車質量的義務,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四)無人駕駛汽車所有權人和駕駛人
首先,駕駛員與所有人一致的情況下:自動化程度達到有條件自動化的無人駕駛汽車,能夠明確判斷出駕駛人有過錯或未盡義務,由駕駛員承擔責任;在自動化程度達到高度自動駕駛和完全自動駕駛時,一旦發生交通事故由車輛所有人承擔責任。原因在于,該階段無人駕駛汽車一旦出現交通事故,從受害人的角度上考慮尋找要求所有人承擔責任更加便捷、迅速。另外,對基于產品質量導致的機動車事故機動車方承擔責任后有向生產者、銷售者追償的權利。再者,所有人作為無人駕駛汽車的受益者從公平角度出發,理應由其承擔相應的風險。[2]其次,無人駕駛汽車所有人與駕駛人分離的情況下:管見以為可以部分適用普通機動車中關于所有人和駕駛人分離的規定。普通汽車中駕駛人承擔保險責任后的補充責任,所有人只有存在過錯時才承擔責任。無人駕駛汽車中的所有人責任亦是如此。無人駕駛汽車雖然對駕駛員的要求比較低,但仍然要求駕駛人不得做出酒駕等行為。總之,在駕駛員與所有人分離的情況下,無人駕駛汽車所有人只有在過錯下,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駕駛員醉駕或者未定期檢查駕駛系統等過錯時,才適用普通汽車規定承擔過錯責任,否則駕駛員和所有人在保險責任外承擔連帶責任。
三、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歸責原則的確定
普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責任承擔是以駕駛員過錯為核心、根據駕駛員的過錯進行確定。同時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即使是普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時,普通機動車車主無過錯也需要承擔10%的責任,[3]但這樣的責任方式很難在無人駕駛汽車交通責任中適用。原因在于:一是在無人駕駛汽車的自動化程度達到有條件自動化時,智能駕駛系統完成大部分的汽車操作,駕駛人充當安全員角色,如果汽車本身沒有發生其他異常情況,同時駕駛人也盡到了監管義務,那么則不能以駕駛人的過錯承擔責任。而且認定汽車存在過錯也是不合理的,因為汽車屬于“物”的范疇,單純的“物”怎么可能存在過錯。另外,若無人駕駛汽車的自動化程度達到高度自動駕駛和完全自動駕駛,智能駕駛系統已經完全進行操縱汽車,駕駛人就不再操控汽車,駕駛人就更不需要承擔過錯責任。二是無人駕駛汽車的出現也給道路交通帶來了很大的隱患,日益增多的自動化汽車勢必會豐富交通事故的種類,很有可能會出現無人駕駛汽車與無人駕駛汽車,無人駕駛汽車與普通機動車、其他道路主體等之間復雜的交通事故。那么在這樣一個復雜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中如果僅僅適用過錯歸責原則已經顯得力不從心,也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因此,管見以為可以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為基礎,針對不同的交通事故主體,確定相應的歸責原則。
(一)無人駕駛汽車之間
無人駕駛汽車與無人駕駛汽車之間沒有存在一強一弱的地位差別,可以參照普通汽車之間發生交通事故時的歸責原則,即根據過錯大小承擔責任。無人駕駛汽車因有系統的操作,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極有可能是自動駕駛系統出現了故障,從而導致其無法精確地判斷道路的情況和周邊環境,進而產生一系列的損害后果。對于其產生的損害結果,兩方要根據自己的過錯程度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一方能夠證明自己的汽車系統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則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責任。
(二)無人駕駛汽車與普通機動車之間
管見以為無人駕駛汽車的責任承擔應該根據汽車自動化的程度設定不同的歸責原則。如果無人駕駛汽車處在比較低的前四級,此時駕駛人仍然操縱著汽車,在這一環節中如果發生交通事故由駕駛人根據自己的過錯程度承擔責任。如果自動化程度處于有條件自動化級的無人駕駛汽車與普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在事故原因排查后發現是人類駕駛員的操作失誤或者駕駛員未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的過錯導致的,那么適用過錯歸責原則;如果汽車的自動化程度處于高度自動駕駛和完全自動駕駛及以上或者事故原因不是操作人員所導致的,基于普通機動車駕駛人證明難度系數較大,同時也是出于對普通機動車駕駛人的特殊保護,應當由無人駕駛汽車的所有人承擔舉證責任,即采用過錯推定責任。
(三)無人駕駛汽車和其他道路主體之間
依據現行法律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時,首先認定機動車負有責任,然后機動車方如果可以證明非機動車方有法律規定的過錯情形時就可以適當地減輕機動車方的法律責任。[4]另外,學界中對于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發生交通事故側重于機動車方承擔責任的規定一直是存有爭議的。究其本質是因為機動車方不僅要承擔證明責任,而且即使其沒有過錯仍然要給予對方一定的賠償。可見,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之間交通事故的責任承擔是比較復雜的。同樣,無人駕駛汽車與非機動車、行人之間一旦發生交通事故也可以參照此規定進行適用,即首先認定無人駕駛汽車方承擔責任,然后無人駕駛汽車方如若能舉證證明對方存在過錯則可以適當減輕其責任。此外,基于非機動車與行人在其中處于一種弱者的地位,因此即使無人駕駛汽車方毫無過錯也要給予一定的補償。
四、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因果關系的認定
無人駕駛汽車自身的系統特征決定了無人駕駛汽車在運行過程中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很難認定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無人駕駛汽車在運行過程中遇到問題時,系統會根據情況做出路線的選擇、車輛的運行速度、遇見障礙物是否躲避等決策,但當做出決策時,系統內部做出的決策程度和具體情況連最初的程序人員都無法知道,甚至有些也是我們人類無法預測和解釋的,這是無人駕駛汽車一直存在的黑箱難題。因此,解決無人駕駛汽車存在的黑箱難題是行為與結果因果關系邏輯推理認定的重中之重。
管見以為,普通的電子設備雖然可以通過對記錄的觀察和分析還原事故發生時的真實情況,進而認定因果關系。但其保存的大多是容易篡改的視頻,事實并非完全準確無誤。因此,在無人駕駛汽車安裝“黑匣子”以還原事故發生的真實情況十分必要。“黑匣子”作為航空電子設備,具有抗強沖擊、抗穿透、抗高溫火燒等特殊能力,能夠客觀、真實、全面地記錄飛機飛行過程中發生的基本情況,即使飛機失事也可以找到根本原因。“黑匣子”技術不僅在航空中適用,在汽車領域也早已適用,例如德國已主張利用“黑匣子”強化因果關系。“黑匣子”技術可以準確、清晰地記錄和尋找事故發生的原因,如果存在人為因素,則可以準確地認定因果關系;反之若不是人為因素,則直接推定事故的發生和所有人之間是不存在因果關系的。“黑匣子”可以記錄人機共同控制的無人駕駛汽車在運行過程中有無人為因素的影響,所以其適合自動化程度在有條件自動化及以下的無人駕駛汽車。自動化程度在高度自動駕駛及以上的無人駕駛汽車,車輛由系統完全控制,一旦發生交通事故駕駛人與事故已無任何因果關系,其損害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系統缺陷所導致的。[5]
五、無人駕駛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索賠保障
目前我國對機動車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索賠是以保險為主,即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由保險公司在保險額度內對受害人進行賠付,不足部分由機動車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補足。關于機動車保險,除交強險外,其他車險由機動車所有權人自愿投保,這意味著有相當部分的機動車可能僅有交強險,但交強險作為對受害人的基本保障,其賠償限額低的屬性,可能對受害人的保障力度不足。上述我國機動車致人損害的賠償制度無法滿足無人駕駛汽車致人損害的賠償需要,原因在于自動化程度越高的無人駕駛汽車,駕駛人對汽車的操控度越低,甚至在達到高度自動駕駛和完全自動駕駛時,駕駛人則不再存在,汽車內僅有乘客,但乘客不在交強險賠付的范圍之內。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在侵權人欠缺賠付能力的情況下,乘客的合法權益是無法得到有力保障的。
管見以為關于目前機動車致人損害的賠償制度無法完全賠付無人駕駛汽車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損失的問題,可以采取強制投保的方法予以解決。無人駕駛汽車的自動化程度越高,駕駛人的作用越薄弱,在發生交通事故時,事故原因不是駕駛人的問題,更多的是汽車本身的問題,在此背景下由無人駕駛汽車所有權人承擔事故責任有損法律的公平正義。因此,由無人駕駛汽車的生產者向保險公司投保,在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由保險公司對受害人進行賠付,同時為提高效率,生產者可以以生產批次為投保對象,與保險公司約定,當該批次任何一輛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根據法律規定由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的,保險公司都應承擔。以此實現對受害人合法權益的保障、解除無人駕駛汽車消費者的后顧之憂、提高投保效率、促進無人駕駛汽車行業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