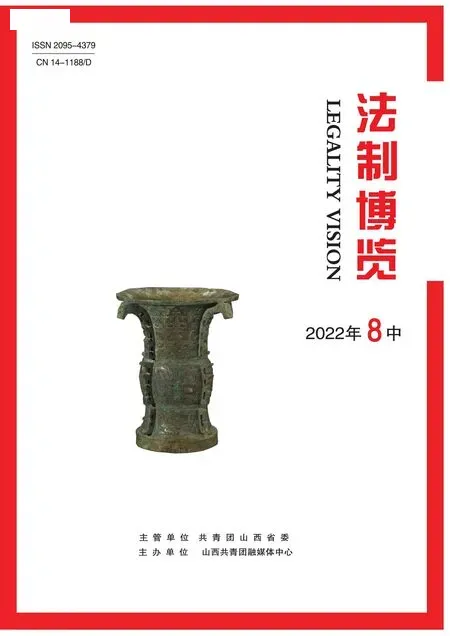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
尹秀峰
濱州職業學院,山東 濱州 256603
征信機構采集的信息,尤其是不良交易信息,對個人和企業的發展影響巨大。在商業交易中,良好的信用可以幫助個人或企業贏得商機,減少交易成本,信用存在瑕疵則會步履維艱。《征信業管理條例》第十三條和第二十一條界分了個人和企業不同的信息采集程序,但兩者都把公開信息作為無條件的采集渠道,在公開信息中,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生效文書最具公信力。然而,在我國的司法上沒有相關的制度設計,造成了征信業信息渠道不暢或獲得相關信息成本過高,甚至出現相關信息的誤傳或歪曲。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有必要確立相應的司法制度,實現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
一、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法理基礎
(一)實體法基礎
1.誠實信用原則
我國《民法典》第七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誠實信用原則就是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1]在市場經濟中,只有在誠信的大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的成本,保證交易順暢。然而,在實際交易中誠信缺失的現象屢見不鮮,使交易主體對交易安全產生了惶恐。因此,誠實信用原則的功能在法律上有兩個方面:一是表現在大力倡導行為主體誠實守信,對誠信行為予以肯定;二是體現在對主體失信行為的懲戒。由于立法往往基于“人性惡”的假定,故誠實信用原則正面的指導作用是有限的,其主要功能還在于以“主體失信”為假定設立相應的法律制度,不良交易信息征信也為其中之一。
2.信用權
在誠實信用原則的基礎上,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許多國家的法律確立了“信用權”制度,我國臺灣地區在其“民法典”債編修改時對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項增列信用,明確其為人格法益之一種。[2]國務院頒布的《征信業管理條例》也在立法層面確立了“信用權”的內涵和外延,賦予信息主體參與征信業務活動的各項權利。正如誠實信用原則的功能一樣,在民事活動和商事交易中,信用權內容也應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主體信用的維護;二是主體不良交易信息的披露。不良交易信息征信作為法定的信息披露方式,是信用權應有之義,也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必然要求。
(二)程序法依據
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以確認主體在特定交易中存在信用瑕疵的方式實現,應當屬于確認之訴的一種。具體而言,確認之訴是指原告要求法院確認其主張的法律關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訴訟。[3]由此可見,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是通過提起信用瑕疵(被告信用權不存在)確認之訴來實現的。傳統民事訴訟法理論認為,提起確認之訴就必須具有值得救濟或保護的法律利益,即訴的利益。我國的《民事訴訟法》雖然對訴的利益沒有明確的規定,但也要求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直接的利害關系。其實,直接利害關系(訴的利益)的判定本質上是一個實體法問題,需要實體法的支撐。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尚未出臺有關征信的相關法律,《民法典》也未把“信用權”作為獨立的權利確認。目前,只有《征信業管理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認了“信用權”,為提起信用瑕疵確認之訴提供了一些借鑒。如前文所述,既然主體不良交易信息的披露是商事交易中信用權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在法理上講,受不誠信行為侵害主體就應當具有值得救濟或保護的法律利益,即訴的利益。
二、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權利救濟功能
法諺云:“有損害,必有救濟”。國家司法的公共權力是以解決社會糾紛而獲得正當性基礎,但是當前完全國家化的糾紛與沖突解決路徑對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疲于應付,因而國家權力難以通過樹立司法權威達到司法公正的目的。[4]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完全國家化的糾紛與沖突解決路徑,實現了司法制度與征信制度的有效銜接,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豐富了權利救濟體系,其權利救濟的獨特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非財產性
傳統的權利救濟以財產性救濟為主,即便名譽權等人身權利受到侵害時,也往往轉化為財產救濟。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規定:侵權人拒不執行生效判決,不為對方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報等方式,將判決的主要內容及有關情況公布于眾,費用由被執行人承擔。而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通過信用瑕疵判決的方式來救濟權利,其內容不直接涉及財產的此消彼長,屬于非財產性的救濟方式。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促成了司法救濟手段多元化,尤其是在責任財產不足時,為司法救濟開辟了新路徑。
(二)間接懲戒性
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懲戒功能主要通過征信業來實現,具有間接性。《征信業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征信業務,是指對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的信用信息和個人的信用信息進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動。”相對于主體的其他信息,不良交易信息才是信息使用者關注的重點。在很大程度上,不良交易信息會導致商業機會等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喪失。通過這種方式對不誠信的行為主體予以間接懲戒的同時,也是對權利人行為的肯定和心理安撫。此外,征信帶來的輿論力量也對主體的懲戒起到的一定的輔助作用。
(三)公益性預防
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使不良交易信息以判決的形式公之于眾,可以為后來發生的交易活動提供借鑒,以預防交易風險。基于“理性人或經濟人”的假定,主體存在“趨利避害”的行為特征。因此,預防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警示交易風險,為其他主體的決策提供依據;另一方面通過懲戒功能以儆效尤,預防類似行為發生。由此可見,不良信息征信司法化的懲戒性和預防性是相輔相成的,互為手段和目的。但是預防性的受益主體是不特定的,在一定意義上使得不良信息征信司法化具有了公益性。而懲戒性的主體是特定的,只能對不誠信行為的實施者進行。
(四)從屬性
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是通過信用瑕疵確認之訴來實現的。只要可以通過確認判決有效適當地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法律爭訟,就可以認為具有確認的利益,必須排除無益的確認訴訟。[5]要排除無益的確認訴訟,就必須明確信用瑕疵確認之訴的從屬地位。信用瑕疵確認之訴是以獨立的給付之訴或變更之訴為前提的。沒有獨立的給付之訴或變更之訴,不允許單獨確認主體的信用瑕疵。其實,信用瑕疵確認之訴的從屬性不僅是防止濫訴的需要,也是信用權行使的客觀需要。信用權作為一種人格權,其有無被濫用,必須結合具體事實予以認定。若信用權濫用,沒有給當事人造成任何的利益損害,其只能停留在道德的層面,而不應以法律手段予以責難。
三、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啟動機制
由于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具有從屬性的特征,其啟動程序也相應具有從屬性,也應遵循給付之訴或變更之訴中法律確立的基本規則。但是并不是給付之訴或變更之訴都可以附帶提起信用瑕疵確認之訴,啟動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需要自身特有的條件。
(一)過錯責任是啟動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先決條件
若利害關系人的損害是由于不可抗力或商業風險等不可歸責的原因導致的,則不能啟動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程序。也就是說,只有在過錯責任的條件下才能啟動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程序,而無過錯責任、公平責任不應適用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程序。過錯推定本質上仍然是過錯責任,應適用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程序。
(二)適格的訴訟請求
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雖然具有從屬性,但其表述應當是獨立、明確的,其訴訟請求可以表述為:請求確認被告在與原告(案由)一案中存在信用瑕疵。當然,信用瑕疵也存在一個程度問題。隨著司法實踐的深入,該訴訟請求應當借鑒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以及信用評級的方法,根據具體案情對訴訟請求進行細化,以確立信用瑕疵的訴求等級。
四、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矯正機制
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矯正機制是信用瑕疵主體可以通過一定的行為撤銷不良交易信息的機制。此機制實為信用瑕疵主體自救而設,是法律給予信用瑕疵主體自新的機會。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目的在于恢復受損害的權利,懲戒等僅僅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若在不良交易信息被法院確認后,信用瑕疵主體通過自身的行為填補了因不誠信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不良交易信息征信也就失去應有的功效。在這個意義上講,信用瑕疵矯正機制會形成一種內在的責任承擔驅動力,促使責任主體自覺履行義務,有效破解履行義務動力不足的難題。
(一)撤銷行為的界定
1.不良交易信息已被法院或征信機構采信。在時間上,只有在不良交易信息已被法院或征信機構采信,才能撤銷不良交易信息的征信。若沒有不良交易信息征信行為或行為正處于某個特定環節,則不能撤銷。在上述情形下,可以在征信行為完成之前撤回不良交易信息征信。撤回和撤銷不良交易信息征信的行為只是時間上的差別,其他的要件相同。
2.不良行為或者事件因后續的彌補行為而終止。彌補行為應為以下兩種行為之一:一是責任承擔,即信用瑕疵主體必須自愿履行了因不誠信行為所應當承擔的全部責任,但僅承擔了部分責任或強制執行承擔責任情形下不得撤銷;二是協議撤銷,即信用瑕疵主體與案件的全部利害關系人達成撤銷協議,僅與部分利害關系人達成協議的情形下不得撤銷。
3.撤銷行為無溯及力。撤銷不良交易信息征信的行為無溯及力,僅對以后的交易或法律行為產生影響。實際上,撤銷行為以前依據不良交易信息決策的行為已經發生,若溯及既往力使之無效,只能徒生糾紛,別無他益。
4.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認可。當事人包括信用瑕疵主體及其利害關系人。當事人在申請時須提交有關的證據,人民法院一般僅需進行形式審查。
(二)個人和企業的矯正機制比較
《征信業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征信機構對個人不良交易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為或者事件終止之日起為五年;超過五年的,應當予以刪除。”在不良交易信息司法化的背景下,本條款應理解為矯正機制的雛形,在法理上應作出如下解釋:一是不良行為或者事件因后續的彌補行為而終止,自終止之日起當事人可以撤銷不良交易信息,超過五年未撤銷的,應當予以刪除;二是不良行為或者事件非因后續的彌補行為而終止,不良交易信息保存期限自終止之日起最長五年。《征信業管理條例》對于企業的不良交易信息保存期限則沒有規定。沒有規定不良信息征信的矯正機制,看似加強了企業的約束,實則對企業的長遠發展和市場經濟的良性運作十分不利。企業作為重要的法律主體,法律沒有理由否定其自救自新的機會。因此,應當建立與企業特點相適應的矯正機制。
五、結語
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是連接司法制度和征信制度的橋梁和紐帶,在現有司法資源和征信業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通過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司法制度和征信制度相得益彰。司法制度借助征信業突破了法律功能實現的瓶頸,為權利救濟注入了新活力。而征信業依靠司法制度的有力支撐,獲得穩定、可靠的信息來源并增強了征信行業公信力。但是,兩種制度的融合還停留在理論研究階段。在法律實踐中,還存在許多障礙:第一,如何解決《民事訴訟法》和《征信業管理條例》效力層次不對稱問題;第二,如何解決兩種制度融合中知情權、隱私權、商業秘密保護權等權利的位階和沖突問題;第三,怎樣實現法院與征信機構的行業認同與信息平臺對接。以上問題的解決必將釋放不良交易信息征信司法化的正能量,也為司法制度與其他制度的融合提供了范例,助推社會綜合治理的大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