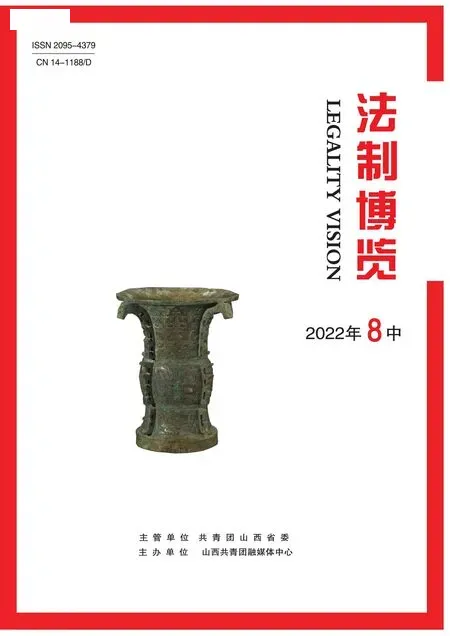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犯罪重刑化之空間
——刑事立法應力戒情緒化思潮
李丁祎 趙東方
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如今中國已經進入立法活躍化的時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高空拋物、搶奪方向盤入罪”“冒名頂替行為入罪”“非法催債行為入罪”可以說是回應性刑事立法最好的體現。然而,當立法面對洶涌的民意時,切不可被帶有強烈情緒性色彩的輿論所裹挾,而我們主張謹慎而積極立法的同時,應不忘運用好刑法解釋這一最基本的手段。張明楷教授也言道:“解釋論努力窮盡的地方,才是立法論思考的起點。”引起復雜社會現象的因素有很多,而這恐怕不是一時的修法所能解決的問題,因此筆者以時下爭議頗多的“買賣同罪”問題為切入點,旨在探尋收買犯罪重刑化的可能性。
一、問題的提出
A市B縣“鐵鏈女”的事件的調查結果,無疑是對當地官民相護、肆意買賣女性現象的無情揭露。這說明不僅僅是拐賣行為,收買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也同樣值得我們關注,而從《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的規定上看,假設沒有數罪并罰的情節,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最高只能達到三年有期徒刑,而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最高可以判到死刑。立法者的態度顯然是對出賣和收買行為做了不同的價值評價,兩罪之間的法定刑何以如此懸殊?我們不妨把目光轉向買賣婦女現象的現實背景。
受偏遠農村地區根深蒂固的父權價值觀、重男輕女觀念等因素的影響,“買媳婦”甚至被認為是一種當地風俗,買家和人販子在當地司法辦案人員的庇護之下,往往認為這種現象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多數被害婦女為了維持平穩的生活,選擇安于現狀,這也就是在后續解救工作中認定“違背婦女意志”存在困難的原因。
當然,現實背景只是為立法的設置提供了社會土壤,讓我們再把目光轉回規范本身,思考立法者創設不同法定刑的意圖。
二、將收買行為放入刑法體系中的輕重衡量問題
將收買行為放入刑法體系中是否已經構成重罪標準?筆者認為,要衡量刑法買賣二者之間的輕重,可以從法定刑、追訴時效、量刑情節三個方面來進行界定。
(一)法定刑
將收買行為放入刑法體系中是否已經構成重罪標準?學理上一般以三年有期徒刑為界,作為區分重罪與輕罪的標準。假設案件中不存在數罪并罰的情節,《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最高只能達到三年有期徒刑,而第二百四十條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基本刑規定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如果單獨對比買賣犯罪的基本刑,收買行為顯然比出賣行為更為輕緩。
(二)追訴時效
仍以基本刑比較,如果對被買婦女、被買兒童只存在單純的收買行為,意味著追訴時效只有五年;
筆者認為,這里的追訴時效困局其實是可以化解的。雖然收買罪不是繼續犯,但在收買犯罪之后,有繼續犯緊隨其后。一是收買婦女后,只要對被買婦女進行非法拘禁,就會同時構成非法拘禁罪,而非法拘禁是繼續犯,追訴時效可以一直延伸到拘禁行為終止之日。二是收買兒童后,即使不對兒童進行非法拘禁,但使其脫離監護人的狀態,便構成拐騙兒童罪,而拐騙兒童罪也是繼續犯。[1]因此,考慮到收買行為中隨時都有向其他犯罪轉化的可能性,兩罪在追訴時效問題上的入罪空間都是很大的。
(三)量刑情節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對收買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設置了從寬處罰情節,即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被買婦女意愿,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這款是立法者結合被買婦女在當地久居的現狀,為早日解救被害人做出的情理考量。
反觀《刑法》第二百四十條對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規定,立法者并未設置法定從寬處罰情節,鑒于本罪的社會危害性以及人販子本身的人身危險性,規定了8項從重處罰情節,以期能夠全面打擊出賣人在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過程中可能對被害人及親屬造成的損害。
總之,就收買行為自身而言,由于隨時具有向其他犯罪延展的可能性,并不能夠單純評價為一個輕罪;但相對于拐賣行為設置的法定刑和量刑情節而言,是相對輕緩化的。
三、收買行為重刑化的法理基礎與正當性
從《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所侵犯的客體來看,此類犯罪無疑是對婦女和兒童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嚴重損害,而一般人格權本身是不能被物化的,更不能成為用金錢等一般等價物進行交易互換的商品,這也是憲法學意義上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遵循。同時,落后地區的愚昧觀念與惡劣風俗并不能理所當然地成為該類犯罪的阻卻事由。但若想真正實現買賣同罪同罰,我們便需要探尋其內在的法理基礎與正當性。
(一)收買行為本身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面對封建落后的愚昧觀念和漸成自然的收買陋習,立法不能給企圖投機取巧、尋求司法蔭蔽的當地小團體留有任何余地,而是應該通過嚴厲的刑罰來表明態度。這不僅事關婦女兒童的基本人權,對革除落后地區的愚昧觀念與不良習性同樣有著重大的意義。
(二)買家行為背后黑暗的利益鏈條
實際上,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落戶、婚姻登記等手續必然存在很多的非正常操作的情形,很多是通過人情,甚至是行賄受賄等幕后操作才可能完成。
由于《刑法》對買受婦女兒童罪所規定的罪責很輕,所以幫助辦理戶口、結婚登記等手續的工作人員的犯罪成本也相應地低廉,這在無形中助長了買受婦女兒童共同犯罪的利益鏈條。利益鏈條一旦形成,大家就成了一條船上的人,如果碰到追查相關責任的情形,地方管理機構和人員的敷衍、相互扯皮甚至掩蓋罪行的情況也就在所難免,這會進一步惡化對買受婦女兒童犯罪行為進行追責的基層生態。
(三)實務中對于收買行為數罪并罰的概率微乎其微
曾有媒體分析了2014年至2021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以“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檢索的400份司法裁判文書,并得出結論: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強奸罪并罰,以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非法拘禁罪并罰的判決的占比很小,絕大部分案件僅判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刑罰輕緩,為1年左右。由此也說明,即使收買行為有向后延展為其他犯罪的可能性,但由于買家與被買婦女之間往往存在婚姻關系,婚內強奸與非法拘禁成立犯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實務中適用數罪并罰條款的概率很小。
四、收買行為重刑化認定中的難題
(一)人與動物的法益衡量
在討論收買行為的刑罰輕重時,羅翔教授提到人與動物保護法益嚴重失衡的問題。他以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保護法益為參照物,[2]指出兩罪雖然在罪數上相去甚遠,但在基本刑方面,單純的購買婦女、兒童與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存在罪行的嚴重失衡,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觀點作為其主張提高本罪法定刑的一個論據。
羅翔教授的當然解釋推理從一般抽象的意義上看似乎是合理的,但筆者認為,人與動物的法益衡量并不能單純地進行這樣的價值判斷。法益衡量不是主觀的、恣意的,而是具有嚴格的標準。通常來說,道德倫理、價值判斷、公平正義、社會秩序都是影響法益衡量的重要因素,其中尤以價值判斷為要。
當然,法益衡量說并非只是考慮行為的結果、法益的價值,事態的緊迫性、行為的必要性、手段的適當性等因素同樣在考量范圍之內,但這旨在考察行為所具有的法益侵害的危險性,而不是行為本身的反倫理性。人與動物的關系歸根到底是倫理底線的問題,然而就收買野生動物與收買婦女來說,雖然形式上看都是“收買行為”,但兩者的法益實質上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況且個案中法定刑的衡量不僅要考慮到保護的法益,還要綜合案件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處罰必要性進行判斷,[3]因此,僅僅以兩罪保護法益作為重刑化的依據,似乎顯得有些單薄。
(二)用預備犯理論解釋收買行為輕刑化的可行性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了收買婦女、兒童與強奸、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重罪并罰的情形,那么能否將收買行為視為這些罪名的預備犯呢?車浩教授認為,[4]整體評價來說,違背女性意愿的“買媳婦”行為,幾乎天然地包含了強奸、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重罪的內容。在此意義上,收買被拐婦女罪甚至可以被評價為前述罪名的預備犯。將該預備犯單獨定罪,無論行為人是否實施后續的重罪行為,都給予刑事處罰,正是體現出刑法對收買行為提前懲罰與從重打擊的嚴厲態度。
筆者認為,這一解釋并不充分。首先,收買行為在客觀上是獨立的,不可能將其解釋為其他犯罪的預備犯。如果將本罪解釋為其他犯罪的預備犯,那么拐賣男童的情形就說不通了。從實務情況來看,收買男童大多不是用來虐待或施加其他侵害,而是買來自己撫養的。如果收買犯罪是其他犯罪的預備犯,那此類收買男童的行為就不需要《刑法》來處罰,那么《刑法》規制此類行為也就失去了意義,這顯然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原理的。[5]況且,即使是收買婦女的情形,后續行為從表面上看似乎有類型化的牽連(強奸、拘禁等行為),但前后行為本質上是完全符合異種數罪并罰的法理的,因此也應當評價為數罪,而非所謂的預備與實行的銜接。
(三)刑法設置共同對向犯的意義
共同對向犯,又稱對合犯,系指基于雙方互為行為對象的行為而成立的犯罪。車浩教授主張,《刑法》中對向犯本就有處罰買方和不處罰買方這兩種情形,評價收買被拐婦女的行為不能僅僅與拐賣行為相比,還要與那些《刑法》根本就不處罰的其他買方行為(如購買發票、購買毒品自用)相比,顯然立法者是給予收買婦女以犯罪化的嚴懲。而羅翔教授則堅持,收買與拐賣作為一組共同對向犯,二者刑罰之懸殊已經到了法理不兼容的地步。
筆者認為,拐賣與收買這一組對向犯確實具有“共生行為”的性質,但共生的行為未必都是等值行為。雖然具有對合性的行為都具有社會危害性,但是,《刑法》予以規制的只能是具有相當嚴重程度的危害社會的行為,這是刑法正當性的基礎。在具有對合性質的情況下,拐賣婦女、兒童一方的行為往往具有連續性和多次性的特點,而且期間會伴隨相當嚴重的情節(殺傷、強奸等),而收買一方的行為往往是不固定的、一次性的。[6]考慮到具體個案實際情況千差萬別,基于個案正義的考量,筆者在這里更贊成車浩教授的觀點,并且,單向構罪的規定,也是刑法謙抑性的體現。
綜上,在考慮提升收買犯罪法定刑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與刑法體系上的問題相沖突,這其中要考量的因素還有很多,切不可因為公共輿論的推力陷入情緒化修法的泥潭。
五、結語
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后,解釋者根據正義理念與文字表述,并聯系社會現實解釋含義不同的法律;經過一段時間后,立法機關會采納解釋者的意見,修改法律的文字,使用更能實現正義理念的文字表述;然后,解釋者再根據正義理念與文字表述,聯系社會現實,解釋法律再重復上面的過程,這種過程循環往復,從而使成文法更加完善,使司法不斷地追求和實現正義。
誠然,法律不是萬能的,道德也不夠強力,而人性又是如此晦暗難明,即使我們再清醒,也總有人活在暗夜里。而刑法本身的持重性與謙抑性,更決定了無論是面對熱點還是冰點問題,都要謹慎持重,避免掉入情緒化的陷阱,這也說明了法律本身基于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不可能對每一個案件都實現實質正義的保護。最后,筆者還要強調的一點是,回歸樸素的法感情視角,鐵鏈女事件是向全社會敲響的警鐘,它告訴我們,人的尊嚴需要全體人一同維護,在這條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