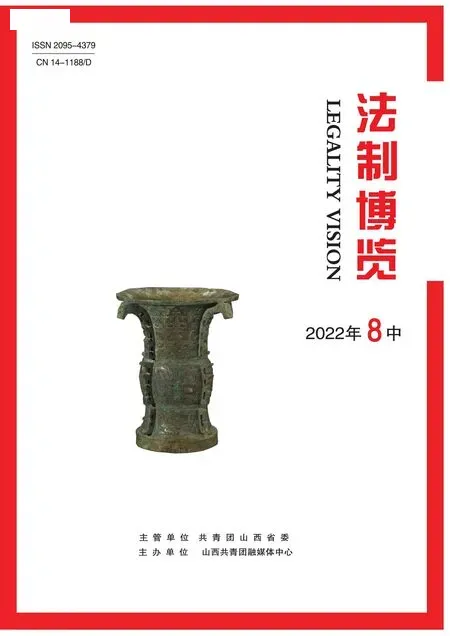醫療糾紛中“告知內容”精致化的反思
——以“幽靈手術”案件為視角
尤中琴
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廣東 東莞 523000
醫療手術常在病患麻醉后喪失意識時執行,故特別容易在未經病患同意下,由其他醫師甚至非醫師替代。此種手術行為,在英美國家俗稱為“幽靈手術”(Ghost Surgery)。于醫方而言,外科醫學作為一種臨床技巧,需要實務培訓方能接力傳承,基于醫學教育等因素考慮,某些情況下并不愿患者知曉實際主刀者身份;于患者而言,作為醫療成本以及后果的承載者,“誰開這一刀”事關切身利益,實不愿被隱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條確立了我國的醫療告知制度,然而,對主刀醫師的資訊、參與手術的方式等是否應當納入告知范疇付諸闕如,司法對于審查認定“幽靈手術”缺乏體系性。本文以我國司法實踐中“幽靈手術”多元場景為視角,結合域外經驗和案例,通過對醫療告知內容精致化反思,解開“誰開了這刀”的現實困境。
一、“幽靈手術”多元場景的司法檢視
基于醫療行為的高度專業性,司法審判存在較為嚴重的“鑒定依賴”現象[1]。在發生醫療糾紛時,患者習慣于將更多的目光投注于醫方過錯方面。隨著權利意識的覺醒,部分患者開始對“誰開了這刀”提出質疑,并以此作為推定醫方過錯的借口。本文以“更換主刀醫師”“實際主刀醫師”等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選取了30份有效案例,并據此分析模糊立法狀態下司法對“幽靈手術”的立場。
(一)“幽靈手術”場景多元
“幽靈手術”并非想象中單一的“以劣代優”,樣本案例呈現五種場景。1.未和患者溝通臨時更換指定主刀(占比50%)。雖實際主刀具備手術資質,但未和患者術前溝通,患者據此主張醫方侵害知情權。2.實際主刀醫生身份不明(占比20%)。發生醫療糾紛后,患者要求調閱手術記錄,但主刀醫生一欄沒有簽名,醫方也拒絕透露。3.實際主刀為醫師助理(占比10%)。院方指定的主刀醫生雖參與手術過程,但主刀簽名為醫師助理,且不具備相應等級資質。4.實際主刀醫生并非是協議主刀醫生(協議主刀為專家,占比10%)。患者基于對專家的信賴(通常需支付專家費)選擇其擔任主刀醫生,但專家并未參與手術,患者認為醫方構成欺詐,并全部發生在民營醫院的醫美行業。醫方以“院長手術”等噱頭招攬顧客,院方實則另安排醫師主刀。
(二)“是否告知”評價不一
主刀醫師資訊和參與手術方式是否應術前告知患者并征得同意,司法實踐評價尺度不一,主要有以下理念:1.對醫方臨時更換主刀或基于醫學教育由助理醫師手術評價相對寬松。部分案例雖未曾直接給予肯定評價,但回避了患者的質疑,并未對此作出過錯認定①(2016)蘇04民終1944號案。。2.對于醫方拒絕提供實際主刀醫師身份資訊,消極應對舉證義務,法院大多對醫方作出過錯推定②(2018)浙0103民初8025號案。。3.法院對于醫方擅自更換醫患達成協議的主刀,無一例外做出了否定評價。尤其在醫美行業,基于隱含的“消費”因素,大多認定醫方構成“欺詐”③(2016)吉0381民初3189號案、(2020)浙03民終5658號案。。以上復雜多樣的評價理念,折射出審判人員在考量“幽靈手術”個案時會引入多重價值思維。
(三)“未予告知”結果迥然
雖多數情況下司法對“幽靈手術”給予否定評價,但醫方是否對此擔責卻迥然不同。過錯和結果的關聯有四種層次:1.無因果關系,醫方無需額外賠償,依然以鑒定意見為裁決依據④(2016)蘇04民終1944號案。;2.無因果關系,據自由裁量權酌情醫方賠償⑤(2015)鼓民初字第7719號案。;3.有因果關系,參照鑒定意見提高責任比例⑥(2020)浙03民終5658號案,該案判決顯示鑒定意見認定醫方的過錯參與程度為次責,法院以醫方履行告知義務存在瑕疵將責任比例提高到主責。;4.有因果關系,醫方承擔全部責任⑦(2018)浙0103民初8025號案。[2]。在多數情況下,司法即便認定醫方未經同意更換主刀存在過錯,但只要實際主刀不缺乏資質或是助理醫師,即可阻斷因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從結果上虛化了醫療告知制度的意義。
綜上,醫療告知制度在面對“幽靈手術”時呈現失范,對主刀醫師資訊以及參與手術方式等是否適用“告知后同意”法則尤顯遲疑,急需價值體系重塑醫療告知邊界,以規范“自由發揮”的司法裁量。
二、醫療告知邊界考量的價值維度
(一)內生價值:醫療告知是人格權覺醒的要求
隨著社會發展及人格理念的轉變,比較法上逐漸承認了人格權的自我決定和控制方面的內容,人格權被從積極動態方面予以理解和構建,這其中就包含了自我決定權⑧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13年(礻)第4020號判決。。不少國家和地區是通過判例形式逐漸肯定了這項權利的獨立性。如日本“乳房切除案”⑨如日本《醫師法》第十九條第1項:“從事診療之醫師,在診察治療之請求存在的場合,若無正當事由,不得拒絕該請求。”判決中指出“醫師因違反告知說明義務而侵害患者選擇治療方式之意思決定,且乳房切除將牽動女性細微的心理感受,雖醫師于后續切除乳房治療過程也無疏失,亦應承擔患者撫慰金與律師費之請求”。我國2009年《侵權責任法》(已廢止)首次以民事基本法律的形式對患者知情同意權進行了規定,此后我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條更明確特殊介入治療應當實現“醫方清晰告知、患者明確同意”,體現了對患者自主決定權的格外尊重,充分彰顯人格權積極利用的價值。“誰開這一刀”是影響患者自我決定權實現的重要信息,醫方理應如實說明并取得病患同意。醫方應當告知患者主刀醫師的身份資質、手術角色,這是患者人格權積極利用價值的內生要求。
(二)倫理價值:告知例外是維護公序良俗的體現
《民法典》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立法宗旨,并進一步確認和強化“公序良俗”。延伸到醫療行業,提供醫療服務的主力軍依然是公立醫療機構,且醫療機構有著救死扶傷的社會責任,強制締約應用在醫療領域,是醫學倫理法律化的結果,大部分國家的立法都肯定了醫療機構的強制締約義務[3]。但醫療行為原本就充滿高度風險及不確定性,若要求醫師就所有可預期或不可預期之事項加以說明,并課以醫師過高的違反責任,醫病關系可能從此更加疏離,導致病患“被拋棄到空虛的自主中”[4]。
曾有這樣的案例,一名孕婦伴發臍帶脫垂被緊急送醫,主刀醫師牟某和其他醫務人員迅速展開緊急搶救,但主刀醫生在手術未完成的情況下突然暈倒,失去意識,其他醫生迅速上臺完成手術,確保了孕婦胎兒安全[5]。此種情形下,要求醫務人員履行告知義務,取得患者或其近親屬的明確同意并不現實,在患者急需搶救且醫方無法取得患者本人及其近親屬的明確同意時,患者將身陷雙重困境,既無法接受告知,亦無法獲取近親屬同意,如恪守成規將阻卻醫方對生命垂危的患者及時救治,并最終損及患者生命健康。此時,醫務人員應當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條的規定立即安排人員搶救,其體現了醫療告知的倫理價值。
(三)社會價值:醫療告知應當兼顧公共利益
若讓患者在嫻熟的手術醫生和經驗匱乏的實習醫生之間選擇,相信極少患者會選擇后者。但手術是一種臨床技藝,具有很強的實操性,往往需要學習曲線的經驗累積,除了依靠動物實驗、科技輔助的虛擬手術之外,醫學教育只有依靠臨床訓練才能將手術技巧傳承,醫學方能持續進步并青出于藍。故從醫學教育和醫學進步的公益觀點出發,某些情況下由實習醫師實際主刀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醫療告知制度應充分考慮醫學教育的公益性,注重平衡“目前的患者自主權益”和“未來患者的社會公益”,而不應偏廢一方。在術前告知并征得告知對象同意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協議醫師通過在場監督的方式執行手術,并非一定要親自完成手術主要部分。
三、醫療糾紛中“幽靈手術”的審查認定
“誰開了這刀”屬事實認定環節。目前,司法實踐對主刀醫師信息披露的審查較為模糊和混亂,審查規則也缺乏體系。解決“幽靈手術”問題的前提是規范醫療告知制度,進而理清如何審查“替代醫師”是否存在。具體個案中,可先從形式合法性角度審查醫方是否履行了告知義務,再轉為對是否存在“替代醫師”實質性判斷。如無法通過直接證明的方式認定,則借助法律推定的方式審查認定。
(一)形式審查:告知義務是否有效履行
現今手術之典型方式為團隊合作式的組織醫療,一個手術的完成皆須整個手術團隊的分工協力,尤其手術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從剛開始的下刀到縫合傷口,并不可能要求主治醫師一人獨立完成。何謂主刀?醫師和患者眼中的“主刀”或并不相同。“湯某移植術案”即有此爭議。以醫方觀點而言,或認為該醫師即使未親自劃刀或縫合,但是整個手術過程皆在其完全掌控與監督下,并不影響手術成功率。但從患者角度,手術記錄上主刀一欄的簽名意味著承諾和責任,誰愿意簽名誰就是真正的主刀,“誰來主刀”“如何主刀”是影響患者決策的重要信息,應當均納入告知范疇,以避免“幽靈手術”爭議。
(二)直接認定:“幽靈手術”的可證性
患者認為主刀醫師沒有實際參與手術,屬于一種消極事實。消極事實的證明存在一定的難度。雖然消極事實很難通過正面去證明,但可結合與積極事實之間的辯證關系來認定消極事實的存在。“幽靈手術”是否存在是很難通過醫方的證明而被認定,但可以通過醫患雙方提供的證據和證明過程綜合判斷。如在某醫療糾紛投訴案中,患者主張主刀醫師洪某并未參加手術,但手術記錄上主刀醫師一欄確為洪某的簽名。在醫方無法提供手術錄像的情況下,執法機關通過調取洪某的12306火車票信息和洪某在老家的微信消費記錄證實其實際并未參加手術。
(三)推定的適法性:推定“幽靈手術”的存在狀態
如果篤定關注于確證,那么可能使司法審查流于對事實的無窮探究,且未必有確定結果,應當允許司法機關采取推定的方式在合理期限內確定案件事實。法院在認定事實的過程中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間,即具有要件裁量權。在證明責任的視角下,可以初步明確患者和醫療機構在醫療損害糾紛中應當各自證明的對象,因此可以確定各自的舉證責任。
“誰開了這刀?”是法律應當直面的社會問題。醫療告知制度是解決“幽靈手術”的利器,但制度落地的細節還需司法摸索和立法完善。基于篇幅有限和能力不足,本文僅探討了“幽靈手術”是否應當納入醫療告知制度、告知的范圍和程度、如何審查認定等議題,涉及因果關系、法律后果等問題還有很大探討空間,期待拋磚引玉,激發法律同仁更多的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