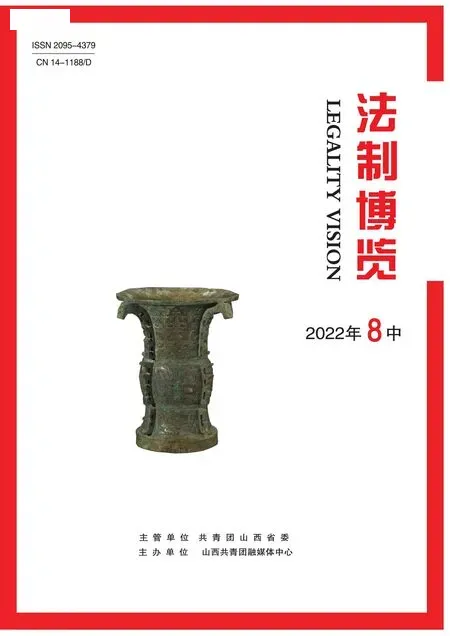《民法典》視角下探究我國居住權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沙 爽
山東省濟寧市金鄉縣法律援助中心,山東 濟寧 272200
居住權源于羅馬法,是一種特殊的人役權,即為特定人群的利益利用他人所有物的權利,從權利人角度來看,這是一種以他人所有物供自身使用和獲益的權利。它與地役權從屬兩個概念,人役權不需要如地役權一般以有需役地的存在為前提,但是具有有限期限等限制。居住權在《民法典》中的制定與其他物權制度存在多方面的重合,但對于不同情況又具有其應用的正當性,所以即便《民法典》的制定從起草開始就對這一內容做了考量,但是關于制定該內容制度的必要性的爭議始終貫穿整個制定過程。《民法典》正式推出后,怎樣去理解和應用這一權利成了人們廣泛討論的課題[1]。
一、《民法典》完善居住權制度的正當性
(一)保障群體居住需求
羅馬法最初設立居住權,其初衷是要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如流浪兒童、孤寡老人、沒有繼承權的人,而這一權利制度在后世的使用,也是基于各國的情況(對弱勢群體的考慮)展開。如我國要進一步提升對人民群眾生活的保障,就需要建立這一權利制度,對以上的弱勢群體乃至長期非婚同居者的個人利益進行保護,只要其屬于無房可住的范圍,都可以成為居住權的主體或受益對象,以為社會的穩定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2]。對此曾有些學者提出用現有法律解決弱勢群體居住問題,從而避免設立居住權與其他物權相重疊,但《物權法》(已廢止)就因為沒有規定居住權而缺乏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可見租賃等其他方法解決特定群體的居住問題不符合實際,更不要說應對日益突出的養老問題,這是《民法典》設立居住權的正當性原因之一。
(二)完善住房保障體系
目前我國住房主要分商品性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兩類,為減少立法的重復性,有人曾嘗試以社會保障制度來促進特定人居住問題的解決,為此我國實施了多個針對住房問題的社會保障制度,如廉租房、公租房、經濟適用房以及安居工程,但是這些措施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如制度對城鎮居民的適用性高,農村居民無法從中獲益。且現今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待完善,以上措施的實施并不能應對特定人群住房難的所有問題[3]。當然對于廉租房與公租房的使用,當事人也被局限在租賃的形式中,讓人們對房屋使用不具備穩定性和靈活性,從這一角度來看,以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特定人群住房問題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居住權的設立具有其正當性、必要性,它能有效解決以上問題,還可以幫助處理“小產權房”問題,是城鎮化推進下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措施。
(三)房屋利用率最大化
隨著社會發展的推進,居住權涉及的問題已不僅限于婚姻家庭與財產繼承領域,人們的投資和消費也會觸及居住權益問題,在這一視域下,如何讓房屋利用率最大化,進而滿足人們對居住權的多樣化要求成了《民法典》不得不考慮問題。例如基于老齡化現象的以房養老模式正逐漸興起,如果用既有的反向抵押或售后租回的辦法進行養老,則制度不足以調節可能出現的種種矛盾。但是要設立居住權,老人可通過對房屋所有權的讓與獲得穩定的生活環境和一筆資金上的保障。另外如果是合資購房的情況,出資人共同擁有房屋就可以享受有關房屋的一切物權,但如果出資人不同時作為房屋共有人,其也無法享有與該房屋相關的物權,而這違反了契約原則。如若建立居住權,合資人雙方可分別享有所有權和居住權,對于房產的利益分配將更加合理,而這也有益于房產的充分利用[4]。
(四)回應司法實踐需求
從司法實踐角度來看,法院對一些糾紛的判決也亟需居住權制度的確立給予回應,如遺囑繼承糾紛、贍養糾紛和離婚案件等,如果能設立居住權,則這些糾紛的判決也會更加合理。以離婚案件的處理為例,婚姻關系中一方有經濟困難的,另一方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思為對方設立居住權,以對其離婚后生活進行基本的保障,當然弱勢的一方也可以根據自身情況主動請求取得居住權,如被法院認定生活貧困,可向另一方爭取居住權,直至其居住問題得到解決。而如果沒有設立居住權,顯然在這類案件中就會有人面臨生存的窘境,從而增加社會問題[5]。
二、《民法典》中居住權制度的有關解釋
(一)居住權主體——居住權人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規定,“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指出了居住權的主體和客體,但居住權人作為居住權的主體,并沒有明確的范圍界定,因而在應用這一制度時要對居住權人的范疇做以進一步的厘清,如明確是否包括法人及其他的組織。一般法條制定主體會明確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在居住權沒有對此進行明確時,有學者認為當以自然人為限,也有學者認為法人應當被劃到居住權人范圍中。而從居住權制定的初衷來看,居住權主要是要解決特定群體的贍養和撫養需要,在于幫助有居住困難的自然人解決基本生活問題,所以自然人自然應包括在居住權人范圍內,但從新時代人們多樣化的房產使用需求考慮,僅是自然人限制了房產的有效利用,因而從這一角度,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也應包含在居住權人的界定之內。
(二)居住權客體及其界定
居住權的客體顧名思義是住宅,在《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規定中指“他人的住宅”,但是僅是這樣不足以限定客體的范圍,像是房屋所有權人享有對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利,不需要設定居住權,所以法條標明“他人”自然是對居住權的客體另有嚴謹的界定。人們首先要區分房屋的概念與住宅并不相同,房屋包括住宅,但是對其使用功能有更多要求,例如遮風擋雨、御寒保暖、給人的生活與工作提供穩定環境等等。所以對于居住權來說,用住宅不如“房屋”準確,而有時居住權人不一定要占據房屋的所有使用權,在房屋所有人也居住在房屋當中時居住權人只是占據房屋的部分使用權,如客廳、單獨的某一房間,這要根據房屋的空間結構進行具體的劃分,進而排他使用。所以法條將居住權客體界定成整體的房屋也不很恰當,應該就具體的房間、物品使用有所限定,如他人房屋整體或部分及其附屬設施。
(三)居住權的獲取與變更
根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三百六十八、三百七十一條,可梳理出居住權的設立方式,即意定設立。《民法典》中居住權的設立一般為合同或遺囑,本著尊重當事人處分自由與意思自治的原則確立權利的建立,而非法定確立,這樣設置的初衷在于給予雙方當事人以自由的權利,如有一方沒有確立該權利的意愿,也可不生成相關法律效益。而居住權的合同簽訂需以書面形式,合同條款要包含當事人姓名、住所、住宅位置、居住條件以及其他具體要求,關于居住權期限和對爭議的解決辦法也要包含到其中,以讓合同內容更加清晰[6]。如以遺囑方式建立,遺囑內容也要就遺囑和遺贈做好區分,以減少誤解,避免分歧。居住權的消滅在《民法典》的第三百七十條中可以找到有關規定,即居住權期限屆滿或居住權人死亡,居住權即消滅,即時應辦理注銷登記。然而除居住權人死亡外《民法典》沒有更具體的變更或消滅說明,所以有關人員還應在設立這一權利制度時對權利混同、合同解除、居住權人濫用權利等情況予以考慮,以保證居住權人利益。
(四)居住權的有關限制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條規定“居住權無償設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對居住權進行了限制,相較于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有關制度,這一設置給予了房屋所有人以更多的選擇權利,也是為居住權應對新時代人們房屋使用需求多樣化的發展做出了鋪墊。從這一法條的限定內容來分析,其將居住權合同的簽訂視作一種交易行為,因而將居住權完全限定成無償也不很合理,附加的部分內容更便于新時代人們對于居住權的使用。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條規定“居住權不得轉讓、繼承,設立居住權的住宅不得出租,但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也是對居住權的又一種限制,但其本身出于對社會性居住權的保護,讓居住權的設立初衷得以維持,所以也是相對合理和嚴謹的。
三、《民法典》中居住權制度的具體適用
(一)居住權人的權利
基于以上對居住權人、居住權客體以及居住權設立、變更和限制的界定的分析可明確居住權人的權利義務,以及對該權利制度的保護措施。其中居住人權利包括對房屋(部分房屋及設施)的占有、使用權,其他人不應當干涉當事人行使占有權利,如果約定居住權范圍較小,為完整實現居住權的使用,可將權利范圍擴大至公共區域,如客廳等。收益權,根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條規定,當事人能夠根據約定出租居住權所在的住宅,滿足居住權人以房屋進行獲益的需求,但需在房屋所有權人的同意下展開,屬于當事人自治的范疇。可根據居住權人的具體需求對房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良,但不得改變原房屋結構或是減損房屋價值,費用由受益方承擔,如居住權人是經濟情況較差的老人,費用可協商由房屋所有權人擔負[7]。優先購買權,這一點雖然《民法典》中沒有明確標明,但根據現有權利的性質與相關法律規范,權利人滿足一定條件可對房屋具有優先購買權,而具體內容由當事人雙方根據合同來確定。
(二)居住權人的義務
居住權人享有居住權益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義務。首先,出于居住權消滅前房屋價值不受減損的原則,居住權人要保證以正常的使用方式對房屋進行使用,如要對房屋進行結構性的改造,必須經由房屋所有人許可,同時,居住權人在行使權利期間也要對房屋進行一定的維護,以令房屋(所有權人的住宅)免受危險與侵害;其次,居住權人在使用設立居住權房屋時所產生的費用也要由居住權人自己承擔,如水電煤氣、取暖和修理等,除非房屋所有權人要對房屋進行翻新,否則一旦居住權人不履行對房屋的正常維護和修繕義務,或因管理不到位而造成房屋需要修繕的情況,就要承擔所有相關費用;最后,居住權人如果已不存在居住問題,應當履行房屋返還義務,這一點《民法典》沒有詳細規定,但原則上居住權消滅居住權人的有關權利也會消失,所以這也是居住權人需要履行的義務之一。
(三)房屋所有權人的義務及居住權的保護
與居住權人義務對應的是房屋所有權人的義務。根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規定,居住權人行使自身權利時房屋所有權人不應予以干涉,同時在房屋所有權人行使其物權對房屋進行處理時,其他人也不應當干涉,但在存在居住權時,需要對居住權人履行通知的義務,以維護居住權人的有關權利。基于居住權在《民法典》中允許有償設立,所以居住權人和所有權人之間的關系還可以是基于利益的合同關系,此時所有權人不但要對居住權人產生的對房屋的損毀、損壞行為承擔起維護、修繕義務,還要對居住權人進行追償,以保證房屋的價值。除此之外,要保證居住權的合理使用,對當事人雙方未明確的合同條款、細則也要進行合理的補充和修復,運用合同漏洞填補規則對未約定居住條件與要求、未約定居住權期間、未約定解決爭議方法、未約定其他非法定事由等情況進行補充完善,以合理化糾紛的解決。
四、結語
所有法律的存廢都要經過全面、周密的考量,尤其《民法典》的制定要以社會生活及人民群眾內心期盼、實際需求為參考來區分具體的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居住權正是基于社會人口老齡化、城市住房緊張等社會現象而被添入《民法典》物權編的內容,其制度界定與使用也要綜合考慮人民群眾實際的需求,盡量明確好適用范疇,以讓其功能在具體的案件糾紛中得到最大的釋放,使人民群眾的居住需求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