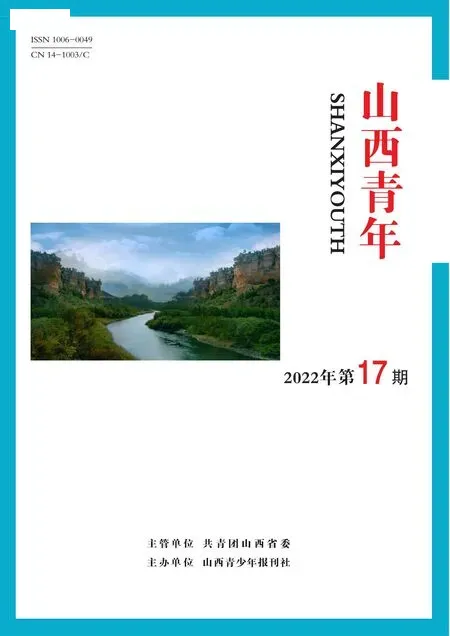淺析聯覺機制在演唱過程中的效用
——以《長征組歌》為例
畢亞濤
太原師范學院,山西 太原 030619
聯覺是人人都有的心理機制,它在音樂的創作、表演、審美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人們公認的十分抽象的聲樂演唱學科中,聯覺的作用更是貫穿聲樂技巧學習、作品理解、表演的全過程。本文從聯覺入手,首先簡單介紹了聯覺機制、音樂聯覺的相關研究和《長征組歌》的創作背景,然后通過《長征組歌》的片段,具體說明聯覺機制在演唱過程中的效用。
一、聯覺與聯覺規律
(一)感覺與聯覺
感覺是指“腦對直接作用于感覺器官的客觀事物的個別屬性的反映”[1]。感覺依照感覺信息的來源可以被分為內部感覺和外部感覺,反映客觀事物個別屬性的感覺叫外部感覺,包括聽覺、嗅覺、味覺、膚覺和視覺[2]。例如,當一顆梨作用于我們的感覺器官時,通過視覺可以反映它或黃或青的顏色屬性;通過味覺可以反映它或酸或甜的味道;通過嗅覺可以反映它的清香氣味;通過觸覺可以反映它的平滑表面。內部感覺是反映生物體自我本身的狀態的感覺,包括運動覺、平衡與機體覺。例如,在游泳時我們可以感受到自己手腳的運動位置、動作是否協調以及在嗆水咳嗽的時候身體內臟的劇烈收縮等,這種對自己身體的感覺就是內感覺。感覺使得我們能夠感知和分辨客觀存在物的不同屬性,感知它們的色彩、音響、溫度等等,也使得我們能夠感知體會自身的身體運動狀態和身體姿勢以及身體內部的器官狀態。此外,感覺還是其他高級、復雜心理現象如知覺、聯覺、聯想、意志等的基礎。
聯覺是指“從一種感覺引起另一種感覺的心理活動”[3],即某一種感覺刺激物在引起對應感官感知的同時引發了另外其他的感官感知,而能夠帶來這種額外感官感知的對應刺激物卻從未出現。例如,人們在看到暖色類顏色紅、橙、黃色會感覺到溫暖;在看到冷色類顏色藍、青、綠色時會感覺到寒冷,這就是一種聯覺現象。聯覺體驗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種心理現象,它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二)歌唱運動中的聯覺體驗
歌唱作為一種全身心的運動,在訓練中歌者也是依據內感覺的判斷來不斷調整歌唱狀態。但因為內感覺對身體的感知既“看不見”也“摸不著”,所以在聲樂教學和歌唱狀態調整中,教師和歌者運用最多的還是建立在感覺基礎上的聯覺活動。例如,要求聲音有金屬感、面罩感,調整聲音柔軟一點、硬一點、圓潤飽滿等。在歌唱運動中,氣息是基礎,聲音是支柱,兩者可以說是歌唱的最基本要求。下面就歌唱中的呼吸運動與發聲運動的聯覺現象進行詳細闡述。
呼吸運動中的聯覺體驗是由呼氣和吸氣動作引發的肌體運動形成的,是由內感覺壓覺引起外感覺視覺的聯覺體驗。例如,在吸氣的時候,有的老師要求學生要感覺自己像一個氣球,要吸滿氣讓氣球膨脹。它是由于吸滿氣后肺部膨脹、橫膈膜下壓,由壓覺引起了視覺上的聯覺體驗。有的老師認為“吸氣的過程,就是我們的‘心靈’舉起盆來的預備過程;呼氣的過程,就是將‘心靈’之水徹底潑出的過程。吸氣越是徹底到位,水潑的就越是干緊利落,呼氣就越是淋漓盡致。”[4]呼吸運動中的聯覺現象在我們的聲樂學習中十分常見,教師根據聯覺體會加上自己的聯想和體會傳達給學生,以達到其教學目的。
發聲運動中的聯覺體驗是由氣息沖擊聲帶引起的聲帶肌體運動的形成的,發聲運動中的聯覺體驗要比呼吸運動中的聯覺體驗更繁多、更復雜。在日常練聲中,我們常用意大利語中的五個元音字母“a、e、i、o、u”來進行。一般認為“a、o、u”被分類為“寬”母音,“i、e、”被分類為“窄”母音,在這里,元音的發聲就已經有了聯覺體驗。在元音發音和練習的過程當中,窄母音“i、e”母音被要求唱的“敞開”一點,不能太“扁”“窄”。通常情況下,寬母音“a、o、u”則要求唱的靠前、“窄”一點。這種由聽覺引導的視覺與觸覺聯覺體驗,在不斷相互作用中調整著歌者的發聲狀態,提高著歌者的發聲能力。發聲部分的聯覺體驗還有很多,如聲音要貼著后咽壁繞過后腦勺“甩”到眉心處,美好的聲音要像“天鵝絨”一般、聲音要“立起來”“豎起來”等等。這些帶著聯覺感受的語言充斥在聲樂教學和發聲運動中。
二、長征組歌綜述
長征組歌這首聲樂套曲由10首各自獨立的歌曲共同組成,肖華將軍作詞,由晨耕、唐訶、生茂、遇秋作曲。用生動形象的音樂語言重現和贊美了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的偉大、感人情景,是我國音樂史上一部重要的合唱作品。
(一)創作背景
詞作者肖華的創作動機來自觀看了描寫長征歷程的畫作——《西行漫畫》。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層層圍追堵截,跨過了河流沼澤,爬過了雪山草地,歷經磨難取得長征勝利。黃鎮的《西行漫畫》引起了肖華的創作欲望,1964年4月,他到杭州西湖療養時開始了創作長征詩稿,最后完成了12首詩稿。
1964年11月,肖華的創作被當作政治任務交給了戰友文工團團長晨耕,要求譜曲并演出。由戰友文工團晨耕、生茂、唐訶、遇秋4位作曲家為《長征組詩》譜曲。因為最后的兩首詩稿反映的是紅軍長征之后進行抗日戰爭的歷程,所以就只為前10首譜了曲。四位作曲家集體構思,然后按照個人特長分工進行,在繼承當時流行的大合唱和抗戰歌曲的同時加入了許多民族曲調素材。
(二)創作特點
在歌詞的創作方面,肖華具有深厚的文學底蘊,在杭州養病的期間又大量閱讀了中國古典詩詞。在形式上肖華運用了自創的詩歌形式——“三七句,四八開”,每段由四個三字句加八個七字句組成,所以詩歌本身的節奏突出、韻律鮮明,有利于傳唱。
為了使作品更加通俗易懂和便于傳唱,作曲家們糅進了長征路線上路過的一些地方音樂素材。例如,苗家山歌、湖南花鼓、江西采茶戲等地方特色民歌和戲曲曲調;在樂隊上,也加入了很多的民族樂器,如云南傣族鑼、竹板等。
三、聯覺機制在演唱《長征組歌》中的效用
“音樂表演是賦予音樂作品以生命的創造行為”[5]——音樂表演是音樂的再創作。演奏者通過多種藝術手段,將作曲家創作的樂譜符號化形式的音樂作品變為聽覺可感的音響形式傳達給聽眾,音樂作品的生命才能得以真正展現。音樂表演是連接作曲家與聽眾間的紐帶,是音樂活動中不能缺少的一環。而聯覺是每個人都具有的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所以是每個音樂表演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在聲樂演唱中,從演唱者對樂譜符號的分析理解,再到結合運用演唱技巧把歌曲傳達給聽眾,在這個相對獨立而又復雜的鏈條上每一個鏈接節點都與聯覺這種心理現象密切相關。在聲樂表演中,只有充分發揮聯覺的作用才能正確把握音樂形象、理解音樂內涵以及融入音樂表演技巧,從而提高音樂作品的表現力與藝術價值,將樂曲的內容準確地傳達給觀眾。
(一)分析樂譜符號,把握音樂形象
分析理解樂譜符號是演唱者在演唱歌曲前的一項必要準備工作,是歌者對音樂感性體驗和理性認知的過程。演唱者的聯覺體驗在這個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歌者能夠通過分析了解樂譜內涵和作曲家創作技巧,從而準確地把握音樂形象。
例如,第一首混聲合唱《告別》,是不帶再現的三部曲式。第一部分中開頭前奏的前兩句由小號奏出在中音區的號角性的音調,號角性的音調往往給人帶來積極、向上的感覺,但在作曲家選擇了中聲區且速度放慢加上連續的三連音進行,則給聽者帶來紅軍悲壯無奈被迫出發的視覺形象體驗。
緊接著弦樂出現,調性轉為小調,給聽者以抑制、壓迫的情態體驗,使得情緒更加悲涼。更加鞏固和突出了無奈的、被迫出發的紅軍形象。到了后半段速度由慢轉快,加了小軍鼓使得節奏更加緊湊有力,同時音越來越強,給聽者帶來積極向上、興奮的情態體驗,使得聽者感到紅軍腳步越來越有力、離我們距離越來越近,觸發觸覺和視覺體驗。我們心中先前的悲涼無奈的紅軍形象一改為一種充滿樂觀、積極面對的形象,這就是我們的聯覺在不知不覺中發揮作用。
第六首男高音領唱與合唱《過雪山草地》,結構為二部曲式。引子中弦樂奏出連續的半音顫音進行,小二度音程的緊張度給人以惡劣、嚴酷的感覺,連續的上行與下行進行則給人以狂風陣陣、大雪紛飛的觸覺與視覺體驗,是一個描寫紅軍生存和需要克服的惡劣環境的音樂形象。
隨后的突然進入器樂合奏,管樂奏出宏偉的旋律音型,強音給聽者以積極向上的情態體驗、擁有強大力量的紅軍視覺體驗,塑造了一個堅強不屈、勇于面對困難的戰士形象。
不需要歌詞的幫助,僅僅通過一段引子,聯覺體驗就使我們可以從視覺上看到了一群在嚴寒惡劣環境中克服困難、堅強前行的紅軍形象,為我們之后的演唱做了很好的鋪墊。
(二)調整歌唱狀態,融入情感內涵
在大致把握音樂形象和內涵后,演唱者還需要進行一項重要的工作,即把自己對作品的理解用聲音表現出來,音樂形象用聲音塑造出來,專業的合唱團隊會不斷調整歌唱狀態、靈活運用歌唱技巧,達到曲目表現要求。歌者在這個不斷自我調整的過程中,聯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例如,第四曲領唱與合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段女聲領唱“橫斷山,路難行。天如火來水似銀,天如火來水似銀!”
演唱時要把氣息吸滿,在唱的時候有意識地控制氣息、均勻拉長線條送出,聲音要像有一條絲線拉著從眉心出緩緩流出,這樣才能表現出曲子所要求的真摯與親切的意境。因為這一段的速度較慢,我們在咬字的時候必須要更加注意聲音發聲位置的一致性與統一性。如:我們唱“橫—斷—山,路—難—行”這六個字的時候,“橫—heng”字屬于中東轍,“斷—duan、山—shan”兩字都屬于言前轍,“路”字屬于姑蘇轍,“難”字屬于言前轍,“行”字屬于中東轍。我們日常說話中這六個字的時候發音位置都比較靠后,所以對這六個字的咬字發聲位置要略微的靠前一點,把聲音盡量往眉心處靠,腔體更加的豎起來一些。尤其是“行—xing”與后面一句中“銀—yin”字的對比,一個是后鼻音一個是前鼻音,不可混淆,既要唱得清晰、前后鼻音清楚、聽眾容易分辨,也要將聲音統一起來,即唱“行”的時候聲音更加靠前一些,唱“銀”的時候聲音更加往后靠一靠、空洞一些。在唱第二段“親人送水來解渴,軍民魚水一家人”時,我們同樣要注意聲音位置的統一問題。
“親、解、渴、軍、民、魚、水、一、人”這九個字中“e、i”母音居多,所以我們唱的時候要盡量唱的“寬”一點兒,喉嚨打開、腔體打的要更大一些。而“人、送、水、來、家”這五個字中“a、o、u”母音居多,所以我們唱的時候位置要靠前一點,唱“窄”一些,以達到不同元音的發聲位置統一。通過運用我們的聯覺體驗,在變化中求統一,在統一中求變化,做到聲音動態的平衡。這樣的聲音才能賦予音樂形象以完美的載體,寄托歌者情感,更好地表達作品內涵。
四、結語
本文綜合運用當代的音樂美學領域對聯覺機制的研究成果,結合筆者的聲樂學習心得,通過對作品《長征組歌》的分析,得出了聯覺機制在演唱過程中的效用:一是有助于歌者分析樂譜符號,準確把握音樂形象;二是有助于歌者調整歌唱狀態,融入情感內涵,準確表達音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