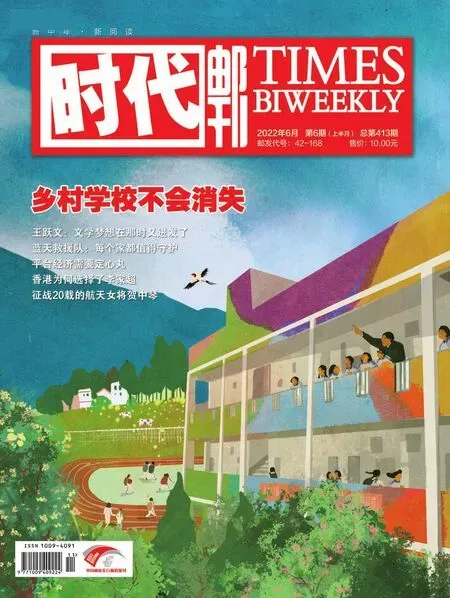平臺經濟需要定心丸
● 曹林
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要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完成平臺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出臺支持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再是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重申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強調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對密集釋放的這些信號,輿論和市場都作出了積極反應。
感到“心里的石頭終于落地”的,何止是平臺從業者和投資者?平臺經濟之所以稱之為“平臺”,是因其存在的系統性、規模性和生態性,把海量公眾吸引到平臺上,從社交、支付、娛樂、出行、購物、學習等方面,為人們提供貼心的服務。——環顧我們的日常生活,很少有人生活能離得開平臺經濟。所以,對平臺經濟利好的消息,也給平臺化生存的公眾帶來了信心。
之前印度宣稱,印度的新興獨角獸公司數量已超越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數字不一定客觀,但可以感覺到,這兩年中國平臺經濟發展勢頭明顯不如從前,頭部平臺企業與國外同行的競爭力相比在減弱。中國作為人口超級大國,為平臺經濟創新所需要的規模提供了一個非常理想的試驗場,領先世界的平臺經濟曾讓國人自豪,當下的減速讓人扼腕嘆息。
平臺經濟對一個國家,遠不只“衣食住行”的便捷和舒適那么簡單,它還事關市場信心,比如就業信心。背靠平臺好發展,平臺經濟造就了不少大廠,也就是“頭部平臺”,“畢業后努力進大廠”“積累資歷后進大廠”成為很多年輕人的夢想。大廠不僅創造了很多就業崗位,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種對“更好工作”的想象和追求,成為某種意義上“好工作”的標準和階層流動、生活上升的信心。當平臺經濟遇到發展困境,多米諾骨牌效應下,首先對就業信心形成某種沖擊。
平臺之所以稱其為“平臺”,除了生活和服務的平臺性,也在于其作為一種就業穩定器的平臺作用。這種就業穩定,不僅是“大廠”之類的高端就業,更有平臺系統所架構起的中小微企業就業。一個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共享經濟領域的平臺員工數達到了623萬人,比上年增長4.2%。共享經濟還創造了7800萬個靈活就業崗位。兩年多的疫情,這種基于平臺的用工模式在緩解就業市場結構性矛盾、增加收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加凸顯。平臺經濟關系到整個經濟生態系統中無數家庭的“飯碗”。
除了就業的信心,平臺經濟還維護著人們對生活舒適度的信心,外賣、打車、快遞,“平臺化生存”意味著“便捷化生存”。支撐起人們對科技創新的信心,作為一種依托云、網、端等網絡基礎設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數字技術工具的新經濟模式,有專家稱,平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意義可能是讓中國第一次有機會緊隨工業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國際經濟技術創新的前列。我們在電商、支付、社交和短視頻等領域的科技創新活力,不弱于任何國際同行。平臺還連接起了城市與鄉村、線下與線上、實體與網絡、當下與未來,滋養著人們對共富的信心。
野蠻生長,發展速度跑在了規范前面,累積了不少問題,完善平臺經濟治理,非常有必要,但需要良法善治,需要善待這些引領改革、帶來活力、推動發展的創新者,切不可用力過猛,不可窒息創新的活力與動力。平臺經濟需要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