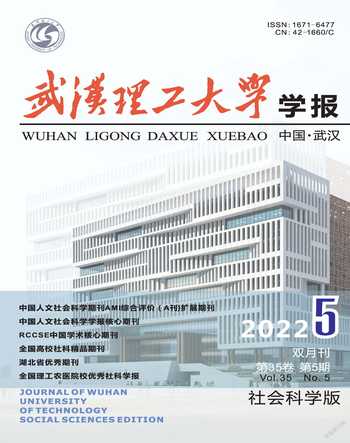應急法治視域下公民權利克減的價值證成
方路錦
摘要: 在應對諸多突發事件的過程中,我國逐漸探索出一套極具自身特色的應急行政執法模式。其深植中華傳統文化,汲取現代文明成果,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具體化、現實化的重要建樹,展現出厚重的理論價值、制度優勢與實踐偉力。應急行政執法過程中對公民權利的正當化克減,是公益與私利的權衡之舉,是法治政府的良善之治。應理性認識應急行政執法過程中的“變通執法”,正確把握行政執法實施時的“合理限制”,探求嚴格規范公正文明應急行政執法的運作機理,實現人權與秩序的動態平衡,期以展現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的巨大優勢。
關鍵詞: 應急法治; 公共秩序; 公民權利; 行政執法; 人權
中圖分類號: D922.112文獻標識碼: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5.010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突發事件,對普通民眾正常生活造成諸多困擾,同時也對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其中,行政執法在保障公民生命健康和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可否認,相較于西方國家疫情肆虐的境遇,我國疫情治理凸顯成效,我們有充分理由回應某些西方媒體與社會輿論的質疑。然而,在法的秩序價值得以充分彰顯的同時,法的人權與自由價值往往被迫過度限縮,群眾基本生活受到很大限制,公民基本權利受到諸多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職責,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中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水平”[1]。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認為,緊急狀態下,法律可授予政府十項緊急行政權,對公民個人權利予以適當限制。同時也指出,限制公民自由不能突破人道主義底線,要避免對基本人權過分限縮,防止公共權力任意擴張和濫用[2]。汪習根教授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體系的理論基點是‘人民主體論’,即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主體和人民權利作為始點和歸宿。”[3]。可見,在應對突發事件中,行政執法行為對公民權利之克減應遵循科學的邏輯理路和實踐模式。
有鑒于此,探討突發事件中權利克減的學理依據,總結應急行政執法的實踐經驗,避免不當限權、過度侵權等現象的發生,顯得十分必要。本文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擬從法的價值、文化傳統與法教義學等方面為切入點,剖析行政執法中涌現的典型案例,論證執法主體采取特殊執法方式的必要性與正當性,探究應急法治視域下行政執法的完善進路。在追尋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的“楚河漢界”中,最大程度地實現社會穩定和個人自由的雙重目標,期以展現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模式的巨大優越性。
一、 問題檢視:應急行政執法的回顧與批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嚴格執行疫情防控和應急處置法律法規,加強風險評估,依法審慎決策,嚴格依法實施防控措施,堅決防止疫情蔓延。執法機關要強化法治理念、增強法治意識,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嚴禁過度執法、粗暴執法,始終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維護穩定工作”[4]。疫情席卷全國期間,社會穩定堪憂,某些行政執法機關為維持社會秩序,有時會采用“過度”的方式進行社會治理,往往很容易忽視公民個體的基本權利,這顯然不合乎法治的理性。實際上,清華大學曾發表維穩報告指出,某些行政部門對其編制進行擴充,增加“維穩辦”“綜治辦”等輔助機構,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就會出現社會大規模動員,眾多單位共上陣來維護社區穩定的情況。但是,發動大規模人力和動用大量物力財力來維穩,社會矛盾和沖突并未因此減少,反而“越管越多”[5]。而具體到應急行政執法中,執法主體不明確、執法方式不合理和執法目的不正當等現象十分突出。
(一) 執法主體合法性之辯
執法主體作為法律的捍衛者,是法律得以落地實施的關鍵,執法主體的質量,關乎著法治國大廈房梁的牢固程度。因此,必須保證執法主體的合法性,以確保法治國得以順利運行和維系。而在疫情期間,執法主體的合法性值得追問。首先,在非緊急狀態下,依照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行政主體只能是行使行政職權的國家機關或者是法律、法規明確授權的組織,其他組織和個體均不得成為行政主體,自然也就沒有資格成為行政執法的主體。其次,即便是出于特殊時期,情況較為緊急,委托非行政主體協助開展執法工作符合應急性原則和法理的一般精神,但在非機關單位或者個人受行政主體委托或協助執法主體管理和控制疫情的過程中,不加限制肆意增加公民義務和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行為值得追問。例如,新型冠狀病毒事件發生以來,為阻斷病毒惡性傳播,維護社會秩序穩定,保護全體公民整體利益,行政執法主體大規模發動社會團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志愿者等無執法權的組織或個人協助政府參與疫情防控工作。但是,在此過程中,或是基于阻斷病毒傳播的主觀愿望,抑或是基于熱心公益的奉獻精神,未曾受過專業執法訓練的抗疫隊伍實施“硬核執法”①,一度成為社會關注焦點,其執法主體合法性存在很大爭議。
(二) 執法方式合理性之考
行政執法主體除需具備合法主體資格外,其具體行政執法行為也要受到法律法規的嚴格限制。行政執法機關背后有國家公權力支撐,若不加以嚴格規范與限制,則公民基本權利將難以得到保障。例如,在南方某城市,幾名警察帶領聚眾打牌的公民游街示眾,并帶領這些人當街喊話,以警示民眾不能打牌。由于該案例發生于全民抗擊疫情的特殊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警示作用。但是,警察作為法律規定的行政執法主體,其任何執法方式均有嚴格法律規定加以規范和約束。每一位公民都應當有尊嚴地活著,每個人的人格尊嚴都不應成為執法機關實現其目的的工具。關于警察帶領聚眾打牌的民眾游街這一行為,實質上嚴重侵犯了涉案人員的人格尊嚴權,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人身自由權。相關法律法規,無論是適用于常態下的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抑或是適用于特殊狀態下的突發事件應對法,均未授予警察與此相關的執法方式。無論是從執法的種類,還是執法的幅度上,均無法律依據。該行政執法行為雖發生于疫情這一突發事件的背景下,但其行為方式已明顯超出限制公民權利的合理范圍,如不加以嚴格約束,公民基本權利的根基將形同虛設,法治國家的大廈就會岌岌可危[6]。
(三) 執法目的正當性之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7]。因此,在應急行政執法過程中,也應將人民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價值依歸,保證所有行政執法都圍繞人民利益展開,用人民滿意的方式完成執法任務,解決執法難題,實現執法目的,任何偏離人民宗旨的執法行為都是不合時宜的,必須糾正[8]。
前述討論中,更多是基于行政執法主體在秉持正當執法目的假設前提下展開。也即假設其在進行執法行為時,是基于公共利益與社會穩定的正當目進行。但調研中也發現,存在一些疫情防控工作人員假借疫情防控目的開展執法活動,嚴重侵害普通公民合法權益的情況。例如,在山西某基層社區,一些疫情防控人員絲毫沒有防控疫情的目的,而是本著“關系好的可以自由出入,不認識的禁止出入”的主觀想法把手社區出入口。這種思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控疫情,但這帶有明顯的“人治”思維,不利于實現平等對待,也不能嚴格保證疫情防控工作的順利實現。也正是由于這一不良思維方式的存在,某地一患有輕微感冒的人員在“封城九日”之地還能夠“突出重圍”②。在疫情的收尾階段,安徽某縣城社區卡點,執法機關為避免承擔責任,在安徽全省都已經將突發衛生事件降為三級防備后,還在執意封鎖社區卡點,限制居民出行的自由,這顯然不具有正當執法目的。此外,部分執法人員的執法動機也存在問題,如一些執法人員進行嚴格執法并不是為了社會利益,而是為了追逐其他個人私利,如通過隔離措施壟斷日用品消費市場以謀取高額經濟利益。當然,這種思維方式在一般非緊急狀態下也廣泛存在,但在疫情期間其對法治的破壞力更強,對普通民眾權益的侵害也更為嚴重。這也是我們在國難當頭、疫情之下仍竭力尋求公權力與公民個人私權利相平衡的原因所在。
二、 價值證成:公民權利克減的分析與證立
一個民主國家政府權力的集中是它在面臨緊急危機中對分權理論所潛在的反應遲鈍的改正③。在緊急狀態的情況下,在一個法治國里,為了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公權力機關有必要在法治允許的范圍內對公民個人權利予以必要限制。特殊時期對公民個人權利的克減,既符合人權原則的理論,也不違反人道主義的要求。合法合理行使行政應急權,既是行政執法機關的法定職責,也是全體民眾的共同呼喚[9]。
(一) 價值論視角——實質法治的權衡之舉
法的價值主要包括正義、秩序、人權、自由、平等、效率等。按照通說之觀點,在一般狀態下,法的人權、自由價值應當是前置的。但在緊急事件發生、社會有失控之虞時,法對秩序價值的要求往往要比社會穩定狀態時要更加迫切。此時,國家生存、社會安全和全體公民利益遭受嚴重威脅的特殊狀態,消除危機、恢復正常社會秩序理應成為首要價值。此時,行政機關行使權力,可打破常規法的價值位階原則,更好地應對危機[10]。
就法的正義價值而言,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不能僅僅追求表面的正義和狹隘的正義,而應追求實質的正義和全面的正義,要用整體和變化的眼光審視和評判社會變遷與發展是非。在社會穩定有序的情況下,注重實現人權和自由價值是正義之舉,而在緊急狀態下,強調社會秩序與治理效率則代表了特殊時期真正的正義。康德曾經引用“緊急狀態下沒有法律”這樣的格言。亞里士多德則主張,“依絕對公正的原則來判斷,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的政體”[11]。這些均表明,緊急狀態下刻板地依靠常態法治理社會的政府是不正義的。
從權利視角而言,秩序更多地代表著公共利益,而人權和自由更多地代表著個人利益。緊急事件發生時,公共利益的保護要優于個人利益。因為在這一狀態下,只有公共利益得以維系,個人利益才有存續的可能,否則,個人利益將無從談起。古羅馬法學家西賽羅曾有“公益優先于私益”的名言,美國法學家龐德主張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統一的觀點。在常態下尚且如此,應急情況下更應如此[12]。
(二) 合法性視角——依法行政的良善之治
總體而言,在新冠疫情防控應急行政執法過程中,具有較為明確的法律依據。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下文簡稱《突發事件應對法》)頒布并施行,標志著全國應急管理體系基本建立,是新冠疫情防控應急執法的重要法律依據。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下文簡稱《傳染病防治法》)和《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條例》都為新冠疫情防控應急執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撐。首先,在疫情發生時,得益于黨、政府以及基層組織的大力發動和號召,大量社會組織和個體積極參與到抗疫工作中,彌補了疫情期間人力不足問題,在提升執法質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傳染病防治法》第九條,《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六條、第五十五條均有明文規定。其次,本次抗疫最大亮點是基層社區充當著主力軍的角色,不僅緩解了行政機關的工作負擔,同時也有力提升了防控實效。這在《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五十五條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最后,關于醫療組織對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觸者或疑似者進行強制隔離的行為,也在《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條有明文依據④。
當然,也應意識到,立法工作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即便在主觀上期待公共應急法律規范趨于完美,但事實上很難窮盡突發事件中的應對策略,很難對其做出全面且符合實際的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只要是為保障社會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根本權益,那么在面臨重大突發事件等緊急情況下實施行政應急舉措便具有正當性,其中既包括有明確法律規定的行為,也可以包括一些沒有直接法律依據的行為,但事后應當依法予以審查或追認[13]。正如有學者所言,“在某些特殊的緊急情況下,出于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者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采取沒有法律依據,甚至與法律條文字面含義相抵觸的措施,而這些措施的合法性應當予以追認……是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例外。”[14]
(三) 集體觀視角——公益與私利的“楚河漢界”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加強集體主義教育。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國家,集體主義精神在中國傳統觀念中一直都廣受贊譽⑤。中國傳統社會強調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家族利益為表征的公共利益,個人利益被壓縮在極小的空間范圍內且處于絕對的服從地位。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當做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這體現了儒家倫理精神的家國觀念。這種“重義輕利”“大公無私”的價值取向,無疑體現了道德的歷史自覺,在凝聚社會向心力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幾千年來一直對我國社會的發展產生著重要影響[15]。中華民族歷經苦難但也多難興邦,龐大的人口數量和有限的可耕地面積導致習慣性資源匱乏。歷史的經驗證明,要克服天災人禍,必須永葆集體主義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集體主義的精神得到進一步弘揚,集體主義的力量得到進一步彰顯。早在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中就明確規定了保護公共利益原則⑥。此后,在1982年《憲法》中又再次對這一原則予以規定。此后在各部門法中也對集體主義原則加以具體的規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五條有關征收征用補償的規定,就吸收了集體主義精神,體現了公共利益優先的原則⑦。此外,在經濟法、知識產權法等法律部門均對集體主義精神有所貫徹和體現⑧。
實際上,堅持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統一也是馬克思主義利益觀的一大特色[16]。雖然馬克思主義肯定和尊重個人利益,并積極倡導人們為維護個人合法權益而斗爭。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也反對個人利益的絕對化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反對為了實現個人利益而不尊重集體利益和公共利益。著眼于人民利益是馬克思主義利益觀鮮明的階級立場。只有依靠集體才能真正彌合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割裂,最終實現個人利益,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利益觀的先進性所在[17]。
當人類聚群而居,個人與集體利益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在兩者發生沖突時,為了實現集體利益,帶有集體主義傾向的個體總是樂于讓渡個人利益。中國社會制度和國家治理,從微觀的普通老百姓到宏觀的國家機器、政治體系都具備著厚重的集體主義色彩,這是區別于西方制度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國“制度優勢”的根源。這種植根于中華民族的集體主義意識來源于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由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而得到升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下的優勢得到凸顯,是這次戰勝疫情的有力武器[18]。正如世衛專家艾爾沃德所言,“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精神,愿意為抗擊疫情作出貢獻”,“中國展現了驚人的集體行動力與合作精神”[19]。
三、 進路優化:應急行政執法的革新與完善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加大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的執法力度[20]。即便是在緊急情況下,這一法治標準仍不能有絲毫降低。誠如有學者所言:“緊急狀態對公民基本權利進行限制是一種手段與方法,限制本身不能成為一種目的[21]。
(一) 嚴格執法——遵循比例原則,克守限權底線
比例原則是公法的“皇冠原則”,同時也是行政應急執法所必須遵循的核心原則之一。該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政執法活動時,應對社會公共利益與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利進行必要的權衡,盡量以對行政相對人侵害最小的方式實現執法目的。從學理上講,比例原則可以分為“隱含規范”和“明示規范”[22]。作為法哲學概念的“隱含規范”主要表現為比例原則的精神要義,實際上我國自古便有之⑨,且在現行立法之中多有體現,而作為法釋義學概念的“明示規范”是對比例原則進行具體化的規范,我國在立法層面實際上已明確緊急狀態下行政執法主體適用比例原則的行為規范⑩,但實務中所受重視程度遠遠不足。應當認識到,法治國家目標的達成應當是全方位系統性的法治,除了常態下應遵循法治思維與方式外,在緊急狀態下,也應依據法律,參照法理,用法治精神給養去治愈社會創傷。比例原則要求實施行政行為時應進行適當性審查、必要性審查和均衡性審查,除此之外,緊急狀態下的比例原則也存在其不同之處。一方面,從職權主義角度而言,如若行政機關執法權受到過度限制,將會導致突發事件加劇,有礙行政目的和公共利益的實現。另一方面,從權利觀視角而言,在應對突發事件時,運用比例原則須特別注意堅守底線思維,明確權利克減的最低限度。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應采取多樣化的形式(如制定基本權利清單)區分應急執法在不同情況下的最低限度,明確權利克減的底線與原則,并對相應侵權責任予以規范化管理,促使行政執法主體盡可能以對公民最少侵害的方式實現“嚴格執法”。
(二) 文明執法——突出行政指導,彰顯執法“溫度”
行政指導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據其職權,或者依據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定,在其所管理事務的范圍內,以指導、勸告、提醒、建議等非強制性方式,引導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種行為的活動[23]。實際上,行政指導本身就是一種文明制度,在一個真正的法治國里,行政指導應該成為行政機關廣泛使用并嚴格區別于其他強制性行政行為的一種制度。目前,我國立法中已對突發事件中行政機關發布行政指導的行為予以規定,理論上針對行政指導與強制性的行政行為劃分了明確界限,但由于缺乏較為具體明確的發布與實施程序,突發事件中的行政指導仍存在諸多模糊地帶。如實踐中所論及的諸多不規范行政執法行為,都或多或少地帶有混淆行政指導和抽象行政行為的傾向。實踐中適用混亂的問題,主要存在以下兩種情況:第一,發布行政命令的機關將行政指導與規范性文件混淆在一起,不加以區分。其結果是,執行機關均將其當作“上級命令”加以執行,顯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第二,發布規范的行政機關僅發布一些指導性建議,而執法機關卻采用強制方式加以實施,此種情況與行政執法主體的責任相關性較大[24]。很顯然,在應對突發事件過程中,較為常見的是后者。例如,新冠疫情期間,政府號召公民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實際上是典型的行政指導行為。普通公民在戶外空曠場地活動未佩戴口罩,屬于違反行政指導的行為,并不具有可罰性,因而也就更不應當采取強制性措施。在現代文明法治國家中,更多地使用行政指導措施,是文明執法的體現,這不僅可最大限度減少公權力侵犯私人領域的頻率,弱化政府與公民間的直接沖突,還能夠使公權力機關更好地充當“人民保姆”角色,充分彰顯服務人民的社會主義法治政府形象。
(三) 公正執法——落實行政補償,彌補限權減損
突發事件中,行政執法主體有必要采取比常態下更為嚴格的措施,以確保秩序穩定。這意味著,應對突發事件中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現象會更為突出。即便行政主體基于合法、正當的執法目的,其對于公民個人權利造成的侵害,在事后也要進行合理補償。美國首席大法官Marshall在1803年Marbury v.Madison案的判決中指出:公民權利之精髓就在于受到侵害時能夠得到來自政府的救濟與保護。特別是在緊急狀態下,政府事后給予個體權利受侵害的公民以補償,既是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是文明政府的體現,更是公正執法的彰顯。
關于行政補償,學界對其有多種定義。總體而言,將政府因公共利益對公民合法權益造成侵害之行為劃分到行政補償范圍內,基本未有爭議。從權力保障角度而言,在公民因緊急情況遭遇權利克減的情況下,行政執法主體更應在該特殊狀態結束后,給予其心理和物質上的合理補償。從約束政府角度而言,在該特殊情況下,執法機關權力空前膨脹,為了防止其權力濫用,對其造成的侵權后果予以規制,既能限制其權力肆意膨脹,又可以彌補權利減損之后果[25]。除理論上的融洽性外,我國法律對此也有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關于公民權利受侵害予以補償的規定,使得行政補償有了基本法依據。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十二條關于應對突發事件中行政補償的規定,則是為特殊狀態下的行政補償提供了法律依據。總之,在應對突發事件的執法過程中,對公民個人權利之減損實施合理行政補償,是公正執法的積極彰顯。
(四) 規范執法——堅守程序正義,固牢法治根基
應對突發事件,過度強調行政權力并不能挽救社會民眾于危難,也不能緩解國家民族之危機。相反,不規范地行政執法,無形中會將民眾推入“火坑”,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國家治理負擔,進而影響社會繁榮穩定。現代社會,行政程序是控制執法人員濫用職權,構建行政權力運行機制穩固的基礎。某種意義上講,行政程序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核心與基礎,現代行政法就是關于程序的法律制度。只有不斷完善程序控制,應急行政執法才能日臻規范。國內學者大多主張應急行政執法程序可對比常態簡化一部分程序事項,但不得完全缺位。筆者認為,行政執法主體應對突發事件時必須遵循法定簡化程序,以防止權力肆意和妄斷。在應對突發事件過程中,應當尤其關注時限的相關規定,即在突發事件的因素消除后,行政執法機關應當盡快解除因特殊情形給予公民的限制,不得為了其他不正當目的而過度侵權。因緊急情況未依法履行相關執法手續的,應當在事后合理期限內補辦和追認。正如馬懷德教授所言,“行政執法機關應當盡快解除因危機而建立的憲政獨裁,于危機消失后,不應再延續。危機是憲政獨裁存在的要件,危機消失,憲政獨裁即應終結,如不終止,便是違憲而走向邪惡之途。那時國家緊急權不再是防衛民主憲政的武器,而將成為禍國殃民的工具”[26]。
四、 特色彰顯: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模式的描摹與展望
經過長期的法治實踐,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應急行政執法模式。該模式源于革命年代,經過新中國多年實踐的修正,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日臻完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在應急行政執法方面的重大建樹。相較于西方的應急行政執法模式,具有無可比擬的制度優越性。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模式的優越性在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始終體現在行政執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其一,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模式是對中華法治文明傳統和豐富法文化資源進行梳理和甄別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和揚棄,與中國優秀文化一脈相承,與現代法治文明融會貫通,兼具厚重感與現代化。其二,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模式是一個包容并蓄的體系,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不斷汲取新理論、新實踐,在保證原則要義不變的情況下,不斷滿足新的時代發展要求。其三,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模式能夠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同時控制突發事件升級、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實現個人權利與社會秩序相統一。其四,中國式應急行政執法模式經過非典疫情、新冠疫情等應急執法實踐的不斷修正與驗證,與中國大地的風土人情相適應,具有雄健的實踐偉力。
疫情防控成效,關乎全球民眾生命健康。當前,我國抗擊疫情之戰已基本取得勝利,但世界范圍內的疫情還遠未結束,“后疫情時代”的防控形勢也不容懈怠。恩格斯曾講道,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回顧我國應急行政執法的“是”與“非”,分析權利克減的“得”與“失”,把握限權理論正當性法理探討,探尋突發事件應急執法合理化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未來,應積極發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將“黨的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與“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有機結合,奮力實現應急行政執法模式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的革新與完善。
注釋:
①回顧疫情中出現的真實案例:湖北某地疫情防控人員,身著軍人作訓服,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直接進入公民家中進行巡查。關于該執法人員是否是軍人,案例中并未得到考證。暫且假設他是一位軍人,其執法主體地位也值得追問。首先,軍人何來的執法權?根據緊急狀態的相關法律法規,并沒有賦予任何軍人執法主體的規范內容。其次,入戶搜查這一行為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權利——住宅安寧權,這一重要權利,只有特定國家機關(公安或司法機關)在依法符合法定事由時才可加以剝奪和限制,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不得隨意加以限制。即便在特殊時期,考慮到公共利益和社會穩定,出于當時的緊急情況——全國正處于抗擊疫情的攻堅時期,湖北也是重災區,嚴加管控和適當限權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家人之間在均為感染病情的情況下,且在自己家內部的娛樂活動難道還要受到外部的管控嗎?試想如若加以管控,如何落地實施?這顯然不符合法治思維與邏輯。
②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湖北一刑滿釋放且帶有低燒的人員才在封城九日且各通道均有民警把手的武漢“突出重圍”返回北京,事后,中央紀委調查此事。參見“北京全面調查武漢刑滿釋放確診患者進京一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2002/t20200227_212378.html。
③See Clinton Rossiter,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8:p.288.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九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單位和個人參與傳染病防治工作。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完善有關制度,方便單位和個人參與防治傳染病的宣傳教育、疫情報告、志愿服務和捐贈活動。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組織居民、村民參與社區、農村的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建立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增強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風險的意識,提高全社會的避險救助能力。第五十五條規定:突發事件發生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和其他組織應當按照當地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進行宣傳動員,組織群眾開展自救和互救,協助維護社會秩序。
⑤參見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⑥1954年《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對城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實行征購、征用或者收歸國有。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
⑧如在市場規制法中的《價格法》,它規定了價格聽證制度,即由消費者、決策者和其他相關人士共同協商決定某項事物的價格。這種規范政府定價行為的聽證制度充分體現了經濟法的社會整體利益觀,而由社會各個利益主體的代表參與討論協商,最終得出的決策結果是有利于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實現的。
⑨如“殺雞焉用宰牛刀”(《論語·陽貨》);“于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墨子·大取》);以及“削足適履”、“過猶不及”等表述均體現了比例原則的思想。
⑩《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十一條規定: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采取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措施,應當與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的性質、程度和范圍相適應;有多種措施可供選擇的,應當選擇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益的措施。
關于權利克減的最低限度,197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9年《美洲人權公約》以及葡萄牙、蒙古等國的憲法對突發事件中最低標準的權利保障均有相關規制。一般而言,最低的人權標準一般應當包括生命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司法保護權和國家賠償權等。參見Cecil T.Crisis Legislation in Great Britain.Columbia Law Review,2020(04):24.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四十五條第一款第五項就規定:“及時向社會發布有關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減輕危害的建議、勸告”。
在法國,行政補償包括公用征收補償和公用征調補償兩種。德國則細分為征收補償、準征收補償、特別負擔補償和征收性侵害補償等。日本的行政補償稱為損失補償,是指對因合法的公權力的行使而蒙受的財產上的特別犧牲,從全體公平負擔的角度予以調節的財產性補償。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便是保護他們的財產。在維護公共安全時,投入的成本除了公共財政的支出外,不可避免地會涉及私益的非對稱性支出。從私人的角度看,這種成本的投入原本并非計算之內,因此該投入形成其利益的損失,表現為私益增值機會的失卻、私益的直接減損和私益成本的增加。”我國學者李建良認為行政補償為行政法上之損失補償,為一種制度;林勝鷂認為,行政補償是補償義務;張載宇將行政補償看為公法上的金錢給付之義務。
我國《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十二條規定: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為應對突發事件,可以征用單位和個人的財產。被征用的財產在使用完畢或者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結束后,應當及時返還。財產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毀損、滅失的,應當給予補償。
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3條第3款規定:行政廳在作出不利處分的場合,除因緊急而無暇出示理由外,對不利處分的接受者,須出示構成該不利處分根據的理由。但是,當因緊急未出示理由時,應在處分后一定期限內出示理由。
如《行政強制法》第19條規定:“情況緊急,需要當場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執法人員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并補辦批準手續。行政機關負責人認為不應當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應當立即解除。”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強調全面提高依法防控 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報,2020-02-06(01).
[2]江必新.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疫情防控工作[J].求是,2020(5):28-34.
[3]汪習根.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權價值[J].東方法學,2021(1):37-46.
[4]習近平.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0-02-24(01).
[5]清華大學課題組.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長治久安[J].學習月刊,2010(23):28-29.
[6]賀治方.社會動員在國家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合理邊界[J].學術界,2019(07):83-91.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36.
[8]申來津,白森文.以人民為中心的行政執法:核心理念、影響因素與實踐模式[J].學術交流,2020(12):14-21.
[9]應松年.突發事件公共應急處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5.
[10]高軒.行政應急權對當事人行政訴權的威脅及司法規制[J].法學評論,2016,34(02):55-56.
[1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23.
[12][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M].馬清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5.
[13][英]邊沁.政府片論[M].沈叔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56.
[14]何海波.實質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213.
[15]論語[M].張燕嬰,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21.
[16]楊相琴.馬克思主義的利益觀探究[J].理論月刊,2010(03):14-17.
[1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4.
[18]孟子[M].萬麗華,藍旭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6-12.
[19]張朋輝.中國展現了驚人的集體行動力與合作精神[N].人民日報,2020-02-27(003).
[20]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1]張方華.公共利益觀念:一個思想史的考察[J].社會科學,2012(05):4-12.
[22]蔣紅珍.比例原則適用的規范基礎及其路徑:行政法視角的觀察[J].法學評論,2021,39(01):52-66.
[23]胡建淼.行政法學: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489.
[24]梁上上.公共利益與利益衡量[J].政法論壇,2016(06):3-17.
[25]Oren Gross.Chaos and Rules Should Responses to Violent Crisis Always Be Constitutional? [J].The Yale Law Journal,2003,112:1011-1042.
[26]馬懷德.應急反應的法學思考[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42-45.
(責任編輯文格)
The Valu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Rights Dero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ency Rule of Law:
Also 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hinese-style Emergenc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Model
FANG Lu-jin
(Law School,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In responding to many emergencies,China has gradually explored an emergenc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model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It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bsorbing the fruits of modern civilization.It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cretization and actualiz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the rule of law,showing great theoretical value,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power.The legitimate derogation of civil rights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s a 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and a good rule of a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We should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flexible law enforcement”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correctly grasp the “reasonable restric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seek to strictly regulat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fair and civilized emergenc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order,looking forward to showing the huge advantages of Chinese-style administrative emergency law enforcement model.
Key words:emergency rule of law; public order; civil rights;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human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