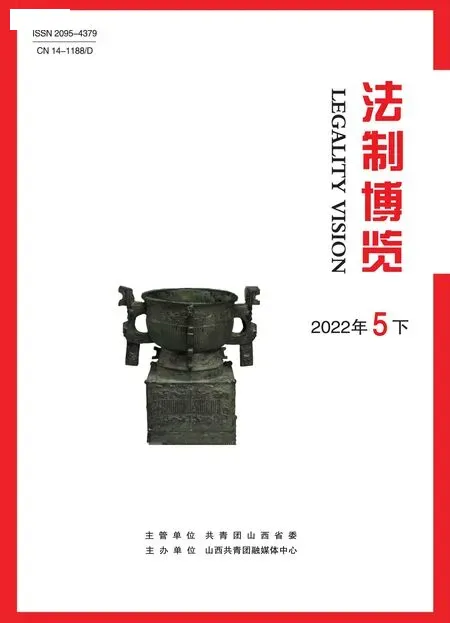市場事前監管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的難點及完善
張遼圣
甘肅財貿職業學院,甘肅 蘭州 730207
市場監管系列改革在深化市場體制改革的背景下推進。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重申了市場的重要作用,強調應該繼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1],而國務院于2017年印發的《“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中提出,市場監管改革應該是全面的、綜合的、系統化的改革,而從法學領域研究來看,目前學界對事前監管轉向事中事后監管改革的重視程度較低,對其核心問題缺乏合理回應和闡釋,就如何轉變,所涉及哪些具體監管事項需要適應此改革以及應采取哪些具體措施來保證改革后的監管效果等問題缺乏有效的經濟法解釋[2]。本文將結合以上背景,就市場事前監管向事中事后監管轉變從經濟法角度進行研究。
一、事前監管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的難點分析
(一)學界理論落后于改革要求
從目前政府正在推進的改革政策來看,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仍集中在簡政放權、寬進嚴管等問題,部分觀點甚至將監管立法改革和監管向事中事后轉變畫等號,缺乏應有的理論洞見和理論基礎。其原因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由于市場實踐領域的制度性成本高是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改革需要持續地深入推進;另一方面,部分推行的改革措施仍具有事前監管的性質。
(二)現有的分析理論存在偏差
需要區分市場監管改革和事前監管轉向事中事后監管的區別。若僅根據“成本vs收益”理論進行推導分析,難免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況。因此,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時,需要對所涉及的企業進行經營許可事項清單管理,充分調動市場的效應,并在過程中進一步分析和歸納事前轉向事中事后監管的統一標準,將具體的討論集中在“市場監管vs資源有效配置”的命題上去理解[3]。
(三)市場監管三個環節的資源分配存在分歧
市場監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為支撐,在現有的市場條件下,監管資源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在制度設計時充分考慮到這一事實,并將監管資源與監管環節進行最優的資源分配,以期達到資源利用的最大化[4]。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在事前、事中、事后三個環節中進行平衡和調配,如何在資源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既做到可以實現事前監管轉向事中事后監管的改革目標,又可將監管資源做到最優配置,這是立法機關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
二、市場監管環節的法律構造
在明晰以上市場監管改革難點后,從經濟法角度進一步分析三個環節間的法律關系,為改革的規范性標準提供理論基礎。
(一)事前監管的法律構造
事前監管一般具有雙重內涵。首先,事前監管是指市場監管部門是否予以市場主體準入資格,一般學界將其簡稱為“主體資格的事前監管”;其次,事前監管也泛指監管部門審查并決定申請人的某些市場行為能否準許其實施,一般被稱為“特定行為的事前監管”。
(二)事中監管的法律構造
事中監管通常是指市場監管部門對市場參與者及經營者在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實行的監督與管理工作,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包括場所設施檢查、經營信息核查、市場價格合理性檢查、傳播內容的審查、資產評估及經營信息備案等,通常采用抽查的方式進行[5]。
(三)事后監管的法律構造
根據前文針對事前、事中監管法律構造的分析,本文認為事后監管是對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及行為的結果進行監管[6]。從法律責任的角度需要注意的是,市場主體在事前監管、事中監管環節的違反義務行為,是不應該納入事后監管的范圍的。因而,本文認為事后監管首先是針對產品質量的檢驗及驗收,其次是對經營信息規制的審查,而后是強制市場退出以及市場參與者存在的或者實施的違法行為。
三、事前監管轉向事中事后監管的規范性標準探討
(一)基于社會成本探討改革標準
由于立法者及監管者大多數為風險的厭惡者及市場秩序責任的最終承擔者,以此在監管機制的設計上,往往更傾向于事前監管,與其將市場中的“害群之馬”放入市場中,后期再識別及落實監管責任,不如通過事前設計的識別就阻止其入市。回顧以往研究,強制性實體標準、程序化的審查設計在傳統的立法實踐中被廣泛使用,立法機關認為事前的監管設計有利于其甄別不符合市場經營標準的市場主體,并通過設置較高的入市門檻將其阻擋于市場之外。
但是,從經濟成本的角度重新審視事前監管,發現往往需要耗費更高的成本。這是由于事前監管需要對每個預參與的市場主體進行審查,其成本可量化為:“事前監管成本=(潛在參與市場主體的平均監管成本)×(所有被監管市場的個體數量)”;“事前監管的守法成本=(預參與市場的主體為滿足事前監管要求而支付的成本)×(所有被監管市場主體的人數)”。
若假設預參與市場的主體符合市場準入要求的數量超過50%,則事前監管會造成必然50%的效率損失,并相應為潛在的市場參與者帶來更高的守法成本,和我國政府推行的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相悖。
從經濟成本的角度比較事中事后監管的成本可以發現,由于事中事后監管需要監管機構針對經營過程、經營行為及經營結果進行抽樣調查,因而在實施監管時將花在符合市場要求的誠信市場主體耗費的成本降到最低,僅需要對違法者定向追責,從而支付遠小于事前監管的監管成本;由于沒有過多的事前審批,簡化潛在市場參與市場的門檻及難度,其守法成本也大大減少,從結果上看,有利于市場監管及市場參與的良性循環。
基于以上分析,可初步推斷出由事前監管向事中事后監管的規范性標準如下:
1.前提一:政府的市場監管資源是有限的;前提二:無論處于哪一個監管環節,需要市場監管實現的監管效果是降低市場違法、違規行為;
2.若為達到同樣市場監管效果,事前監管的總成本>事中事后監管的總成本+(定向監管造成損害的成本)
3.以此可得出結論:將市場領域的事前監管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是優化資源合理配置的舉措,可在一定程度上節省實施監管的制度性成本和市場參與者所需支付的守法成本。
(二)規范標準有效性檢驗實例分析
早期《公司法》對最低注冊資本、法定驗資有明確的制度要求,在后期的實踐中證明這些事前監管措施從經濟角度是失敗的,既耗費了巨大的監管成本,同時,未能有效地達到預期的監管成本,無法有效甄別市場主體是否有資金能力及債務償還能力,所設置資本實繳及驗資等制度實際上未能抑制虛假出資及資金抽逃等問題,但仍耗費巨大的監管成本。而近年來,除特殊主體外,已逐步將以上制度廢除,建立事中事后監管,在監管者發現違法行為后再進行處理,不僅降低了監管成本,而且有效提高監管效率。
四、進一步完善和優化事中事后監管機制
事前監管向事中事后監管轉變是大勢所趨,因而需要深入探討如何提高事中事后監管機制的效率。本文認為事中事后監管必須具有如下的功能:首先,要能及時發現違法行為從而減少潛在的損害性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監管中出現的“信息不對稱”;其次,在監管過程中對發現的違法行為要能迅速作出反應,從而防止損失擴大,配合及時追責措施最大限度對沖損害后果,降低救濟成本。
(一)建立健全市場參與者激勵型監管機制
激勵型監管機制指的是相關部門在設計監管機制時,除了懲罰措施外,還應結合如權益優先獎勵、經濟或榮譽獎勵、義務責任減免等激勵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市場參與主體主動守法。市場參與者是否遵守市場的監管要求及相關法律并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經濟問題,是由違法成本決定的。在事中事后監管時務必要做到違法違規必然懲處,提高市場參與者的違法違規成本,但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監管執法及懲罰的過程需要耗費高昂的成本,效果可能仍不盡人意。因此,建議立法者可將部分用于懲處的執法成本用作守法激勵機制建設,鼓勵市場參與主體主動、自覺遵守法律規范。如各地可建立“誠信經營名單”機制,對市場內誠信經營達到一定標準的市場參與主體納入該名單中去,并輔以一定的政策減免作為獎勵或賦予其優先權益等鼓勵和引導企業進行誠信經營,通過激勵機制的設立鼓勵企業積累其聲譽和美譽度。
(二)建立健全市場參與者舉報獎勵機制
信息是一種社會資源,需要花費一定的成本進行獲取。由于違法行為具有隱蔽性,這就意味著違法行為的信息收集和核實需要耗費大量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監管過程的良性運行。實現事中事后監管的目標絕不能單純寄望于在監管中增加監督的抽查次數或僅僅擴大抽查的覆蓋面,這是因為市場改革目標就是進一步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和市場參與主體及潛在參與主體的守法成本。而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發動群眾的力量,鼓勵群眾對市場參與主體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舉報,并予以一定的經濟獎勵及獎勵措施,往往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目前在各地的具體實踐領域,舉報獎勵機制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具體的配套舉措,在實施過程中落實不到位的問題屢見不鮮,因而需要立法者進一步進行機制的構建,需要進一步貫徹落實《關于加強和規范事中事后監管的指導意見》第十六條規定。
(三)引入第三方機構參與市場共治
激勵行業組織以及專業機構等第三方機構參與到市場監管中來,有利于推進政府市場監管職能轉變,落實監管方式的轉變,并充分調動和使用社會監管資源。具體到市場監管環節,可將行業及商業協會、律師協會及律師事務所、會計審計事務所等具有檢驗認證資質的機構納入市場監管過程,在第三方的有效監督下,營造多方參與的、公正、透明的市場監管環節。并逐步構建社會共同治理格局,鼓勵市場主體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政府監管等力量參與。而在落實各類市場服務機構監督上在以下方面加強:1.在市場行為負外部性較強且維權成本高的領域,需要增強專業服務機構在監管中的決策影響力;2.追究相關從業人員違法的責任,充分發揮第三方監督責任;3.相關政府機構需要提升購買服務能力,用市場的思維降低購買專業服務的成本,提升監管的有效性;4.引入多元的監督機制,排除行政壟斷。
五、結論
近年來,進一步增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營商環境,降低制度性成本,增強市場活力,在監管方面我國政府及立法機關正推進市場事前監管向事中事后監管轉變改革。本文認為事前監管向事中事后轉變監管的難點在于,學界理論構建落后于改革要求,且現有的分析理論存在偏差,以及市場監管三個環節的資源分配存在分歧。在明晰以上市場監管改革難點后,從經濟法角度進一步分析三個環節間的法律關系,為改革的規范性標準提供理論基礎,將市場領域的事前監管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是優化資源合理配置的舉措,可在一定程度上節省實施監管的制度性成本和市場參與者所需支付的守法成本。同時,針對事中事后監管機制的現狀,提出了三條舉措建議,即建立健全市場參與者守法激勵機制,建立健全市場參與者舉報獎勵機制,引入第三方機構參與市場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