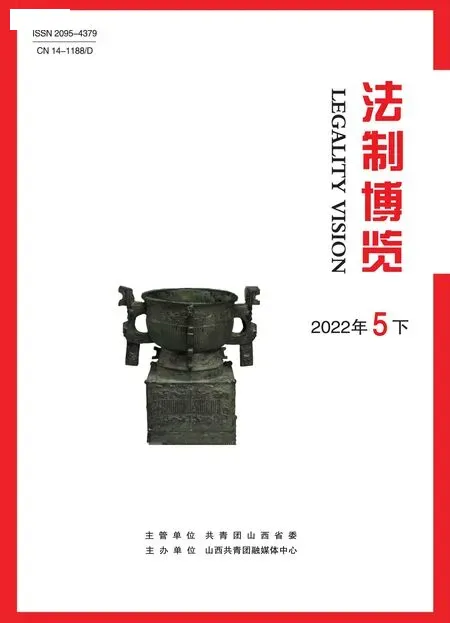認繳制下實務操作中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依據認繳或實繳比例確定表決權之探討
張道東 于 杰
1.上海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335;2.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上海 200032
股東表決權是股東對股東會之決議事項為可決或否決之意思表示,借以形成公司意思之權利[1]。有人說:“如果說有限責任構成了《公司法》最顯著的特征,那么在彰顯《公司法》的特征方面,投票機制則無疑穩居第二。”[2]由此可見,股東表決權是股東能夠直接參與公司治理的根本性權利,該權利能否有效行使不僅直接影響公司的未來經營,也影響著股東其他權利的行使及股東投資目的的實現,所以一直以來其受到格外重視。
股東表決權是股東基于其出資義務而享有的。然而,我國《公司法》關于公司注冊資本的規定經歷了從實繳制到認繳制的立法演進,與1993年《公司法》第四十一條相比,目前施行的修訂后的《公司法》將1993年《公司法》第四十一條變更為第四十二條,并增加了但書部分。該但書部分雖然明確公司章程可以對表決權行使原則進行約定,但是由于未明確規定“出資比例”是“認繳出資比例”還是“實繳出資比例”,因此給實務操作留下一個難題,即:未來公司設立時,股東依據認繳出資比例抑或實繳出資比例享有表決權?本文在認繳制下,在同股同權的假設前提下,從實務操作角度出發,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依據認繳或實繳比例確定表決權進行探討。
一、關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表決權規定的主要法律及政策沿革
關于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表決是以認繳出資比例還是實繳出資比例為依據,一直以來爭議較大。而且由于社會背景的變化,雖然《公司法》經歷了幾次修訂,但仍未有明確結論。
我國《公司法》首次頒布為1993年,從該法第二十三條、二十五條、四十一條可以看出: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額,即一次性繳納,且實繳后還應經過驗資程序方能申請注冊公司,所以此時股東表決權應以實繳出資比例來確定。
在1999年、2004年,我國《公司法》進行過兩次小修訂,但未涉及公司資本制度和股東表決權部分。2005年,國家對《公司法》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修訂,本次修訂幾處應引起注意:第一,從該法第二十六條、二十九條可以看出,雖然仍要求股東的首次出資應經依法設立的驗資機構驗資后方能申請注冊公司,但是也同時規定了股東可以分期繳納注冊資本;第二,立法中出現了“認繳”“實繳”之描述,且“實繳出資比例”直接關乎股東的分紅權、優先認購權;第三,將原四十一條變為四十三條: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增加“但書”,即股東表決權可以依據公司章程規定。即便如此,在公司章程未明確約定以“認繳出資比例”還是“實繳出資比例”作為行使表決權的依據時,股東表決權該如何確定,本條文并沒有明確規定。
在“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創業活力,催生發展新動力”的背景下,2013年《公司法》迎來再次修訂。與此同時,2014年2月7日,國務院印發《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改革公司注冊資本及其他登記事項,實行注冊資本認繳登記制。結合該文件來看,本次修訂后的《公司法》主要關注點為:第一,從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可以看出,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實行認繳制,驗資不再是公司設立的前提;第二,第三十四條沿襲原第三十五條的規定,未做改變;第三,將原第四十三條直接變更為第四十二條,內容未做任何實質性修訂。
直到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紀要》中提到:股東認繳的出資未屆履行期限,對未繳納部分的出資是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表決權等問題,應當根據公司章程來確定。公司章程沒有規定的,應當按照認繳出資比例來確定。其態度較為明確:如果公司章程不約定,那么按照認繳出資比例確定。而當股東(大)會作出不按認繳出資比例確定的,股東請求確認決議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該決議是否符合修改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決程序。然而,依據《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需經代表三分之二表決權的股東會表決的情形并不包括《九民紀要》提到的上述情形。
二、認繳制下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對表決權依據選擇的困惑
認繳制下,股東很少會在設立公司時將注冊資金出資到位,此情形下,股東選擇以認繳出資比例還是實繳出資比例行使股東表決權,就成為了一個難題。股東的難以抉擇,主要受困于下面四個方面:
(一)困于法律條款的不明確
首先,縱觀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表決權的立法歷史沿革,筆者認為,無論是《公司法》還是《九民紀要》,對股東表決權的依據問題都沒有很好地予以解決。《九民紀要》第六條針對的是實務中出現的因股東出資未屆履行期限情況下表決權是否受限的問題,對股東選擇以認繳出資比例還是實繳出資比例確定表決權雖然有一定指引作用,但本紀要的效力有限,其非司法解釋更非法律、行政法規,因而不能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
其次,當股東(大)會作出不按認繳出資比例確定的,股東請求確認決議無效的,其提出:人民法院應當審查該決議是否符合修改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決程序。該處理辦法顯然與《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相違背。從立法層級看,《公司法》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而《九民紀要》為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民事行政專業委員會通過的會議紀要,其效力顯然不能與《公司法》相提并論。
最后,《九民紀要》提出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該決議是否符合修改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決程序”,其究竟如何審理,審判思路如何,都未明確,更無可參考案例,這也給法律的適用、判例的參考帶來諸多困擾。
(二)困于司法審判的不一致
在注冊資本認繳制的背景下,實繳出資是否影響股東表決權,在不同的審判機構可能會出現不同的審判文件。筆者找到如下兩則案例:在鄭某新與新疆某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決議糾紛案中①鄭立新與新疆雙興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決議糾紛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中級人民法院(2018)新01民終591號。,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院依照《公司法》的規定確認股東未實繳出資不影響股東行使表決權,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予以支持。而在上訴人某甲有色投資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某乙有色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決議糾紛案中②上訴人休寧中靜華東有色投資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江蘇華東有色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決議糾紛案,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寧商終字第795號。,二審法院認為:股東在未全面履行章程規定的出資義務的情況下,其權利的行使也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按照實繳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是對股東的權利與義務的平衡,符合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基本原則。從審判文書的措辭中不難看出,二法院對股東行使表決權的依據持不同的態度。司法審判尚且如此,作為當事人的股東對選擇通過認繳抑或實繳取得表決權更是疑竇叢生。
(三)困于登記機關的約束
在申請設立有限公司時,根據《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股東通常將依據投資協議之約定先行擬定好公司章程送交登記機關。然而實務操作中,個別登記機關要求必須使用登記機關提供的公司章程示范文本,該公司章程示范文本基本照搬《公司法》上相應條款,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表決權之描述為: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而依據認繳或實繳比例確定表決權卻沒有明確表述。
(四)困于對專業知識及實務層面的經驗缺乏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之所以細究表決權選擇認繳比例或實繳比例確定,究其原因為尋找方法以預防瑕疵出資股東給公司未來經營可能帶來損失和損害自己權益的情況的發生,是股東為化解未來風險的一種防御性需求。對于股東來說,表決權恰恰是預防和化解風險的最重要的抓手。然而囿于法律知識的專業性和法律條文的冗雜性,股東很難梳理出如何合理抓牢表決權,能重視公司章程已屬不易,更不用說細化到“以認繳比例還是實繳比例行使表決權”了。
筆者在盡調工作中發現絕大多數章程通常表述為:“股東表決權以出資比例行使”。公司章程的歷次修正中也不會涉及該條款。不知未來股東間發生爭議時,該章程是否可以有效保護其利益。
三、認繳制下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表決權依據困擾的解決路徑
當處于法律規定對股東表決權依據留白的外部環境下,又受制于自身對司法實務的鉆研深度不夠,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在選擇表決權依據時常常會感到如入暗室。為解決股東的上述困擾,筆者提出如下三個方面建議。
(一)建議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修訂《公司法》相關條款
《公司法》四十二條雖然沒有明確股東是按照實繳比例抑或認繳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其但書部分實質上為公司章程設置表決權的行使依據作了留白,即設立公司時,股東可以根據需要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制定公司章程。而對設立后的公司,《九民紀要》針對“章程有約定”“章程未約定”“股東不同意按照認繳比例執行”三種情形分別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只是受制于《九民紀要》的效力,其在理論層面和實務層面均存在一定障礙。
所以,筆者建議將《九民紀要》第六條納入《公司法》修訂工作中,從立法層面綜合考慮將表決權的行使依據及規則提升為《公司法》中的法條,增強其法律效力,實務中也可以直接引用,打通理論與實務的障礙。
(二)建議登記時與市場監管部門做好溝通
公司章程是由書面形式固定下來的,代表了股東或發起人的一致的意思表示。[3]其所體現的是一種意思自治,即除法律規定的事項之外,均可以由公司章程約定。市場監管部門主要職能為負責市場主體統一登記注冊,指導各類市場主體的登記注冊工作①參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主要職責:(二)負責市場主體統一登記注冊。指導各類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從事經營活動的單位、個體工商戶以及外國(地區)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等市場主體的登記注冊工作。。在企業登記注冊環節,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一方面的功能是“負責登記注冊”,另一方面是“指導登記注冊”。筆者認為該指導應為形式審查,其邊界為:審查公司章程中是否缺少《公司法》規定的必備事項。而對于《公司法》規定可以“由公司章程約定的”,諸如表決權依據認繳比例抑或是實繳比例享有等,則應尊重各股東之間的約定。這不僅需要市場監管部門轉變職能積極打造服務型政府,更需要公司在資料提交過程中多與監管部門積極溝通,依法據理闡述訴求。
(三)建議在投資協議及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確
“《公司法》的結構規則和信義原則一起,也僅僅能夠一般性地調整公司參與方之間的關系”[4],所以體現股東之間意思自治的公司章程就至關重要。股東擬合資設立公司時,應在投資協議中以書面形式明確以“認繳出資比例”或“實繳出資比例”作為表決權行使的依據,約定股東實繳出資時間,并以書面形式明確股東出資瑕疵時的后果。同時,投資協議的相關約定應同步、準確、如實地反映在公司章程中,即應保持公司章程與投資協議的約定一致,防止引發糾紛。
應當注意的是:當創始人也就是設立后的公司的股東出現出資逾期、出資不能等情形時,股東之間的表決權比例會出現階段性的變化。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按時出資到位的股東可能會積極推進股東會的召開和表決,而出資瑕疵的股東為了應對表決權比例減少的客觀事實會消極對待股東會的召開,甚至通過積極主動方式阻礙股東會的召開和表決。該情形下,極易誘發公司僵局,給公司的正常經營管理帶來重大風險。所以,一旦選擇以“股東實繳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就應當提前在公司章程中細化操作方式,通過設置對股東之間有約束力的剛性條款,及在合資協議中設置相應的規范條款對此予以預防。
四、結束語
筆者認為:股東無論選擇以認繳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還是選擇以實繳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應先知悉法律規定、司法實踐現狀,在此情形下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模式,進而有針對性地在投資協議和公司章程中作出相應風險防范措施。同時,筆者也建議司法機關短期內盡快通過司法解釋為司法判決提供相應的依據,通過指導案例提供一定的指引,更希冀法律制定者未來能在立法層面對《公司法》第四十二條進一步完善,為解決股東表決權的依據紛爭提供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