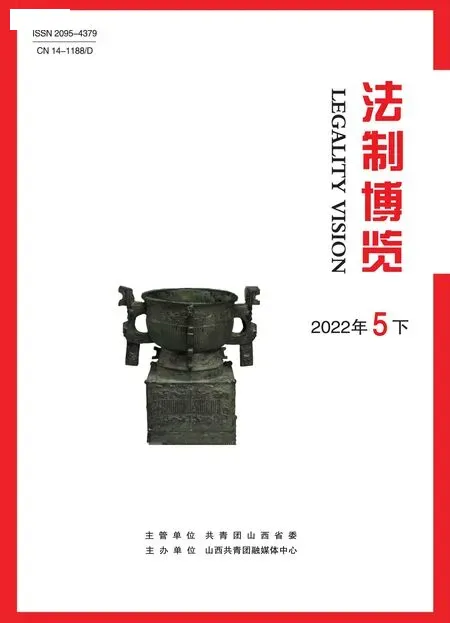我國法律援助的路徑選擇和探索
侯明遠
西藏大學,西藏 拉薩 850000
2022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以下簡稱《法律援助法》)正式實施,標志著我國正式進入法律援助專門法時代,表明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及規范程度逐漸走向成熟,是我國對人權保障的新高度。梳理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歷史沿革和發現其中的問題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展望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方向。再者,國家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題中之義就是要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可以認為,伴隨援助范圍不斷擴大的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史,就是我國依法治國和不斷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注腳。
一、我國法律援助探索階段
法律援助制度源起于15世紀的英國,起初是一種富人階層救濟窮人的自發的慈善行為,后來逐步上升為一種國家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救濟,如今世界各個國家都開始普遍適用。從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來看,雖然制度建設起步較晚,但是進步速度較快。我國的法律援助建設始于20世紀90年代,從1994年廣州市政府設立第一個法律援助中心開始,我國的法律援助正式進入由政府加以規范的階段,后續試點范圍逐步擴大。1996年年底,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開始對全國法律援助機構進行業務指導,其主要職責是制定全國性的法律援助規章制度,推動和指導地方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自此,我國法律援助工作經過幾年的地方試點開始進入中央司法行政部門的規范階段。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有力推動了國家和地方各級司法行政部門法律援助法治化的步伐。1999年年初,司法部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列入司法行政法制工作五年規劃。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聯合下發《關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問題的聯合通知》。這期間,廣東、青島、杭州、廈門、武漢、哈爾濱等6省市的地方立法機關已經通過并頒布地方性的專項法律援助法規。[1]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中首次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做出原則性規定,包括公訴案件中被告人經濟困難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當被告人為盲、聾、啞、未成年人、可能判處死刑人員并且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情況,人民法院需要提供法律援助。同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以下簡稱《律師法》)對法律援助的事項范圍、律師承擔法律援助的義務進行了明確。2001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次會議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立法律援助體系,表明國家制定專門的法律援助制度提上日程。
2003年7月,國務院第十五次常務會議通過了《法律援助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我國針對法律援助的全面落實在制度上的巨大跨越,奠定了國家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基本框架。《條例》規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圍、標準、實施程序和法律援助各方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了我國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責任、社會參與、律師義務構成的。這無疑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對推動我國法律援助事業的進步舉足輕重,意義重大。《條例》中明確,為確保經濟實力有限的公民也能獲得法律援助,應為符合條件的公民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同時也明確了法律援助是政府機構的義務,縣級以上政府機構需要關注并落實法律援助工作,給予法律援助財政支持,確保法律援助和地方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法律援助所需費用要實現專款專用,各級司法行政部門對本轄區法律援助服務予以監督。直轄市或市級、縣級政府行政部門根據需要設立本轄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范圍予以規定,同時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還可以圍繞法律援助事務進行一些規定上的補充。“可以根據需要”“給予財政支持”“各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監督管理本轄區法律援助工作”等,可以看到《條例》給予了縣級以上各級行政機關很大的自主性和彈性空間,沒有做強制性要求,客觀上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濃重的行政色彩。但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看,《條例》只是全國性的行政法規,法律效力相對薄弱,有天然的局限性。《條例》將法律援助確定為政府的義務,但實際上法律援助的主旨核心——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穩定、人權保障等價值,對于單靠行政部門承擔顯然太過沉重,法律援助并非僅僅是政府所提供的一種法律服務,同時也應是法治體系中的一個關鍵構成,將法律援助圈定為政府職責使得法律援助的地位降低,原本的作用也難以充分發揮。從本質上來看,獲取法律援助的權利是以人權當中的平等權為基礎,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憲法原則的自然延伸。各國對人權的保障都寫入憲法當中,我國在2004年明確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修正案》,而這種保障的具體實行應當體現在一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各個方面,這樣理解,那么對法律援助保障應該被定義為“國家責任”而不僅僅是“政府責任”。因為通常我們認為的“政府”僅代表國家的行政部門。《法律援助條例》作為國務院制定的全國性行政法規,僅對國家的行政管理部門具有規范作用,而不能約束司法部門,也自然削弱了司法部門對法律援助的重視程度和參與的積極性。雖然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對法律援助亦有規定,但是存在援助范圍小的問題,造成了對法律援助保障的不完善、不統一的分散局面。此外,也間接造成我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數量明顯高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情況。
二、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圍的不斷擴大
正如前文所說,對法律援助范圍的不斷擴大構成了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歷程。從國際方面來看,法律援助更傾向于對人權的保護,所以刑事法律援助自然優先于民事法律援助。這是因為刑事訴訟案件往往關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財產甚至生命的憲法性權利保障,是法律援助的最初形態,屬于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援助。
相比1996年版的《刑事訴訟法》,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做了重要補充。在第三十四條增加了“或者其他原因沒有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第五編特別程序中還規定對未成年人和強制醫療的法律援助。概括起來就是擴大了刑事法律援助對象的范圍,延伸了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不僅僅是人民法院的審判階段還包括了偵查階段和審查階段。獲得法律援助的方式由過去人民法院單純指派增加了被告人及近親屬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其中包括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健全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持續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強化民生方面法律服務水平。明確了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完善、援助范圍的延伸、救助體系的優化等,在民眾遇到法律問題需要得到援助時可以及時為其提供法律援助。
2015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中明確了我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則——堅持以人文本,促進公平正義,推進改革創新。具體措施包括對民事以及行政法律援助范圍進行拓寬,逐漸將勞動保障、食藥安全等與民眾日常生活有關的事項納入法律援助的補充項目之中。積極探索法律援助在申訴案件代理中的參與機制,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優化法律援助參與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試點工作,建立法律援助在刑事和解以及死刑復核案件中的參與機制。法律援助咨詢服務實現全覆蓋。
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聯合印發了《關于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明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先行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廣東、四川、陜西省(直轄市)八地進行試點工作,2019年范圍擴大到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基于現實原因,《辦法》將全覆蓋的范圍僅確定為刑事案件的審判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規定除《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和第二百六十七條的情況以外,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一審案件、二審案件、按照審判監督審理的案件、簡易程序、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在辯護律師介入之前,被告人及其親屬可以申請獲得值班律師的幫助。其中明確規定,一審法院履行職責不到位導致被告人在審判期間未獲得律師辯護、侵犯當事人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二審法院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辦法》更加詳盡明確了執業律師知情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申請出庭作證權,要求尊重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完善律師權利救濟渠道。創新經費保障機制,探索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擔部分援助費用。《辦法》對完善刑事訴訟中審判階段的控辯平等、維護程序正義、促進實質正義有重大意義。
201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其中引進了律師專屬辯護機制,將死刑復核案件的指定辯護納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圍,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的全面覆蓋試點工作進一步提高。
三、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逐漸走向成熟
2021年8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法律援助法》,是我國對人權保障的新高度,標志著我國法律援助建設逐漸走向成熟階段。《法律援助法》首次明確了我國法律援助的定義,即國家為經濟能力不足的公民或滿足法定條件的其他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包括法律咨詢、代理與刑事辯護等,明確法律援助是我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中的關鍵構成,進一步提升了法律援助的地位,并且將原來分散在《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及各相關部門規范性文中有關法律援助的規定進行有效統合,明確了法律援助的國家責任性和力度,即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上為法律援助提供保障的一攬子解決方案。
法律援助范圍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法》第二十五條,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范圍增加了“申請法律援助的死刑復核案件被告人”“缺席審判案件的被告人”,將《法律援助條例中》規定的“被告人是盲、聾、啞人”的范圍擴大為“視力、聽力、言語殘疾人”,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圍新增“確認勞動關系”“支付勞動報酬”“生態破壞損害賠償”,新增申請法律援助不受經濟困難條件限制的情形。
四、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探索
很明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具有“先地方,后中央,先法規,后法律”的特點。法律援助制度建設不應當僅僅理解為國家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的一種法律救濟,它還體現著一個國家對人權保障的重視程度,是國家法治體系中人本主義的人文關懷一面,反映國家法治體系的法律溫度。從1999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起草《法律援助法》起,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經歷了長時間的立法探索、實踐檢驗,《法律援助法》總體較為完備,進步巨大。包括法律援助服務渠道的延伸、法律援助過程監督監管、有關財政支持力度的提高等。律師作為法律援助的參與主體以及社會組織在法律援助中的供給,雖然讓法律援助變得更具多元化的特點,但本質上依然是受行政指派領取定額補貼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其實質是行政化供給的延續。有必要對法律援助市場化、行政化、社會化的供給方式進行重新定位和設計。[2]現實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多,例如法援經費緊張、律師資源嚴重不均衡,律師對參與法律援助的整體意愿不高進而影響法援服務質量等。應對的主要方向應聚焦在通過制度建設真正調動法律援助參與各方的積極性,法援參與熱情是參與各方真實意思的表達,而不僅僅是依靠法律規定。建立訴訟保險制度擴大經費來源,建立公設辯護人制度、明確政府購買法律服務的具體模式,拓寬優質律師來源,建立有效辯護制度、提高法律援助補貼標準、探索建立律師參與法律援助的積分獎勵機制和績效評估提高律師服務質量,加大普法宣傳增強公民權利意識都是很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