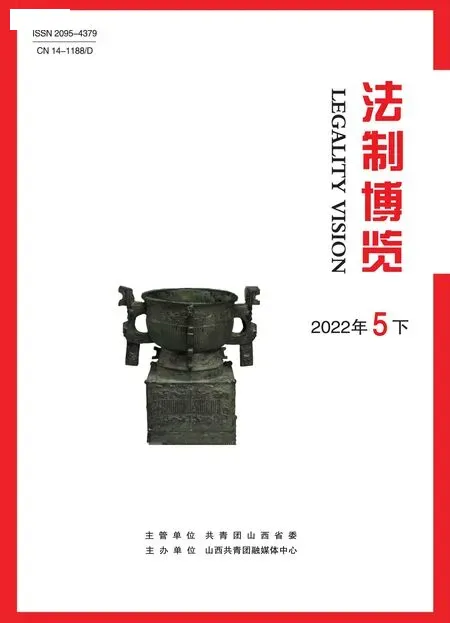違約方申請合同解除權之解釋路徑
孟 斌 毛艷艷
浙江子城律師事務所,浙江 嘉興 314000
一、問題的提出
合同解除是“契約必須嚴守原則的例外”,在成文法對解除權的規定上必須不斷修正,以確保其能在應用于實際場景時既符合立法目的,又最大化保護社會總體利益。2018年8月30日到31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次會議審議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解除權人不解除合同對對方明顯不公平的,對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請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響其承擔違約責任。”①《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二次審議稿)基于社會各界的激烈反應,在條文措辭上作出一些調整: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有解除權的當事人不行使解除權,構成濫用權利對對方顯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對方的請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響違約責任的承擔。此草案條文一出,一時激起民法學界的熱烈討論,討論的問題是:該條文是否有將違約方合同解除權轉化為成文立法的嫌疑?而此一疑問更是反映出學界對于應對合同僵局的手段所抱有的擔憂情緒。
直至《民法典》于五百八十條中確立了違約方申請合同解除的相關條款,司法層面才對該問題的解決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然而,出于對法條行使條件的質疑和批評,對于合同僵局問題的解決,似乎依然未能稱之為完善。
二、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之權利性質爭議
(一)“司法解除權”說
王利明教授認為,采納違約方解除權,不僅導致嚴守合同原則被破壞、還會導致道德風險,對社會秩序產生不良影響,更將導致法律出現“隱藏的漏洞”[1]。因在一方違約的情形下,非違約方有權請求違約方繼續履行,而繼續履行的前提是合同未被解除,如果賦予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在違約方行使解除權的情形下,非違約方請求繼續履行的權利基礎將不復存在,繼續履行這一責任承擔形式也將名存實亡。因此,其主張當出現不屬于情勢變更的事由并且非違約方拒絕解除合同的合同僵局下,違約方也僅享有向法院提出請求解除合同的申請的權利。該種權利不同于“違約方解除權”,因解除權作為形成權,其一般形式即為單方解除權,即當事人可以通過通知對方的方式解除合同,而該種解除權屬于特別解除權,是否解除合同有法院作出決定,并不因當事人的通知而生效。
(二)“司法終止權”說
清華大學的韓富鵬提出該種說法,是為了對應《民法典》法條的體系位置及淡化“解除”一詞,因其易引起公眾的誤解,同時自稱是對上述司法解除說的補充、糾正。其在上述理論基礎上補充認為,因合同解除的本質不是違約救濟,而是終止由合同產生的給付與對待給付,給付請求權不等于合同權利,故此應當使用“終止”表述而非“解除”,淡化適用該條時的違約救濟屬性。同時,其認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規定的“當事人”應當包括債權人與債務人,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違約方與守約方,因債權人也可能具有可歸責性,[2]其亦具有申請終止合同之權利。
(三)“違約方解除權”說
上述理論均未否認司法層面的判斷對于合同最終的終止效果產生的決定性影響,但王俐智老師則摒棄學界和實務屆早已基本達成一致的看法,認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規定的權利實質是解除權而非合同終止權,是當事人解除權而非司法解除權,且僅為違約方享有”。[3]首先,其認為我國法律未明確區分解除與終止,而終止的表述是為與第五百六十三條的法定解除權加以區分。其次,其認為若解除權屬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的權力,則無存在的基礎,法院享有對權利的裁量但不代表其享有權利,《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所規定的訴訟或者仲裁是當事人實現解除合同權利的程序性要件,是當事人所享有的解除權(形成訴權)的實現方式,而非法院等享有的司法解除權,況且,我國并無司法解除權此一權利類型。最后,其認為產生合同僵局的主要原因是合同不能或者不適于繼續履行情況下守約方不行使解除權,其并無解除意愿,因此在破解合同僵局時只能賦予有解除意愿一方即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
三、違約方合同解除權應定性為不完全的合同解除權
上述幾種觀點為學界主要認可的幾種類型,然筆者認為皆有不足之處,“司法解除權說”形成時間早于《民法典》編纂時間,因此經后人不斷探討改造,才衍生出各項對合同解除權的更深層探討,其優缺點前文也已提及,筆者不加以贅述;“司法終止權說”是在前一理論上的一次升級,在體系解釋、文義解釋的角度上將解除與終止加以區分,但筆者認為其意義不大,且因其多參考德國法上的可歸責性學說,債務人的可歸責性曾是德國、日本等國規定的合同解除的構成要件,可歸責性表彰了合同解除對債務人的“懲罰”,但該種要件已為德、日摒除,從“懲罰說”過渡至“解放說”,故其有關觀點值得商榷,不應以域外法的過時理論來限制《民法典》的解釋路徑;最后,“違約方解除權”雖似乎自圓其說,但無法對否認者的擔憂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站在“合同解除制度”的理論高度,提出了過于嚴苛的適用條件,并未考慮實踐層面違約方解除權可能帶來的社會治理的不穩定及道德風險,忽視了司法機關對法條理解、適用的局限性及法條規定本身的不完備性,況且,所謂“違約方解除權”已確定為《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全國人大法工委所否定[4]。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應當對《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的解除權含義進行新的探索。
孫良國教授認為,上述不同觀點存在潛在的兩點共識,即:(一)均不贊同在一般意義上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二)只有在嚴格條件下,法律才允許通過制度適用使違約方部分或者完全擺脫合同約束。[5]筆者認為,由于上述觀點在潛在的價值判斷上有共通之處,因此,可以在此框架下對《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尋找符合價值標準的解釋路徑。
張素華教授從合同解除本身存在的目的論出發,認為合同解除服務于合同目的,當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時,合同解除是合同雙方擺脫合同拘束的機制和手段。因此合同解除屬于救濟性權利,作為救濟性權利,其不應單獨為守約方享有。張素華教授認為并非只能通過剝奪違約方救濟權利這種極端的方式來實現利益平衡,完全可以通過設置不同的權利行使路徑來實現守約方與違約方的利益平衡。[6]
解除權分為簡單形成權和形成訴權,簡單形成權屬于私力救濟權,是形成權的常態,一般由權利人直接向相對人作出意思表示即發生效力,亦即一般情況下的合同單方解除權;形成訴權屬于公力救濟權,是形成權的特例,需要在滿足嚴格條件下,通過司法途徑來行使,形成訴權的判決即具備既判力。該種將私力救濟排除,僅認可公力救濟對合同的解除效力的權利即為本文所認可的“申請合同解除權”,亦可將其稱之為“不完全的合同解除權”。
在合同的解除權行使上,張素華教授建議采納法國法上的“司法解除”概念①參見1804年《法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七條規定:“任何情況下,當事人均可請求法院解除合同”。,要求行使解除權不能僅憑解除合同的通知,還必須借助國家司法程序提起訴訟或仲裁才得以完成。事實上,該種做法與王利明教授所主張的“司法解除權”的要求一致,亦體現出學界對該問題的解決路徑的一致看法。
筆者認為此理論肯定了違約方享有的是解除權中的形成訴權部分,對違約方申請合同解除的內在邏輯提供支撐,但又嚴格在形成訴權的場域內,將行使方式限縮于司法,否定了違約方單方解約的可能性,因此是對其他理論的融合改造,符合實踐需求。
四、《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的司法適用路徑
(一)行使申請合同解除權的限制條件
基于現實情況與理論研究歷程,無論采用何種理論的學說,均肯定該條適用存在以下幾項前提條件:實體要件上,首先合同要符合三種情形之一。其次已經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并且出現了合同僵局的情形;在程序要件上,需要向法院或仲裁機構提出申請。在結果上,合同解除后并不影響違約責任的承擔。
(二)采納不完全的合同解除權體系
“某公司訴馮某梅商鋪買賣合同糾紛案”在2006年刊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直至近幾年才引起學界的廣泛討論,究其原因,是基于實踐層面的處理需求,因此,認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是《民法典》合同編的特殊規定,具有合理性,其是為了解決實踐中合同僵局問題而特別規定的,具有很強的功能性,并不能簡單從邏輯、法理上推演得到。正如肯定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學者認為的,其必然是得到實踐的顯著成效,才得以被吸納入我國的法律體系中。
《民法典審議稿》幾易其稿,該條文反復進出法典多次,可以見得,對合同僵局的解決必須依靠成文法的規定,使得法官在面臨實際案件時有法可依,不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立法機關也必須通過嚴格的條件限制來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而不完全的合同解除權體系在實踐層面,吸取了各種理論之所長,既保障了違約方的申請解除合同的權利,又確保了只有司法機關可以決定合同解除與否的結果,防止過度損害非違約方利益。
(三)逐步淡化《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參照效力
《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四十八條對守約方申請合同解除提出了與《民法典》不同的條件限制,其中包含了對違約方顯失公平,守約方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要求,“顯失公平”與“誠實信用原則”均為不確定法律概念,需要法官經自由裁量確定是否符合。在具體適用中可具體化為債權人是否對合同存續仍然存在正當利益等內容,可裁量范圍較大,且混淆了與《民法典》其他法條的適用范圍,易引起法條的不當競合。
(四)明確合同解除的時間點
筆者基于對相關案例的研究,發現法院基于對違約方解除權的錯誤認知,可能對合同解除的確切時間產生誤判,故在此提請法官注意。在武漢天恒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朱文沁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①參見(2020)鄂01民終2630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的裁判要旨中在認可違約方通過承擔違約責任解除合同的同時,采納了違約方的意見,將違約方向守約方發出解約通知函的日期認定為合同解除的日期。該案中法官基于對違約方解除權性質的錯誤認識,認可了違約方單方解約的行為,本質上是認為違約方單方面對守約方發出解約的意思表示即可達到解約之目的,這是對違約方請求解除的司法程序要件的忽視,此情況應當在后續《民法典》的適用過程中予以謹慎排除。
就筆者檢索到的相關案例來看,上述判決并非個案,可見在理論層面厘清違約方申請合同解除權的性質,對實踐中法官做出正確判決具有重要作用。
五、余論
違約方申請合同解除權雖已在成文法中得以體現,但學界的爭議并未停止,其客觀上確實存在較多適用困境,例如:該條款置于違約責任章節是否優于置于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章節?僅適用于非金錢債務的《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存在適用范圍上明顯覆蓋不全。以上問題不僅需要從解釋論的角度予以紓困,更需要在不斷檢驗過程中予以修正、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