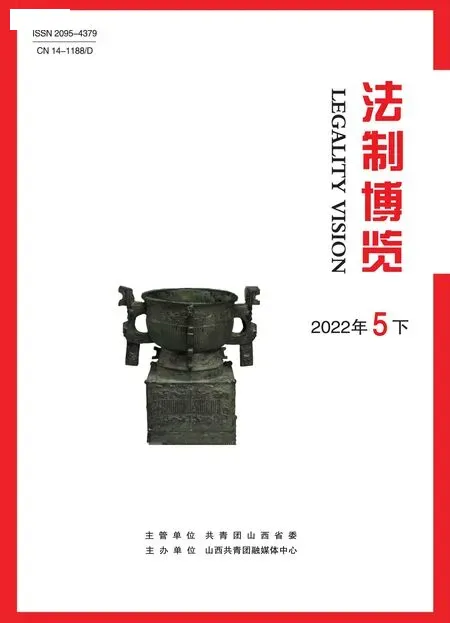離職員工侵害原單位專利權糾紛案例探討
王解濤
廣東百勤律師事務所,廣東 東莞 523000
一、案情簡介
2010年9月20日,東莞XX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莞公司”)成立,經營范圍是機器人、智能電動車及相關產品的研發、生產、銷售等。周某原為東莞公司的總經理,郭某原為東莞公司的技術經理,陳某原為東莞公司的營銷經理,閆某原為東莞公司的董事、營銷主管,王某等人原均為東莞公司的研發人員。
2011年8月至2012年10月,東莞公司組織周某、郭某、陳某、閆某等人從事M2項目(一款智能電動平衡車項目)的研發,后經多輪技術改進,最終完成了產品的研發工作,并生產出了樣車。隨即,東莞公司開始了量產前的準備工作。由于東莞公司的研發成本開支較高,起初與郭某等人并未明確股權激勵機制情況,后續東莞公司在與郭某等人在股權激勵機制談判協商中分歧較大。
2012年10月22日,東莞公司(包括周某、郭某、陳某、閆某等研發人員在內)的骨干成員集體離職。
2012年12月4日,深圳XX有限公司成立,后更名為深圳XXXX有限公司(以下均簡稱“深圳公司”),經營范圍與東莞公司近似,由周某任深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郭某任深圳公司的董事、股東,由王某等人任深圳公司的研發人員。由于周某等人的研發技術加持,深圳公司在短期內便完成了多輪融資,迅速發展壯大。
2012年12月11日,郭某等人作為發明人,以深圳公司作為專利權人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就“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和“一種雙輪平衡車”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并獲得了相應的專利證書。
2017年3月3日,深圳公司以東莞公司侵害其“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和“一種雙輪平衡車”的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為由將該兩案起訴至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主要訴請東莞公司停止制造、銷售、許諾銷售侵權產品,銷毀侵權產品及模具,賠償深圳公司的經濟損失2000萬元及維權費用,并由東莞公司承擔兩案的訴訟費用。
2018年4月15日,東莞公司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深圳公司及郭某、周某、陳某、閆某等人,主要訴請確認東莞公司為“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和“一種雙輪平衡車”的專利權人,本案的訴訟費由深圳公司承擔。
二、案件焦點
(一)涉案兩實用新型專利是否與郭某、王某、陳某、閆某等人在東莞公司處任職的本職工作相關,是否屬于執行東莞公司的任務所完成的職務發明創造,東莞公司主張其為專利權人應否予以支持。
(二)深圳公司的索賠訴請2000余萬元等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三、代理意見
(一)涉案兩實用新型專利與郭某等人在東莞公司處任職的本職工作相關,屬于郭某等人執行東莞公司的任務所完成的職務發明創造,案涉兩實用新型的專利權人應為東莞公司,而非深圳公司
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間,郭某等人分別入職東莞公司技術部門等部門,擔任東莞公司產品的結構、控制、外觀等研發設計工作,參與了東莞公司升級換代平衡車車型M2研發。
2012年10月22日,郭某等人從東莞公司離職后入職深圳公司。
2012年12月4日,深圳公司方注冊登記設立。
2012年12月11日,深圳公司僅成立7日即以郭某等人作為發明人,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分別申請名稱為“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和“一種雙輪平衡車”的案涉實用新型專利并獲得授權,專利人為深圳公司。案涉兩實用新型專利均涉及平衡車,與郭某等人在東莞公司處工作及研發產品直接相關。郭某等人在離職后的兩個月內、深圳公司成立之日起7日內便提出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應屬于其在執行東莞公司的任務所完成的職務發明創造。深圳公司及郭某等人均不能舉證證明案涉兩實用新型專利系其另行立項研發。同時,經鑒定可知,深圳公司的研發數據代碼基本和東莞公司的研發數據代碼一致。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六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二條規定,郭某等人在其人事關系終止后1年內作出與其在原單位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創造屬于職務發明創造。
因此,案涉“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和“一種雙輪平衡車”兩實用新型專利權屬應當屬于東莞公司。
(二)深圳公司的索賠訴請2000余萬元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由于案涉兩實用新型專利權屬應當屬于東莞公司,故深圳公司的索賠訴請2000余萬元等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關于深圳公司及郭某等人對東莞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屬糾紛以及由此給東莞公司造成的損失索賠問題,東莞公司將另案處理。
四、判決結果
2019年9月27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東莞公司為名稱“一種雙輪平衡車”和“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案件受理費2000元,由深圳公司及郭某等人共同承擔。
2019年11月20日,深圳公司將起訴東莞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兩案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訴,被依法準許;減半收取案件受理費41017.315元,由深圳公司承擔。
五、案例分析
(一)東莞公司與郭某等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和職務發明行為
在郭某等人入職時,東莞公司依法與其簽訂了書面《應聘登記表》《勞動合同》《保密協議》,并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同時,東莞公司的考勤制度、考核制度、工資發放制度和離職制度完善,全部工資均是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予以發放,明確備注“X月份工資”。雙方書面約定了職務發明的產品知識產權歸屬于東莞公司。因此,郭某等人無法否認其與東莞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的情況。
在立項、研發、試模和生產樣車等過程中,東莞公司通過多種形式保存了相應的證據;可以印證郭某等人各自在職務發明過程中的職務與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六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二條規定,勞動者在本職工作中作出的發明創造與履行本單位(包括臨時工作單位)交付的本職工作之外的任務所做出的發明創造為職務發明創造。
勞動者在退休、調離原單位后或者勞動、人事關系終止后1年內作出的,與其在原單位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創造仍屬于職務發明創造。
綜上可知,郭某等人雖然搶先申請并獲得了“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和“一種雙輪平衡車”的實用新型專利權證書,但是,根據法律規定上述兩個實用新型專利權應當歸東莞公司所有。
(二)郭某等骨干人員(含研發人員)同時集體離職并秘密竊取了東莞公司的文件資料涉嫌觸犯侵犯商業秘密罪
2012年10月22日,郭某等骨干人員(含研發人員)同時集體離職,并擅自取走了部分《勞動合同》《保密協議》及東莞公司M2研發過程中的部分資料,后續供深圳公司申報專利和生產等使用,嚴重侵害了東莞公司的合法權利。東莞公司依法向公安機關以郭某等人涉嫌犯觸犯侵犯商業秘密罪為由報案。經偵查和鑒定發現,深圳公司的軟件資料中多套源程序代碼等數據與東莞公司M2研發數據存在一定的關聯性。隨后,郭某等人因涉嫌犯觸犯侵犯商業秘密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和逮捕。
(三)深圳公司及郭某等人搶注專利獲得的權屬證書無效,同時,其生產、銷售類似產品和先行起訴索賠等侵害東莞公司專利權屬的行為還將面臨巨額的賠償
郭某等人原本為東莞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研發人員,在同時集體離職兩個月內和深圳公司設立起7日內搶注案涉“一種快速拆裝方向桿”和“一種雙輪平衡車”兩實用新型專利;在其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頒發的實用新型專利證書后,一方面大力組織產品生產和銷售,另一方面主動先行起訴東莞公司侵害其專利權索賠2000余萬元等。
郭某等人隨即設立了深圳公司從事與東莞公司類似產品的生產、銷售進行不正當競爭等行為,第一,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等法律法規;第二,涉嫌違背基本的誠信原則和商業道德;第三,其步步緊逼不留余地的行為徹底激怒了東莞公司,最終“偷雞不成蝕把米”。
六、結語和建議
(一)源頭保護、主動防御
隨著社會發展的日新月異,企業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但多數企業特別是同行業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還是人才的競爭、知識產權的競爭。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的寶貴資產,是企業重要的經濟資源,一定程度上可以稱之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發動機”[1]。但是由于企業對于新產品的研發周期相對較長、前期投入成本相對較高,研發成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所以,企業,特別是以知識產權為源泉的高新技術企業更應該明白“源頭”保護的重要性。企業應當強化人事管理部門、法務部門和知識產權部門的資金投入和團隊建設,努力促使保密措施嚴格、研發制度(特別是對于研發人員的股權激勵機制)明確、管理機構規范、申請專利權證書及時。企業選擇何種創新形式,取決于自身的經濟技術實力和面臨的外部技術、市場環境。無論選擇何種創新模式,企業需要結合所處行業的競爭結構和創新環境,以知識產權戰略指導創新活動,以知識產權戰略引導企業技術創新,將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技術創新有機結合起來[2]。
(二)慧眼識英才、明智辨良將
研發團隊是企業知識產權的核心締造者,研發團隊的組織架構應當清晰,各成員之間應當分工明確、搭配合理,注重研發人員的培養和梯隊建設。企業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應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管控,努力杜絕將其掌握在某個人的手中。在試用期間,企業應完成盡職調查,努力去發現研發人員的職業背景、個人業務能力、忠誠意識與忠誠度,制定相對公平合理的考核體系和激勵機制,及時與研發人員簽署相應的保密協議、競業禁止協議和競業限制協議,保持研發團隊的穩定性;同時,將核心技術分散,盡快申請相應的知識產權,及時促使研發成果轉化。在知識產權轉化為商品銷售營收之后,可以考慮提取一定比例的費用反哺研發團隊。在研究開發階段,企業最重要的目標是充分運用現有的創新資源和人力資本,獲得預期的創新成果。企業知識產權創造能力可以通過研究開發活動得以提升,企業可以通過選擇創新模式、研究開發路徑、對創新成果的保密等方式促使創新成果的誕生并取得自主知識產權[3]。在研發后期,企業應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識產權優勢,快速轉化研發成果,縮短轉化周期,及時搶占商品市場,充分發揮和體現知識產權的價值,早日完成產、學、研相結合的一體化建設。
(三)果斷出擊、依法維權
企業應建立一套完整的知識產權風險預警機制,發現侵權行為要及時制止、果斷出擊、降低損失、維護權利。雖然專業性特征決定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具有很多共性特征,甚至不同企業在知識產權管理的客體、基礎法律制度、操作流程等方面都有規律和規則可循,但由于各企業在企業實力、經營理念以及企業文化等方面有各自的特點,從而導致各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又都有著與眾不同的特點。知識產權制度是鼓勵創新的機制,管理是一門藝術,知識產權管理會自然地融入其企業文化之中。
建立健全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配合積極的維權手段對于侵權的行為主動出擊,為企業專利保護建成完整的保護網。同時,通過維權、打擊侵權行為以及許可使用等方式,為企業回收在專利研發中的前期高額研發成本,將專利的無形財產轉為有形的經濟利益,推動企業創新活力,激發企業創新動力。實踐中,企業知識產權的維護過程中,不應局限于個案維權成本的高低與得失,不應局限于眼前一時維權成本的支出,應當長期綜合地分析維權成本與維權收益之間的關系;整體上來看,只要維權的長期收益大于維權的短期成本,就應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維護自身知識產權,搶占市場,擴大收益。
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產權是保障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有力武器,企業應當建立并且不斷完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和體系,積極采取有針對性的防控措施,保障企業創新成果,促進企業的持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