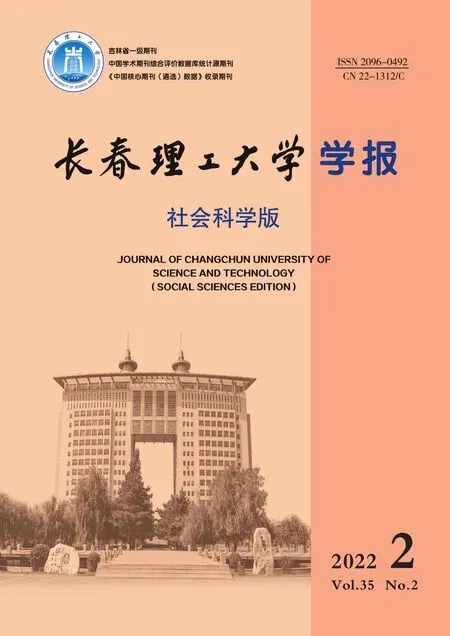周大新小說《第二十幕》的空間敘事解讀
付蘭梅,周妍妍
(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22)
《第二十幕》(1998)是河南當代作家周大新的長篇代表作之一,深沉雋永,可謂是南陽小說家周大新的集大成之作。小說洋洋灑灑一百萬余字,講述了南陽一個織絲廠在百年間的風雨歷程及尚家五代人為了織出“霸王綢”所做的努力與拼搏。這部小說既是一部厚重的民族工商業蛻變發展史,又是一部以百歲老人尚達志為中心展開的家族奮斗史,更是一部全方位展現手工業者(尚家)、知識分子(卓家)、農民(栗家)、官宦(晉家)之間相互斗爭與糾纏并不斷裹挾著歷史滾滾前進的社會發展史。
這部作品內涵豐富,在一定程度上給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多種角度。截止到目前,從知網檢索到有關《第二十幕》的詞條共34條,包括2篇碩士論文,32篇期刊論文,研究內容主要涉及人物形象分析、主題發掘、比較分析、意象探討、藝術價值探究等方面。其中不乏從敘事角度探究《第二十幕》的歷史書寫、權利書寫及非歷史敘述。雖然這些研究更傾向于從傳統的以時間為維度的敘事方式出發,忽略了空間在小說中的作用,但也為本論文的寫作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作為一部較為典型的現實主義小說,傳統的線性敘事手法在《第二十幕》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但除了時間以外,空間也在小說敘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空間表征法、空間變易等敘事技巧的運用,不僅大大增強了文本的空間感,對作品主題的呈現也有一定的助力。基于龍迪勇的空間敘事相關理論,從空間敘事策略、空間敘事的文學功能及空間敘事的意義等三方面對《第二十幕》的空間敘事進行深入的剖析與闡釋,以期對這部小說有一個更為深入的理解。
一、《第二十幕》的空間敘事策略
作為一種時間性的存在,小說首先表現為依據一定的時間順序進行敘事,完全強調空間而拋棄時間、漠視時間的作品是難以成功的;但小說同時也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其敘事需要依據一定的空間邏輯,純粹的時間性敘事是不存在的。只有協調好時間和空間的關系,讓空間通過特殊的時間性媒介——語言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才能更好地為作品服務,實現超越。空間敘事結構的擇取、敘事空間的變易及空間表征法的運用的結合構成了《第二十幕》的空間敘事策略。
(一)空間敘事結構的擇取
《空間敘事學》將空間形式劃分為中國套盒、圓圈式結構、鏈條式結構、橘瓣式等類型,在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中,“中國套盒式”和“圓圈式”這兩種空間敘事結構表現較為突出。“‘中國套盒’是一種故事里套故事——大故事里套著一個中故事,中故事里又套著一個小故事——的小說結構方式,也稱‘嵌套結構’或‘俄國玩偶’。”[1]154在這種敘事結構中,文本中的敘事者往往不止一個,就像秘魯學者巴爾加斯·略薩(1936—)說的,“通過變化敘事者(即時間、空間和現實層面的轉換),在故事里插入故事”[2]。在《第二十幕》中,作者為了揭示曹寧貞的悲劇命運,使用了這種空間敘事結構。文中出現了三個故事:現代女性曹寧貞的故事、安留崗女尸王文蕊的故事及寧貞夢中的黑裙女孩的故事,這三個故事的敘事者各不相同。曹寧貞作為小說中的一個重要女性角色,作者在塑造她時運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她生存的空間即20世紀的南陽盆地,具體活動空間是尚吉利織絲廠。王文蕊是安留崗上出土的女尸,她所生存的空間是公元125年的南陽,其具體活動空間是城門校尉閻耀的家。作者在揭示其命運經歷時運用了倒敘的手法,以考古學家卓月的視角進行觀察,經過層層推理,最終使真相被抽絲剝繭般展現出來。而黑裙女孩以夢的形式出現在寧貞的潛意識中,自然是以寧貞的視角來展現,她的具體活動空間就是寧貞的夢境。黑裙女孩在小說中共出現四次,幾乎貫穿寧貞短暫生命的始終,且每次都是以相同的形態出現,即“她從自己頭頂里抽出一縷一縷如蠶絲的東西給寧貞看,并告訴她這是感情!當寧貞想要仔細看時,她卻突然把自己的頭顱取下朝她遞來,讓她看個清楚”[3]。
“圓圈式”結構是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中分析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時提到的一種空間敘事結構。他指出,“小說總體寫的是過去,而小說又是從這一過去的某個‘將來’開始敘述的,它最終總要回到‘將來’——小說的開頭。于是小說的結構形成了一個時間性的圓圈”[1]158。《第二十幕》中多次出現這種“圓圈式”的結構,如抗戰結束,栗溫保遇見政敵蔡承銀時,作者用了這樣一段話:“栗溫保此時還沒意識到,這個分別的場面將要永遠地刻在他的記憶中,在今后的歲月里,他還將無數次地憶起這個場面,并為在此刻自己沒有掏出來槍而后悔……”[4]其實作者在此時就已揭示了栗溫保兵敗的結局,但是他沒有直接言明,而是從未來栗溫保的自責后悔說起,從而與其后的敘事達到合理呼應,使文本空間更為完整。可以說,這短短的一句話,就已經容納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時間維度,展示了小說敘事結構的空間特性。除此之外,文中還有多處“許多年以后”“那件事現在想起”“在那樣一個晚上”這樣的句子,正是這一個個封閉的環形敘事,將歷史與現實有機地聯系起來,從而營造出《第二十幕》的空間感。
(二)空間表征法的運用
“空間表征法”[1]262是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中首次命名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由于傳統人物形象塑造方式的朦朧性,一些有創造力的天才作家在考察了人物行為動作、性格特征與空間的關聯性后,往往傾向于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空間里完成人物性格的塑造。無論是古典小說還是現代小說,都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法國作家巴爾扎克(1799—1850)和普魯斯特(1871—1922)、英國作家狄更斯(1812—1870)等都是擅長利用空間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龍迪勇便將這種利用特定空間來塑造人物的方法命名為“空間表征法”。
周大新在小說中正是通過尚吉利織絲廠和通判府來分別塑造了尚達志和栗溫保兩個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人物。首先,尚吉利織絲廠作為一個統攝全文的切入點,它是尚家五代人為之傾盡畢生努力的存在,與其說它是一個空間,不如說是一種精神,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家族精神。這種家族精神內化到了尚達志的性格中,使得尚達志的性格呈現出復雜多樣的特點。尚吉利織絲廠與尚達志是一種雙向同構的關系,尚吉利的特定空間孕育了尚達志復雜多樣的性格,而尚達志為家族事業敢于犧牲一切的性格又推動著尚吉利織絲廠的改革變遷。其次,通判府(后來的栗府)作為一個政治場所,這里的一切都與權力密不可分。百年之間,這個房間里先后更換過五批執政者,而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栗溫保,他在進入這個權力場所的前后轉變使讀者看到空間(權力)對一個人性格的塑造(異化),在他身上,灌注了作者對權力的深刻反思。
(三)敘事空間的變易
《第二十幕》中兩個極具代表性的空間是尚吉利織絲廠和通判府,它們在整個20世紀都經歷了一個空間變易的過程。首先,尚吉利作為故事發生和主人公活動的具體空間,經歷了四次被毀、三次易名。從最開始的小作坊尚吉利大機房到八國聯軍割地賠款,南陽通判晉金存敲詐商人導致其關閉停業,尚家第一代經營者自此身死氣絕;到尚達志經營良好,將其擴充為尚吉利織絲廠,引來當時執政者栗溫保的眼紅,尚達志拒絕與其一起合辦的要求后房子被燒;再到東山再起,織機卻在抗日期間被日軍炸毀;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尚吉利織絲廠被迫公私合營,改為“國營尚吉利織絲廠”;再到文革時期,尚吉利被宛城紅色造反團占領,后廠房再次被燒;最后到改革開放后,國家允許私人辦廠,尚吉利又恢復了私有身份,成為尚吉利集團。
不僅如此,通判府也經歷著一個空間變易的過程,從最初的晉府(封建勢力代表南陽通判晉金存的住址府)到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栗府(民軍總頭目栗溫保的住址);到國共兩黨內戰期間栗溫保倉皇出逃后成為蔡承銀市長的政府專員宿舍;至文革時期被抄,變成紅衛兵造反總部;再到文革結束后成為副市長蔡承達的住宅。可見,經過幾十年的變遷,這棟房子儼然成了權力的象征,當一個執政者將上一個執政者從房子中趕出的時候,就代表著一個政權的結束。
二、《第二十幕》空間敘事的文學功能
與時間一樣,空間作為小說故事發生的場所也在小說敘事中發揮著一定的文學功能。在《第二十幕》中,周大新主要通過“中國套盒”式、“圓圈式”的空間敘事結構來展現南陽女性甚至是南陽人走不出命運怪圈的生存困境,空間表征法塑造尚達志和栗溫保兩個典型人物形象以及運用空間的變易來推動小說的敘事進程。
(一)南陽人生存困境的展現
周大新在訪談中處處直言不諱自己對南陽女性生存命運的關注。“中國套盒”敘事策略的運用,首先展現了女性千百年來不變的生存困境。作者通過“中國套盒”式的結構有意設置兩個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中的女性,但她們卻有著同樣的悲慘結局,都是以身誘敵,慘遭報復,含冤身死。不同的是,寧貞死于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中,人們丑陋的逐利本性逐漸暴露,最終淪為金錢利益與權力陰謀較量下的犧牲品;而王文蕊則死于宮廷政變中的政治陰謀論。但無論是哪種死亡,女性面臨的生存困境都未因時空的轉變而消亡,不過是跨越千年以另一種方式在另一個時空中再度上演。而那個黑裙女孩的夢,則成了兩人命運交匯的聯絡點,一邊揭示著歷史的真相,一邊預示著現代女性為愛而死的慘烈結局。與其說這兩個女人跨越時空完成了一次命運的交匯,不如說“過去”的陳年舊事被作者用夢的形式帶到“當前”,以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上演著千百年間女性無法改變的悲劇命運。
除了女性,周大新還重點關注故鄉人民的生存苦難。他在《第二十幕》中描繪著南陽人民的生生死死、忙里忙外,兜兜轉轉無論如何也走不出人生中的一個個的怪圈。“在南陽盆地里,一切都是輪回的,非歷史的,包括時間,不可能存在典型,只有影影綽綽匆匆過客式的人的身影。”[5]尚家男性因著“霸王綢”的執念,一代代人在欲望與自我的沉淪交替中走向各自的悲劇;卓家堅持自我不入政的知識分子們在世事無常的變動中陷入迷茫失落和自我懷疑;通判府中前赴后繼逐利而去的官場人士,如過江之鯽,在時代的浮沉交替中石沉大海;而書中的女人們,仿佛夜間盛開的曇花,只一瞬,便流入時間的荒原,不知所終。書中第五代人的故事還未結束,他們與命運的抗爭終將一代代延續下去,沒有盡頭,由此更加體現了命運的無法捉摸和人對自身困境的無法超越。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空間表征法”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集中在尚達志和栗溫保身上。尚吉利織絲廠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尚家大家長尚達志,在面臨家族事業和個人利益的抉擇時,他永遠將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尚吉利織絲廠在他的經營下經歷了三起三落都死而復生,可以說,他是一個精明的領導者,一個有魄力的生意人,更是一個致力于將南陽絲織業發揚光大的民族工商業者。然而,家族精神的高揚卻導致了尚達志個人精神的失落,為了守護住織絲廠,他從一開始就必須放棄一些東西。作為情人,他為了家族事業,對年少戀人盛云緯始亂終棄,導致了這個女性凄慘悲哀的一生;作為丈夫,他從未對結發妻子順兒正眼相待,由始至終都只是把她看作一個織布機器、生育機器;作為父親,為了籌夠買機動織機的錢,他罔顧人倫,用了四十五兩賣掉了自己的親生女兒;作為祖父,為了懲戒沾染不正之風的孫子尚昌盛,他親手砍掉了他左手的五個指肚;作為外祖父,為了保證家族產業后繼有人,生生把熱愛唱歌的曾孫尚旺旺的嗓子毒啞……這些看似違反人性的行為,其實都和尚吉利織絲廠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與其說尚吉利織絲廠是尚達志賴以生存的空間,不如說尚吉利織絲廠已經內化為一種民族精神刻進了他的血肉,廠在人在,廠亡人滅。我們很難從是非倫理的角度對尚達志進行評判,作者塑造出這樣一個多維性格的人物,也顯示了作者對他的復雜態度,既有對他身上流露出的以民族工商業兼濟天下的儒家文化性格的贊賞,又有對他自我意識失落從而導致多重悲劇的民族精神的反思。
栗溫保本是南陽城西落霞村一個打兔子出身的農民,由于生活所迫,加入了民軍,并因著不怕死的勁頭,成了民軍的總頭目。他以“使天下窮人有衣、有糧、有房”為目標,受到民眾擁護,那時的他嫉惡如仇,將老百姓視為手足,嚴懲強搶民女的肖四,儼然一副人民的代言人。而當他戰勝晉金存,搬入通判府,將其改為栗府之后,先是收受賄賂打破自己當年不行賄的承諾,接著背叛糟糠之妻,豢養外室,后又因對金錢的狂熱提出與尚達志合辦織絲廠,被拒絕后,一把火燒了尚吉利織絲廠。他執政后所犯下的種種罪行罄竹難書,顯然與建立“三有社會”的初衷背道而馳,對權力的盲目追逐讓他喪失本性,不僅在行房時自己扮演皇帝,讓薛小亞扮演寵妃以滿足自己無人理解的虛榮心,甚至在被收押之后跟著一眾獄友去參觀紫禁城時要求坐一瞬那龍座,從而體驗一下做皇帝的感覺,可見,空間的變易造成了栗溫保思想性格的巨大轉變。如果不是栗府,不是權力,讀者看到的仍是其嫉惡如仇、正直憨厚的一面,地位的轉變才將其性格中嗜財戀權的一面暴露無遺,透過栗溫保,不僅能看出權力對人性的侵襲和異化,更能看出農民執政的局限,從正直到腐化,只需要經歷一個空間的轉變。
(三)敘事進程的推動
“很多小說家對空間很感興趣。他們不僅將空間視為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敘事必須的場景,還利用空間來表現時間和安排小說結構,甚至利用空間來推動整個敘事進程。”[1]112在《第二十幕》中,周大新正是通過尚吉利和通判府的空間變易來架構小說的,空間在整個敘事進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尚吉利織絲廠的易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百年間民族工商業的艱難蛻變歷程,不僅如此,尚吉利織絲廠的興衰與時局變動、國家政策息息相關,透過尚吉利織絲廠的變化,也可以看出中國時局的整體變動。作家雖無意強調政治,但小說中處處可見政治的身影,清末帝制、八國聯軍侵華、中華民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公私合營、大躍進、三年饑荒、文化革命、改革開放等等,這一系列歷史重大事件都是作為主人公活動的一個背景,被穿插在故事中為推動敘事進程服務。
如果說尚吉利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反映社會發展,那么,通判府則是從政治權力的角度來映襯時代更迭的。百年之中,這棟房子四度易主,晉、栗、蔡三大家族都在此展示過自己的政治抱負,可以說,通判府的每次易主都暗示著政局的變化,而且它作為一個展示社會關系的大舞臺,連接著社會各界人士,這里每天都上演著士農工商各階層的斗智斗勇。時局的每一次變動都會對它產生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大空間的縮影,是社會歷史發展前進的象征。
總的來說,無論是尚吉利還是通判府,都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單純的居所而存在,它們代表的不僅是空間更是時間,周大新正是通過利用它們的變易來推動整個故事的發展進程,從而進行他的社會歷史考察和政治權力反思。
三、《第二十幕》空間敘事的意義
就審美意義而言,《第二十幕》雖然也遵循一定的時間敘事策略,但作者顯然突破了傳統的僅以時間為維度的現實主義書寫,他在小說中自由調配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事件,使小說敘事中的時間和空間達到了有效的和諧統一。周大新不僅在小說中構設出全部小說人物生存的大空間南陽盆地,而且還在此基礎上開拓了人物具體活動和生活的小空間,如尚吉利織絲廠和通判府,并利用空間的來回轉換,擴大了讀者的閱讀視野,給讀者帶來了別樣的審美體驗。此外,周大新還通過有意淡化故事的時間和背景、現實世界與虛幻世界(如想象、夢境)的轉變、敘事視角的來回轉換等空間敘事策略來架構故事,不僅拓展了文本的空間感,還擴大了讀者與文本的距離,增添了文本的審美性。
從現實意義來說,通過空間敘事,周大新不僅對南陽人面臨的走不出生命怪圈的人生困境進行了拷問和探究,也對權力對人性的異化進行了反思。他在特定的空間中塑造著典型的人物形象,并對他們身上堅忍頑強、以德報怨、在災難面前不肯服輸的傳統農民善良樸實的一面進行肯定,也對其相互報復、勾心斗角、罔顧人倫、向利看齊的國民劣根性的一面進行批判和拷問。不僅如此,他還通過空間敘事對故鄉人的生存現狀和現實困境進行審視,從而展開他獨特的文化反思與人性拷問的活動。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人類尤其是女性生存的困境仍未得到解決,人們世世代代都要通過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困窘的外部生存環境做斗爭,如何將有限無限化,達到理想化的生存狀態,是周大新作為知識分子的擔憂及困惑,更是當代人需要思考的問題。除此之外,在商品化經濟急速發展的今天,如何在物質資源極度膨脹中分辨真實與虛假、抵擋金錢權力對人性的侵襲并遏制人性在欲望面前的扭曲異化更值得深思。
本文從空間敘事的角度對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進行了考察。從“中國套盒式”“圓圈式”等空間敘事結構的選擇、尚吉利和通判府兩個敘事空間的變易及空間表征法的使用等三個方面對《第二十幕》的空間敘事策略進行條分縷析;并對《第二十幕》中空間敘事的文學功能即南陽人生存困境的展現、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敘事進程的推動進行探究;最后,分別從審美與現實兩個維度探究了《第二十幕》的空間敘事的審美價值和現實啟示。總的來說,周大新在這樣一部現實主義巨著中,運用空間敘事的手法,打破時間的約束,自由調配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事件,將個人化的歷史認知和對文化的解讀組織進敘事之中,不僅擴展了文本的空間感,更對歷史生活進行了個人化的還原,給讀者勾畫了一個可供想象的歷史文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