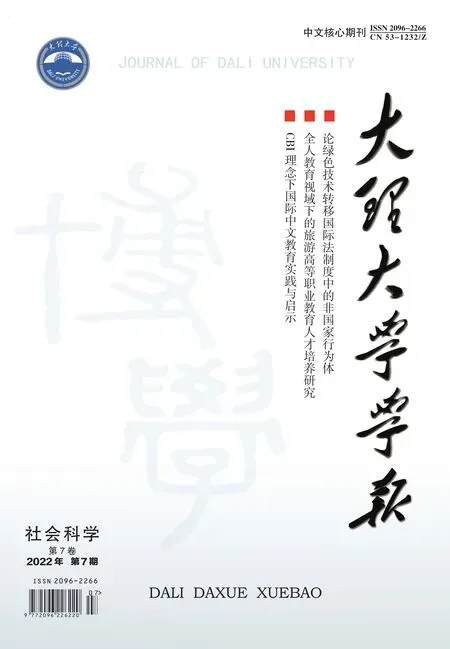論約翰·海恩斯將語言與地球聯結的詩學
胡 英,劉麗艷
(大理大學,云南大理 671003)
詩人約翰·海恩斯(John Haines,1924—2011)是阿拉斯加的桂冠詩人(1969),是當代美國最重要的自然作家之一。他的詩歌與散文創作根植于遠離現代文明的阿拉斯加的廣袤荒野,清新、質樸,如冰雪般冰冷且具有穿透力,成為當代文壇中的一股清流。從小海恩斯就習慣于獨自一人,性格比較孤僻。這種童年的無根之感,令海恩斯在成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尋求穩定性,尋求一個可以令身體安穩的棲身之處與精神的避難所。阿拉斯加就是他要尋找的地方。成年后的二十余年間,他住在人跡罕見的阿拉斯加理查遜外圍,并在那里建了一個農場,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獵人、農夫與自由撰稿人。在這里,他找到了與其內心對應的一個外在風景,實現了“夢幻與地方的完美結合”①此處借用詩評家Baron Wormser的說法,他在給海恩斯作品集(Descent:Selected Essays,Reviews,and Letters,2010)的介紹中曾說過:“海恩斯是一個詩人,一個號召將語言與地球聯結起來的詩人”。。正是阿拉斯加這片土地給海恩斯帶來了靈感,讓他通過自己的作品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并欣賞阿拉斯加的荒野。由于海恩斯詩歌與散文的影響力太大,帶領人們迷戀和欣賞阿拉斯加的荒野,詩人威廉·維特拉普(William Witherup)在詩歌《詩人J.H.》(“The Poet J.H.”)中夸張地評價海恩斯是“施洗約翰”,是一個“薩滿”和“身著海豹皮毛的瘋和尚”,而詩人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更是聲稱阿拉斯加人是社會退化中蠻受歡迎的傳令官,而海恩斯則是用其作品“介入這個民族的崩析”的人〔1〕。
在海恩斯看來,“地球與詩歌之間的聯系源于某種攫取精神的神秘而陰暗的沖動”〔2〕,而他的詩歌就是這種精神沖動很好的證明。詩歌的作用就是重建語言意義的深度,而對于海恩斯來說,這種深度源于我們在地球上的生活。我們來到并行走于地球的表面,這是我們的命運,但是關鍵在于我們如何來處理與應對這種情形。在海恩斯看來,地球完全可以自己照看自己,人類居住在地球上不應當僅僅作為一個使用者的角色,而應當有所貢獻:“這就是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任務,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讓這個已經遭到破壞、但卻仍具復原能力的地球成為一個更健全、更美好的地方。”〔3〕
一、詩歌與地方結合:根植于阿拉斯加
在奧萊利(Mercedes O’Leary)對他的采訪中,海恩斯曾經談論他對一流文學的理解,他說“不論小說或詩歌,多少都和某個地方或者環境相關聯,從而具有它獨特的特征”〔2〕,這印證了海恩斯創作與地方的聯系。在談到他在阿拉斯加幾十年的荒野生活時,海恩斯認為多年的荒野生活經歷影響著他的寫作,尤其是在晚年的時候,“我(他)深刻地發現我(他)在林中所見,不論是植物生長或是動物與鳥類等等,都與我(他)的寫作有著強烈的聯系……我(他)感覺到,古代的故事都起源于某個年代的某些地方,它們都有一定的基礎和背景,那就是人們面對自然時的經歷”〔2〕。
海恩斯在42歲時出版第一部詩集《冬日消息》(Winter News,1966),可謂是大器晚成。因為他原來主攻藝術,甚至想成為一個畫家,直到他“出于本能地”發現了阿拉斯加這片令他重生的土地,他才找到了靈感,決意成為一名詩人。他的散文隨筆《星,雪,火:一個人在阿拉斯加荒野的25年》(The Stars,the Snow,the Fire:Twenty-five Years in the Northern Wilderness,1989)主要基于他在阿拉斯加的真實生活,被譽為與《瓦爾登湖》(Walden,1854)、《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并列的世界三大自然隨筆。自出版以來,已被譯為十幾種文字,被譽為20世紀最優美的自然文學。某種程度來說,《星,雪,火》的巨大成功主要因為海恩斯在阿拉斯加荒野的親身經歷,給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感受,使整部散文都散發著荒野的迷人魅力。
海恩斯一生的重要創作經歷主要根植于阿拉斯加的理查遜外圍。海恩斯一生在近四十年間出版了十余部詩集,大部分都是基于海恩斯在阿拉斯加的親身經歷,這不僅反映在詩歌的內容中,也體現在詩集的標題上。比如第一部詩集《冬日消息》,以及后來的《來自冰川的消息》(News from the Glacier,1980),《薄暮從不消失之地》(Where the Twilight Never Ends,1994),《夏末》(At the End of This Summer,1997),還有其最后一部詩集《夏日流逝》(Of Your Passage,O Summer,2004)。這些詩集的命名幾乎都與阿拉斯加的冰川、氣候明顯掛鉤,其內容也常常將阿拉斯加的北極荒野作為詩歌的描述對象,這使得海恩斯看上去成為一個對于當代政治與時局漠不關心的荒野詩人。實際上,在海恩斯來到理查遜外圍之前,他曾經應征入伍參加二次世界大戰,并且兩次險些喪命。戰爭給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當二戰結束,海恩斯第一次來到阿拉斯加時,那里的環境立刻震動了他,令他作出在荒野中生活的重大決定。海恩斯在阿拉斯加荒野深處尋求孤獨,以及他以自然為基礎的宣泄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治愈戰爭經歷的創傷,因為戰爭讓他對于人類的邪惡力量有了深刻的認識。
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的荒野環境造就了海恩斯詩歌的獨特品質,令他的詩歌具有如素描畫一般的簡潔,同時又具有如冰雪般寒冷的穿透力。他的第一部詩集《冬日消息》出版于1966年,當時正值越南戰爭,但是詩集中詩歌似乎并未直接對戰爭進行評述,相反,在詩中人們讀到的是與現實社會生活完全不同的平和與安靜的景象。詩集的第一首詩歌《如果貓頭鷹再次叫喚》(“If the Owl Calls Again”)就傳達了那種屬于造就他的那片土地的安靜。詩歌一開始就引導讀者進入一個人與自然界限不明的世界:“薄暮中,/河中的島上,/天不是太冷,/我要等到/月亮上升,/便張開翅膀滑翔/與之相遇”〔4〕3(1~7行)。詩歌的基調似乎有些異想天開,在這里人類與動物(貓頭鷹)、月亮似乎在進行一種本能的溝通,這是一個原始的世界,人類與動物間的界限似乎是流動的。從詩歌第三節開始,原先的“我”(“I”)很自然地被“我們”(“we”)取代,然而并不說話,因為我們之間似乎達成一種默契:“當晨曦爬上/枝干/我們將無聲地分開”〔4〕3(21~23行)。
在另外一首名篇《冬日消息》(“Winter News”)中,詩人呈現出一幅準備過冬的情景,讀完詩歌,人們似乎可以感受到從之撲面而來的寒冷。詩歌的開頭是這樣的:“有人說井水正在/結冰/在諾斯韋/寒冷已經來臨”〔4〕4(1~4行),詩歌第一句中的用詞“they”(“有人”)給整首詩歌造成一種不可信和不確定的氛圍,雖然接下來整首詩歌看似以一種類似新聞稿的風格進行寫實,但是這樣的開頭就提醒讀者詩歌寫實內容的不確定性。海恩斯就是通過這種將準確描寫與不確定性糅合在一起的做法,讓其詩歌產生一種精神的效果,帶領讀者進入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他把從地球感受和領悟到的精神通過詩歌直接傳達到讀者,通過詩歌將語言與地球聯結,從而將人類與自然聯結。
海恩斯這種看似純粹景物的描寫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中國古代的山水畫,看上去雖然寥寥幾筆,卻無形中給人一種感動和意境。這也許是海恩斯與典型現代主義詩人的主要區別所在,比起龐德、威廉斯等現代主義詩人對于詞匯與詩句的精心構造,或是如艾略特般強調的“客觀對應”,海恩斯的詩句顯得過于簡樸而平實,但是卻能更加直接地深入人的內心與無意識的深處,成就一種讀者與詩人之間自然而然的共鳴與反響。
阿拉斯加荒野生活的親身體驗令海恩斯深刻地體會人類生命的脆弱,意識到大自然的威力與人類的渺小。在這片冰天雪地中,海恩斯的首要任務是學會如動物般地生存,其次才考慮作為一個人的身份。正是這種艱苦的生活改變人,并將他們帶回本質的自我,因此,荒野的體驗既是一種負擔同時亦是一種祝福。同時作為開荒者與詩人的海恩斯曾經這樣總結他的生活:
在世界的沉寂中有一種催眠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威脅等著我們。當我跪在雪地、思索著如何在遠離居所好幾英里外的山脊設置陷阱時,我感到威脅正在臨近。寒冷刮臉,低處藍光籠罩,短暫的白日即將結束,在這熟悉而友好的陰影中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我從不在意自己是否活著……雪橇下的河冰突然破裂、翹起,我的心跳加速……一個人生命的堅底可以如此迅速地消失。〔5〕
在經歷和體驗了生命的脆弱之后,海恩斯指出,“自然的狀態就是優雅的狀態”,“當我們不帶任何目的地觀察世界時就會發現它是如此美麗”。
因此,海恩斯在詩歌中往往避免普通的人類視角,詩歌《受害者》(“Victims”)就是很好的例證。詩歌用平靜的口吻描述了人類捕殺動物的場景,在他這里沒有“好”“壞”,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與動物一樣,他們獵殺只是為了生存。詩歌前三節敘述者都是以旁觀者的第三人稱視角,到了詩歌最后一節視角突然切換,“注定死亡的動物窒息/仿佛在紅色薄霧中看見/他自己滴著血的尸體”〔4〕15(9~11行)。森林中的捕獵者最終看到自己成為獵物,這是否也暗示作為捕獵者的人類最終也會有類似遭遇?
在海恩斯看來,荒野令人學會感受與經歷,因而變得更加敏銳,可以喚起自我自然人性的一面。海恩斯試圖將文明與荒野并置,他在詩歌與散文中表達了一個理念,那就是文明人來到荒野可以變得更加完全。正如克羅農(William Cronon)所言,因為文明的存在才產生了荒野的概念,同樣,在海恩斯看來,因為荒野的緣故,文明人可以更加敏銳地感受到其自然人的一面,因此變得完全。荒野與鄉村是海恩斯詩歌靈感的來源。在《寓言與距離》(Fables and Distances,1981)中,海恩斯說:“多年以前我開始了解鄉村,并盡量深入地居住其中,結果就是我將那種生活知識變成一部書。作為一個作家,我只能做這些。最后,我無法將藝術與自然分開,將鄉村與寫作分開。它們之間相互依賴,運氣好的話就會形成好作品。”〔6〕
二、看向土地、看向歷史:反對自我中心的內省
海恩斯的荒野生活不但給予他詩歌創作的靈感,而且也促進了他獨特詩學思想的形成。由于常年生活在阿拉斯加荒野,比起一般的現代詩人,海恩斯更加直觀地感受與了解大自然的奧秘與偉大,認識到環境與人類之間相互影響,要想更好地認識自我、了解自然,作家們必須根植于某個地方,通過接近“那堅硬的、無法簡化的自然事物的世界”〔7〕,從而讓自己的作品更有意義、更加接近真理。海恩斯認為,作為詩人應當看向歷史、看向土地、看向前輩,就像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弗羅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威廉斯(Williams Carlos Williams,1883—1963)等就是這樣一批往外看的詩人,而當代詩歌衰落的原因是因為部分作家不再往外看,一味地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內省,比如普拉斯(Silvia Plath,1932—1963)、塞克斯頓(Anne Sexton,1928—1974)、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等自白派詩人都滿足于一些機智的俏皮話和草率的意象①海恩斯多次在其散文中表達過這樣的意見,可以參考Living off the Country:Essays on Poetry and Plac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1出版。。
在海恩斯看來,詩歌應當與地方結合,但并非表面上的結合,并非那種大學生們關于鄉村與農場發出的幼稚的呻吟,而是應當通過詩歌的聲音、意象等,以回憶的方式體現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讓它顯得非常隱蔽同時仍然可以辨認。詩集《冬日消息》《二十首詩》(Twenty Poems)中的詩歌就是根植于理查遜外圍的生活,其中很多詩歌都是基于海恩斯的親身經歷,他通過對自然的觀察與對世界的思考,用簡單而樸素的語言,借著夢幻般的意象,將讀者帶入一個似曾相識的如夢之境。影子、寒冷、黑暗等是海恩斯詩歌中常常出現的意象,加上他那簡樸至極的詩歌語言,以及清靜得近乎飄忽的音響,詩歌生動而形象地展示了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薄暮中,/河中的島上,/天不是太冷,/我要等到/月亮上升,/便張開翅膀滑翔/與之相遇”〔4〕3(《如果貓頭鷹再次叫喚》1~7行)。
海恩斯主張的詩歌與地方結合,不僅是描繪上的結合,更是精神上的契合。在他的詩歌中,海恩斯一方面通過意象、聲音等效果使詩歌中的地方極具特色、辨識度很高;另一方面,他還擅長以不著痕跡的手法,將讀者帶入到一種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理想狀態,深刻體會某一特定地方(比如阿拉斯加)對人的影響與改造作用——自然使人更加深刻地認識自我,尤其是對人類自然屬性的深刻理解。比如詩歌《如果貓頭鷹再次叫喚》中的貓頭鷹(也可能是人)與月亮似乎在進行一種本能的溝通,詩歌呈現出一個原始的世界,在這里人類與動物間的界限似乎是流動的。從詩歌第三節開始,原先的“我”(“I”)很自然地被“我們”(“we”)取代,然而并不說話,因為我們之間似乎達成一種默契:“當晨曦爬上/枝干/我們將無聲地分開”(21~23行)。
如果說海恩斯在荒野的獨特經歷讓他確立根植地方的詩學觀,那么他向前輩學習的過程則發展出他重視歷史與傳統的理念。海恩斯習慣于以歷史的眼觀來看待問題、觀察事物,擅長將傳統與當下融合,而荒野自然則成為這一融合過程的黏合劑。對海恩斯形成主要影響的現代詩人主要包括他的前輩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和自然詩人羅賓遜·杰弗斯與埃德溫·繆爾①埃德溫·繆爾(Edwin Muir,1887—1959),蘇格蘭詩人。。作為戰后的美國詩歌之父,威廉斯非常看好海恩斯并寫信鼓勵和贊賞他的詩歌,而海恩斯也非常看重威廉斯的鼓勵,他珍藏著威廉斯給他的一封鼓勵信(1953年)②威廉斯給海恩斯的鼓勵信可以在《漸進的黃昏》(A Gradual Twilight)中讀到,其中威廉斯稱贊了海恩斯的詩歌節奏:“讓你出眾成為詩人的是那不受影響的節奏感,和你將之聰明地運用并使之成為你寫作的有機部分。”,就如當年惠特曼珍藏愛默生的信件一樣。而杰弗斯與海恩斯之間似乎更多的在于他們之間詩歌詩學的繼承關系。在海恩斯的散文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杰弗斯和繆爾這兩位荒野作家,這兩位作家除了都是出生于1887年之外,從背景到經歷似乎沒有什么相似之處,不過他們的詩歌與作為詩人的命運倒是非常相似。他們在詩歌中都擅長展開神話想象,運用經典、《圣經》詞匯來表達人類的經歷;他們都書寫大自然的偉大力量;他們都是典型的個人主義,因此認為有智慧的讀者不一定是教授,因而在其有生之年都被學術圈所忽視。
海恩斯對于他們的繼承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與他們一樣,尤其與杰弗斯相似,海恩斯通過親歷荒野獲得靈感,并以荒野為中心和主題進行詩歌創作;另外,海恩斯從杰弗斯和繆爾身上學到從傳統與經典中汲取營養,并融入自己在荒野自然中的獨特體驗,從而形成一種超越現代主義美學框架的個人風格。除了在杰弗斯詩中找到了偉大的主題,學會像他那樣如預言家般地關注世界與人類,海恩斯還在杰弗斯那里發現了一種獨特的品質,那就是他的詩歌似乎不是對設定的讀者或者觀眾來說的,他的聲音好像是個人的又好像是公眾的。我們讀詩時,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詩人在向自己或另一個詩人說話,或是向詩歌的讀者群說話。當然,這種理解并沒有錯,但是這種想法就無形中限定了詩歌。而杰弗斯就通過他那種類似戲劇語言的方式來解決了這個問題,令他在詩歌中的聲音既具有權威性又不受特定觀眾的限制。海恩斯似乎也想模仿這種做法,他的詩歌《在理性的睡眠中》(“In the Sleep of Reaso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然,海恩斯還不能像杰弗斯那樣成為一個戲劇詩人,他的詩歌大部分還是沉思,角色和敘述的部分較少。因此,相比杰弗斯那種史詩般的敘事詩,海恩斯的詩歌更加顯得簡潔而直接,就如他所生活的阿拉斯加冰天雪地般透明、簡單但又令人深省。
不論是根植地方,還是重視歷史與傳統,對于海恩斯來說,最終的落腳點都在于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上。海恩斯孤身一人在阿拉斯加冰天雪地長達十幾年的生活,不僅造就了他獨特的詩歌風格,更是他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一理想的生活實踐。他的行為與他的詩歌都同時向世人說明:人類只有回到自然的懷抱才能成長,增加智慧,變得更加寬容,不再以自我為中心。在海恩斯看來,自白派詩歌就是自我中心、自我內省的典型。20世紀60年代,自白派在美國如日中天,詩人坦然暴露內心深處隱藏的一切,即使是自私骯臟丑惡卑鄙的東西也暴露無遺,把內心最不可啟齒的那一面啟齒訴說。自白派是對新批評竭力反叛的結果,是對浪漫主義的繼承和發揚,他們關注的是“坦白地傾訴個性的喪失”,重點在于個人和自我。然而海恩斯認為,面對環境問題這樣全球性問題,作為有社會責任感的詩人,自白派這種做法雖然在藝術上能夠勇敢地挑戰傳統,但是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種對社會、對人類沒有擔當的文學終歸會銷聲匿跡,失去價值。
關于海恩斯的評價分為兩派。一方面因為海恩斯不隨大流、堅持己見的緣故,他在詩人圈子與評論圈中受到一部分人的抵制和批評,甚至在生活上也受到排擠,令他生活貧困。關于海恩斯的負面評價一方面是出于對海恩斯根植阿拉斯加、對時局與政治漠不關心的批判,另一方面主要是出于一些同行的嫉妒①同行的嫉妒主要是指阿拉斯加文學圈中,尤其是在費爾班克斯(Fairbanks)的大學寫作項目中的一些同行排擠海恩斯,不同意聘請海恩斯來學校講課。對此,當時的英語系主任羅伊·博得博士(Dr.Roy Bird)稱之為“職業上的嫉妒”,具體請參考博得博士寫給穆雷(John A.Murray)的信.Murray,John A.A Personal Remembrance of John Haines(1924-2011).The Sewanee Review,2012(1):131.。然而主流的評價還是對海恩斯的支持與稱贊,因而他也最終成為阿拉斯加的桂冠詩人。支持者從思想上與形式上都肯定了海恩斯對于當代文壇獨特的貢獻。首先,他們認為海恩斯的邊疆寫作給當代文壇注入一股冰涼而清冷的新鮮空氣,一掃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壇與政治的沸騰和灼熱,海恩斯在備受排擠、面對貧困的情況下,依然堅持自己的風格,詩中保持勇氣,可以用“重壓下的優雅”②不同時期的評論家如Peter Wild(1985),Dana Gioia(1990)和John A.Murray(2012)都曾表達過類似觀點。來形容。海恩斯根植于阿拉斯加的荒野描寫與19世紀的荒野描寫有著本質的區別,比起19世紀那種給荒野自然強加主觀情感的做法,海恩斯的荒野體驗更多的是融入環境、被環境改造和影響。
從形式上來看,海恩斯的詩歌清新、明了,但同時又具有一種朦朧的夢幻性質與東方氣質③有眾多評論家提及海恩斯詩歌中的東方特質,認為海恩斯受到諸如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等東方文化的影響,主要代表人物有Robert Hedin(1983),John Knott(2006)和Marc Hudson(2009)。,這令他的詩歌既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同時也兼具深度與美感,因為海恩斯總是試圖在經驗的表象下尋找原型,往往通過夢幻般的氛圍來消解現在與過去之間的距離,從而暗示一個經驗的普遍性。海恩斯獨居荒野的體驗令他經歷荒野生存的困難之外更要經歷心靈的抗爭。某種程度來說,他經歷的是一種在荒野條件下如何保持人性的抗爭,因此在他看來,在阿拉斯加居住就是“一種與世界重新接觸的方式”〔8〕,給人們提供了重新思考與生活的全新視角。一開始海恩斯是一位自然詩人,但是接著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具有廣泛智慧的詩人,他的主題是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體現在經驗中的精神聯系,他給人們提供了一種真正的西北觸角,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神話詩學〔9〕。
三、獨特的“夜晚視角”:詩人的隱身
除了強調非自我中心地往外看,重視詩歌與地方的結合,海恩斯的荒野生活還令他形成了獨特的“夜晚視角”(night vision)。所謂“夜晚視角”其實就是強調觀察主體的側面,通過感覺它的整體和運動來進行觀察。對此,海恩斯曾經在他的筆記中專門談論,指出這種視角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個人的凝視……這種凝視不是來自他的雙眼而是來自他內部的某個點”〔10〕。詩集《二十首詩》就是運用這種夜晚視角的典型。當你閱讀其中的詩歌時可以感到,詩歌的力量神秘地走向你,就走在你的意識的邊緣,而詩人就站在詩歌的旁邊,他的形象卻幾乎是不可見的。
詩歌《冬日之光》(“A Winter Light”)與《隱士生活》(“The Hermitage”)就是很好的例子。《冬日之光》短短三節,一共十二行,展示了一種靠著史前原始直覺的力量在荒野生活的一幕:“燭光或是篝火旁/你的臉帶著神秘/它曾經充滿巖洞/顏色來自無法忘卻的野獸”〔4〕76(8~12行)。詩中敘述者的白天意識與其夢幻意識互相碰撞,產生一種聲音上的歧義,讓我們人類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并分享動物與植物的世界。而《隱士生活》則更加強調了孤單與寂靜的力量:“沒有人來看我,/但我聽到外面/爪子刮擦,/與溫暖而好奇的呼吸聲……/曾經在一陣奇怪的寂靜中/我感到非常靠近/一個人類心臟的跳動”〔4〕78(10~16行)。詩中的隱士不僅用雙眼觀察世界,更多的是憑著感覺,加上想象來感受周遭的事物,他那一陣陣凝視加上飄忽不定的視角,將一個隱士的深層感受表達出來,并傳遞給讀者。
“夜晚視角”讓詩人在詩歌中隱身,將讀者推至詩歌場景的中央,得到如親身經歷般的感受和理解,詩歌《蒼鷹》(“The Goshawk”)就是很好的例證。詩歌從“我”的講述開始,像是詩人要講述自己在冰天雪地的故事:“我發現自己獨自一人,/寂靜的嚴寒中/柔軟的皮草貼在臉、腳”〔4〕79(3~5行)。在接下來的7行中詩人似乎很自然地繼續講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當讀者讀到詩歌最后一節時,會突然發現詩人不知在什么時候消失不見了,讀者成了故事的中心,感覺自己站在了冰天雪地之中,成為蒼鷹的盤中餐:“小兔子,你又流血了;/帶著由火而生的古老激情/蒼鷹以你怯懦的心臟為食”〔4〕79(13~15行)。整首詩歌并不長,一共15行,然而正是在這短短的詩歌中,海恩斯自然而隱秘地完成了視角的切換。
這種自我隱退的“夜晚視角”源于詩人對時間概念的重新解讀。海恩斯在荒野中將時間與空間混合交融,其詩歌表現出人與自然混為一體。來到阿拉斯加那冰天雪地的荒野,海恩斯感受到時間的變形。在這里,時間不再是文明社會中那樣的線性流動,取而代之的是時間變得與空間類似,成為一種往復的循環。就如海恩斯在《星,雪,火》的前言中所言:“這本書是關于時間的——是關于人的時間感以及某些事情發生的時間。這個時間內、外之旅,無法以歷年的任何總數加以適當的表達。”〔11〕
海恩斯這種關于時間的體驗讓人聯想到史前人類對于時間與空間的混淆。美國當代生態哲學家梅克斯·奧斯奇拉杰(Max Oelschlaeger)在其著作《荒野的概念》(The Idea of Wilderness,1991)中指出,在農耕年代之前的史前年代,人類對于時間與空間沒有明確的概念,他們生活在荒野中,本身也是荒野的一部分〔12〕,他們的生活與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如動物般地生活,他們從來不會過多地采集或獵取事物以備不時之需,因為他們心中并無過去和未來的時間觀念。而關于荒野概念的形成,則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當人類進入農耕時代,生活方式由采集與狩獵為主轉變成以種植、牧養為主時,荒野自然逐漸讓步成為人類的生活資料和耕作對象,人類也逐漸從荒野自然中脫離出來,因而形成了荒野自然與人類社會的二元對立的概念。
生活的環境似乎對于海恩斯的創作有很重要的影響,某種程度來說,正是阿拉斯加的荒野造就了海恩斯獨特的“夜晚視角”。就如杰弗斯在加州卡梅爾海岸的石屋、鷹塔和海洋成為其詩歌創作的源頭,卡梅爾海岸具有如《荷馬史詩》中伊薩卡般的性質令杰弗斯的詩歌充滿古典史詩的意味,同樣,海恩斯所選擇的阿拉斯加理查遜外圍也是他創作的搖籃和靈感的源泉,而這片冰天雪地的荒野也賦予了海恩斯獨特的詩歌風格——直接、簡潔、透明而又深入刺骨。海恩斯通過自身親歷荒野的體驗,在現代文明發展到極致的20世紀重新體會到史前人類那種與荒野合一的感受,并通過他的詩歌和散文將之表述和傳達出來,給現代讀者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心理體驗與感受。在荒野人們會變得更加敏銳,更加注重感受而非理性,荒野可以喚起人性自然的一面。海恩斯本人也多次談到他在阿拉斯加的經歷對他的重大影響,甚至認為那是令他重生之地。在《預言與距離:新散文選》(Fables and Distances:New and Selected Essays,1996)中,他再次說道:“我對于這一地方的喜愛是我生命中最古老和最深處的東西。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在23歲重生”〔6〕。
“將生活經歷與(宗教)情感結合在他的散文和詩歌中,這是他對于環境文學的一個有價值的貢獻。”〔13〕海恩斯在阿拉斯加荒野深處二十多年的生活經歷既造就了他獨特的詩歌風格與詩學思想,也影響到他的詩歌生涯與被接受過程。他反對以自我為中心的內省式詩歌,堅持看向土地、歷史與前輩的外向詩學,他提倡將詩歌與地方相結合,以及他獨特的“夜晚視角”等,某種程度都與他在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經歷的、如原始人類般的自給自足式的生活密切相關。而他的詩歌被接受過程更加明顯地反映出阿拉斯加荒野生活的重要影響。海恩斯了解他生活的社會背景,知道他的作品在有生之年難以得到廣泛的認可,但是他愿意接受他的命運,那就是作為一個作家在生前被忽視,死后其名聲卻與生前被忽視的程度成比例地增長。事實果真如此,在他有生之年,海恩斯的詩歌雖然具有廣泛的讀者,也得到一些重要獎項,但在詩評圈受到的待遇與其精湛的詩歌毫不匹配,不過在他去世后的幾年間,他的詩歌得到越來越中肯的評價,受到詩評圈與讀者的雙重歡迎。就如評論家穆雷(Murray)所說,如若將文學界看成一個生態系統,那么它也會內部形成一系列的生態位,每過一代都會有新的個人將之填滿,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海恩斯與包括惠特曼在內的幾位前輩填滿了同一個生態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