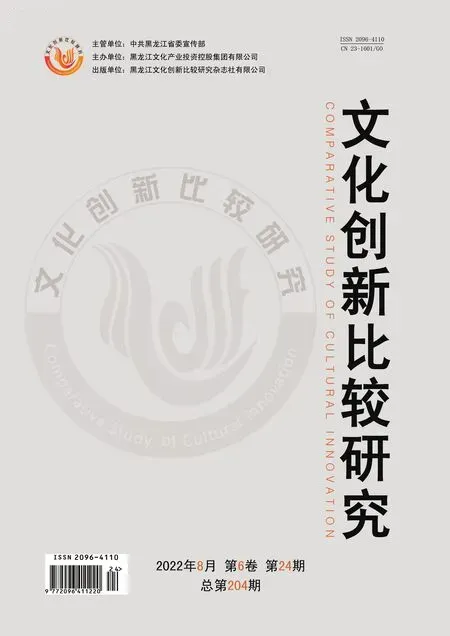《12個溫柔的日本人》與限定時空式電影
李昀育, 周賜勇
(1.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2.重慶市渝北區黃炎培中學校,重慶 401120)
縱觀世界電影, 有這樣一類電影常常能掌握保持觀眾觀影注意力的密碼: 人物被囿于限定的封閉空間中, 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解決某一問題以完成某種任務,以此離開所在的密閉空間,回歸現實生活秩序。 這類影片通常被稱為“限定時空式電影”。
在此,首先需要對“限定時空式電影”這一概念做出界定。 限定時空式電影,顧名思義,是指事件的主要矛盾發生在一個限定的時間、空間內的電影,以封閉的空間和限定的時間為主要特征, 主要發生在懸疑類型電影中。 “劇情主要或頻繁發生在一個或多個封閉的空間中,此空間社會職能不完備,外部力量難以及時介入,法律和普世道德約束暫時性缺位,人物必須依靠自身或封閉空間內集體力量, 在限定時間結束前探明真相,達成目標。 ”[1]
雖然目前學術界還尚未有對“限定時空”模式具體起源的考證, 但限定時空式電影也是一種較為接近經典戲劇習慣“三一律”的電影形式,因此本文認為,限定時空式電影繼承了戲劇的敘事常規方法。布瓦洛將“三一律”概括為“在一天、一地完成一件事,一直把飽滿的戲維持到底”,即一出戲所敘述的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地點在一個場景,情節服從于一個主題。限定的時間與空間,導致了這類影片具有強烈的舞臺美感,以及豐富的對白推動懸念敘事,而電影《12 個溫柔的日本人》,就屬于本文所討論的限定時空式電影。
1991年日版《12 個溫柔的日本人》是由中原俊指導,三谷幸喜編劇的推理喜劇,承襲了美版《十二怒漢》的經典故事內核:陪審團12 人對命案進行激烈討論并對被告是否有罪得出一致結論。 《12 個溫柔的日本人》以假設日本存在陪審制為前提,結合了日本文化,從情節、人物對美版進行了全方位的本土化改造,完成了跨文化的文本變奏。
1 限定時間與空間
限定時空式電影最為突出的就是對限定時間與限定空間的組合運用, 規定的時間與封閉的空間是限定時空式電影的基本屬性。
限定的時間, 指的是影片中事件開展的時間受到限制,矛盾需要在規定的時間之內得到解決,片中人物情緒也會因為緊張的時間受到波及, 從而加速人物負面情緒的爆發,增加了影片的緊迫感。時間同時也是人物動機的催發劑, 封閉空間中的人物會因為限定時間而做出行動。 《12 個溫柔的日本人》基本遵循了“三一律”的“一天內”時間觀念,陪審過程盡管一波三折但終究在一天內完成了決議。 影片中第一次表決結束后,副陪審長以等外賣為由,提議進行再一次的討論,陪審員們才留下來,由此才有第二次表決情節的出現, 案情討論才能繼續開展下去,“等待外賣”這一限定時間推動了情節從“無罪”向“有罪”推進。 一般來說,精準的限定時間會加劇片中人物迫切完成任務的急切心情, 例如倒計時會催發人物行動,雖然《12 個溫柔的日本人》并未嚴格表明會議結束的限定時間, 但絕大多數陪審員心中都有一個“潛在的”限定時間,那就是以最快速度結束決議,因此, 離開審判的封閉空間是片中人物進行投票表決的心理動機,以求得盡快回歸正常生活秩序。
限定空間,又稱封閉空間,是指影片主要矛盾的發生地是一個與外界遠離且相對封閉的敘事場景,是影片中最重要或唯一的場景, 主要矛盾沖突和重要人物的行動都在這個空間中展開,如熊佛西所言:“地點的統一,就是說,一個劇本不管幾幕,應該發生于一個地點……所以嚴格說來, 一個戲劇的動作最好發生于一間房內”[2]。由于空間的封閉性,外部力量難以干預,內部人物的行動也受極大限制,主角們因各種原因而不得不停滯在同一空間中, 從而將空間內部人物的心理與人性逼向極致。表面上,封閉空間阻礙了敘事向外延伸發展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封閉空間卻能放大敘事的張力, 使得人物之間交流更加密切,關系更加緊密,迸發出新的敘事活力。 封閉空間在電影中多為密室、飛機、孤島、荒野小鎮等場景。電影《12 個溫柔的日本人》除了進場出場外,影片的主要情節幾乎全部在會議室這一封閉空間內發生,封閉的會議室是唯一的敘事空間。 “但其有限的空間,及其隔離性,也時時刻刻提醒劇中人物在沒完成議題任務前無法走出去, 這一點也具備引起觀眾注意的能力。 ”[3]例如,陪審還未結束時,事務纏身的公司職員欲離開陪審廳,遭到安保拒絕,內部人物被強制滯留于封閉空間內,自由進出受困,直到任務完成才能離開。 并且,得益于場景的重復出現,封閉空間更能將觀眾帶入這類封閉空間產生的張力之中。
2 限定事件與有限人物
限定事件與有限的人物是限定時空式電影的附屬特征。
“三一律” 戲劇規律要求劇作僅敘述一個事件,影片《12 個溫柔的日本人》正是效仿了這一戲劇理念, 主題情節即討論審判中的被告是否有罪這一唯一議題。 影片伊始就對唯一議題“被告是否有罪”進行了表決,并指明了12 名陪審員若意見不一致判決便不能成立的關鍵前提, 借無罪方代表狩田之口向觀眾交代了案件大致情況:被告是一名25 歲的單親母親,被害的前夫欲與被告復婚,但二人在路邊發生爭執,結果男人被貨車撞死,被告主張自己是正當防衛,導致男人被車撞死。但路過的老婦與貨車司機都間接指出這一案件并非是意外, 老婦堅稱自己聽到了被告對被害人說了“去死”,貨車司機也聲稱按了喇叭警告,并看到了被告將被害人推向了車前。但身份各異的12 名陪審員都有各自的觀點,意見并未達成一致,故而無法做出判決。 看似混亂的言語辯駁,實際上都圍繞著“是否有罪”這一核心問題展開,觀點相悖引發的爭論有助于陪審員們向判決結果靠近,從而合力促進事件發展。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所謂‘復雜的行動’,指通過‘發現’或‘突轉’,或通過此二者而到達結局的行動”[4],其中“‘突轉’指行動按照我們所說的原則轉向相反的方面”。 美版沒有什么突轉,全憑方達一己之力扭轉乾坤。 而《12 個溫柔的日本人》的案件分析經歷了多次突轉, 巧妙運用細節設計,12 人在推理中不斷發現原來知道但不以為然的線索。 12人從最初因同情,未經討論而直接票選出“無罪”,但因1 號陪審員提出“想跟大家徹底討論一下”案情分析才由此開始。 咄咄逼人的1 號質問其余陪審員們為何認為被告無罪, 并以案發時在場的證人的證詞來支持自己的推斷,但并未獲得其余人的支持,甚至在二次投票時造假,但討論并未因此結束。在眾人欲起身離開時, 西裝革履的9 號為法理站出來支持1號的“有罪論”,二人開始把案情進展方向指向“預謀殺人”,同時9 號審判員以頗有話語權威的姿態使得部分人態度漸漸偏向“有罪方”,這時,情節已推進到“有罪”與“無罪”兩方的激烈辯駁,矛盾越加集中。假扮律師的演員提出了把“預謀殺人” 降為“過失殺人”,既解決了“無罪方”擔心判處死刑的內疚,又滿足了“有罪方”懲惡揚善的法理心,卻就在再次投票時,4 號依舊堅定“無罪”觀點,不愿向“過失殺人”妥協,“無罪方”通過系列細節逐漸推倒證人的證詞,最終全員一致得出“無罪”的結論,還是回到了開始時“無罪”的原點。通過關鍵的細節舉措,達到多次顛覆性的反轉,恰好滿足觀眾觀影體驗,使觀眾切身感受身處案件中心的快感。
編劇三谷幸喜被譽為“日本平成喜劇之王”“日本國民喜劇大師”,可以窺見他在日本喜劇界的非凡地位。 《12 個溫柔的日本人》是他的轉型之作,標志著他正式以電影編劇的身份進軍電影界。他擅長“呈現一派熱鬧而有趣的世俗斷面”[5], 聚焦于平凡市井小民的生存處境和人生價值,“那些為了生計而不懈努力的平凡人, 他們多樣的人生才會讓人覺得精彩有趣”[6], 用溫和幽默的喜劇態度帶領觀眾認識日本社會現實。 該片開場設計也十分精妙,僅用“點外賣”這一個情節就交代了人物的各自不同的個性,以鋪墊接下來人物因個性做出的行動,開頭設置了3 號陪審員分發栗子的細節, 儼然打破了陪審廳定奪判案的嚴肅氛圍, 向觀眾呈現了獨具日本市井煙火氣的陪審討論現場,與美版悶熱、壓抑的討論氣氛形成了鮮明對比。
《12 個溫柔的日本人》 局限于限定時空式的模式下,封閉的難以自由進出的空間,就決定了出場人物的有限性, 且片中人物只得通過犀利的言語和荒唐的邏輯,為影片帶來喜劇效果,人物的丑態成為該片主要的笑料來源,12 名性格迥異的陪審員承擔了制造笑料的任務,揭露了日本“溫柔”面具下的眾生相:1 號,即陪審員長,為不讓自己間接“殺人”,所以認為被告無罪;2 號,將被妻子拋棄的憤懣投射到被告身上,也是第一個主張被告有罪的人;3 號,自帶零食來開會, 并在開會時吃冰激凌、 喝酒的中年男人;4 號,唯一的一位自始至終,因為第六感而主張被告無罪的陪審員;5 號,愛記筆記,連花邊新聞都會記在記事本上;6 號,不關心案情真相,一心只想盡快回到公司;7 號,將自己找不到伴侶的情緒遷怒于被害人,認為被害人罪有應得,并因為外貌而同情被告;8 號,無知并愛附和的家庭主婦;9 號,喜歡掌握話語權,十分自負;10 號,搖擺不定、懦弱的老婦,點飲料時做了三次決定;11 號, 演員假扮律師來爭奪話語權;12 號,副審判長,試圖掌握會議領導權。
《12 個溫柔的日本人》 新增加了3 名女性陪審員角色,這是4 個版本中絕無僅有的,盡管3 位女性帶有強烈日本男性視角下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但依舊是“令人稱贊的一步”。 借用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中的一段話來概括片中12 名日本陪審員的民族性格: 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 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極度恭順又極度討厭被使喚,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
3 多聲部復調對話
羅伯特麥基曾指出:“電影也不是戲劇。 電影是看的, 戲是聽的……戲劇作家可以編織精巧而華麗的對白——但銀幕作家卻不能。 ” 認為銀幕對白是“日常談話的形式, 但其內容必須遠遠超越尋常”[7],但限定時空式電影就常常采用復調敘事, 全憑內部空間中有限人物間的對白推動敘事,依靠“經過精巧編織”的人物對白,完成關于人性的思辨。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借用音樂術語, 提出了復調小說的文學理論:“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 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把現實中完全分割開來的互不相通的那些思想和世界觀, 聚攏到一起并讓它們互相爭”[8], 作品中有多個不同且各自平等的聲音,即多聲部,并倡導對話是復調的核心。 復調理論同樣也可以從小說運用到電影藝術領域。 限定時空式電影中, 人物強有力對白成為此類電影的特質,多聲部復調對話是推動敘事發展的主力,具備產生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雙重功能, 語言表達更能將人物從有限的時空中解救出來, 塑造出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 并將限定時空式電影強沖突的優勢發揮到極致。
《12 個溫柔的日本人》 可作為其中一部經典案例來分析。 限定時空下12 名陪審員激烈地辯駁,詮釋了巴赫金所說的多聲部對話:“所有的主人公都激烈地反駁出自別人之口地對他們個人所做的類似定論。他們都深切感到自己內在的未完成性……”陪審會議的中心是討論、說服,人物之間的辯駁構成了影片主要內容,閆懷康引用傳播學中“議程設置”理論假說來概括以“表達”為核心的類型電影。 12 名陪審員性格各異,1 號陪審員是電影的核心人物,始終堅持被告有罪,在9 號牙醫的支持下,部分陪審員轉移到了有罪的觀點, 從而形成了有罪與無罪的兩方勢力,雙方各執一詞,平等表達各自的觀點,討論推理案情,具備多聲部復調對話的特質。因為置于封閉空間和有限時間之下,言語交鋒是引發矛盾的關鍵,影片中的每一句針鋒相對都是電影創作者為敘事主題精心設置的,而每一次交鋒關注的是“言語背后的人文關懷”,12 人帶著強烈的目的性進行著有意義的討論。
4 結語
大衛·波德維爾將封閉空間概括為“奇緣和狹小的世界”,并引用肯尼斯·泰納的一句話:“在本世紀,沒有什么文學手段能為這么多人贏得這么多。 將一群人團結在人為的環境中——一家酒店、 一只救生艇、一架航班——之后,幾乎是自動地,你就獲得了成功。”[9]若將肯尼斯·泰納地對好萊塢敘事方法的概括移用于限定時空式電影, 就會發現這其實同樣適用于限定時空式影片。 限定時空式電影通常能在有限的時空內,設置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論題,利用錯綜復雜的人物及其尖銳話語, 加快故事進行的節奏,將矛盾沖突和人性的揭露淋漓盡致地呈現于銀幕,由此爆發出強烈的戲劇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