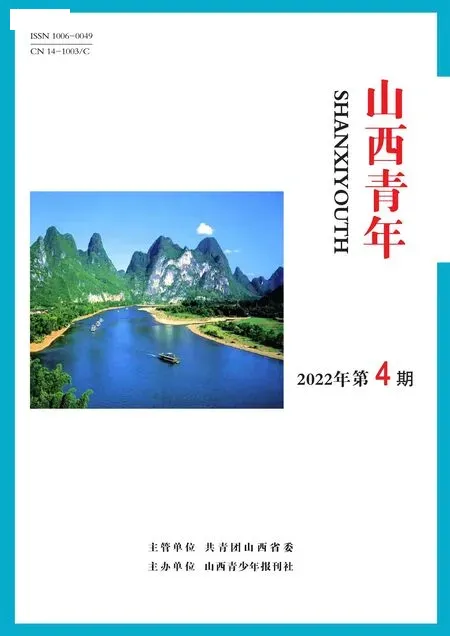王堯《民謠》的文學異質(zhì)性
張亞萍 曹瑞雪
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淄博 255000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新世紀文學”逐步成為一個外延明確的概念,即2000年以來的中國文學。改革、發(fā)展、智能、數(shù)據(jù)、矛盾、危機等等元素相互交錯交融,使得一種既承接著現(xiàn)代性又粘連著歷史性的新世紀素質(zhì)逐漸形成,并且在逐日得到強化與突出。在這種新質(zhì)氛圍的影響下,文學家們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性書寫,在文學文本的呈現(xiàn)方面,則體現(xiàn)出一種鮮明的異質(zhì)性特征。
一、“我”與“歷史”的重建意識
“文學既不是政治觀念的注腳,也不是思想發(fā)展史的解讀。文學就其實質(zhì)而言,是形象和意象的結(jié)合,作家主體意識及社會現(xiàn)實的結(jié)合與呈現(xiàn)。”[1]作者王堯在《〈民謠〉的聲音》里說過:“如果說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與‘歷史’的聯(lián)系。”這種重建意識著重體現(xiàn)在“我”與“歷史”關(guān)聯(lián)的一種主動性和選擇性。“我”并非完全按照“歷史”發(fā)展的時間脈絡(luò)進行人物發(fā)展與命運的書寫;也并非完全將“歷史”綴連到“我”的身上,然后以個人的生存境遇為中心展開關(guān)于宏大歷史的講述。“我”與“歷史”雙方之間的連結(jié)是在“相關(guān)性”意識下而產(chǎn)生的一種自然的選擇、自然的契合。
(一)革命與現(xiàn)代化的延續(xù)性
“村中有莊,有舍,舍圍著莊轉(zhuǎn),莊圍著鎮(zhèn)轉(zhuǎn),鎮(zhèn)圍著縣城轉(zhuǎn),這就是通常的社會秩序。有一天,我們村莊的秩序被打破了。”[2]這句話點出了整部小說的歷史背景,即一個秩序被打破的時代。當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安土重遷、停滯不前的秩序遭遇革命,那種穩(wěn)寂與封閉注定是要被“打破”的。小說寫的正是在這種被沖擊、被“打破”的歷史時期下鄉(xiāng)村的人與事。文本借助主人公返回少年記憶的通道打開了一個村莊的現(xiàn)代蛻變史圖,通過回憶、現(xiàn)實、夢境、幻覺、虛構(gòu)與真實雜糅交織的不同聲音呈現(xiàn)了一首多聲部式的革命史詩。
“現(xiàn)代化”的歷史視野將中國19世紀以來不斷引進和發(fā)展現(xiàn)代新的生產(chǎn)方式的過程,和這一過程里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變化正式放入了歷史考察。莊東頭那邊的“廣播”在鉆井機器的轟鳴聲中再也聽不見了,稻床在脫粒機的工作聲中被放置一旁,莊前大橋上乘涼的人群待在家中吹著空調(diào)的冷氣,曾裸泳的河流在工廠廢氣廢水的排放中發(fā)爛發(fā)臭……現(xiàn)代文明的血液不斷地融入和內(nèi)變著這座古老鄉(xiāng)村的內(nèi)核,時代殘存的瘢痕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漸漸淡化,整座村莊也在改變和被改變中起伏。作者的筆調(diào)審慎又理性,他站在歷史圈子的外圍,既看到了這場大運動里的“收益”,也指出了這個過程中的“虧損”,表現(xiàn)出當代知識分子對于中國“革命”與“現(xiàn)代化”復(fù)雜性的深入理解和關(guān)懷,呈現(xiàn)出作家與現(xiàn)代中國變革之間少有的互動景觀。在那座村莊里,革命與現(xiàn)代化都是綿延不斷的存在。社會文明在向前發(fā)展的過程中,不斷出現(xiàn)新舊介質(zhì)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而它們之間或消解或斗爭的狀態(tài)也將繼續(xù)持續(xù)下去。
(二)碎片化與整體化書寫的平衡性
小說的敘事結(jié)構(gòu)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散碎”且“凝聚”的特征。作者通過回到過去和呈現(xiàn)當下的雙線并軌式的交相敘述話語,建構(gòu)起一個分層復(fù)雜的事件網(wǎng)絡(luò)。不同的人物個體和歷史片段在主人公王厚平的回憶中,輪番上場。它們看似并未遵循任何嚴格的時間或者空間順序,只是隨著主人公意識的流動隨機跳出。實際上,這些碎片化的呈現(xiàn)邏輯恰恰是整個文本內(nèi)在的核心敘事框架。所有記憶碎片共同作用,不僅勾勒出了相關(guān)歷史背景的大圖景,理清了事件的發(fā)展經(jīng)過,還描摹出了處于社會洪流中翻騰起伏的個體人物的人生世相。
“許多人都向往回到失去的童年世界中追尋記憶中的生活殘片,或表示依戀,或表示憤恨。只是藝術(shù)家更執(zhí)著于在夢中和神經(jīng)疾病中回顧,因為藝術(shù)可以提供回歸過去的最佳途徑。”[3]小說巧妙地對回歸過去這一環(huán)節(jié)進行了藝術(shù)策略的加工處理,通過充滿個人特色的童年視角,夾雜著神經(jīng)衰弱病理的加持,借助囈語般的講述,將大量歷史中出現(xiàn)的片段浮現(xiàn)在現(xiàn)實的紙上。但同時,各個碎片化片段又以有機的排列方式,以極強的自洽性鑲嵌在整體的書寫過程中,作品整體的展開像是一張充滿玄機的拼圖,看似分散,實則具有很強的內(nèi)聚性。每個波瀾不驚的小故事以其真實性和不加雕飾地呈現(xiàn),與整體書寫達到了一種碎片化和整體性相統(tǒng)一的平衡狀態(tài)。
二、從“小把戲”到“大結(jié)構(gòu)”的敘事藝術(shù)
(一)形式實驗的探險與“小把戲”
福柯認為:“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chǔ),是任何權(quán)力運作的基礎(chǔ)。”“小說中的空間是重要的敘事承載體。空間的外延可以不斷擴大,直至無限廣闊,其內(nèi)涵可以不斷細分,直至個人知覺視域局限下無限可分性的極限,就像一張紙被撕裂成為無數(shù)的碎片。”[4]空間是人類感知世界和體悟世界的重要因素,平面文本通常借助不同多維空間的塑造,從而增加審美內(nèi)蘊和藝術(shù)感受的立體張力。小說《民謠》尤其擅長對本土空間的藝術(shù)重構(gòu),通過詳細的方位介紹和布局描寫,凸顯出作品鮮明斧刻的畫面感。“莊子的東西兩側(cè)分別是東泊和西泊。如果用線條表示,這個莊子是在南北兩條線、東西兩個圓圈之間。”“莊后的河也就是北河,西邊融通了西泊的北水面,東邊拐了個彎子向東北,流到吳堡大隊,拐向東南,便是東泊。”[5]……像這樣關(guān)于詳細描寫空間的情節(jié)片段在不斷拼貼、交錯的過程中逐漸組合出一個立體、豐滿的江南水鄉(xiāng)模樣。在彎彎曲曲的河泊交界處,有一塊土地忙碌蓬勃、生機煥發(fā),人們在河里做工,從橋上走過,在田埂上看鳥,有時候蹲在碼頭上用淘籮戲魚,有時候趴在土墻上捉蜜蜂。作者真摯且具有地方感的敘述將發(fā)生在不同地點的片段關(guān)聯(lián)起來,讓各個情節(jié)部分之間具有了空間關(guān)系中的聯(lián)結(jié)點,點繪出了一幅展開著的立體圖景,給了小說橫向上敘事發(fā)展的動力。除此之外,作者還在雜篇中將書信、新聞報道、政治通報、申請書等材料拼貼進來,將這些看似仿佛獨立于正文之外的靜態(tài)書面材料與作者不斷流動著的回憶性意識材料相嵌合,形成了“動態(tài)”與“靜態(tài)”的兩種組合形態(tài),彼此穿插,彼此呼應(yīng),共同構(gòu)成了橫縱不同空間維度的敘事結(jié)構(gòu)。
(二)形式實驗的冒險與“大結(jié)構(gòu)”
形式和內(nèi)容共同構(gòu)成一個整體,“無論是活的動物,還是任何由部分組成的整體,若要顯得美,就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即不僅本體各部分的排序要適當,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體積,因為美取決于體積和順序。”[6]在《民謠》中作者嘗試了“形式”如何成為“內(nèi)容”這一形式實驗,將“雜篇”和“外篇”加入整體內(nèi)容中,是一次充滿冒險精神的文體嘗試。
《民謠》是一部村莊的記憶追溯,它的基本表現(xiàn)形式是一部回憶錄,回憶的對象是一個村莊以及生活在這個村莊里的祖孫三輩,通過不同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命運走向講述著發(fā)生在這段歷史區(qū)間的歷史文明進程。但同時,這部作品又不僅僅只是一部回憶錄性質(zhì)的純小說文體結(jié)構(gòu)。“雜篇”和“外篇”作為最后附錄的小部分,內(nèi)化在小說整體的“大結(jié)構(gòu)”之中,“‘雜篇’不僅是補充了前四卷的細節(jié),它還是‘我’與‘時代’的語言生活。”“外篇”則以小說中楊老師的名義,寫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說《向太陽》,也算是了結(jié)了楊老師的一個心愿。這個部分用不同的語言敘述了小說中“圍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三、“似散實聚”的散文化意象隱喻
如歌德所說,從什么方面出發(fā)向知識和科學靠近,或者說,通過哪扇門進來,會有重大的區(qū)別。在寫小說之前,王堯素來以散文研究著稱,其曾憑《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guān)問題》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批評獎。散文清新、恣肆、漫卷、素遠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進入小說寫作的語言和體式,加之其深受汪曾祺先生作品的影響,因此在《民謠》中多次出現(xiàn)運用意象來進行深層次隱喻內(nèi)蘊闡發(fā)的現(xiàn)象。
(一)太陽:自我求索的精神揭示
先秦奇書《山海經(jīng)》中所記載的夸父與日逐走的傳說,很早地表現(xiàn)了個體對于光明追求的精神求索歷程,夸父到渴死都在追逐的太陽即是一種理想的化身,文學家蕭兵先生稱夸父是“盜火英雄”,為了給人類采擷火種,使大地獲得光明與溫暖。小說《民謠》中借“太陽”意象表征作者對時代境遇的認知與慨嘆,具有強烈的感召性和新奇性。
卷一第一小節(jié)里,“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7]小說的第一句話在開篇就奠定了小說的“調(diào)性”。用“一張薄紙”來形容太陽,一瞬間便將熾熱的意象單薄化,“墊在屁股底下”帶有些慵懶和隨性,將全文的氛圍和基調(diào)拉在一條較為“溫和”的水平起點上。卷一第十二小節(jié)里,“外公說:安葬王二大隊長時,太陽已經(jīng)落山了,他說太陽像鮮紅的血。”[8]“鮮紅的血”作為極有震撼力的意象,令人肅然生穆,深刻地暗示了王二大隊長犧牲時的悲壯,表現(xiàn)出了對于反革命力量的憤怒,同時也暗含著革命戰(zhàn)斗的艱苦與慘烈,這個基點開始上升到臨界點狀態(tài)。在卷二第十小節(jié)里,“胡若愚在夕陽下沿著石板街向西。少年將墨鏡打開,雙手扶著鏡架向西望去,眼鏡里的夕陽已經(jīng)沒有了刺眼的光芒。”[9]此時的太陽光芒與胡若愚自身的精神氣融為一體,胡若愚的政治道路出了問題,前途未卜,之前光鮮亮麗的少爺光環(huán)逐漸褪色,這個基點又開始呈現(xiàn)出一種下降的趨勢。卷四第八小節(jié)里,“陽光沒有顏色,陽光貼近大地貼近莊稼貼近少年鼓脹的胸脯時才有了顏色。陽光只有照在向日葵上時才是金子。”[10]陽光由先前的紅色逐漸褪色歸為無色,總體基調(diào)又回歸一種平緩的狀態(tài),并揭示出陽光與土地、少年和生命之間強有力的共生關(guān)聯(lián)。
(二)麥子的霉味:回望中虛幻的精神家園
在中國傳統(tǒng)的農(nóng)耕文化中,麥地承載的是一種無聲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人在麥地上活過又死去,麥地是他們的生命之根,生命之始,亦是生命之終。麥地給他們帶來生的希望,卻又不能完全驅(qū)散他們對生的迷茫。它所表征的偉大質(zhì)樸、智性深沉的地母形象便是作家隱喻的精神家園,令人神往卻又虛幻縹緲。在小說中,麥秸的霉氣是一種凝結(jié)著的精神皈依,也是一種帶有余味的舊質(zhì)符號。
卷一第一小節(jié)里,“渾濁的潮濕抑制住了麥子的霉味,陽光下,發(fā)酵出來的味道慢慢地擴散著。”“凡是空地都鋪滿麥秸,霉味肆無忌憚地沖出來,鉆進所有人的鼻孔,我們這個村子里的人在一個季節(jié)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覺。”[11]麥子的霉味是一種依附和歸屬,麥子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村莊里最為重要的生存資料,它給予生活在莊里的村民極大的安全感和崇高的迷戀感。卷三第十八小節(jié)里,“他感嘆地說:老廠長不在了。一陣風從河道上吹過來,我似乎聞到了1972年麥子的霉味。”[12]這里的“麥子的霉味”是另一種精神上的依戀,親情上的歸屬。那一年我坐在碼頭等的是外公,外公就是我在親情上的牽絆。卷四第七小節(jié)里,“在一頓晚餐上,我終于被彌漫著的麥子霉味嗆到了。”“整個村莊都發(fā)霉了,腐朽了。曬干的麥秸因為腐朽已經(jīng)斷了筋骨,我們無法再用麥秸編制草籠子。”[13]此處的霉味則是一種舊質(zhì)的象征,舊時代固有的生活秩序和生存模式所帶來的混沌蒙昧的狀態(tài),恰似作者所言的陰郁的廢墟。
巴金先生有言:“我寫作不是因為我有才華,而是因為我有感情。”人類的感情是共鳴的,帶著感情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它的調(diào)性才有可能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需要。在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急需拯救小說調(diào)性和文學性的境遇之際,王堯降低速率,減緩節(jié)奏,用十年時間、馬拉松式的寫作,以一個果決堅毅、雅致且謙遜的“回身”,重新闡釋了學者小說的寫法和意義。小說《民謠》不唯有故事,有情節(jié),更有漫漶的情緒、飽滿的情感、翱翔的情懷,其以特殊的調(diào)性為當下滯礙的小說創(chuàng)作注入了一脈新鮮的清流。同時,作品中透露出強烈的主體意識,展現(xiàn)了作者作為蘇人的氣質(zhì)和性情,不僅呈現(xiàn)了江蘇東臺本土村莊的風貌變遷,更呈現(xiàn)了歷史長河中蘊含著的內(nèi)在精神和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