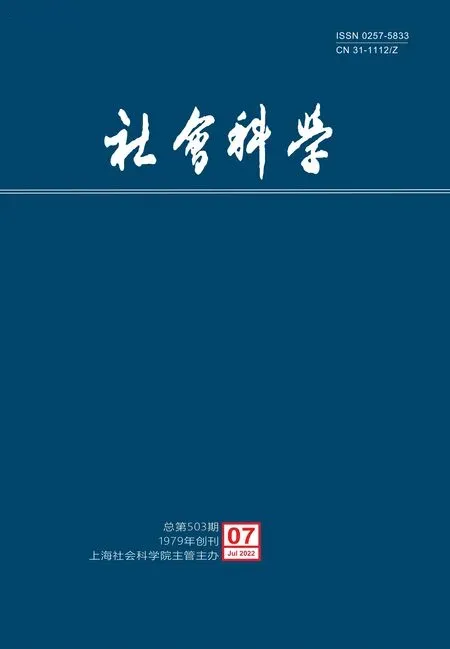智力勞動與知識價值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楊嶸均
當前,數字時代的互聯網已經成為了天然的生產場域,它不僅是“資本的場域、剝削勞工的場域,也是社會的場域、抵抗的場域和階級形成的場域”。①邱林川:《告別i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社會》2014年第4期。如果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我們發現,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相比,雖然今天的人們依舊進行勞動生產,但是勞動范式卻已經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轉型。那么,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是否仍然對這種勞動轉型具有解釋效力呢?如果有,那么是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解釋力?如果具有不完全的解釋力,那么其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和轉型?進一步,在中國的意識形態語境中,我們應該如何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來分析傳播政治經濟學中關于資本主義社會智力剝削與資本增殖矛盾運動的規律呢?再進一步,我們又應該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并進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呢?本文旨在研究上述問題,并嘗試著以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來建構知識價值理論,希冀有助于學界開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新境界。
一、發現馬克思: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商品和勞動議題的提出與爭議
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對傳播活動中商品和勞動議題展開的探討,最早可以回溯到兩位學術領袖的研究。一位是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 Smythe),另一位是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他們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斯麥茲以唯物主義的視角考察了“意識產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物質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受眾商品”理論。在斯麥茲看來,廣播和電視提供的節目是用來吸引受眾的“免費午餐”,它們不構成大眾傳播系統真正的商品,而真正的商品是受眾的注意力。斯麥茲將其稱之為“受眾力” (Audience Power)。廣告商購買受眾的“受眾力”,實際上是為了保持受眾對某一品牌的忠誠度,從而實現對這一品牌的消費。這就是“受眾商品”理論。這一理論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試圖解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傳播產業發揮了何種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拋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即“傳播這一行為,在人類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在《大眾傳播系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盲點》(以下簡稱《盲點》)一文中,斯麥茲開篇便指出: “本文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忽視了大眾傳播系統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意義’這一觀點,試圖開啟一場討論,并非做一個定論。”①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 Blindspot of Western of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1,No.3, 1977.pp.1-27。此文已經被譯介到國內。參見達拉斯·斯麥茲:《大眾傳播系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盲點》,楊嶸均、操遠芃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1年第9期。而斯麥茲對于這一爭論的回應文章,也已翻譯成中文,詳細請參見達拉斯·W.斯麥茲:《再議“盲點”:對格雷厄姆·默多克回應的回應》,楊嶸均、顧佳圓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2年第1期。確實,《盲點》一文一經問世,便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很多學者發文回應。其中,英國學者默多克(Graham Murdock)率先提出批評,認為在《盲點》一文中,斯麥茲過分強調對大眾傳播系統進行經濟分析,從而犯了經濟決定論的錯誤,這種分析本質上是“以另外一種盲點和偏見代替之前的盲點與偏見”。②Graham Murdock,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Vol.2, No2, 1978, pp.109-115。中文譯本參見格雷厄姆·默多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盲點:對達拉斯·斯麥茲的回應》,楊佳鋒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1年第11期。緊隨其后,利文特(Bill Livant)、賈利(Sut Jhally)、米漢(Eileen R.Meehan)相繼發文參與討論。他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對“受眾商品”這一概念的分析和完善上。利文特認為,默多克忽視了“受眾商品”這一概念具有的重要價值;在對大眾傳媒的研究當中的確存在盲點,但盲點并非是未能以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大眾傳媒系統,而是“以非歷史的概念描述受眾”。③Bill Livant,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3, No.1,1979, pp.91-106。中文譯本參見比爾·利文特:《受眾商品: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盲點的爭論》,楊嶸均、盧晗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1年第11期。與默多克觀點不同,利文特認為“受眾商品”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的形式只是在現代社會才得到充分發展。賈利則從“受眾勞動”的角度探討了“受眾商品”,他認為,“市場營銷和消費過程中的受眾勞動并不能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內得到證實”,④Sut Jhally, “Probing The Blindspot: The Audience Commod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6,Nos.1-2,1982, pp.204-210。中文譯本參見薩特·賈利:《探索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盲點之謎:受眾商品》,劉文祥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2年第1期。為此,他從勞動的角度去分析了“受眾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在賈利和利文特共同撰寫的《觀看即工作:受眾意識的維持》一文中,他們進一步發展了“受眾勞動”的觀點,認為在現代商業媒體的操持下,受眾的觀看活動擁有了特定的社會形式:成為商品。在他們看來,受眾的觀看行為是特殊的勞動力商品,大眾傳播系統將受眾的觀看時間出售給廣告商。⑤Sut Jhally, Bill Livant,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36,No.3,1986, pp.124-143。中文譯本參見蘇特·加利、比爾·李凡特:《觀看即工作:受眾意識的價值增殖》,陳玉佩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0年第6期。該版本作者名字的譯法與本文用字不同,但是同一作者。然而,米漢認為,大眾傳播的商品的形式“既非文化商品,也不是受眾商品,而是由收視率構成”的。⑥Eileen R. Meehan,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1, No.2, 1984, pp.216-225。中文譯本參見艾琳·R.米漢:《收視率評估產業及其制度研究路徑:大眾傳媒商品問題的第三種答案》,《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1年第11期。實際上,在斯麥茲發起“盲點問題”的討論之時,資本主義主要的傳播形式是還是電視、廣播等,尚未發展出如今天這般龐大、復雜、交互的網絡傳播系統。總之,隨著傳媒方式的變化,關于“盲點”問題的討論至今仍在繼續,而斯麥茲的分析似乎印證了數字時代的傳播現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麥茲以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在對數字時代的大眾傳播媒介進行分析時,或多或少都是在同斯麥茲進行對話。
相較于斯麥茲從理論基礎上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赫伯特·席勒則開啟了信息時代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席勒認為,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沒有一個文化空間可以存在于商業網之外”,①赫伯特·席勒:《大眾傳播與美帝國》,劉曉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9頁。通過軍事、工業、傳播與娛樂的聯合,美國強大的傳播機構與系統已經成為“美國國家權力以及擴張主義的神經中樞”。②赫伯特·席勒:《大眾傳播與美帝國》,第142頁。赫伯特·席勒對美國文化傳播霸權富有見地的分析直接影響了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擴張性市場邏輯的影響下,丹·席勒認為互聯網正在將資本主義推向“數字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的發展階段,“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與動力”。③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頁。“資本主義正在轉向數字資本主義”這一論斷已然成為今天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背景。丹·席勒的另一重要貢獻在于,回到“勞動”的概念去討論人類傳播活動,因為只有在勞動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先要有‘勞動’的存在,‘傳播’才能自由地為人類巨大而面向廣泛的符號互動潛力,劃清畛域”。④丹·席勒:《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馮建三、羅世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5頁。為此,他主張: “勞動”若要與“傳播”產生一種互動關系,則應當擺脫“勞心”(intellectual)與“勞力”(manual)的二元對立,以“生產性勞動”(productive labour)作為傳播研究的起點。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丹·席勒試圖將經濟視角與文化研究的視角結合起來。他的這一努力,為后來的學者分析傳播領域的勞動問題開啟了智識。
隨著大眾傳媒進入互聯網時代,傳播政治經濟學得到了很大發展。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致力于將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完整的學科進行構建。他對學科輪廓進行了勾勒,并且大致描繪了其理論架構。莫斯可關注到,勞動議題將會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他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中心任務之一是: “闡明傳播與文化如何成為物質實踐,勞動與語言如何相互構建,以及傳播與信息如何成為社會活動的辯證實例。”⑤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胡正榮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45頁。在莫斯可研究的基礎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對傳播領域的“勞動”議題展開了積極探索。如果說在斯麥茲所處時代“受眾勞動”還是作為一種隱喻而存在的話,那么到了當今互聯網與大眾傳媒互滲互融的時代,福克斯則是能夠直接觀察到“受眾勞動”的現實形態。在《信息資本主義及互聯網的勞工》一文中,福克斯從階級的角度提出了“知識勞工”(Knowledge Labor)的概念,他認為“在信息資本主義中,知識已經成為一種生產力”,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信息資本主義及互聯網的勞工》,陳婉琳、黃炎寧譯,《新聞大學》2014年第5期。知識勞工指的是那些“生產和分配信息、傳播、社會關系、情感以及信息傳播技術的勞工”。⑦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信息資本主義及互聯網的勞工》,陳婉琳、黃炎寧譯,《新聞大學》2014年第5期。福克斯認為,知識勞工是構成信息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積累的重要源泉。此后,他又將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應用于關于“數字勞動”的分析論證中。福克斯認為互聯網用戶所進行的“數字勞動”是一種生產性勞動,既包括硬件設備的生產、傳播內容的生產、軟件的生產,也包括“產消者”(Prosume)⑧產消者是指由于“區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分界線日益模糊”而導致消費者與生產者日趨同一。參見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35頁。另外還可參見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社交媒體中的數字產消勞動:基于資本主義時間范疇的研究》,顧佳圓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2年第4期。的生產,因而,在福克斯看來,用戶數據構成了互聯網平臺所需的商品,為獲取數據平臺為用戶提供服務。在此前提下,福克斯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來解釋信息時代的數字勞動,并試圖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應用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尤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詳細分析數字勞動的價值生產以及如何實現資本的增殖過程。盡管這一理論工作也受到西方學界諸多質疑,①例如,塞薩爾·波拉尼奧(César Bola?o)和埃洛伊·維埃拉(Eloy S. Vieira)共同撰文質疑:事實上,用戶在使用平臺提供的服務中并沒有任何實際的勞動,而真正進行生產性勞動的是“信息工程師、研究人員和許多其他類型的專業人員,他們通過統計數據、生產界面和算法,使受眾商品成為可能”。為此,波拉尼奧不贊成福克斯以“生產性勞動”來分析數字勞動,他的理由是:如果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看,那么生產勞動僅僅意味著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勞動。因此,波拉尼奧認為數字勞動研究關鍵在于分析“勞動本身的概念以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分析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之間的復雜關系”。(參見César R. S. Bola?o,“Digitalization and Labor: A Rejoinder to Christian Fuchs”, Triple C, Vol.13, No.1,2015.)而亞當·阿維德森(Adam Arvidsson)和伊拉諾·科萊奧尼(Elanor Colleoni)則明確反對運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來解釋數字勞動,理由是:在社交媒體上價值生產與生產時間沒有必然聯系,因而,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前提是不成立的。為此,他們主張在社交媒體中“價值生產越來越多地與創造和重建情感紐帶的能力聯系在一起”(參見Adam Arvidsson,Elanor Colleoni, “Value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28, 2012, pp.135-150)。但是不管怎么說,在丹·席勒研究的基礎上,上述的觀點拓寬了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勞動議題的研究視野。同時,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對于國內學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回到馬克思:國內學者對商品和勞動議題的分析
進入21世紀,中國大眾傳播系統飛速發展,學界也不得不面對大眾傳播系統發展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問題,這為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媒介環境和現實基礎。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面臨的商品和勞動議題,國內學界在譯介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不懈的探索。總體而言,學者們主張要回到馬克思,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來分析并建構中國大眾傳播系統的話語體系。
最早介紹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是郭鎮之教授。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泰斗達拉斯·斯麥茲》一文中,她系統地介紹了斯麥茲的學術研究,認為“‘受眾商品論’深刻地揭示了廣播電視媒介傳播的某種本質,但僅僅是一個方面——經濟的本質”。②郭鎮之:《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泰斗達拉斯·斯麥茲》,《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3期。劉曉紅教授著重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關系,認為“政治經濟學也應該從文化研究中獲得啟示,不要忽視人的主體性,片面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避免掉入簡化主義或機械決定論的泥沼中”。③劉曉紅:《共處·對抗·借鑒——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曹晉和趙月枝兩位學者也較為詳細地梳理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脈絡以及前沿論題,并根據中國的發展情勢預言: “隨著媒介化社會的來臨,在國家對傳播產業的改革逐步深化,電視、手機與網絡信息等新媒介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的情景下”,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會逐步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④曹晉、趙月枝:《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脈絡與人文關懷》,《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國內學界的研究熱度不斷攀升,他們的預言正在得到證實。陳世華教授則對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話語邏輯進行了分析,認為“跨學科的取向一直植根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因之中”。⑤陳世華:《博采眾長: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跨學科取向》,《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8期。當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不僅要堅持跨學科的視角,還要把握自身的研究主題。此外,馮建三、胡正榮、周延云、楊嶸均、吳暢暢、黃炎寧、姚建華、汪金漢等陸續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譯介到國內。正是在這些學者的不斷努力下,國內學界得以系統地探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深刻洞見,并不斷推動著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國內的發展。
在“受眾商品”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勞動議題上,學者們對源于斯麥茲關于“受眾商品”的相關理論以及“受眾勞動”的形式、“受眾勞動”是否生產價值等一系列問題產生興趣。其中,從理論發展史的角度,汪金漢主張在分析傳播研究的勞動議題時“有必要抓住‘勞動’這個根本,避開勞動的形式問題,而從理論層面去理解勞動在不同的媒介形態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論邏輯”。⑥汪金漢:《“勞動”如何成為傳播?——從“受眾商品”到“數字勞工”的范式轉變與理論邏輯》,《新聞界》2018年第10期。鮑靜和裘杰認為,社交媒體時代“受眾勞動”爭論的核心議題依然是“受眾勞動”是否具有生產性,并認為“受眾勞動”的生產性體現在:作為具體勞動,“受眾勞動”也是生產使用價值的,當“使用價值在未被價值關系滲透之前,不具有交換價值,不可能成為價值的源泉。而一旦擁有價值屬性,無論是非物質的還是物質的勞動都將成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⑦鮑靜、裘杰:《生產性還是非生產性:社交媒體“受眾勞動”論爭的核心議題》,《新聞界》2019年第12期。
與此同時,很多學者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數字勞動相關議題展開研究。這一方向的研究,主要以評述福克斯數字勞動理論,以及如何以數字勞動實踐發展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主。比如,燕連福等認為,福克斯數字勞動問題研究“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領域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①燕連福、謝芳芳:《福克斯數字勞動概念探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2期。蔡潤芳詳細分析了Web2.0時代數字勞動的生產邏輯,認為運用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分析“受眾勞動”的價值生產之所以合理,是因為“‘受眾勞動論’媒介批判的理論之基礎就在于能夠論證受眾勞動具有生產性”。②蔡潤芳:《“積極受眾”的價值生產——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受眾觀”與Web2.0“受眾勞動論”之爭》,《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3期。然而,也有學者對福克斯的理論提出了批評。其中,周延云、王佳亮認為,福克斯以勞動價值理論分析數字勞動固然可取,但在分析過程中以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方法論,重建勞動價值理論“必然使得以‘絕對精神’辯證法建構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內容的客觀性受到質疑”。③周延云、王佳亮:《福克斯的馬克思主義數字勞動批判理論探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同樣,在肯定了福克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入數字勞動分析這一理論貢獻的基礎上,夏玉凡批評福克斯未能正確理解馬克思關于生產性勞動的界定,而是錯誤地認為受眾生產的個人行為和數據成為商品,而事實上,“互聯網用戶的個人數據必須通過相應的算法和后臺程序處理打包變成商品之后,才能出售給廣告商”。④夏玉凡:《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數字勞動理論——以福克斯勞動觀為中心的批判性探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因此,從事互聯網數據收集、管理、分析的程序員才是數據商品的生產者。對此,陸茸也持有相同觀點。陸茸認為,福克斯的數字勞動理論有待商榷,在他看來,用戶活動產生的數據雜亂無章,并不具備價值,只有經過處理分析后這些數據才具有使用價值。因此,“數據商品的價值源于互聯網平臺雇傭的數據工程師處理數據而付出的勞動”。⑤陸茸:《數據商品的價值與剝削——對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用戶“數字勞動”理論的批判性分析》,《經濟縱橫》2019年第5期。
那么,在信息時代,數字勞動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呢?吳歡、盧黎歌認為,“數字勞動其本質是將物理世界一切數字、文本、影像等符號化數據信息進行量化和相關性分析,內涵著數字化經濟和勞動價值論的內核,從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內涵和研究范疇”。⑥吳歡、盧黎歌:《數字勞動與大數據社會條件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繼承與創新》,《學術論壇》2016年第12期。而黃再勝認為,數字勞動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提出挑戰,只有“沿襲馬克思的生產性勞動思想,將以社交媒體平臺在線用戶活動為代表的數字勞動視作生產性勞動的一種新形態”,⑦黃再勝:《數字勞動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闡釋》,《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才能正確認識數字勞動價值生產的本質。
此外,對于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也引起國內學者的高度關注。藍江教授撰寫了一系列論文來分析數字資主義的內在邏輯,他認為,今天的數字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了一個以數字平臺和一般數據為基礎的新型資本主義”,⑧藍江:《數字異化與一般數據:數字資本主義批判序曲》,《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其中,資本的形態已經發生了變化,“一般數據成為最主要的資本形式”。⑨藍江:《一般數據、虛體、數字資本——數字資本主義的三重邏輯》,《哲學研究》2018年第3期。在面對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時,藍江認為: “我們需要進行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產關系,而不是進行存在論批判,將數字技術和數據拒之門外。”10藍江:《從物化到數字化: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異化理論》,《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而邱林川則通過考察富士康“血汗工廠”中工人狀況以及在網絡上沖浪的數字勞工,提出用“i奴”的概念來說明數字資本主義對互聯網勞工的剝削和異化。11為此,有學者認為,數字資本主義遮蔽了資本主義真實的社會關系,實現對數字資本主義解蔽應當“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批判性地審視數字資本主義”;12宋建麗:《數字資本主義的“遮蔽”與“解蔽”》,《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18期。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數字資本主義中存在的數字剝削機制,才能揭示“數字勞動在本質上仍屬于生產性勞動……數字資本從未改變資本增殖的本性”。13孟飛、程榕:《如何理解數字勞動、數字剝削、數字資本?——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1期。因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并沒有消除。
綜合國內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來看,無論是對“受眾商品”的討論,還是對數字勞動的批判,都暗含著一個主題,即:隨著生產方式的轉變,勞動的范式已經發生了轉變。毋庸諱言,資本對工人體力勞動的剝削已經無法解釋今天資本增殖背后的巨大價值來源,但是,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勞動范式的轉型并不意味著資本歷史本質的變化,也沒有根本改變勞動在社會經濟關系中的歷史本質和地位”。①莊友剛:《“非物質勞動”與資本積累》,《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先驅們已經意識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一些理論框架,可以作為分析傳播政治經濟學議題的有力理論武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勞動價值理論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建立在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之上的剩余價值理論,正是馬克思用以揭示資本增殖的價值源泉本質上是來源于資本對工人勞動的剝削。事實上,正是由于以計算機、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技術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才導致人類生產、生活、生存方式的巨大改變。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將這種轉變稱為“第三次浪潮”。在第三次浪潮的席卷之下,人們“對世界的體會、認知和領會世事的能力都會產生革命性的轉變”。②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黃明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67頁。既然“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154頁。那么,在信息時代傳播領域的勞動如何體現價值?它們又是如何成為資本增殖的籌碼?資本對于傳播具有哪些權力?這些問題都是傳播政治經濟學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正如歌德所言: “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如果不對理論進行發展,就不足以解釋信息時代資本積累之價值來源,也無法體現出信息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化。事實上,無論是斯麥茲所言的“受眾商品”還是用戶數字勞動產生的數據商品,在本質上都是人類智力勞動的產物;它們的勞動并非發生在生產領域,而是在商品的流通領域發揮著營銷的職能。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本文認為,它構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因而本文嘗試著以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來建構知識價值理論,以求有助于學界同仁開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新境界。
三、智力勞動及知識價值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時代創新
很久之前,人們就意識到“作為有目的行動的勞動,是由智力指導的,是人類的特別產物”。④哈里·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方生、朱基俊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45頁。可以說,在任何一種具體的勞動中都包含著體力與智力兩個因素。然而,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地位卻是不同的。在中國,孟子曾提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同樣,在西方,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即:一個城邦最理想的狀態應當是勞力者與勞心者各行其是。這用現代經濟學理論術語來說就是“分工”,而正是“分工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頁。由此可見,“勞力”與“勞心”的分工既是一種歷史現象,也是人類社會分工的必然產物,因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然而,丹·席勒卻在理論上忽視這一事實,企圖通過“生產性勞動”的概念消解“勞力”與“勞心”的差異,因而其最終的理論批判就只能將“批判的鋒芒轉向了虛無”。⑥胡翼青、楊馨:《解構神話:傳播政治經濟學學科合法性問題辨析》,《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為此,本文將努力避開丹·席勒的理論陷阱——要使勞動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其關鍵不在于取消“勞力”與“勞心”的差異性,而是要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的框架內實現勞動范式的轉換,從而建立起二者的聯系。
唯物史觀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頁。然而,“勞動不僅是物理的生產或形體的勞役,勞動更是人這個物種的特殊能力,是人自我活動的能力,因此,言談與思索、行動與活力都是勞動所不能缺少的部分”。①丹·席勒:《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第6頁。在我們遠古的祖先那里,勞動中的智力因素與體力因素差別并不是很大,它們在很長時間里交織在一起。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就必須首先在大腦中進行構思,然后為此采取一定的行動。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馬克思提出: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頁。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類逐步實現了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當社會上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已經比較明顯的時候,智力勞動才能夠真正脫離體力勞動而具有獨立的社會存在形式,例如巫術、祭祀、卜筮等成為專門的職業。由此可以推斷,智力勞動本身是一個歷史范疇的概念。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科技的應用雖然使勞動中“物理的生產或形體的勞役”部分地由機器去代替完成,但是智力勞動不可能完全讓渡給機器,在一定意義上仍然是專屬于人的勞動,因而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為此,馬克思指出: “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頁。馬克思這一論斷表明,智力勞動控制和引領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事實上,對于這種發展趨勢密爾也有所認識: “由于我們對外部物體所能產生的作用,是與我們對它們的知識成比例的,因此,任何時期的知識狀態是其可能的工業進步的限制條件;而且工業進步必定緊隨而且依靠知識的進步。”④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精神科學的邏輯》,李滌非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14頁。美國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也證實了這一看法,認為“后工業社會以知識價值論為基礎”,⑤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頁。并將以理論知識的集中與匯編作為社會的中軸。如果密爾、馬克思、貝爾的觀點是有預見的,或者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斷言:由于知識的積累,人類社會正在經歷著體力勞動范式向智力勞動范式的轉型。未來的社會,二者將互相滲透,并將逐步形成互融互促的勞動樣態。就此意義而言,正確認識智力勞動便已經成為今天分析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那么,智力勞動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呢?讓我們繼續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路徑去尋找答案。
馬克思是通過把人類勞動進行抽象而得到勞動力的概念的,即“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勞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頁。顯然,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既包括體力勞動的耗費,也包括腦力勞動的耗費。在一般意義上,智力勞動其實就是腦力勞動,它在整個勞動過程中具體表現為運用人類知識解決一個特定問題或滿足人類特定需要的過程。因此,從勞動過程來看,與體力勞動相對,智力勞動所強調的仍然是勞動中人的腦力的損耗;而從勞動結果來看,智力勞動所強調的是為人類創造的價值,而且相比體力勞動,智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要大得多,其影響也深遠得多。
然而,并非所有的學者對于智力勞動的理解都是一樣的。譬如,麥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就曾以“非物質勞動”⑦非物質勞動,又被稱之為“生命政治勞動”。涵括智力勞動,認為非物質勞動是“生產一種非物質商品的勞動,如一種服務,一個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⑧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4頁。顯然,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語境中,從事非物質勞動的人仿佛超脫了生產關系的束縛,成為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來進行自己情感的、知識的或是文化的生產。在這里,我們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實際上是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非物質勞動的控制作用。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隨處可見的是,無論是現在的“網紅經濟”還是“飯圈文化”,或者其他樣式的智力勞動或者知識經濟,只要這種勞動有利可圖,資本就會無孔不入地將其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為此,對智力勞動的考察,首先必須限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下,因為“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頁。由此,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商品的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頁。通過將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商品化,資本家可以實現使用價值到交換價值的轉變,這也就構成了資本積累的過程。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起始于對商品的考察。那么,在馬克思的語境中,是什么構成了智力勞動的商品呢?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點在于它將勞動力變成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5頁。在智力勞動中,“純粹的智力具有隱士般的、不顯眼的特征”。④保羅·諾爾維:《諸眾的語法:當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9頁。由此,智力勞動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屬性與資本進行交換,它是勞動力商品使用價值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認為,資本將“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頁。如果從具體勞動的角度看,醫生、律師、教士等職業并不生產某種特定的商品,但是他們的勞動是運用自身掌握的人類知識去滿足他人需要的,因而是一種有用勞動;而如果從抽象勞動的角度看,他們的勞動過程伴隨著人類勞動力的損耗,只不過與體力勞動相比較,他們的腦力損耗是占主導的。如此,從表面上來看,智力勞動似乎脫離了物質基礎。其實不然。因為,歸根結底,智力勞動還是建立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的勞動,其主要體現在智力勞動具有生產性。這里所謂“生產性”,并不是指智力勞動生產一種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物品,而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性,即“只有生產資本的雇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13頁。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智力勞動如何生產資本?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資本并非天然形成,只有在特定的生產方式下貨幣、生產資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才會轉化為資本。當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時,它意味著對他人“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0頁。在智力勞動以雇傭勞動的形式為資本工作時,無論具體形式如何,它都是在為資本進行勞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智力勞動在進行資本生產的同時也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再生產出來。因此,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于它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因而也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說,把以腦力勞動為主或者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系是雇傭勞動者的關系,是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的關系。”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18頁。這表明,在不同生產條件下,資本具有不同的形式,體現為不同的社會關系。
今天,在知識經濟、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我們看到,知識不僅是智力勞動的基礎,也是智力勞動的成果;知識不僅成為一種生產要素,更是一種可以實現增殖的資本。然而,需要強調的是,知識具有依附性,它并不能以獨立的形式參與到生產中,而必須與勞動結合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由于知識具有依附性,所以以知識生產與運用為內容的智力勞動也必然具有依附性。知識只有在智力勞動被雇傭的過程中,才能夠不斷地被轉化為資本。此外,知識和智力勞動還具有社會性。顯然,人在進行智力勞動時依靠的是他通過學習和積累的知識,但無論是通過直接經驗還是間接經驗獲得的知識都不會憑空產生,它們都是社會的產物,也是教育培訓的結果——從事智力勞動的勞動者,為了“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0頁。由此可見,智力勞動并不是脫離物質基礎的精神活動,而是現實地參與資本增殖的生產性勞動,亦即,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智力勞動只有成為資本的雇傭勞動,才能夠現實地參與到資本增值的生產性勞動當中,將知識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并創造價值。由此,智力勞動的二重性,便體現在了智力勞動的過程中:在具體勞動方面,它體現為人類運用自己的智力/知識因素去實現某種需要;而在抽象勞動方面,它體現為勞動過程中腦力和體力的消耗,其中以腦力消耗為主。所以,作為勞動力商品的一種特殊品質,智力勞動的價值就凝結在勞動力商品的使用過程中。
現在回到傳播政治經濟學。如果我們要回答“傳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傳播領域中勞動的價值如何體現”等問題,那么就不得不回到人類傳播活動之初。從傳播史角度來看,從“口口相傳”“結繩記事”到“文以載道”再到今天的“大數據分析”,人類傳播活動的發展過程體現了這樣一種規律:因生產生活以及社會交往的需要,人們在勞動中不斷創造出各種符號系統作為媒介來描繪他們直接生活的物質世界。因此,在卡西爾看來,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人的符號活動能力”。①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43頁。事實上,人類知識、文化也在此過程中形成,因為“人類知識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號化的知識”。②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第95頁。而符號化的知識,只有經過傳播才能被社會群體廣泛接受,才能普遍地與勞動相結合,并進而實現對客觀世界有目的的改造。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傳播活動本身就屬于一種智力勞動。事實上,“社會不僅因傳遞與傳播而存在,更確切地說它就存在于傳遞與傳播中”。③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3頁。由此可見,在人類的文明之初,傳播作為一種智力勞動便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在歷史中發揮著延續人類文明的作用。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后,人類的傳播活動更是成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手段。電報、計算機等人類智力產物成為交往的工具,就足以證明“現代交往手段的實質是科學和知識的力量,是人的創造能力和人的智力的發展”。④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0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在資本邏輯的控制下,傳播活動以及傳媒領域的生產關系主要表現為受眾和資本的關系。為了實現資本增殖,資本的所有者就需要通過傳播活動或者大眾傳媒將其所生產的商品推銷出去,而為了推銷商品,就需要創造大量的社會需求——盡管這種社會需求很多時候是虛假的需求。而這就需要通過諸如電視、廣播、網絡媒體的廣告等創造大量的“受眾商品”和“受眾勞動”。這時候,“觀看即工作”便成為現實的活動: “觀看成為工作既是一個真實的經濟過程,一個價值生產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一個隱喻(即經濟整體創造價值的表現)。”⑤Sut Jhally, Bill Livant,“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36,No.3, 1986, pp.124-143.對于廣告商來說,讓受眾在特定時間看到特定產品的廣告,他們的任務就已經完成。但是,對于支持廣告商的商品生產者來說,受眾觀看并不是他們最終目的,因為觀看行為并不能產生任何經濟上的收益;商品生產商的最終目的,是讓受眾在觀看過程中形成消費的欲望,并最終“花費他們的收入去購買特定‘品牌’的消費品”。⑥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 Blindspot of Western of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1,No.3,1977, pp.1-27.也就是說,在這一過程中,只有想方設法讓“受眾”成功地轉變為消費者,“受眾商品”才能最終實現它的價值及其增殖。換句話說,“受眾商品”的價值并不是體現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中“受眾”具有價值,而是體現在“受眾”同時也是潛在的消費者。通過消費,“受眾”便能夠實現資本流通的最后一環。但是,由于“受眾商品”是否被有效使用難以直接進行觀察,所以在市場中便出現了專門從事受眾行為研究的部門。這些部門通過對受眾行為的收集以及分析,“以受眾商品成員受廣告和編輯內容影響下的行為作為市場的研究對象”,⑦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 Blindspot of Western of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1,No. 3, 1977, pp.1-27.并最終形成量化的數據呈現給商品生產商,這些數據就是“收視率”。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米漢認為收視率構成了大眾傳播的商品形式。
在網絡信息時代,以上過程變得更加簡潔。互聯網以平臺的形式將受眾聚集在一起,這為收集、提取信息提供了便捷。平臺是“將不同用戶集在一起的中介,這些用戶包括客戶、廣告商、服務提供商、生產商、供應商,甚至實物。通常,這些平臺還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戶能構建自己的產品、服務和市場”。①尼克·斯爾尼塞克:《平臺資本主義》,程水英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頁。在網絡平臺中,這些受眾也有了一個新的名稱——“用戶”。通過相應的數字設備,“用戶”以“虛體”的形式登錄到網絡平臺中,成為千萬互聯網用戶的一員。在本質上,“虛體”是物理空間的個人在網絡空間的投影,而“虛體”的個人在網絡空間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將個人信息以數據的形式記錄到平臺后臺。之后,平臺通過收集、分析、提取將用戶的個人數據轉化為“一般數據”,而“一般數據”作為價值的穩定載體,可以將一切有利于資本增殖的個人信息包含在其中,供平臺無償使用。②“虛體”和“一般數據”概念及相關分析可參見藍江:《一般數據、虛體、數字資本——數字資本主義的三重邏輯》,《哲學研究》2018年第3期。如果從現代經濟學理論角度來看,這一過程大大消除了生產者(這里指生產企業或者個體生產商等產品生產者和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當然,其功用并不限于此。
總之,綜合來看,無論是享受“免費午餐”的受眾,還是獲得平臺服務的用戶,勞動在這里只能作為一種隱喻存在,它象征著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通過人的智力分析,人類的一切行為都能夠被提取出并為資本賴以生產而提供信息,而且,這些信息都能通過“免費午餐”或是平臺服務實現商品化。隨著信息技術在生活中日益滲透,整個社會仿佛變成了一個數據生產的工廠,不僅“人的再生產過程也直接成為生產過程,生命與勞動混沌不分,一切生命時間都要成為勞動時間,一切生命活動或社會活動都要成為勞動”;③夏永紅、王行坤:《機器中的勞動與資本——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機器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4期。而且,在這個工廠中,網絡平臺成為生產組織的中心,而一個個用戶就成為了數字勞工,他們所生產的包含著個人信息的一般數據被資本無償占用。但是,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用戶生產一般數據,只是整個生產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因為一般數據只以“原材料”的形式存在,而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就需要網絡平臺組織專業部門來收集、加工、分析等。因此,在整個數據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受眾”或者說用戶生產的只是具有交換價值的一般數據,而只有對數據進行收集、加工、分析、提取等才能產生數據的使用價值。由此可見,只有數據生產者和平臺企業二者相結合,才能共同構成“大數據社會條件下以數據信息等智力成果為基礎的無形資產”。④吳歡、盧黎歌:《數字勞動與大數據社會條件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繼承與創新》,《學術論壇》2016年第12期。然而,不管怎樣,這些“無形資產”的背后,體現的卻是智力勞動的結晶。下面,我們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層面上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評立場,來揭示智力剝削和智資矛盾的規律。
四、智力剝削與智資矛盾: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立場
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頁。事實上,針對當今傳媒領域的資本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立場,即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立場,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輝。上文所論述的智力勞動及知識價值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會不會改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剝削關系呢?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范式向著以智力勞動為主的勞動范式轉變,使得資本主義社會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剝削關系將會呈現出怎樣的新的樣態呢?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力變成商品,資本家通過購買勞動力商品,將其投入到生產中,從而實現資本增殖。在雇傭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勞動時間由兩個部分構成:其一是“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9頁。其二是“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1頁。在馬克思看來,超過必要勞動時間,工人勞動形成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它被資本占有者的資本家無償占有,并以此實現對工人勞動的剝削。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延長工作時間,無償占有絕對剩余價值;二是提高社會生產率,實現對相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對于前一種,馬克思稱之為“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00頁。在這種形式下,勞動過程受到資本的監督和支配。但是,延長工作時間必然會受到人體生理條件的限制,也會導致工人的反抗。因此,為了攫取更多剩余價值,資本家就將目光放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為此,馬克思指出:“資本只有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才不僅在形式上使勞動過程從屬于自己,而且改變了這個過程,賦予生產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從而第一次創造出它所特有的生產方式。”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頁。于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了,隨著大規模勞動的發展,科學和機器在直接生產中的應用也發展了”。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7頁。這一過程則被稱為“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6頁。而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經歷了從“形式上的從屬”到“實際上的從屬”的轉變。但是,科學技術參與到生產當中并未改變資本占有相對剩余價值的規律,生產力提高的結果只不過是使資本更加深入地剝削勞動者。對此,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比其他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更加浪費人和活勞動,它不僅浪費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費人的智慧和神經”。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05頁。馬克思的分析是基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三種基本形式——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在前兩種形式中,工人的勞動是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完成,工人掌握勞動技能和經驗,勞動在形式上從屬于資本。到了機器大工業,機器參與到生產過程中,勞動進一步被“拆成若干部分,交給工人分別承擔,整個勞動過程就不再是任何單個工人的活動范圍了”。⑥哈里·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第151頁。由此,工人被降低為生產工具,不再掌控完整的勞動過程,而這種狀況的出現,是由于技術應用而導致勞動在實際上從屬于資本。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提出: “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7頁。在當今的信息化時代,勞動從屬于資本的生產特征則更加直觀、更加顯明。
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勞動范式發生轉變。在信息與數字媒介的參與下,人類勞動雖然仍然離不開一定的體力消耗,但是由于信息社會中的許多工作都是依靠計算機完成的,一旦脫離計算機,勞動者甚至無法從事普通的勞動。當體力勞動范式發生向智力勞動范式的轉變,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形式也隨之發生轉變。那么,剝削方式發生了何種轉變呢?如我們所知,當前的互聯網企業中存在著“加班文化”“996工作制”等,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獲取絕對剩余價值,但是總體而言,今天我們的整個“社會已不再通過禁錮運作,而是通過持續的控制和即時的信息傳播來運作”。⑧吉爾·德勒茲:《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劉漢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99頁。也就是說,新型傳播工具的商業化使得資本家擁有對信息的壟斷和控制成為可能,某種程度上,這已經演變成為一種霸權。而作為剝削的新形式,這一霸權構成了對個人生活的支配(Domination)。哈特和奈格里基于非物質勞動概念將這種剝削稱之為“生命政治的剝削”(biopolitical exploitation),⑨唐正東:《非物質勞動條件下剝削及危機的新形式——基于馬克思的立場對哈特和奈格里觀點的解讀》,《哲學研究》2013年第8期。他們認為在非物質勞動的范式下,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剝削已經過時,因為非物質勞動的產品并不以物質形式出現,而是以知識、情感、信息等非物質為內容,這些產品無法以勞動時間衡量。也就是說,在非物質勞動中不存在剩余生產,那么就更不會產生剩余價值,因為“工業沒有生產剩余物——除了社會活動的產物——而且這就是為什么埋藏在偉大生活中的價值超越于標準之上的原因。如果生產沒有完全被社會智力、一般才智同時也沒有被情感表達所激活,將不會有剩余物,而情感表達決定著社會關系并統治著社會存在的體現。如今決定價值過量的因素有情感、知識交叉的身體、大腦的智力和純粹的行為能力”。①唐正東:《非物質勞動條件下剝削及危機的新形式——基于馬克思的立場對哈特和奈格里觀點的解讀》,《哲學研究》2013年第8期。因此,對生命政治的剝削,實際上,就是指“資本對非物質勞動過程即生命政治的勞動過程所創造的勞動成果的占有或剝奪”。②唐正東:《非物質勞動條件下剝削及危機的新形式——基于馬克思的立場對哈特和奈格里觀點的解讀》,《哲學研究》2013年第8期。我們看到,從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的批判立場來看,哈特和奈格里顯然是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勞動的影響,因而他們所構建的非物質勞動理論,就必然會忽視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矛盾,即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沒能完整理解“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4頁。從本質上看,資本主義社會對生命政治的剝削也不過是資本為了實現增殖的方式。因此,站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的批判立場上,我們在分析資本剝削勞動與支配個人生活時,依然需要堅持運用資本的批判邏輯,而不是哈特和奈格里所理解的“非物質勞動成果越出了資本所能控制的程度”。④參見唐正東:《非物質勞動條件下剝削及危機的新形式——基于馬克思的立場對哈特和奈格里觀點的解讀》,《哲學研究》2013年第8期。
事實上,支配與剝削的概念內涵是有所不同的。支配,其實并不以直接占有剩余價值為目的,它體現的是“社會內部權力的不平等分配:一些人命令,而另一些人服從”。⑤Emmanuel Terray, “Exploitation and Domination in Marx’s Thought”, Trans.by Joseph Serrano, Rethinking Marxism, Vol.31,No.4, 2019, pp.412-424.在傳播領域中,它表現為:一些人傳播,而另一些人觀看。這形成了傳播領域的權力關系。在福柯看來,話語不是隨意出現的,它是受到控制并且為了一定的目的而生產的——“在每個社會,話語的制造是同時受一定數量的程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的”。⑥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3頁。而且,“話語不僅僅是一套功能符號和語言表征,更重要的是在話語的背后存在著一套權力關系”。⑦朱振明:《福柯的“話語與權力”及其傳播學意義》,《現代傳播》2018年第9期。也就是說,按照福柯的理論,傳播是被構建起來,并且,在傳播領域,規定傳播內容則是掌握話語權力的具體體現。事實上,今天的各類報紙、電視臺、互聯網平臺等都掌握在大型傳媒公司手中。它們以其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掌握大量媒介資源。在傳播過程中,它們會通過有意識地篩選內容來實現對受眾行為的暗中操控。那么,為何傳媒公司會具有這樣的權力?麥克盧漢認為: “媒介即訊息,因為是媒介對人的協作與活動的尺度和形態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第19頁。由此,掌握傳播媒介的傳媒企業,就自然地擁有控制“受眾”生活的權力。德波以一種更加抽象的方式描述了這種控制傳播的權力,他認為“在現代生產條件占統治地位的各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顯示為一種巨大景觀的積聚”。⑨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頁。在德波看來,景觀的生產與資本緊密相連,個人生產和消費都成為景觀的一部分,“景觀讓活著的人們服從于它,原因是經濟已經將人們完全降服”。10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第7頁。然而,媒介技術的發展,則為景觀的積聚提供了智力支撐,“在其種種獨特的形式下,如新聞或宣傳、廣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費,景觀構成了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生活的現有模式”。11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第4頁。正因如此,邁克爾·帕侖蒂認為,“只有媒體的老板和經營者們能決定哪些人、哪些故事和新聞、哪些觀點可以進入公眾的視野”。12邁克爾·帕倫蒂:《少數人的民主》,張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5頁。對此,如果我們認真反思一下,就會發現,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傳播的權力,我們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都已經被規劃好,我們的消費早已被各類傳播媒介支配: “我們一提到籃球首先會聯想到NBA,在看電影的時候會選擇好萊塢的大片,一提到吃快餐就要去肯德基、麥當勞。”上述表明,傳播過程本質上就是一種權力關系的體現;通過傳播的權力,資本在更深層次上為社會塑形。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題,理所當然應該是“社會權力關系與傳播生產、流通、消費的相互構建”。13魯曙明、洪浚浩主編:《傳播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13頁。那么,這種權力關系對個人的支配是如何體現的呢?
考察信息時代資本對人的支配,我們必須回歸到個人的生活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當中。在信息時代,人們享受著網絡帶來的各種美妙體驗,殊不知互聯網的饋贈,其實在暗中早已被資本標好了價碼。互聯網平臺把我們每個人都變成了免費的數字勞工。我們在網上的所有信息都可以被記錄下來,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而“對大數據的收集、存儲、控制和分析因為受到了政治經濟利益的驅使,其目的是實現對個人的經濟和政治掌控”。①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大數據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羅錚譯,《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4期。因此,平臺收集、使用數據首先是為滿足商業和政治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平臺要求個人成為它的用戶。然而,這是一次交換。因為個人只有用自己的信息與網絡平臺交換,才能換取用戶的身份。當然,資本在任何時候都會試圖控制消費者,以期“最終取得‘自然’的地位,成為理所當然的產品提供者”。②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第142頁。在成為用戶后,人們在網絡中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記錄下來,形成數據。網絡平臺則根據數據去提取所需要的信息,以便有針對性地為不同用戶推送感興趣商品的廣告,目的在于刺激他們消費的欲望。也就是說,網絡平臺通過控制傳播內容支配個人消費。當前,隨著自媒體平臺興起,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主播、up主、博主,并在各類自媒體平臺中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傳播自己的觀點,這是否意味著用戶在網絡空間中獲得了傳播的權力?
曼紐爾·卡斯特將上述這些傳播形式稱為“大眾自傳播”,③曼紐爾·卡斯特:《傳播力》,湯景泰、星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1頁。而將這些用戶稱之為“創造性的受眾”。④曼紐爾·卡斯特:《傳播力》,第102頁。表面上看,在傳播過程中,創造性的受眾中似乎“能夠更深刻地參與到文化、社會和經濟事務中去,甚至能獲得一定的控制權”,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主編:《馬克思歸來(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25—126頁。甚至,“隨著大眾傳播中信息來源的多樣化,觀眾在作為信息接收者的同時,選擇范圍有所增加,也可以利用媒體提供的新機會來表達其偏好”,⑥曼紐爾·卡斯特:《傳播力》,第104頁。他們中的部分用戶在網絡中也可以通過自我包裝、自我展示等方式來獲取了更高的關注度,成為所謂的“網紅”。然而,我們發現,正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便會找上門來:商家正是看中了他們的“粉絲”量(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說,這些“粉絲”其實就是“受眾”),讓他們在分享觀點時有意識地打廣告、推銷商品。典型的如各類直播平臺興起時所發展出的“直播帶貨”營銷模式,而“網紅生產”甚至成為一門產業,并由此出現了一種經濟的新業態——“網紅經濟”。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深究“網紅經濟”背后的原因,而是想說明資本在當前傳媒領域的作用。數字平臺“依賴于‘網絡效應’——使用平臺的人越多,平臺對其他人而言就越有價值”,⑦尼克·斯爾尼塞克:《平臺資本主義》,第51頁。正因為這一點,它們會盡可能培養更多種類的主播,吸引不同類型的受眾。而對于網紅、主播而言,他們的勞動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轉變——不再是一個個獨立的用戶,而是成為被資本雇傭的數字勞工,并承擔著資本賦予的營銷功能,而這便為資本的剝削打開了間隙。事實上,一旦這些用戶成為資本的雇傭勞動者,他們受到資本剝削那就不言而喻了。綜上,技術的延伸并未帶來權力的擴展,“大眾自傳播”也并未逃出資本的掌控,反而被資本納入實現再生產的重要一環,即流通領域。無論是用戶在網絡上產生的數據被平臺無償占用,還是“網紅”、主播的直播營銷,他們的勞動都成為了資本增殖的籌碼。顯然,他們不同于工廠進行生產的勞動者,因為他們并不參與到商品的直接生產過程中,但是作為勞動力商品,他們是在商品的流通和消費領域發揮作用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主要考察的是生產領域,揭示的是資本通過雇傭勞動形式而實現了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幾乎沒有涉及流通領域。而在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受眾的勞動并不生產出實際的商品,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規定在這里也變得模糊,這樣就導致商品價值量無法確定。因此,如果以勞動價值理論去考察流通領域的勞動,就會顯得不太合適了。正如前文分析,在信息時代,勞動發生轉型的明顯特征是腦力勞動逐漸成為勞動的主要方面,而知識在勞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物質文明的每一次巨大進步總是以知識上的進步為先導;而且,當任何重大的社會變化,或者以逐漸發展,或者以突然沖突的方式發生時,在觀點或社會的思維模式上必然發生了作為其先導的巨大變化”。①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精神科學的邏輯》,第115頁。物質文明如此,精神文明的發展進步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就此而言,本文擬在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構建出一種新的價值理論——知識價值論,以解釋今天傳播對于價值增殖產生倍增效果的社會事實。
五、以知識價值論為基礎的智力勞動與智資矛盾運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建立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之上。通過雇傭勞動,商品的使用價值已經被生產,但對資本家來說,他們追求的并不是使用價值,而是交換價值。只有實現使用價值到交換價值的轉化,勞動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可,這就必須通過流通領域,也即,商品必須拿到市場上去出售。只有商品被賣出去了,再生產的過程才真正結束了,資本才占有了剩余價值。正因如此,馬克思才說“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3頁。事實上,這就意味著“資本是按照時間順序通過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兩個階段完成運動的”。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8頁。也就是說,資本無償占有剩余價值,包含了兩個過程:首先,在生產領域。工人的剩余勞動,為資本家產生了剩余價值。其次,在流通領域。通過商品出售,資本家獲得了剩余價值。在大工業時代,馬克思早已看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以商品的大規模生產為前提的,而大規模生產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規模的銷售。那么,流通領域的勞動對于資本增殖發揮著何種作用呢?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流通時間,一般說來,會限制資本的生產時間,從而也會限制它的價值增殖過程”;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42頁。“如果說勞動時間表現為設定價值的活動,那么資本流通時間表現為喪失價值的時間”。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7頁。因此,資本總是力求“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頁。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以時間消滅空間”。為了實現這一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卷入它的流通過程”。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27頁。然而,對于商品生產者而言,這個過程并不一定是一帆風順的。所以,馬克思曾以“驚險的跳躍”來比喻商品價值的實現過程,“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7頁。顯然,商品生產者不滿足于生產的不確定性,不希望自己面對“驚險的跳躍”,因而,“他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去生產滿足消費者所需的商品,或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資本家便想盡辦法宣傳和兜售他們的商品。這就需要諸如廣告等的促銷活動或者傳播活動,也便誕生了傳播商品。而“傳播是一種相當特殊的、十分強大的商品,因為它除了能生產剩余價值以外,還制造了符號和形象,其意義能夠塑造人們的意識”。⑨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第143頁。這樣,商品生產者就大量雇傭有才干的傳播領域的從業者,而作為雇傭勞動者,他們在勞動過程中事實上不是在進行物質生產,而是在進行文化工作,是運用其自身知識從事設計、包裝、營銷等腦力工作,目的在于減少資本的流通時間,快速銷售生產的商品以便快速地實現資本增殖。那么,作為雇傭勞動者的智力勞動是如何實現這一目的的呢?
如果結合鮑德里亞提出的“消費社會”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符號政治經濟學”等相關理論,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了。鮑德里亞認為,今天的資本主義出現了“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10他將這一現象稱之為“消費社會”。在消費社會
10 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頁。之中驚人的消費以及物的豐盛,仍然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因此“制約它的不是自然生態規律,而是價值交換規律”。①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第2頁。但是,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鮑德里亞試圖“打破僅僅通過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來說明政治經濟學的觀念”,②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0頁。為此,他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命名為“符號政治經濟學”。在鮑德里亞看來,在“‘消費’的社會學分析中,基礎性的假設并不是與需求有關的使用價值,而是象征性交換價值、社會回饋的價值、競爭的價值以及階級區分的價值”,③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第5頁。而所有這些價值則體現為一種“符號價值”。在鮑德里亞的分析中,符號價值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但“使用價值早已不再存在于體系之中”。④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第97頁。由此,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實現了由經濟交換價值轉化為了符號交換價值,這是因為: “物不僅是一種實用的東西,它具有一種符號的社會價值,正是這種符號的交換價值才是更為根本的——使用價值常常只不過是一種對物的操持的保證。”⑤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第2頁。由上,我們可以看到,鮑德里亞的分析,在根本上與馬克思產生了分野。在馬克思看來: “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在里面。”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1頁。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下,價值形成與人類勞動密不可分。然而,鮑德里亞卻通過符號將價值變成了一種“無指涉的結構性價值”。⑦夏瑩:《符號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嗎》,《哲學動態》2008年第1期。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將符號價值普遍化,從而使自己的分析陷入唯心主義。事實上,在傳播過程中,符號化商品的價值遠大于其實際存在的價值。通過廣告宣傳,產品的流通時間大大降低;只要一件商品的廣告足夠吸引眼球,商品就能在瞬間以符號的形式存在于消費者的心里,還有什么方式比廣告宣傳更能降低流通時間呢?這樣,商品的使用價值就被其符號價值遮蔽了。正因為以符號形式而存在的廣告等具有這種功能,所以鮑德里亞在他的“符號政治經濟學”中放逐了使用價值,并提出以符號價值取代交換關系中使用價值的觀點。然而,符號價值并非跳出了商品的二因素,而是其本身就存在于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這兩種對立的價值中。那么,商品的符號價值與其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之間具有何種聯系呢?
首先,當工廠中的工人完成商品的生產后,他們生產出的剩余價值已經包含在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當中。因此,剩余價值的生產在商品生產領域已經完成。但是,為了將這些商品賣出去,商品所有者還需要雇傭專業的傳媒工作者對這些生產出的商品進行包裝、營銷。而這一過程,本質上就是傳媒工作者運用自己的知識、創意為這些生產出來的商品賦予文化內涵,使商品不僅僅是商品,同時還是一個個跳躍著的文化符號。當某品牌的白酒生產商,通過廣告將雨果的詩歌“世界上最寬廣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廣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廣的是男人的情懷”與他們的產品聯系在一起時,消費者在宴請時所聯想到的就不僅僅是喝酒這一活動,同時還能通過喝酒體現他們的情懷。如此,文化符號就巧妙地和商品融合到一起了。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需求并不僅僅只有一個層面,它是由從低到高的階梯結構而構成的。如果說對必需品的消費構成了人的最低層次的需求,那么對特定品牌商品的消費,無疑是為了滿足人類更高級的需要。就拿白酒的廣告為例,當飲用該品牌的白酒時,我們不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物質的需要,同時也滿足了人們精神上的需要。因此,符號價值本身也是一種使用價值,也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只不過這種需要是由廣告商創造出來的,同時通過消費此種商品而得到的滿足。
其次,當符號被生產出來之后,還有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因為“符號是集體意識的產物,符號消費不是自娛自樂的行為,而是既為自己又為別人(社會)的消費行為”。⑧陳月明:《商品符號與符號消費》,《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當大眾傳媒讓各式各樣的“網紅”、明星等人頻頻出鏡并展示他們符號化的生活方式時,對大眾來說,他們就發揮了引導消費的作用。因為,這些“網紅名人大多來自草根平民階層,網絡中他們具有個人生活化的內容更容易感染與打動觀眾,引起公眾的共鳴,網紅自身的價值觀念也更容易傳導給公眾”。①王衛兵:《網紅經濟的生成邏輯、倫理反思及規范引導》,《求實》2016年第8期。然而,正是通過他們將這些商品所具有的符號意義展示出來,商品的品牌作為最直觀的符號就被社會所認可。因此,“商品符號價值形成的主要途徑,是通過營銷傳播工具的生產而獲得”。②桂世河:《符號消費時代商品廣告的本質功能》,《經濟管理》2006年第9期。
人類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符號價值也概莫能例外。但符號價值并不是與商品一同被生產出來的,它不是在生產領域產生的,而是在流通和消費領域產生的;而且,符號價值也并非由一般的物質生產勞動所生產,而是由營銷、策劃人員等以他們的知識為基礎,通過智力勞動在符號與商品之間建立起的意指關系而生產出來的,并通過傳播活動讓社會成員普遍認同。因此,構建以智力勞動為基礎的知識價值論來解釋今天傳播行業的傳播價值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在構建知識價值論時,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前提,即:知識價值論必須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不能脫離勞動價值論而空談知識價值論。這是因為:勞動始終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這里,勞動既包括體力勞動(即勞力),也包括腦力勞動(即智力),它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有機統一。沒有生產勞動就沒有商品流通,更沒有消費實踐。剩余價值只能是由勞動者生產,而且也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彰顯其勞動產品的價值。如果脫離了這個前提,知識價值論就失去了其解釋效力。而且,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智力勞動也是勞動,是具有其獨特本質的勞動,既與體力勞動相區別,又離不開體力勞動。因此,只有沿著這一思路進行智力勞動與知識價值論的雙重構建,才能開辟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以及唯物史觀新境界。但是,正如馬克思告誡我們的,我們不能忽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更不能忘記資本的本質: “資本是把自身設定為價值的價值,因而資本不僅是自我保持的價值,而且同時是自我增加的價值……資本家被看成這樣一種人,他只關心一定產品(他靠出賣他的商品來占有這些產品)的消費,而不關心預先存在的價值、購買力本身、抽象財富本身的增加。”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頁。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無論是人類的體力勞動還是智力勞動,都是資本增殖剝削的對象;只有到了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當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被消除、當資本被消滅的時候,資本對于勞動的剝削才可以被消滅,進而以知識價值論為基礎的智力勞動與資本的矛盾也才可以被消滅。
結 語
今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深化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④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求是》2021年第2期。仍然是我國當前及今后很長時間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們的重要目標。作為一種新出現的勞動形態,數字勞動不僅帶來了更加強大的生產力,而且同時也蘊含著生產關系變革的潛力。為此,如何正確認識數字勞動以及數字勞動產生的龐大價值,對于我們國家和社會發展就尤為重要。而在這一方面,源于西方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的確可以給予我們啟迪。
事實上,我們國家對此也是非常重視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將數據列為同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相并列的第五類生產要素。然而,毋庸諱言,長期以來,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人們卻忽視了傳播這一行為背后的知識因素以及智力勞動。這是因為,傳播行為和活動,從本質上來說,其本身就是人類智力勞動的具體形式以及人類知識價值的具體體現。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人類一方面通過構建各類符號以實現文明的演進與更迭,而這一演進與更迭的根本動力,則在于人類運用已有的知識積累并通過最大限度地發揮智力勞動推動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另一方面,以數字信息技術為代表的認知技術和傳播工具的誕生和發展,又進一步將人類的認識能力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并進而推動人類的知識更新。在網絡信息化時代,我們看到,通過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等的處理與分析,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產生的大量的雜糅數據,都可以被提取出供社會生產借鑒的有用信息,以減少生產、流通、消費以及分配等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給人們所造成的盲目性,而當這些信息凝聚在一起的時候,通過人類實踐反復檢驗后就會最終形成知識,這些知識便邏輯地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智力生產力。為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隨著人類認知能力的進步、傳播方式的升級,人類智力水平不僅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而且人類社會的知識范圍也會得到極大的拓展,由此而導致知識因素及其價值在人類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極大提升,而智力勞動則逐步演化為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進一步,如果以歷史的眼光觀察,我們就會發現,與人類認知能力的突飛猛進和傳播方式的更新迭代交織在一起的是整個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表明,人類社會由農耕時代發展到工業時代,是由科技發展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近代知識創新(包括哲學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工程技術科學等所有知識創新)推動實踐創新而取得的成果。而每一次的科學技術創新與突破,都可能會帶來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今天的智能時代,也同樣如此。在今天,我們看到,各類數字技術、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算法以及“云計算”等,已經全面地滲透到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每一個細節當中,這導致整個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社會交往變得越來越信息化、智能化、數字化。而正是這些技術的普及和運用,人們部分地乃至整體地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才成為可能,其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與之前社會變革呈現出不同態勢——人類的勞動工具、勞動對象以及勞動產品,不斷地以數據化、智能化、虛擬化、運程化、便捷化等形式呈現出來,而人類的情感、文化、知識等也不斷地被融入勞動過程之中,由此而導致的結果就是生產與消費、流通與分配、閑暇與工作、娛樂與休息乃至白天與黑夜等的自然邊界模糊了。在網絡空間中,人們的娛樂甚至被視為一種勞動,這樣,原本被馬克思看作的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17頁。的領域,現在卻對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的作用。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在于揭示經濟發展導致的政治、社會文化等的內在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關系。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基礎,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進行了最徹底、最深刻、最無情的批判。從商品的二因素、勞動的二重性出發,馬克思透徹地分析了資本的形成以及積累過程,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并發展出了邏輯嚴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資本主義不滅亡、資本家仍然存在,那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就依舊會發揮效力。然而,現實發展的種種新境況,卻對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面對由認知能力與傳播技術帶來的生產力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財富時,我們是否仍然需要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立場,這是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進道路上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是對中國共產黨能否科學執政、民主執政、文明執政所提出的重大考驗。為此,構建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的與時代發展相一致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和學科理論,則是當代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時代擔當和歷史任務,必須高度重視。
事實上,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學科建構過程中,有關“商品”與“勞動”議題的爭端從未消除,甚至今天已經陷入“死胡同”。究其根本就在于,一方面,傳播政治經濟學拘泥于泛化的“勞動”概念,未能清晰認識知識、技術在傳播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就忽視了智力勞動產生的巨大價值;另一方面,造成傳播政治經濟學今天的理論發展窘境以及學科建構的困難,還在于未能真正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去挖掘其理論基礎和理論前提——即“商品”和“勞動”在傳播領域中的基礎地位及其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的理論前提。而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本文試圖歸納總結國內外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為人們認識智能時代、數字時代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系的發展與變化提供的真知灼見,并在此基礎上,力求分析人類的智力勞動、認知能力與傳播方式等的進步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產生的重大影響。為此,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想更好地解釋數字時代社會政治、經濟等的一系列新變化、新發展,就必須要在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人類智力勞動以及知識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性及其重要價值。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解釋社會變化,從而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智識,并進而拓展和開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新境界。與此同時,本文還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和理論體系,也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立場的基礎上,進行智力勞動與知識價值論的雙重構建,才能更加科學地描繪數字時代傳播行為對于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