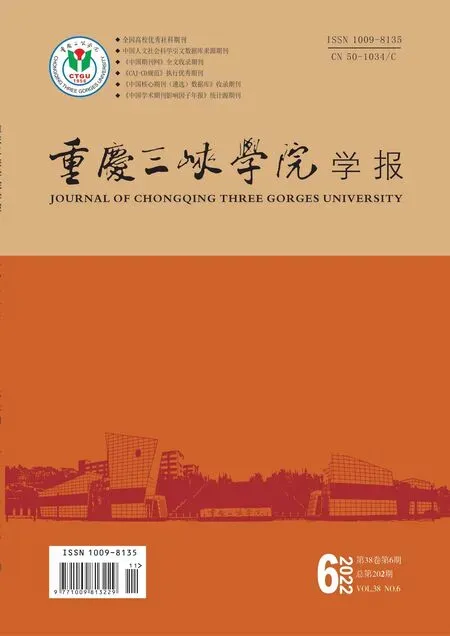“扜關右尉”及相關問題探析
夏保國 吳功翔
三峽研究
“桐飛一葉海天秋,戎馬江關客自愁。”千古扜關,在《史記》《后漢書》《華陽國志》均作“捍關”,巴楚角逐,氣吞山河。本期發(fā)表關于三峽庫區(qū)出土文物“扜關右尉”銅印的辨釋,并考察其行政管理、軍事防御的雙重功能,庶幾溯本清源,以正視聽。
“扜關右尉”及相關問題探析
夏保國 吳功翔
(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扜關的位置歸屬問題歷來眾說紛紜,有學者主張在巴郡魚復縣,亦有人認為在硤州巴山縣,遽難定論。重慶市豐都縣出土的一枚漢代“扜關右尉”銅印,根據其他印譜資料和梳理文獻典籍中關于“扜關”的相關記載,可以初步確認扜關應在巴郡魚復縣。扜關作為漢初五關之一,兼具民政與軍事的雙重功能,其軍事功能尤為突出,正因如此,掌管武備的關尉出現了左右分置的特殊現象。梳理扜關的基本功能、職官體系與關名流變,對了解古代關津制度有重要參考意義。
扜關;地理位置;職官體系;印章;關津制度
2003年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位于重慶市豐都縣鎮(zhèn)江鎮(zhèn)杜家壩村西南500米的長江北岸一、二級臺地上的二仙堡墓群展開田野勘探和發(fā)掘工作,共清理墓葬16座。其中,BM9墓室隨葬品中有一方刻有四字篆體印文的銅印,出土于墓室北部。橋型紐,銅質,方印,長2.4厘米,寬2.4厘米,厚0.8厘米,通高1.8厘米(圖1),發(fā)掘簡報將該印印文釋為“□關左尉”[1]。根據該墓出土的12枚“貨泉”錢和138枚“五銖”錢,其中有部分“光武五銖”,發(fā)掘簡報把該墓的年代推定至新莽東漢初期。

圖1 BM9出土的“□關左尉”銅印

圖2 BM9出土的銅印拓片
一、“扜關右尉”印
從“□關左尉”銅印的尺寸大小看,應屬漢代官印,這與墓葬年代斷為兩漢之際是一致的。依漢制,“御史大夫,銀印,青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秩。仆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2]卷一一五《王禮考》。又《漢官儀》:“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銅印。”[3]由此可知漢代官印一般呈方形,且漢尺一寸約合現今的2.2~2.4厘米。以上漢代官印的幾個突出特征,在豐都出土的這方印上都能得到體現,而且原發(fā)掘簡報從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方面綜合分析,認為BM9的年代應屬新莽至東漢初期(已出有“光武五銖”,BM9的年代應在東漢早期或東漢早期之后),故這方“□關左尉”印當屬東漢早期官印無疑,且官秩在比二百石以上,比二千石以下。
BM9出土的銅印由其印文“關”和“尉”兩字可知,該印印文采取“正刻反讀”的篆刻方式。簡報作者可能將印上“陽文”從左至右進行釋讀而作“□關左尉”,但漢印印文釋讀通常根據封泥上的“陰文”從右起讀。《豐都二仙堡墓地》為我們提供了該印的拓片(圖2)[4],由該印拓片可以看出,其印文應釋作“扜關右尉”更為合理。清人陳介祺等編撰的《封泥考略》,其中收錄有“扜關長印”和“扜關尉印”二枚封泥(圖3)[5]424。從字體篆刻的筆畫、走向等方面看,豐都二仙堡BM9出土的這方銅印印文,與“扜關長印”及“扜關尉印”的封泥印文雷同,與《說文》中的“扜”字極具相似性[6],故這方印的印文釋作“扜關右尉”當不足為疑。有學者亦持這樣的觀點①《豐都二仙堡墓地》也釋做“扜關右尉”,應是對《豐都二仙堡墓群2003年度發(fā)掘簡報》中的印文做的改釋,可從。另見羅小華《“扜關右尉”印章小識》,牛鵬濤、蘇輝《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45頁。。

圖3 《封泥考略》所收的“扜關長印”與“扜關尉印”封泥
翻閱《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正史材料,均不見有扜關的相關記載,但南宋王應麟所撰的《玉海》其中有關“扜關”一節(jié):“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扜關以距(拒)之。”又引《公孫述傳》:“(公孫述)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任滿下江州,東據扜關。”[7]卷二十四查《史記·楚世家》關于“楚肅王四年蜀伐楚”事件,司馬遷說:“(楚悼王)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為捍關以距之。”[8]卷四十《楚世家》1720又《后漢書·公孫述傳》:“越巂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捍關,于是盡有益州之地。”[9]卷十三《公孫述傳》536可見,扜關在《史記》《后漢書》中作捍關。除此之外,《史記·張儀列傳》:“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捍關。捍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8]卷七十《張儀列傳》2290《三國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埽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fā)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捍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10]卷二《文帝紀》79由此可知,如不考慮典籍歷代版本刊刻失誤的因素,司馬遷、范曄、裴松之等都將扜關寫作捍關。
除史料文獻的記載外,近世出土的簡帛材料也有扜關的相關記載。如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
制詔御史,其令扜(捍)關、鄖關、武關、函谷(關)、臨晉關,及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黃金、諸奠黃金器及銅,有犯令。[11]206
議,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扜(捍)關、鄖關、函谷(關)、武關及諸河塞津關。其買騎、輕車馬、吏乘、置傳馬者,縣各以所買名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各以馬所補名為久久馬,為致告津關,津關謹以藉(籍)、久案閱,出。諸乘私馬入而復以出,若出而當復入者,出,它如律令。御史以聞,請許,及諸乘私馬出,馬當復入而死亡,自言在縣官,縣官診及獄訊審死亡,皆津關,制曰:可。[11]47-50
張家山出土《二年律令》漢簡的墓葬年代約為西漢呂后二年(前186)或其后不久[11]前言,其內容反映出西漢早期的法律制度及社會發(fā)展狀況,材料比較可靠。以上所列舉的材料證明漢代確有扜關存在,而且扜關的戰(zhàn)略位置十分突出,與函谷關、武關等著名關隘地位相當。
綜上,無論是《張家山漢墓竹簡》,還是《封泥考略》所收的兩枚封泥,亦或是豐都出土的這枚漢代官印,皆可證明漢代確有扜關設置,是為地下之考古實證材料,其可靠性比一般文獻史料要高,正如裘錫圭先生所說:“我們不應該舍實證而信書本。”[12]因此,《史記》《后漢書》《三國志》等典籍中所謂的“捍關”實為“扜關”。
二、扜關職官體系疏議
漢代管理重要關隘的人員自成體系,這在文獻中是可以找到證據的。據《漢書·武帝紀》載:“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13]卷六《武帝紀》202另一方面,從出土的實物材料看,漢代關津職官體系由關令、關長、關都尉、關候、關尉丞、關嗇夫、關門嗇夫、津嗇夫、關佐、關執(zhí)奸等職官組成,層級體系為令、長、尉、丞、候、尉丞、候丞、嗇夫、佐、執(zhí)奸[14]。我們確定了豐都縣出土的這枚印章是扜關右尉印后,亟待解決的便是漢代關尉左右分置的現象以及兩漢時期扜關職官體系構成問題。
由前文所引張家山漢簡的內容可知,漢初的扜關、鄖關、武關、函谷關、臨晉關具有近乎同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扜關扼守由長江進入巴蜀地區(qū)的咽喉,幾乎是除了漢中外能進入蜀地的唯一通道。《華陽國志》曰:“鄖鄉(xiāng)縣,本名長利縣。縣有鄖關。”[15]83《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16]201過鄖關、武關可直通都城長安,故鄖關、武關在漢中——襄陽一線,是為秦之東南、楚之西北邊界。秦末,劉邦就曾破武關,戰(zhàn)藍田,進而直搗帝都咸陽,推翻秦王朝。函谷關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歷來是關中通往關東的咽喉要道,故《水經注》云:“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崄。”[17]109臨晉關,即蒲津關,因在臨晉縣,故名,倚靠黃河天險,控制晉南經冀中直抵幽州的東北通道,正如唐玄宗李隆基《早渡蒲關》詩所描述:“鐘鼓嚴更暑,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zhèn)尚雄。”[18]卷三由此可見,扜關、鄖關、武關、函谷關和臨晉關都置于水陸要沖之地,西漢王朝通過控制由此五關構成的“大關中”區(qū)域②關中可分“狹義關中”和“廣義關中”,扜關、鄖關等漢初五關劃定的區(qū)域即為“廣義關中”,與“關中”概念相對的是“關外”概念。參見王子今《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所見五關》,《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執(zhí)行“關中本位政策”,以御四方。《二年律令·津關令》反映出的漢初關禁制度,通過五關嚴格控制馬匹、黃金、銅等重要戰(zhàn)略物資流出關外地區(qū)即為一個例證[19]。
漢初五關的職能既具有維護社會治安穩(wěn)定的民政功能,也有抵御外敵入侵或諸侯反叛的軍事功能,其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故探究其職官體系結構十分必要。但與扜關軍事職能直接聯(lián)系的“扜關右尉”,卻不見于歷史文獻記載,甚至“關右尉”這一基本軍事職官亦未見有相關記載。“右尉”一職常設于大縣或市,如《后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雒陽(縣)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9]卷一一八《百官志》3623于險要關隘設尉,文獻記載中最常見的是關都尉。《漢書》曰:“關都尉,秦官。”[13]卷十九《百官公卿表》742說明關都尉在秦代便已有之,漢承秦制,關都尉制度被保留了下來。關都尉掌治一關,通常為重要關隘的最高長官,由皇帝的親信任之。《漢書·武帝紀》云:“(天漢二年)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群盜,其謹察出入者。’”[13]卷六《武帝紀》204又見《魏相傳》:“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函谷)關都尉,子為(雒陽)武庫令。”[13]卷七十四《魏相傳》3133-3134東漢初期,關都尉一職甚至一度成為皇帝恩寵的象征。據《后漢書·陰識傳》:“(建武)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托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鎮(zhèn)函谷。”[9]卷三十二《陰識傳》1130陰識是光武皇后陰麗華之異母兄,帝任之為函谷關都尉,鎮(zhèn)撫關東。可見關都尉在漢代是極其重要之職位。豐都縣出土的這枚印章雖不是關都尉之印,但“關右尉”三字是明確的,可證兩漢時期確有關尉之職官設立,墓主人生前還可能擔任過扜關右尉的職務。
目前考古出土實物中,所涉扜關者僅《封泥考略》收錄的兩枚封泥和豐都二仙堡BM9出土的這方銅印。其印文分別是“扜關長印”“扜關尉印”“扜關右尉”。《封泥考略》所收二枚封泥的出土情形現已不得而知,但從中反映出的扜關官職結構卻不容忽視,至少我們知道扜關有關長、關尉或者關尉直接分設左尉、右尉以代之。特別是關尉左右分置的特殊現象,在以往的研究中鮮有提及,文獻中也找不出明顯的證據,但《封泥考略》對于“扜關長印”與“扜關尉印”的釋文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其釋文分別為: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扜關長印’。按《續(xù)漢書·郡國志》:“巴郡捍水有捍關。”錢氏辨疑曰:‘《公孫述傳》,東守巴郡捍關之日(口)。’李賢曰:‘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西。’關長之官,不見于兩漢表、志。瞿氏印證曰:‘《后漢書·張禹傳》言祖父況,光武以為常山關長,意守關之官,比縣邑之稱長,僅按縣邑之長,有尉。’今封泥有扜關尉,瞿說是也。扜,《漢書》作捍,當以印為正,此關長之印也。[5]424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扜關尉印’,扜關及關尉詳前。[5]426
這段材料不僅說明了扜關的位置,也比較了關長與縣邑之官的品秩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說明了有關尉的事實,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我們此前的論證。
關長。文獻中僅《東觀漢記》有關“常山關長”一小段記載:“(張)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后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yǎng)。’復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zhàn)死,上甚哀之。”[20]704出土實物有“陜谿關長”[21]卷七57“桃萊外關長”[22]67,還有上文所引《封泥考略》的“扜關長印”,關長應是關隘的最高長官。
關尉。相關的文獻記載有《華陽國志》:“白水縣,有關尉,故州牧劉璋將楊懷、高沛守也。”[15]91《水經注》引《晉書·地道記》:“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二關勢接,疑斯城即是關尉宿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17]286出土實物則有陳介祺所收之“扜關尉印”封泥,結合文獻記載與出土實物,歷史上有關尉設置無可置否。
關左右尉。前文提及,關尉左右分置的現象不論在文獻中還是考古實物上均不足以證明,即便本文已將豐都出土的這枚印章釋作“扜關右尉”,但想要證明這一特殊現象真實存在,就必須依靠更多的分析。事實上,通過仔細爬梳史料,也不免能看出一點端倪。兩漢時期,尉左右分置常見于縣,《后漢書·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又引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9]卷一一八《百官志》3623《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也說:“左尉為東漢縣左部都尉省稱。漢代大縣,置左右部尉分治之。”[23]181由此可知,尉左右分置的現象多體現在萬戶以上的大縣。再根據《封泥考略》“意守關之官,比縣邑之稱長,僅按縣邑之長,有尉”的記述,可以看出扜關的最高長官應是大縣縣級屬官。大縣最高長官稱縣令,作為掌管軍事、兵備的縣尉則分置左、右尉。同樣,扜關的最高長官應是關長或關令,職掌武備的關尉應次之。如前文所述,扜關在漢初占據十分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扜關的地位顯然要比一般大縣要高很多,一般大縣之縣尉尚要左右分置,則作為比一般大縣地位要高很多的重要關隘,扜關關尉左右分置應在情理之中。
總之,扜關在漢初國家統(tǒng)治體制中占據重要一環(huán),其關隘建制應十分完備。即便目前出土的材料只能夠證明扜關存在關長、關尉和關右尉,但扜關控扼由長江進入巴蜀地區(qū)的門戶,在軍事防御和維穩(wěn)社會治安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關尉之下應還有關尉丞、關嗇夫、關佐等一系列屬官,構成完整的關隘職官體系是毋庸置疑的。
三、扜關位置考
前述文獻典籍中“扜關”通常作“捍關”,亦作“捍關”。扜關位置歸屬問題歷來存在較大爭議,多家學人也做過相關考述,但仍然難成定論。
引發(fā)扜關位置論爭的史料主要有三:其一,《史記·楚世家》載:“(悼王)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為捍關以距之。”其二,《鹽鐵論·險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捍關以拒秦。”[24]526其三,《水經注》:“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捍關而王巴。”[17]862-863諸多學者以這三條史料為基礎,主要持有“長陽說”“奉節(jié)說”和長陽奉節(jié)皆設扜(捍)關三種意見,具體考論簡述如下:
歷史文獻中關于扜關位置的分歧,主要體現為魏晉以降人們給《史記》《漢書》《后漢書》等典籍所作的注解,分奉節(jié)和長陽兩說。《續(xù)漢書·郡國志》:“巴郡魚復捍水有捍關。”[9]卷一一三《郡國志》3507徐廣也認同司馬彪的說法。南朝劉昭注《續(xù)漢書·郡國志》巴郡條:“《史記》曰,楚肅王為捍關以拒蜀。”[9]卷一一三《郡國志》3507《括地志》云:“捍關,今硤州巴山縣界故捍關是。”[16]191李賢注《后漢書·公孫述傳》則說:“《史記》曰,楚肅王為捍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9]卷一三《公孫述傳》535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捍關在楚之西界。《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8]卷七〇《張儀列傳》2290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根據《古今地名》“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的記載,認為捍關“在硤州巴山縣界”[8]卷四十《楚世家》1720。可見,徐廣、劉昭、司馬貞皆沿襲晉人司馬彪之說,認為扜關在巴郡魚復縣;另一說則以李泰的《括地志》為本,主張扜關位于硤州巴山縣,李賢、張守節(jié)皆從之,三者似有一定從屬關系。此二種說法從歷時關系上看,前一種說法應更為準確。
近現代學人針對扜關究竟在哪也做過多方面論述。王先謙于《漢書補注》中采取《水經注》的說法,認為江水自西向東,先經江關,次弱關,后捍關,捍關應屬長陽縣境[25]709-710。錢穆則認同《張儀列傳》的記載,認為捍關以在魚復縣為是[26]567。顧頡剛認為發(fā)生于楚肅王四年的“蜀伐楚”事件,是蜀人東出,越過巴國,奪取楚的茲方,于是楚國在奉節(jié)修筑了捍關[27]83。徐中舒在《論巴蜀文化》中認為捍關在奉節(jié)縣,弱關在秭歸縣[28]21。童恩正則主張取茲方者實為巴,出兵的路線是沿著大溪—清江東下的,因此在長陽縣設置捍關更加符合史實[29]139。陳劍的看法與童恩正的說法相似,只不過在進軍路線選擇上有所不同。他認為所謂楚“拒巴”“拒秦”,以及廩君“浮夷水所置”“據而王巴”,所說都是同一處捍關且位于長陽縣[30]。魏嵩山的論斷與童恩正的說法恰好相反,他考證大溪、清江于古代并不相通,川鄂之間的水路交通自戰(zhàn)國以來就經由長江三峽,因此主張捍關位于奉節(jié)縣東長江邊,于漢代屬巴郡魚復縣[31]。楊昶則認為《水經注》中關于廩君“置捍關”,“據捍關”等記載均屬“傳聞”,故考證捍關具體位置時《水經注》中關于“廩君設捍關”的相關記載應予以剔除,他主張捍關曾在多處設立,一是拒蜀捍關,在今奉節(jié)縣,建于公元前377年前后;另一捍關則是拒秦捍關,在今長陽縣境內,是戰(zhàn)國后期楚國為防備秦軍而建[32]。藍勇則認為長陽捍關乃廩君所置,奉節(jié)捍關乃楚所筑[33]301。可見,扜關與捍關究竟是何關系、扜關的具體位置等問題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討論所涉范圍較廣,時間跨度大,難免會出現混淆的可能,以至于個中問題長期懸而未決。
扜關究竟在哪兒?我們認為首先應該注意捍關與扜關的辨誤。前文已指出,“捍關”實乃“扜關”,“捍”與“扜”的訛誤應屬在后世的典籍版本刊刻及傳布過程中被謬誤所致,楊建即持這樣的觀點,認為“捍關”應該寫作“扜關”,捍關是文獻傳抄過程中出現的失誤[34]43-46。干、于易誤,在典籍中較為常見,典型的例子如《漢書》所載鄯善“王治扜泥城”,而袁宏在《后漢紀》中則做捍泥城[35]。這與現在要討論的“捍關”與“扜關”的誤讀如出一轍,可見“捍”字在典籍中常被誤寫作“扜”字,從而致誤。
我們認為在漢代沒有將“扜關”通作“捍關”的可能,只能是古書在魏晉以后隸變、楷正過程中先將“扜關”誤作“捍關”,而“捍關”實乃“捍關”同音轉寫之誤,屬后世學人因意求字而曲解為之。這一點在《水經注》中即可得證:“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17]789自此以后,學人多取捍關之捍乃“捍敵之捍”,即捍衛(wèi)之意,故多做捍關③參見繆文遠訂補:《七國考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0頁。童恩正于《古代的巴蜀》也持此意;羅權在《瞿塘關名稱、位置及空間布局的演變——兼及歷史時期瞿塘關的軍事地理形勢》一文中也采用這一說法。見羅權《瞿塘關名稱、位置及空間布局的演變——兼及歷史時期瞿塘關的軍事地理形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4年第4期。。
其次,扜關的位置之所以含混不清,難成定論,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分清捍關與捍關。既然捍關乃扜關之誤,那么歷史上應只存在扜關,而沒有捍關,因此分析文獻史料也能為我們確定扜關的位置提供重要參考。本文主要考察漢代扜關的位置,故兩漢正史材料中關于扜關的具體記載顯得尤為重要。扜關在正史中主要有以下幾處記載:
《史記·楚世家》:
(悼王)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為捍關以距之。[8]卷四十《楚世家》1720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捍關。捍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8]卷七十《張儀列傳》2290
(巴郡)江州;宕梁,有鐵;朐忍;閬中;魚復,捍水有捍關;臨江;枳;涪陵出丹。[9]卷一一三《郡國志》3507
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yè),覆以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zhàn)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9]卷一三《公孫述傳》535
其中《楚世家》《張儀列傳》所涉扜關雖不是漢代扜關,但其內容仍然能為我們判斷兩漢扜關的位置提供線索,尤其《張儀列傳》的記載,線索更為明晰。張儀所意尤為清楚:秦軍進軍楚國的路線有二,其一是從巴蜀順江東下;其二是出武關南下,形成夾攻之勢。從內容上看,扜關應距黔中郡、巫郡不遠,因此秦軍逼近扜關后,才可能“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后也。”[8]卷六九《蘇秦列傳》2259巫郡,《正義》引《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百里。”[8]卷五《秦本紀》216辰州即今天的湖南懷化;夔州即現今的重慶奉節(jié)。再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軍出武關可至宛(南陽),宛與楚都郢在秦并六國后同屬南郡[8]卷六《始皇本紀》223,長陽距郢都很近,秦軍“南面而伐”進攻郢都,則長陽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因此,張儀所說的扜關似不太可能在今湖北長陽,而應在今天的重慶東部、湖南西北部,且在長江邊上,唯有如此,張儀所言的雙線進攻才能達到目的。
《后漢書·郡國志》與《公孫述傳》則進一步指出扜關位置在巴郡,且表明了扜關的重要戰(zhàn)略地位與漢中褒斜道相似。褒斜道,見《史記·河渠書》:
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舡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余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谷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fā)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8]卷二九《河渠書》1411
可見由關中經過褒斜道可南通巴蜀,戰(zhàn)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樣,扜關亦處于與褒斜道戰(zhàn)略地位相似的地理位置上。而長陽則位于三峽之外,過長陽向東即到荊州(楚國郢都),地平千里,根本無險可守,因而其地位遠不能與扼守三峽之口,“實為益州福禍之門”的奉節(jié)縣所能比擬。且漢代設扜關時間較為長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穩(wěn)定。如發(fā)生于元鼎三年的“廣關”事件,這是西漢中期國家行政區(qū)劃調整的重大事件,漢武帝將函谷舊關東移約三百里建立函谷新關,但扜關、鄖關的位置卻沒有發(fā)生變動[36]。后世歷朝歷代也都將魚復作為至關重要的軍事屏障,長久以來發(fā)揮著強大的軍事效力[37]。但所謂長陽捍關自戰(zhàn)國后鮮有提及,逐漸湮沒于歷史塵埃之中。
前文指出,長陽有捍關的立論依據多源于“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捍關而王巴”的歷史記載,后世學者多從夷水出發(fā),考證夷水在今湖北長陽縣,故而得出捍關就在長陽縣夷水邊上。這樣的考證看似比較合理,但據《水經注》載:“(江水)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17]775《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李賢注引《水經》也說:“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9]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3840,也就是說,捍關仍有在魚復縣的可能。李賢雖引用了《水經》的材料,但卻不予采用,而是認為捍關在“硤州巴山縣”,因此以夷水論斷捍關位置不免有些牽強。另外,《封泥考略》所收的二枚“扜關”封泥已經失去考古出土情景,對于我們判斷漢代扜關的具體位置價值不大,但豐都出土的這方“扜關右尉”銅印,無疑是扜關位于奉節(jié)的一個考古學實物旁證。
至于捍關,我們認為楊昶的意見可從,也認為“廩君置捍關”的史料實屬神話傳說,不可盡信取。但根據《華陽國志》中“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捍關、陽關及沔關”與《水經注》的“昔巴楚數相攻伐,籍險置關,以相防捍”[15]58的相關記載,我們認為這兩條材料所記錄的史事應為史實,可以信據。據《資治通鑒》載:“《華陽國志》: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即古捍關也。杜佑曰:巴山縣,古捍關。如此則別是一處。”[38]卷四十二《漢紀三十四》1366此“別是一處”即為長陽捍關。故綜上所述,歷史上確有扜關、捍關之實,捍關實屬扜關訛誤,扜關位于今重慶奉節(jié)縣,捍關則位于在今湖北長陽縣的可能性較大。
四、結語
重慶市豐都縣二仙堡BM9東漢早期墓出土的銅制印章,原發(fā)掘報告將其印文釋為“□關左尉”,但根據《張家山漢墓竹簡》等近世出土的簡牘材料,結合《封泥考略》《漢印文字征》等印譜資料以及相關研究,認為此印文釋為“扜關右尉”更加合理。扜關作為漢初“五關”之一,其戰(zhàn)略地位不言而喻,就扜關的戰(zhàn)略層面來說,討論其關隘職官體系十分必要。目前所見的材料僅能證明扜關有關長、關尉、關右尉,而沒有關右尉以下的屬官,其職官體系似乎不完備,但翻閱《后漢書·百官志》《漢官儀》等文獻資料,不難看出扜關的職官體系在理論上是完備的。盡管目前還缺乏更多的文獻史料以及出土材料的進一步論證,但“扜關右尉”銅印的出土,無疑對討論扜關職官體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也是中國古代關津制度的重要補充。與此同時,扜關位置之爭由來已久,通過爬梳文獻典籍和前人學者的相關考述,并考察豐都出土的這枚“扜關右尉”印可知捍關實乃扜關,“干”“于”易誤,這在文獻中不乏例證。“扜”字應是由于魏晉以后漢字楷正過程中被訛誤為“捍”字,加之在典籍傳抄過程中極易將扜關錯寫成捍關,故扜關、捍關二者常被混淆使用。扜關的實際位置在今重慶市奉節(jié)縣,而捍關的位置則可能在今湖北省長陽縣,為先秦時期巴楚相持之時所設,在秦統(tǒng)一后便逐步廢棄不用。扜關關制長時間保持穩(wěn)定,雖在漫長歷史時期經歷過發(fā)展與演化,其名稱也一度變換,但一直是我國西南地區(qū)最具戰(zhàn)略意義的重要關口,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門戶,同時也逐漸發(fā)展成為巴蜀地區(qū)與兩湖地區(qū)地理界標,是三峽文化的重要代表。
[1]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豐都縣文物管理所.豐都二仙堡墓群2003年度發(fā)掘簡報//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水利局.重慶庫區(qū)考古報告集:2003年卷[G].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2380.
[2]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6:1035.
[3]孫星衍,等.漢官六種[M].北京:中華書局,1990:188.
[4]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豐都二仙堡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154.
[5]陳介祺,吳式芬.封泥考略[M].北京:中國書店,1990.
[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10.
[7]王應麟.玉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80-381.
[8]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1.
[9]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0]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1]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2]裘錫圭.考古發(fā)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于校對古籍的重要性[J].中國社會科學,1980(5):3-28.
[1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4]郭俊然.漢代官僚制度研究——以出土資料為中心[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8:247-252.
[15]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賀次君.括地志輯校[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7]陳橋驛.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8]彭定求,等.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35-36.
[19]董平均.津關令與漢初關禁制度論考[J].中華文化論壇,2007(3):62-67.
[20]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8:704.
[21]瞿中溶.集古官印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7.
[22]謝景卿,孟昭鴻.漢印分韻合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7.
[23]龔延明.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181.
[24]王利器. 鹽鐵論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2:526.
[25]王先謙.漢書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709-710.
[26]錢穆.史記地名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567.
[27]顧頡剛.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83.
[28]徐中舒.論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1.
[29]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139.
[30]陳劍.古代“捍關”今何在[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3):99-102.
[31]魏嵩山.楚捍關考——兼及清江和大溪源流及巴族遷徙路線[J].江漢論壇,1980(5):81-84.
[32]楊昶.楚捍關辨正[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6(5):48-52.
[33]藍勇.長江三峽歷史地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301.
[34]楊建.西漢初期津關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3-46.
[35]王北辰.若羌古城考略[J].干旱區(qū)地理,1987(1):45-51.
[36]辛德勇.漢武帝“廣關”與西漢前期地域控制的變遷[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2):76-82.
[37]羅權.瞿塘關名稱、位置及空間布局的演變——兼及歷史時期瞿塘關的軍事地理形勢[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4(4):71-80.
[38]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1366.
A Discussion on “Right Lieutenant of Yuguan” and Related Issues
XIA Baoguo WU Gongxiang
The current location of Yuguan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a long time. Some scholars advocate that Yuguan lies in Yufu, Ba County, while others believe that Yuguan is located in Bashan County, Xiazhou. With the support of a recently excavate bronze seal of “Right Lieutenant of Yuguan” from Han Dynasty and studies on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 records on of “Yuguan”, it can be preliminarily confirmed that the current location of Yuguan is in Yufu county, Ba prefecture. As one of the five passes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Yuguan has both military functions and civil functions, in which military functions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is prominent military function leads to the special separation of Yuguan’s Left Lieutenants and Right Lieutenants.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Yuguan’s basic functions, official system and the changes of its names, since it may serve a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ancient Guanjin System.
Yuguan;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ficial system; seal; Guanjin System
夏保國(1969—),男,河南三門峽人,歷史學博士,教授,主要研究先秦史、先秦秦漢考古學。吳功翔(1998—),男,水族,貴州三都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區(qū)域與民族考古、中外交流史。
貴州省社會科學規(guī)劃重點課題“戰(zhàn)國秦漢時期云貴高原的聚落、人口與文明進程研究(21GZZD35)”。
K234.2
A
1009-8135(2022)06-0025-12
(責任編輯:滕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