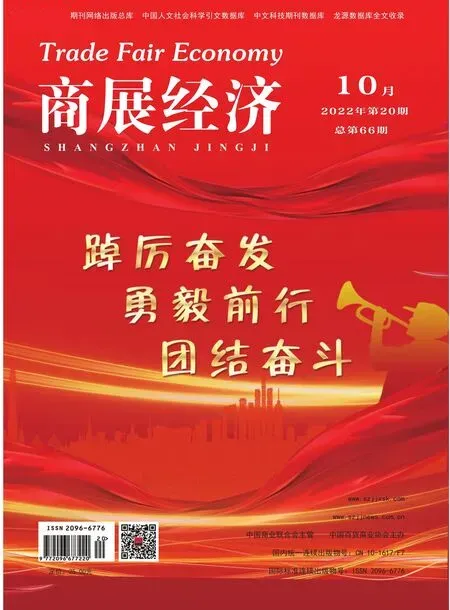平臺經濟反壟斷的困境與對策研究
陳盈盈 顧彧婧 鄧如一
(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江蘇南京 210094)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平臺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具體運行過程中,我國平臺經濟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壟斷現象,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基本權益,也影響正常經濟秩序。為此,必須基于我國基本國情和市場特點加強平臺監管,兼顧市場效率與競爭公平,切實推動平臺經濟健康發展,促進共同富裕。
1 平臺經濟及其特征
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定義,經濟活動中的平臺是指在雙邊(或多邊)市場中運營的企業,該企業使用互聯網在兩個或多個不同但相互依存的用戶群之間進行交互,從而為其中至少一個群體創造價值[1]。考察國內外平臺經濟,總體上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規模效應。相較于傳統商業模式,平臺經濟由于不受地域、時間、空間和自然資源等條件限制,存在優越的規模經濟發展優勢;二是具有集聚效應。平臺經濟以信息流為紐帶,能在短期內將不同市場有效連接在一起,集聚形成新的業務流程、產業融合及資源配置模式,并表現出實時高效的特征;三是具有網絡效應。網絡效應是指產品或服務對用戶的好處隨著用戶數量增加而增加。通過網絡鏈式傳播,平臺經濟的擴張性更加明顯;四是具有鎖定效應。用戶漠視成本變化,堅持使用當前平臺的現象,即為鎖定效應。
2 平臺經濟的壟斷現象
2.1 算法控制
算法控制主要體現在平臺參與方對算法調整的被動接受與平臺自營業務和第三方商家利益沖突等方面。平臺匹配消費者和生產者促進其完成交易,算法調整勢必會影響到平臺生態圈的任何一方,但算法調整的權力只掌握在平臺手中,其他各方只能被迫接受。以用工平臺為例,平臺就業者(司機、外賣員等)對算法的構建與調整普遍一無所知,平臺與平臺就業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平臺的控制能力和主導地位不斷增強。
2.2 價格操控
價格操控的典型表現就是掠奪式定價策略與價格歧視。對平臺經濟而言,初創期最重要的不是獲利而是獲得并穩定流量。大多數互聯網平臺在發展初期都表現出盈利遠遠落后于平臺用戶增速的特征。但當平臺的市場規模逐漸擴大時,平臺企業將取消價格補貼策略,迫使用戶接受壟斷高價。在國內,掠奪式定價策略最為典型的現象是“紅包補貼”“免費拉新”等營銷手段。在市場活動中,價格歧視分為一級價格歧視、二級價格歧視、三級價格歧視。其中,一級價格歧視指完全價格歧視,對每一單位的商品實現單獨定價;二級價格歧視指商家對不同的銷售收取不同的單位價格;三級價格歧視指商家對不同市場的消費者實現不同的定價[2]。在傳統市場中,壟斷方很難得到某一顧客的心理價位,因此,他們大多根據銷售數量差別定價,實現二級價格歧視,或是根據不同消費群體差別定價,實現三級價格歧視。而在平臺經濟中,借助大數據工具,平臺可以收集用戶瀏覽、購買等各種交易數據,實時掌握并利用消費者的消費偏好、支付能力、潛在需求,精確針對每一位顧客進行彈性定價。
2.3 合謀協議
牛津大學法學教授Ariel Ezrachi和美國田納西大學法學教授Maurice E.Stuckle在2015年共同提出了算法共謀的理念[3]。如今算法的即時性使得合謀遍布各個行業的數字平臺,算法也使隱性合謀成為可能。此外,由于算法合謀基于先進的算法和大量數據支撐,使得市場行為更加透明化,這也降低了各方壟斷勢力違反協議的可能性,提高了聯盟的緊密性與穩定性,進一步危害市場競爭的公平公正。
2.4 客戶挾持
平臺經濟具有排他性交易的特征,這是一種典型的客戶挾持。不同于傳統商品市場中上游賣家限制下游買家只能采購自家產品的單方向壟斷,平臺經濟的客戶挾持表現得更為復雜。一方面,掌握巨大流量和用戶資源的平臺要求賣方只能向自己提供商品或勞務;另一方面,平臺利用低成本和低價格優勢誘導和捆綁消費者,從而提高顧客對平臺的依賴。
2.5 過度并購
并購是互聯網巨頭擴張的典型手段。過去,傳統壟斷常見的兼并方式主要有橫向兼并與縱向兼并。而今,數字時代下的平臺經濟衍生出跨行業、跨領域的對角兼并,即兼并競爭對手的上游供應商或下游采購商以達到入駐新行業、控制競爭對手關鍵生產材料供應商或產品銷售商的雙重目的,相較傳統兼并更具壟斷傾向[4]。總之,這些并購策略一方面會使得市場份額過度集中,加劇壟斷和安全隱患;另一方面也使行業內的創新被抑制。
3 平臺經濟反壟斷治理的困境
當今學界普遍認為,當經濟增長減速、產業集中度提高、收入分配惡化,公眾對大公司的厭惡程度會提高[5]。當前,平臺經濟諸多問題逐漸顯露出來,多個國家和地區紛紛開始整治超大型數字平臺,平臺經濟反壟斷浪潮被推向高點。
就國內而言,在推進反壟斷立法方面,2021年2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正式發布,充分回應平臺經濟領域亟待解決的平臺“二選一”“大數據殺熟”等焦點問題;2021年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修正草案)》,進一步從法律層面規范平臺經濟的市場行為。
在強化反壟斷執法方面,2020年12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對阿里巴巴收購銀泰商業股權等并購案做出頂格行政處罰決定書,這是我國反壟斷執法機關首次對數字經濟領域經營者的集中交易做出行政處罰;2021年7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騰訊收購中國音樂集團股權的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立案調查。該案是國內首例責令經營者采取措施恢復到集中前狀態的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件,成為我國反壟斷執法的里程碑事件。
盡管市場監督管理機構的一系列舉措對平臺反壟斷治理有一定成效,但國內平臺經濟治理由于起步較晚、歷史較短、經驗不足,仍然存在一系列反壟斷監管問題亟待解決。
3.1 壟斷認定困難
在傳統市場壟斷認定中,關鍵因素是市場份額,但這種判斷顯然不適合平臺經濟的壟斷認定。平臺經濟的典型特征是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因此對平臺經濟而言僅依靠市場份額認定是否壟斷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同樣,平臺經濟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也對是否存在壟斷的認定造成了阻礙。例如,平臺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范圍十分廣泛,跨市場、多行業的經營難以建立起普適性標準來統一核算平臺在不同行業的市場份額。此外,就某個領域而言,該平臺也是一個多邊市場,涉及多方利益,我國目前采用的假定壟斷測試方法難以適用。
3.2 協議鑒別困難
由于算法的技術優勢,平臺經濟的壟斷行為往往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如平臺利用算法優先展示平臺偏好的產品或勞務,或通過濫用數據控制權進行不公平數據信息限制,如限定消費者的支付方式等。此外,算法合謀也會形成隱性合謀并以傳統監管手段難以捕捉的方式進行多發性限制行為與高壟斷價格制定。這些利用算法優勢形成的壟斷協議通常具有隱蔽性,即使在調查取證期間,平臺也可利用算法的即時性銷毀線索,從而使對壟斷行為鑒別與監督的難度大大提升。
3.3 監管治理困難
由于平臺算法具有保密性,監管機構通常要分析海量數據,推斷算法的工作原理,并以此判斷平臺是否濫用市場地位。這項工作具有龐大的工作量,需要周期較長的行政調查和司法訴訟。這樣的監管流程無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漫長的調查周期容易導致市場治理滯后,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此外,伴隨著互聯網算法加速演進,平臺的壟斷行為愈發復雜,治理難度不斷提高。
4 平臺經濟反壟斷的治理創新
黃國平(2021)[6]指出,不加規范的野蠻式和壟斷化的平臺經濟不但有損社會福祉的整體增進,更是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背道而馳。加強對壟斷的監管治理、維護市場的公平有序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爭取早日實現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4.1 完善壟斷認定
根據平臺經濟的特點,對平臺壟斷的認定不應僅以市場份額為決定因素,而應綜合考慮平臺是否存在濫用市場優勢、技術優勢、資本優勢及平臺規則的行為。相應地,平臺經濟的壟斷效果認定也不應僅考量是否存在壟斷高價,對零價格和低價補貼等新型壟斷手段也應加以重視。為此,有必要探索壟斷認定的合理指標。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提出可競爭性理論,主張從動態角度進行壟斷認定。可競爭性理論認為,如果該市場的進入和退出不存在沉沒成本,即該市場是可競爭的,那么即使在壟斷產業中,壟斷者也會制定一種維持價格以獲得平均利潤,而不是制定壟斷高價。基于可競爭性理論,可以嘗試脫離市場份額這一傳統指標,通過判斷平臺所在市場是否為可競爭市場,即是否受到潛在進入者的威脅,來認定該平臺是否存在壟斷性質。
4.2 加強全程治理
傳統的市場治理大多是事后監管,這種監管模式已不再適用于平臺的監管治理。針對具有較強隱蔽性和即時性的平臺壟斷行為,應采用事前、事中、事后相結合的全方位監管。在加強事前預警方面,對壟斷風險高的敏感行為必要時可采用強制執法手段,如采取臨時禁令制度[7],即在確認違法前直接禁止平臺的某些行為,以解決反壟斷執法機構存在的滯后管理問題。在提高事中監管方面,由于特定行為產生的結果尚未確定,所以此時對其進行差異化管理與精準施策最為有效。對明確危害市場公正的行為,如“二選一”、不合理屏蔽、大數據殺熟等,應施以嚴厲的強制措施進行整頓。對尚未有明確危害、對提高效率有所促進的行為應保持觀察和柔性監管。在健全事后監管方面,監管機構應將大數據等互聯網工具融入調查取證、監管治理工作中,促進監管智慧化、精準化。此外,應重點健全各地消費者保護協會的維權渠道,完善行業內壟斷行為舉報制度,開發第三方監督機構與平臺,構建全方面、多層次、寬領域的維權與監管渠道。
4.3 打造專業隊伍
加強對平臺的監管,離不開高素質的專業化隊伍。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各級反壟斷監管機構執法人員整體規模偏小、力量較為薄弱,一些平臺體量較大的省區市如江蘇、上海也僅有20人左右從事反壟斷執法。因此,必須根據平臺規模和監管需求適當擴大反壟斷隊伍。同時,平臺反壟斷監管需要有法律、經濟、互聯網技術等領域的交叉知識,而我國反壟斷監管尚在發展階段,監管與執法人員經驗較少、專業能力相對欠缺。所以要加強對相關人員的培養與培訓,不斷提升其業務素養和執法水平。此外,各地方市場監管機構還存在執法尺度不一、執法水平不齊等問題,容易影響執法公正性,降低執法威信。各市場監管部門應完善協調溝通機制,對齊執法尺度,形成平臺反壟斷的執法合力。
4.4 推進制度規制
當前,我國反壟斷法仍存在威懾不足等問題,無法強有力地對平臺經濟產生應有的法律約束力。政府應完善并賦能新監管規則,加大對某些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以保證平臺合規工作落到實處。此外,傳統市場監管以事后懲戒為主,平臺反壟斷主要是外源動力,自我治理常常被忽視。就域外經驗而言,韓國出臺的反壟斷合規評級機制[8]通過獎勵的方式激勵平臺開展自我合規,彌補了傳統反壟斷機制存在的內生動力不足的缺陷。這一成功范例值得我國平臺經濟反壟斷加以借鑒并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