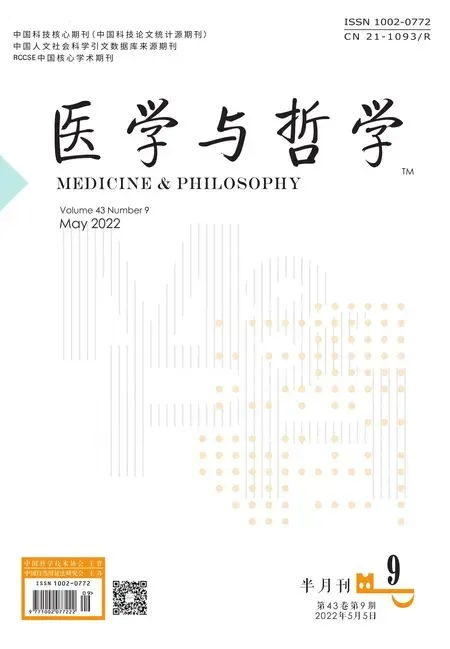具身學習視角下當代醫學教育的問題與改進探析*
張 玥 楊君潔 鄭佩瑤 沈瑞林
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在西方的心理學、哲學、神經科學等領域中,具身認知、具身心智、具身化等概念日益被廣大研究者所提及和關注。在課程教學中,基于被教育者視角的主體體驗逐漸得到關注,目前比較流行的自主學習、主動學習、深度學習的理念及問題式教學、案例式教學、小組式學習等教學方法,都是對具身學習理論的一種實踐回應。但是,如何將具身學習理念運用于課程教學過程,形成課程教學要素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生成,需要結合醫學教育管理和教學實際,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因此,研究旨在立足于具身學習理念,分析當前醫學教育教學中的非具身化現象,闡明上述課程教學要素之間的具身關聯,并嘗試給出一定的改進建議。
1 具身學習
一般意義上的課程教學要素可以劃分為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組織形式。在教師主導式的課程教學中,包括教學內容與方法組織在內的課堂情境,基本上都是源自于教師主體性的教學價值判斷。自古希臘時期到20世紀末以來,身體在教育中一直受到貶抑或忽略,身體要么被視為走向真理的障礙,要么只是一個把心智帶到課堂的容器。因此,學習被視為一種可以“離身”(disembodied)的精神訓練。
傳統認知以身心二元論為基礎,把心智劃分為認知、情感和意志三階段,認為認知是理性的標志,是心智過程的根本;傳統教育受官能心理學影響,以“形式訓練”通過對記憶、思維等“官能”的強化訓練來提高心智能力,再遷移至其他學習內容。這種基于心智的訓練缺少身體的感覺運動體驗或身體的空間位置等成分的參與,忽視了學習過程中的身體活動及其對學習結果的直接影響。
真正把身體作為學習的主體,強調身體對心智塑造作用的是法國現象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他在著作中以“肉身化的主體”替代了傳統哲學中的“意識主體”,提出認知、身體、環境一體觀[1]。海德格爾“being-in-the-world”概念清楚地體現了三者之間的整體聯系,即心智在大腦中,大腦在身體中,身體在環境中。Goldman等[2]將身體對認知活動的影響概括為身體解剖學的解釋、身體活動的解釋、身體內容的解釋、身體形式的解釋。具身認知觀中的身體,除了我們通常所指的解剖學意義上的身體外,它還指一種經過“歷史進化”(evolved)了的身體,處于特定情境中的“情境性”(situated)的身體,“社會化”(socialized)了的身體,以及形成了身體圖式(body schema)的身體[3]。因此,具身學習強調環境的影響力。因為具身學習主張把心智根植于身體,而身體根植于環境,需要從身體與環境互動的視角看待學習。學習并不是孤立的,同時受到內部與外部雙重影響,具身學習就是達到心理、身體、環境動態平衡。
2 醫學教育中的非具身化現象
從生物醫學模式到現代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顯示出醫學發展在自然屬性和人文屬性中的不斷調和。但這一現代醫學模式是否已經扎根于醫療實際、醫學教育實際,還難以下定論。有學者指出當代醫學存在的一個危險傾向就是淡化、弱化、虛化臨床認識主體的“身體看”,深化、強化、實化“機器看”[4],醫學的確定性和與之相隨的標準化教育成為難以實現具身學習的直接誘因。研究關注到當前醫學教育中兩種典型形式的教育是課堂教學和虛擬教學,這兩種教學形式具有不同的實施特點,在具身學習的要求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別。
2.1 現實醫學教育中學生的身體和思想難以“雙在場”
現實的情況常常是,學生的身體在教室里,但思想游離之外;或者是在學習的情境里,學生的思想并未與身體高度關聯,學習效果停留在表面的知識型記憶,缺乏內在的邏輯性整合。這個問題指向在高等醫學教育中、在大學課堂中,如何打破身心二元對立,實現學生身體和思想雙在場。
傳統的形而上學理論中,身體僅狹隘地指向動物性的、肉體性的客觀存在物,精神則是具有意識、思維的人的本質性存在。但具身學習首先明確“身體既關系到知覺又關系到實踐,因而能使我們超越主體和客體的二元性”[5],從生命出發的教育實踐就表現為一種“身體實踐”,即完成對身體的塑造和改變,將身體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并賦予其更多可能性的過程[6]。教育過程對學生身體的忽視,實質上就是對他們生命本真狀態的忽視,更是對他們生命本質的一種扭曲。因此,醫學教育需要在身體轉向的視角下看待如何實現學生身心統一的學習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首先來自于醫學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以及教師,需要改變以往單一的教學觀,以身體轉向為基點,協調醫學教育的整體設計、課程的縱橫關系和課堂教學的變革。
僅以課堂變革為例,情境化的教學創設是具身學習實現的積極途徑。例如,在解剖學課程中,如何創設學生從人體器官和捐獻中領悟生命價值真諦的情境?在細胞與微生物課程中,學生如何能從病毒、細菌感受到疾病背后的故事?在公共衛生的課程中,能否幫助學生從“重治療、輕預防”到全生命周期的概念變化形成整全的健康觀?在若干臨床課程中,能否引導學生透過疾病著眼到患病之人?等等。
2.2 虛擬醫學教育中學生身體和思想“雙缺場”
21世紀以來,現代技術輔助教育極大地豐富了教學手段與方法,以線上課程為表現的虛擬教育發展尤為突出。客觀來看,這種虛擬教育技術和形式突破了教學的時空限制;但從效果來看,虛擬教學的實效性難以簡單評價。
以線上學習為例,教師和學校何以能確保學生完成學習要求、達到學習效果?慣常的方式是網絡點名、要求發言、布置作業、閱讀資料等,但在教師無法肉眼目睹學生“身體在場”的情況下,其“思想在場”更是難以保證。一個關鍵的前提是,每個學生都是一個特殊的“我”的存在,這個特殊不是指思維、精神、意識,而是根本性的身體。身體作為教育與文化的連接場域意味著“脫離了身體談社會、文化和教育的關系,相當于抽空了根基和底座來思考問題”[6]。以臨床醫學課程的學習為例,如果學生只是從先驗的知識里機械記憶闌尾切除術的臨床指征,而并未形成以病人身體為基點的社會、文化與教育的關聯,他畢業行醫后對于病患是否需要手術的判斷將會陷入主觀和盲目。
另一個維度,梅洛·龐蒂的知覺概念強調身體的體驗與感覺能力,認為對于人的存在而言,身體的感覺因素要比單純的理性思維更為切己、更為本原,因為人的生活和幸福歸根到底要靠其社會化的“五官感受”和心靈感受來體驗[7]。例如,一些醫學生因為從小耳濡目染長大后會以醫生父母為榜樣,護理專業的很多學生在初學靜脈穿刺時都是用自己的手和同學的手作為試驗,等等。
那么聚焦醫學教育和課程中,如何規避上述消極因素、引入更多的積極因素,用更多融合身體體驗與感覺的教學形式,從虛擬但具體的醫學教育情境中生發出與學生個體密切相關并能引起心靈共鳴的切身體會,可能是解決當下虛擬醫學教育中學生身體和思想“雙缺場”問題的要害。
2.3 學生難以實現時間和空間碎片化的有效整合
這一問題來自于身體本身的含混性及內涵的豐富性[7]決定了醫學教育必須是一種全面的教育。區別于以往將身體教育責任劃分給體育課、活動課的簡單認知,按照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教育要求,德育、智育、美育、勞育都是醫學生身體教育中關于總體和諧的追求。如果將健康的體魄視為學生身體教育的顯性目標,那么醫學生的品德教育、智力發展、審美能力等就是身體教育的潛在追求。當前醫學生面臨的學習實際是:一是醫學學科交叉與知識膨脹導致學生的學習壓力不斷增加;二是復雜教育技術手段輔助教學可能引發的教學內容膚淺化和技術理性傾向;三是知識膨脹與技術泛化的延伸問題,即醫學生個體在現實與虛擬空間下的學習有效性問題,也就是說,學生是否具備應對、處理復雜醫學信息與技術的發展性能力。
現行醫學教育教學模式亟需應對這種交叉膨脹而進行變革,同時規避技術至上、強化人文,需要在醫學教育中,幫助學生綜合運用現實的、虛擬的教育空間,形成有效整合時間碎片化與空間碎片化的時空統一能力。早在2002年,《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就為各國醫學教育發展提供了國際標準,共計7個方面,分別為:醫學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交流與溝通技能,臨床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維[8]。仔細分辨可知,這7個方面和細化的60項要求絕不僅僅是線性的、固化的從醫能力目標,而是立體的、發展的醫學教育標準[9]。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于2003年頒布《本科醫學教育全球標準》,經修訂的《本科醫學教育質量改進全球標準》于2012年問世。標準共計9個領域和36個亞領域,其中有5個一級指標、7個二級指標和29個相關描述與人文醫學密切相關[10]:全球衛生、自主學習、人口與文化環境、學科知識的縱橫整合能力、社會責任等已經成為本科醫學教育質量改進的全球標準,這意味著將醫學教育置于大教育范疇內去審視的結果得到了國際間的認同。上述標準實際是對醫學教育在激發醫學生有效整合時空碎片化能力方面提出了要求,而這些要求恰恰需要在具身學習的理念下才有可能實現轉變。
3 當代醫學教育的改進思路
醫學人文界的諸多學者已經對醫學教育進行了不同角度的闡釋。一方面,醫學主要是人性的醫學;另一方面,醫學是科學與文化相融基礎上的醫學,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在醫學根本的價值上具有的一致性。醫學人文應融入臨床并貫穿全程,建立適應新時期的高素質醫學人才培養模式。
3.1 構建“環境-身體”二元統一的醫學教育
如前所述,理想狀態的學習是將個體心智根植于身體,身體根植于環境,這樣才能實現學生身體和思想“雙在場”。作為“人”學的醫學,對醫學生基于身體和環境的學習體驗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那么,以結果為導向,反推醫學教育的變革,首先需要考慮環境的問題。例如,醫學院校的整體環境是否人文,學校硬件設施和軟環境建設是否能夠給予學生醫德醫風的熏陶,醫學院校的校風、校訓、校史教育是否具有實效、是否能夠給學生帶來持續的精神動力,這與美國教育體系中的隱性教育理念基本一致;學校的師生關系、生生關系是否具有溫度,這也會影響醫學生生命觀的塑造。
其次,關于身體的考慮。如果具備了上述的和諧環境,如何讓身體處于其中并與環境融為一體?在現實的教育時空中,需要設計更多的、立體的幫助學生身體體驗環境的機會和可能。在學校教學管理和課程建設方面,國外有可參考的經驗:哈佛醫學院自1985年啟動Pathway項目以來,已經從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專業訓練中的人文滲透和隱形教育三個方面強化了醫學人文教育[11]。其中重要的做法是醫患關系類課程貫穿于臨床前期以及整個臨床教學階段;教育內容突出教育實效性,關注現實問題,按照理論教學和臨床需求來組織,教材或講義內容參考法律雜志、醫學倫理學雜志和醫學衛生政策期刊。
因此,在課堂教學層面,僅僅關注書本知識就是身心對立的教學,引導學生將書本知識形成內在轉化就是基于身體的教學,常見的學習內化方式如結合案例的教學、基于問題的學習、設定學生自主學習、情境教學、翻轉課堂等。在情境教學方面,標準化病人參與教學模擬、細讀經典和撰寫平行病歷、進行敘事醫學教學、情景劇形式教學是近年來國際醫學教育中呈現的積極經驗。
3.2 創設具身情境的虛擬醫學教育
虛擬醫學教育的意義在于讓學生收獲現實課堂無法完成或需要在課后反復訓練的技能。但事實上,我們的若干課程開始使用慕課和教學視頻串聯起一門課程的教學時,虛擬醫學教育出現了脫離身體談學習的傾向,學生無法通過感受來體驗學習,就會導致身體思想“雙缺場”的結果。
因此,第一需要注意的是教師需要更新教育理念和設計。虛擬課程教學并非就是簡單化的專題視頻教學、若干自測題、形式化的學生留言和助教回復,教師需要在虛擬課程的時空下,對課程教學進行具身情境的思考、設計、實施、反饋和循環的改進。例如,闌尾炎切除術臨床指征教學,教師可以通過設計若干要素(急性、慢性、化膿性、壞阻性、蛔蟲性、穿孔、并發、保守治療、72小時效果等)引導學生甄別,同時納入心理、社會要素(如恐懼手術、有過誤診經歷、要出差、無人陪伴等)與臨床要素進行組合,通過學生小組學習制定不同情境下的治療方案,在虛擬條件下引導并激發學生思想在場。因此,基于具身情境的虛擬課程教學對教師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這將會促進人機結合的虛擬醫學教育走向進步。
第二個需要注意的是,虛擬教學目前的定位仍然是傳統課堂教學的有效延伸。對生理學、診斷學等課程來說,使用虛擬仿真實驗,幫助學生鞏固訓練則是最優;對預防、人文、中醫等課程來說,引入打動人心的經典閱讀、電影欣賞、醫美結合的作品鑒賞也是具身情境的學習方式。據統計,美國經認證的醫學院校有133所,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占總教學課時數的20%~25%,其中68所醫學院校將人文類課程列為必修課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等24所知名醫學院校開設醫患關系課程[12]。紐約大學醫學院將藝術鑒賞引入醫學教育,建立集文學、藝術、醫學素材為一體的免費共享資源庫,為醫學人文教育提供便利的教學和科研資源[13]。
3.3 樹立時空統一下醫學生的全面發展觀
僅僅依靠有限的現實教育和延伸的虛擬教育,醫學生面對復雜醫學知識及身體的含混性很難在幾年的大學教育中收獲全面的發展,尤其是難以形成醫文結合的綜合素養。有學者具體闡釋人文崗位勝任力包括6個方面:判斷診療實踐及其他醫療實踐是否安全、效優、價廉的能力;確定并評價處理診療實踐中倫理、社會、法律問題是否適當的能力;醫患和醫際溝通的能力;適應社會、醫療體制、醫療團隊合作的社會適應力;對患者關愛和親和的能力;對各種困難、挫折的心理承受力[14]。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通過現實、虛擬教育空間的利用,幫助學生形成有效整合時間碎片化與空間碎片化的時空統一能力,并轉化為知識遷移的學習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因此,全面發展的能力內涵還應包括確定個體發展的軸心能力、嵌套多重任務的自我管理能力、日常生活管理能力等。從這個角度來說,醫學生的全面發展是醫學院校、教師、輔導員、管理者等相關利益者們共同作用的結果。
4 醫學教育課程的具身設計
上述關于具身學習現象和問題分析不僅涉及到醫學教育的管理改進,也涉及到微觀層面的課程建設。這里僅就微觀層面的醫學課程教學為例,以根植原則(grounded principle)[15]進行具身化的情境教學案例設計。
(1)主題聚焦。學習者進入教育過程中,由于環境條件或個體本身的變化,個體的初級平衡可能被打破,個體的學習需要學校、教師幫助學習者在心智、身體和環境之間確定不平衡點,并且幫助他們在更高水平上恢復新的平衡。那么作為教師,你能否著眼于教學的內容、方法及過程,把握到學生在課程教學中呈現的不平衡點,進而進行針對性的螺旋上升式的平衡建立。
(2)認知吸取。學習者進入新的環境后,最初的學習動力主要來自于環境的壓力。如何將外在壓力轉變為個體內在的需求,是醫學教育教學過程中的認知汲取。那么作為教師,你能否通過具身化的學習環境,引導學生轉變“必須學”的壓力,轉變為“我要學”的動力。
(3)社會參與。學習不是孤立于個體內部的私有過程,具有內部學習需求的個體加入到社會互動中,通過陳述、表達等方式互相分享觀點,并對觀點進行修正,醫學教育教學需要實現個體-環境的互動。社會參與原則聚焦于課堂環境,就是要教師不僅關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更要考慮方法與內容的匹配度及與課堂教學環境的適切性,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4)社會結構。這里的社會結構是指學習者所處群體的關系模式。在學習者所處的群體中,包括了熟手、專家、初學者和新手,群體間的相互影響和限制也是醫學教育教學中需要注意的方面。課堂教學的人群結構主要是教師和學生,如何發揮學生中較易成為熟手的群體效應,將之擴散為以教學班級為單位的整體效應,取決于教師是否具有具身教學的設計安排和教學班總人數的控制。簡單來說,教學班總人數越少,客觀上這種擴散效應越容易形成,因此在教學管理中我們倡導中小班教學。但考慮到教學實際,大班教學中,如果授課教師在開課前進行較為充分的具身課堂設計,也能夠以師生、生生互動的辦法,促進課堂積極學習結構的形成。
具身學習和根植原則對醫學課程的微觀教學提出了情境化的要求。身體經驗在情境的展開中獲得實現,學生或教師在這種情境中體驗到接觸知識的快樂,體驗到身體的意志和歸屬,情感的心智和理智的心智在這種情境中雙雙獲得成長[16]。當然,根植原則只是具身教育中的一個典型,具身的認知和教育還有更多的原則可參考。但是,如何在具身學習視閾下,去看待當代醫學教育的問題和改進,尤其是發揮醫學人文在醫學教育中的應有作用,正如美國學者Pellegrino[17]所說:“醫學人文學科在醫學中具有正當的合理位置,它不應只是一種紳士的品質,不是作為醫療技藝的彬彬有禮的裝飾,也不是顯示醫生的教養,而是臨床醫生在做出謹慎和正確決策中應必備的基本素質,如同作為醫學基礎的科學知識和能力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