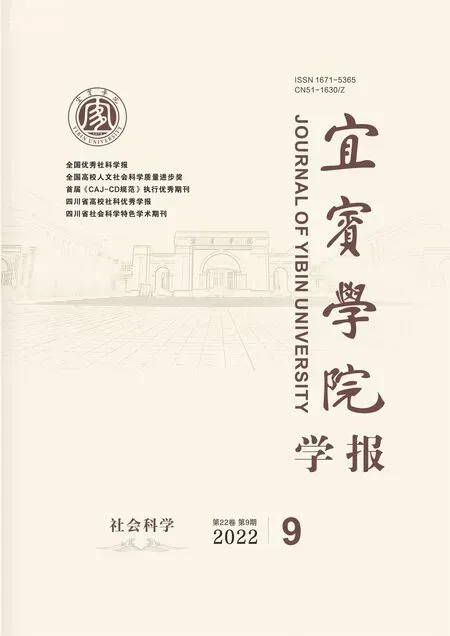論“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中的作用
李勇
(中國政法大學(xué)民商經(jīng)濟(jì)法學(xué)院,北京 100088)
“權(quán)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簡稱《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在適用過程中難以繞開的一個要件。“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歸根結(jié)底是一種造成競爭性損害的行為,也即特定行為因為參與市場競爭并造成競爭性損害,并產(chǎn)生不當(dāng)?shù)氖袌鲂Ч环稍u價為不正當(dāng)競爭”[1]。我國《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二條也將“合法權(quán)益”的損害確定為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構(gòu)成要件之一。在缺乏明確的具體行為列舉條款的情況下,權(quán)益的受損一般是司法實踐中必然進(jìn)行論證的一個問題。如何理解“權(quán)益”的作用,關(guān)涉到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實然結(jié)構(gòu)。
但是,目前我國無論在司法實務(wù)界還是學(xué)術(shù)界,對于“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中應(yīng)當(dāng)發(fā)揮的作用,均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解。其中,有的觀點繼承了侵權(quán)法理論,將“權(quán)益”視作侵權(quán)法中的“絕對權(quán)利”加以保護(hù);有的觀點則嘗試開創(chuàng)新的分析路徑,將“權(quán)益”一律視為一般的利益,通過利益之間的衡量來判定行為的正當(dāng)性。這些觀點殊途同歸,均造成了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的擴(kuò)大以及法律確定性的降低,違背了《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應(yīng)當(dāng)秉持的價值取向。因此,本文試圖在分析總結(jié)現(xiàn)有問題的基礎(chǔ)之上,以《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應(yīng)有的價值追求作為依據(jù),借鑒其它部門法理論,探索一種新的“權(quán)益”適用范式。
一、對“權(quán)益”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中作用的兩種誤解
對于“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中的作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wù)界主要分為兩類觀點,本文將其歸納為侵權(quán)范式和利益衡量范式。在侵權(quán)范式的理解下,“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中起到?jīng)Q定性的作用,而在利益衡量范式的理解下,“權(quán)益”則又變成了可有可無的、被忽視的要件,這兩種觀點都存在著一定問題。
(一)侵權(quán)法范式:對“權(quán)益”作用的過度重視
在我國的早期理論和實踐中,對于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判斷,“權(quán)益”往往成為其中的決定性要件。是否存在經(jīng)營者的合法權(quán)益以及其受損與否,是分析不正當(dāng)競爭的重點所在。這種觀點濫觴于最高院“海帶配額”案,其判決將“其他經(jīng)營者的合法權(quán)益確因該競爭行為而受到了實際損害”明確為不正當(dāng)競爭的一個必要前提①。雖然“海帶配額”案并未將合法權(quán)益的受損確立為構(gòu)成不正當(dāng)競爭的唯一要件,但卻是首次確立了“權(quán)益”的地位,為此后理論和司法實務(wù)開始主張的侵權(quán)范式打下了基礎(chǔ)。
理論界以學(xué)者吳峻的觀點為代表。其將合法權(quán)益受損理解為“海帶配額”案三條件的“重心”,甚至認(rèn)為,如果“侵害他人權(quán)益,就違反了誠信原則及公認(rèn)的商業(yè)道德”,直接將商業(yè)道德要件的判斷也借助“權(quán)益”來完成[2]。這相當(dāng)于將經(jīng)營者合法權(quán)益的受損結(jié)果等同于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全部構(gòu)成要件,是典型的侵權(quán)法中“權(quán)益損害征引不法”的認(rèn)定思路。
實務(wù)界同樣開始出現(xiàn)這種侵權(quán)式的判定思路。在作為指導(dǎo)性案例的“百度訴聯(lián)通青島”案的二審中,山東省高院直接根據(jù)百度公司商業(yè)模式、經(jīng)濟(jì)利益和商業(yè)信譽(yù)的受損推導(dǎo)出聯(lián)通青島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商業(yè)道德的結(jié)果②。相當(dāng)于將商業(yè)道德標(biāo)準(zhǔn)的判斷也訴諸經(jīng)營者權(quán)益受損的事實,實際上消融了“海帶配額”案中確立的第三項商業(yè)道德條件本身的獨立意義。又如“愛奇藝訴飛益”案,法院在認(rèn)定愛奇藝的“依托于視頻訪問數(shù)據(jù)獲取的商業(yè)利益”應(yīng)受保護(hù)后,認(rèn)為被告對于這一數(shù)據(jù)進(jìn)行的干擾、破壞行為即違背了商業(yè)道德③。這同樣是將“合法權(quán)益受損”等同于“違反商業(yè)道德”的思路。以此為代表,司法實踐往往看似遵循了“海帶配額”案的三條件標(biāo)準(zhǔn),實際卻只分析了合法權(quán)益的損害,并由此論證商業(yè)道德的違反,而并沒有具體分析具有獨立性的商業(yè)道德的內(nèi)涵。通過對商業(yè)道德要件的消解,法院實際上賦予了合法權(quán)益侵害在不正當(dāng)競爭判定中的決定性地位,裁判說理的中心集中于論證被告的競爭行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quán)益,亦即遵循的是“侵權(quán)范式”。
進(jìn)一步,在這種侵權(quán)式思路的影響下,對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理解開始出現(xiàn)了“泛權(quán)益化”的傾向。通過主觀賦予《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所保護(hù)的類型化權(quán)益,進(jìn)而由該權(quán)益受損而推論出競爭行為的違法性。在理論界,有學(xué)者將《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保護(hù)的權(quán)益歸納為“不正當(dāng)競爭權(quán)”[3]“公平競爭權(quán)”[4]“自主經(jīng)營權(quán)”[5]“合同權(quán)益”和“財產(chǎn)權(quán)益”[6]等類型。而在司法實踐中,各類判決更是創(chuàng)設(shè)了名目繁多的“權(quán)益”:“自主經(jīng)營權(quán)”④、對廣告內(nèi)容的“處分權(quán)”⑤、消費者個體的“自主選擇權(quán)”⑥、“經(jīng)營自主權(quán)”⑦“用戶選擇權(quán)”⑧“企業(yè)名稱權(quán)”⑨、用戶的“知情權(quán)及選擇權(quán)”⑩等等,不一而足。
侵權(quán)范式并不具備合法性。在侵權(quán)法理論中,進(jìn)行“權(quán)利侵害征引不法”認(rèn)定的前提在于,法律明確賦予了被侵害人以絕對權(quán)利[7],因此這里的“權(quán)利”具有嚴(yán)格的權(quán)利法定的限定,且須為數(shù)目極其有限的絕對權(quán)。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顯然沒有規(guī)定市場參與者享有的任何絕對權(quán),因此無法單純依靠權(quán)益受損推導(dǎo)出競爭行為的違法性。這表明侵權(quán)范式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上的應(yīng)用缺乏法理的支撐。
侵權(quán)范式也不具備合理性。從《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行為列舉式規(guī)范即可看出,其規(guī)制的是行為,而非損害結(jié)果。亦即它更接近“行為不法”而非“結(jié)果不法”。競爭必然導(dǎo)致?lián)p害,《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并不禁止權(quán)益受損,而是禁止危害市場競爭秩序的行為。侵權(quán)范式本身顯然不符合《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競爭法品性,使得對于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關(guān)注重心產(chǎn)生了由行為轉(zhuǎn)向結(jié)果的偏移。
侵權(quán)范式還進(jìn)一步引發(fā)了衍生問題:法官證立義務(wù)的降低。一方面,侵權(quán)范式使得“海帶配額”案中的“三條件”實質(zhì)限縮為二條件,顯然是降低了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認(rèn)定門檻,導(dǎo)致了論證標(biāo)準(zhǔn)的寬松;另一方面,在侵權(quán)范式思維的影響下,法官通過簡單創(chuàng)設(shè)法律沒有明確規(guī)定的權(quán)利,來達(dá)到自己論證的目標(biāo),實質(zhì)上是對于嚴(yán)密論證程序的逃避,因此而導(dǎo)致法官的自由心證在不正當(dāng)競爭糾紛中的急劇擴(kuò)張。
(二)利益衡量范式:對“權(quán)益”作用的過度輕視
侵權(quán)范式的問題開始引發(fā)學(xué)界的反思,隨之而產(chǎn)生的是利益衡量范式。這種觀點主張不應(yīng)當(dāng)通過權(quán)益損害而簡單地推論出不正當(dāng)競爭,而應(yīng)當(dāng)通過市場中多方利益的權(quán)衡,以實現(xiàn)整體效益最大化為目標(biāo),對競爭行為的性質(zhì)做出判斷。相較于侵權(quán)范式,利益衡量范式本身有其合理性,也更接近于《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價值目標(biāo)和法律品性,是一種進(jìn)步的觀念。
但是對于利益衡量的過分推崇卻也會引發(fā)問題。對于利益衡量的強(qiáng)調(diào)導(dǎo)致了對“權(quán)益”作用的輕視。例如孔祥俊教授就認(rèn)為:“我國《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所保護(hù)的合法利益,乃是制止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結(jié)果。”“不正當(dāng)性或者違法性的基礎(chǔ)和依據(jù)是對于行為本身的否定性評價,而不是從保護(hù)靜態(tài)的或者動態(tài)的利益出發(fā)的結(jié)果。簡言之,此類利益因受到制止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保護(hù)而成為法益,而不是因首先是法益而受到保護(hù)”[8]。這意味著“合法權(quán)益”只具有一種“反射利益”的地位,其并不具有作為不正當(dāng)競爭構(gòu)成要件的作用,而只是規(guī)制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一個附屬性的結(jié)果。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現(xiàn)實可行性的缺乏。利益衡量理論符合《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應(yīng)然層面的根本價值追求,卻不符合實然層面的司法實踐需要。正如形而上的終極追求往往因為人類理性的先天局限性而造成現(xiàn)實中的事與愿違。利益衡量范式、以及為實現(xiàn)效益最大化而采用的經(jīng)濟(jì)分析方法,要想達(dá)成科學(xué)合理的結(jié)論,需要投入大量調(diào)查成本。而和擁有較多執(zhí)法資源的反壟斷實踐不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司法實踐往往只能憑借法官依據(jù)當(dāng)事人雙方提供的材料而進(jìn)行的“紙上談兵”,而缺少進(jìn)行市場分析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調(diào)查資源。因此即使法院在近些年來開始在判決中應(yīng)用利益衡量分析方法,其論證過程以及最終結(jié)論卻依然不令人信服,甚至存在著矛盾。
例如著名的“騰訊訴星輝”案,針對同一個屏蔽廣告行為,一審、二審?fù)瑯舆\用了利益衡量的分析范式,卻對于公共利益的增損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一審判決認(rèn)為,屏蔽廣告行為保障了用戶的知情權(quán)、選擇權(quán),促進(jìn)了商業(yè)模式的更新,亦不會對視頻網(wǎng)站產(chǎn)生毀滅性打擊,因此有利于社會公益的增加;二審法院卻認(rèn)為,屏蔽廣告行為有利于消費者短期利益,不利于長期利益,會威脅到視頻網(wǎng)站的生存,因此會造成社會公益損失?。
又如,在“愛奇藝訴搜狗”案中,原告愛奇藝認(rèn)為搜狗通過在輸入法中的誤導(dǎo)行為,導(dǎo)致用戶在愛奇藝網(wǎng)站進(jìn)行視頻搜索后,進(jìn)入了搜狗搜索引擎的視頻結(jié)果。法院認(rèn)為,“一方面,如前所述,被控行為未能完全避免用戶產(chǎn)生混淆;另一方面,被控行為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消費者的福利。”這種消費者福利指向的是搜狗跳轉(zhuǎn)的結(jié)果為用戶提供了更多的視頻選擇。最終判決認(rèn)定,消費者因選擇增加而獲得的利益要大于因混淆而帶來的損失,因此否定該行為的不正當(dāng)競爭性質(zhì)?。
上述案例體現(xiàn)了司法實踐運用利益衡量范式的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不同種類利益之間的定性取舍。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體系內(nèi),各個市場參與者以及不同類型的利益之間應(yīng)當(dāng)接受的是等序保護(hù)[9],不同的利益在同一價值位階上進(jìn)行考量[10]。肯定或否定某種競爭行為,往往都意味著保全一種利益而犧牲另一種利益。而對于具有同等地位的利益,上述判決并未充分說明為何利益A在重要性上就大于利益B,由此產(chǎn)生了對于同一種法律事實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利益傾向:“騰訊訴星輝案”中,在用戶的知情權(quán)選擇權(quán)、視頻網(wǎng)站現(xiàn)有的商業(yè)模式(以及可能的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之間,一審判決認(rèn)為后者重要,而二審判決認(rèn)為前者重要;“愛奇藝訴搜狗案”中,在因混淆而導(dǎo)致的用戶知情權(quán)受損,以及因跳轉(zhuǎn)而帶來的用戶選擇權(quán)增加之間,判決認(rèn)為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在不同種類利益之間進(jìn)行的選擇缺乏充分的理由,而似乎完全取決于法官的主觀決斷。
其次的問題是同一種類的利益之間的定量分析。例如“騰訊訴星輝”案中,一審判決認(rèn)為屏蔽廣告行為不會對視頻網(wǎng)站造成毀滅性沖擊,后者仍有應(yīng)對的技術(shù)手段,而二審判決則認(rèn)為屏蔽廣告行為是對于視頻網(wǎng)站的“降維打擊”,后者絕無規(guī)避可能。被告的行為到底會對于原告經(jīng)營造成何種沖擊,往往決定了是否應(yīng)當(dāng)對該行為予以禁止。但這涉及對市場競爭的細(xì)致定量分析,并且這種分析在每一起個案中都因競爭者的具體經(jīng)營狀況、經(jīng)營環(huán)境而有所不同。而當(dāng)下的司法實踐中,我國法官既缺乏進(jìn)行定量經(jīng)濟(jì)分析的專業(yè)知識和經(jīng)驗,也鮮有依據(jù)職權(quán)直接進(jìn)行就有關(guān)數(shù)據(jù)進(jìn)行調(diào)查取證的行為。結(jié)果便是在上述案件中,法官所得出的結(jié)論背后缺乏有力的證據(jù)和論證的支撐,更多的是依據(jù)現(xiàn)有的事實和自己的樸素價值觀念進(jìn)行邏輯上的推演。
上述問題并非僅存在于個案,而是利益衡量范式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司法實踐運用中的普遍問題。司法實踐的現(xiàn)實注定了對于利益衡量只能進(jìn)行帶有濃厚主觀色彩的、略顯粗糙的定性分析,而非定量分析。由于不正當(dāng)競爭案件中的行為往往涉及范圍甚廣,引發(fā)的是多方市場主體的利益增損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變動,而非民法中局限于雙方當(dāng)事人的利益變更,這就導(dǎo)致了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糾紛中進(jìn)行利益衡量的高難度。當(dāng)多種價值或利益難以直接斷定誰更具有優(yōu)先性的時候,最終的結(jié)論就很難具有說服性以及穩(wěn)定性,而更讓人認(rèn)為是法官的自由裁量在其中占據(jù)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帶來的結(jié)果是不正當(dāng)競爭判決本身客觀性的下降,乃至《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作為法律的確定性的缺失。
盡管不同于理論界過于強(qiáng)調(diào)利益衡量而忽視了權(quán)益的作用,司法實踐在形式上仍然大體遵循著“海帶配額”案的三條件模式,依然將“合法權(quán)益的損害作為認(rèn)定不正當(dāng)競爭的一個構(gòu)成要件。但是在利益衡量范式的驅(qū)使之下,“權(quán)益”作為構(gòu)成要件,已經(jīng)在司法實踐中被極大地弱化,甚至僅僅起到一個“走過場”的作用。很多判決簡單地將權(quán)益損害等同于經(jīng)營者的商業(yè)利益受損、交易機(jī)會流失等,但這一認(rèn)定幾乎是“不證自明”的:試想哪個經(jīng)營者提起不正當(dāng)競爭之訴的前提,不是自己的商業(yè)利益受到損失或威脅?因此權(quán)益損害的認(rèn)定幾乎成為判決中“正確的廢話”。
總體來說,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wù)界,近些年來都出現(xiàn)了在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中強(qiáng)調(diào)利益衡量、忽視或者極度弱化權(quán)益地位的趨勢。利益衡量本身具有合理性,卻缺乏一定的可行性,特別是在利益存在沖突,很難通過定性比較得出結(jié)論,又缺乏定量調(diào)查的資源支持的情況下。利益衡量范式最終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法官過高的自由裁量度,以及法律確定性的缺失。
二、賦予“權(quán)益”新地位:《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對預(yù)見性和謙抑性的要求
實際上,上述的兩種誤解,無論是對于《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中“權(quán)益”的過度看重還是過度輕視,導(dǎo)致的都是一個共同的結(jié)果: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中過度追求“正當(dāng)性”而忽視了“合法性”。“合法性”要求《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闡釋和實踐應(yīng)當(dāng)具備一般法理意義上的謙抑性與可預(yù)見性,這要求盡可能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賦予市場競爭中的參與者以穩(wěn)定的行為預(yù)期。事實上,“過度寬泛的、不確定的保護(hù),同時也為不合理的保護(hù)提供了土壤”[11]60,在這種意義上,合法性的缺失也會造成正當(dāng)性的損害。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對于提升“合法性”的需求,是讓我們反思以及修正“權(quán)益”地位的基礎(chǔ)所在。
(一)微觀層面:競爭參與者的可預(yù)知性
“課以法律責(zé)任必須符合‘期待可能性’ 理論,即只有在加害人對自己的行為義務(wù)有所預(yù)見,但是仍然違反該行為義務(wù)導(dǎo)致的損害才能課以責(zé)任”[12]。特別是在競爭行為中,由競爭帶來的損害往往是“純粹經(jīng)濟(jì)損失”,純粹經(jīng)濟(jì)損失不同于邊界清晰的絕對權(quán)利,它所指向的對象具有高度的廣泛性和不確定性。一旦對于這類損失給予寬松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那么此類糾紛就會像洪水一樣泛濫開來,這將使得被告“在不確定的時間,對不確定的人,承擔(dān)數(shù)額不確定的責(zé)任”[13],因此需要法律發(fā)揮水閘的作用,以限制這種不確定性,這正是法律中的“水閘理論”[13]。
“水閘理論”應(yīng)當(dāng)成為規(guī)范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考量。從競爭者個體角度來看,良好的經(jīng)營業(yè)績需要以經(jīng)營自由作為保障,而經(jīng)營自由的實現(xiàn)則需要通過法律劃定一個邊界,“該邊界的存在和效果在于,邊界內(nèi)的個人有一個安全、自由的空間”[14]。“保護(hù)競爭者對其行為的合理預(yù)期,是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重要功能”[2]。唯有如此經(jīng)營者才能充分發(fā)揮其競爭活力與創(chuàng)新才能。
這種可預(yù)知性不僅僅是對“加害人”的保護(hù),也是對于“受害人”的保護(hù)。只有可能作為加害者的經(jīng)營者明確地知道自己在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潛在的受害者才能得到預(yù)防性的保護(hù)。而目前《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司法實踐中法官過高的自由裁量權(quán),往往容易導(dǎo)致對于同一類型的競爭行為,不同判決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例如同一起“瀏覽器屏蔽視頻廣告”案件,一審否認(rèn)違法性,二審肯定違法性,二者的說理思路截然不同,如同各自創(chuàng)設(shè)了兩套法律規(guī)范?。也就是在這種法院飄忽不定的態(tài)度以及缺乏統(tǒng)一依據(jù)規(guī)范標(biāo)準(zhǔn)的情況下,相同類型的案件屢次發(fā)生。
要實現(xiàn)《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預(yù)見性目標(biāo),不能依靠已被理論界否定的商業(yè)道德標(biāo)準(zhǔn)[15],如前文所述,利益衡量和經(jīng)濟(jì)分析方法也無法達(dá)成這一目標(biāo)。唯一的路徑依然是從“權(quán)益”著手。
盡管《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并非以保護(hù)權(quán)益為目標(biāo)(侵權(quán)范式也已被本文否定),但正視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中應(yīng)有的作用,有利于提升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規(guī)范的可預(yù)見性。因為一旦對權(quán)益的內(nèi)涵和地位形成穩(wěn)定性認(rèn)知,讓“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認(rèn)定中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作用,有助于市場競爭者明確自身經(jīng)營行為的邊界所在,從而激發(fā)其競爭和創(chuàng)新的動力,增進(jìn)市場活力。
(二)宏觀層面:對競爭秩序干預(yù)的謙抑性
“踐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立法精神,不僅需要司法制止擾亂市場秩序的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也需要某種程度上的司法克制,賦予市場自由競爭的空間”?。《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目標(biāo)并不在于“建立”一個競爭秩序,而在于“維護(hù)”良好的競爭秩序。這要求對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規(guī)制應(yīng)當(dāng)具有謙抑性,這種謙抑性具體體現(xiàn)在兩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謙抑性體現(xiàn)在對模糊地帶競爭行為的包容。由前文對于利益衡量范式相關(guān)案例的分析即可發(fā)現(xiàn),對于某些損益很難通過定性分析得出結(jié)論的案件,司法機(jī)關(guān)不應(yīng)當(dāng)妄加干涉。否則很容易扼殺了寬松自由的競爭環(huán)境,而過于狹隘、刻板的競爭秩序同樣是一種扭曲的競爭。
另一方面,謙抑性體現(xiàn)在對于干預(yù)界限的劃定。競爭秩序不應(yīng)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層面,而是需要具體化。所謂的“秩序”指向的其實是“界限”,而劃定這一界限的方法正是需要借助“權(quán)益”要件。“扣扣保鏢”案中,最高院就曾指出:“競爭自由和創(chuàng)新自由必須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權(quán)益為邊界”?。秩序來自于產(chǎn)權(quán)界限的明確,正如私有財產(chǎn)制度鞏固了近代歐洲的社會基礎(chǔ)一樣,企業(yè)的產(chǎn)權(quán)也是確立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的基石。如果能夠確定經(jīng)營者合法權(quán)益的邊界,那么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競爭秩序的框架。
三、權(quán)利和利益區(qū)分三標(biāo)準(zhǔn)的引入
對于“權(quán)益”的兩種誤解、《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對于預(yù)見性和謙抑性的需求,都要求重新認(rèn)識“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判斷中應(yīng)有的作用,而這需要借助民法理論。《民法典》以及民法原理為《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中的權(quán)益保護(hù)提供了基礎(chǔ)性支撐。[16]“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適用不可能完全自足自洽,仍應(yīng)以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為指導(dǎo)。如民法的法益理論和侵權(quán)責(zé)任法精神,對于確定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和法律模式具有參照和指導(dǎo)意義”[8]。“在當(dāng)前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適用中,忽略民法的根本性是在權(quán)益保護(hù)和行為判定上出現(xiàn)誤解和誤區(qū)的重要原因”[8]。
在民法理論中,對于“權(quán)益”的保護(hù)不是一概而論的,民法將權(quán)益劃分為“權(quán)利”和“利益”兩部分,權(quán)利指向的是所有權(quán)、人格權(quán)、智慧財產(chǎn)權(quán)等絕對權(quán)利,其往往在法律條文中被明確列舉出來,侵犯此類權(quán)利的行為會受到嚴(yán)格規(guī)制。以《德國民法典》為例,其規(guī)定侵犯絕對權(quán)的行為,只要主觀上具有故意或者過失(亦即具備過錯),即構(gòu)成侵權(quán)行為;而侵犯利益的行為,必須在主觀上具備故意的同時,還違反了善良風(fēng)俗,才能構(gòu)成侵權(quán)行為。其原因在于,相較于一般利益而言,權(quán)利是“密度更高”的利益,它更具有保護(hù)的價值。通過將“權(quán)益”劃分為不同等級而賦予不同的保護(hù)強(qiáng)度,民法得以兼顧對于行為主體的行動自由和正義的保護(hù)。
盡管一般認(rèn)為,《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所保護(hù)的“權(quán)益”對應(yīng)的是民法上的“利益”。但這種對應(yīng)是形式上的,即《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所保護(hù)的權(quán)益并沒有被法律明文類型化、法定化和絕對化。但在各式各樣的競爭權(quán)益中,其實質(zhì)上是可以依據(jù)值得保護(hù)的程度而劃分出等級,從而給予不同強(qiáng)度的保護(hù)。其中有一些權(quán)益具備了民法中“權(quán)利”的特征,可以在確定權(quán)益受損之后,依“權(quán)利損害征引不法”直接給予救濟(jì),而其它權(quán)益則不具備這種強(qiáng)度,因此要想給予救濟(jì)必須進(jìn)行全面的利益衡量。具體的劃分方法,需要借鑒民法理論中對權(quán)利和利益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
在德國法理論中,劃分權(quán)利與利益依據(jù)的主要是三個標(biāo)準(zhǔn):歸屬效能、排除效能和社會典型公開性[11]55。同時具備了這三個特征的權(quán)益,就具備了權(quán)利的特征,反之則應(yīng)當(dāng)屬于利益范疇。這三個特征同樣能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所保護(hù)的競爭權(quán)益中找到與之相對應(yīng)的內(nèi)容。
歸屬效能指的是某項確定的利益內(nèi)容歸屬于特定主體,其強(qiáng)調(diào)的是歸屬內(nèi)容的確定性[17]。這要求所保護(hù)的利益應(yīng)當(dāng)有明確的界限,由此能夠?qū)⑦@一范圍清晰的客體與歸屬的主體相對應(yīng)。體現(xiàn)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領(lǐng)域,要求的應(yīng)當(dāng)是權(quán)益與經(jīng)營者存在特定的、清晰的、穩(wěn)定的聯(lián)系,而這種判斷一般應(yīng)當(dāng)立于相關(guān)公眾的視角。例如在涉嫌混淆的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中,前提是商品的購買者能夠?qū)⒛骋粯?biāo)識與特定的經(jīng)營者相聯(lián)系。歸屬性是給予利益以高強(qiáng)度保護(hù)的基本前提。
排除效能是指利益主體能夠排除其它主體的任何不法干涉,這種排除性是對一切其它主體的,而非通過合同約定而成的特定主體[17]。體現(xiàn)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中,要求權(quán)益主體應(yīng)當(dāng)是通過誠實勞動而獲取了特定利益,勞動賦予了利益以商業(yè)價值,也因此具備了排他性。例如對于網(wǎng)絡(luò)用戶數(shù)據(jù)的保護(hù),單純的原始用戶數(shù)據(jù)是不應(yīng)當(dāng)?shù)玫礁偁幏ūWo(hù)的,而必須是經(jīng)過算法或簡化技術(shù)加工處理所獲得的用戶衍生數(shù)據(jù),唯有這種數(shù)據(jù)才具備不可替代性以及獨占性[18]。
社會典型公開性指的是基于人們共通的社會、文化的認(rèn)知和經(jīng)驗,對于某種權(quán)益的可識別性,這指向的是權(quán)益在一般意義、社會意義上的法律地位[17]。在市場競爭領(lǐng)域,這一特性實際上對應(yīng)的是《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公共利益屬性,一種權(quán)益之所以應(yīng)當(dāng)受到競爭法保護(hù),不是因為它僅僅關(guān)涉某一特定主體的利益增損,而是因為它關(guān)系到不特定的市場群體的利益增損。例如,基于私人之間的合同而形成的權(quán)益不具備社會典型公開性,也正因此不能因經(jīng)營者的行為損害了其他經(jīng)營者與第三方之間的合同權(quán)益而認(rèn)定具有反不正當(dāng)競爭的違法性,否則將造成《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與私法界限的混同。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上述三個標(biāo)準(zhǔn)是判斷利益本身是否值得保護(hù)的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19],它指向的是應(yīng)然的判斷而非實然的解釋。除了極少數(shù)被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絕對權(quán)之外,還有廣大的利益范圍,這其中的一些利益因具備了上述三標(biāo)準(zhǔn),而具備了如絕對權(quán)利一般的保護(hù)價值。因此在充斥著各類形態(tài)和種類的利益的市場競爭領(lǐng)域,可以借助這三項標(biāo)準(zhǔn),為這些利益劃分等級,從而給予不同強(qiáng)度的保護(hù)。
對于同時符合這三項標(biāo)準(zhǔn)的競爭利益,應(yīng)當(dāng)給予其高強(qiáng)度保護(hù),這意味著一旦這類利益受到或?qū)⒁艿綋p害,原則上實施行為的經(jīng)營者就具備了不正當(dāng)競爭的違法性,而無需再考量行為人的主觀故意或者進(jìn)行利益衡量;而對于不能同時滿足這三項標(biāo)準(zhǔn)的利益,則給予的是中低強(qiáng)度保護(hù),必須進(jìn)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只有可以得出競爭行為會顯著損害市場效益的結(jié)論的情況下,才應(yīng)當(dāng)予以禁止。
這種不正當(dāng)競爭的認(rèn)定范式實際上是“侵權(quán)范式”與“利益衡量范式”的一種折衷,而對各自進(jìn)行揚長避短。來自民法的侵權(quán)范式具有明確的構(gòu)成要件和清晰的說理路徑,其問題在于簡單地、形式化地將民法中的“權(quán)利”等同于《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權(quán)益”,而忽略了“權(quán)利”背后使其值得保護(hù)的真實特性;利益衡量范式符合《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價值指向和法律品性,但缺乏法律規(guī)范應(yīng)有的穩(wěn)定性和確定性,且缺乏一定的現(xiàn)實可行性。在根本上,二者的問題都在于沒有正確擺正“權(quán)益”在不正當(dāng)競爭認(rèn)定中應(yīng)有的位置,它既非一切違法性的決定性要件,也不是僅僅作為規(guī)制的反射結(jié)果,而是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情形,當(dāng)競爭行為指向的是具有“權(quán)利”品性的權(quán)益時,可以發(fā)揮決定作用,而當(dāng)競爭行為指向的是具有“利益”品性的權(quán)益時,則應(yīng)讓位于更加精細(xì)的利益衡量。
結(jié)語
在不正當(dāng)競爭的認(rèn)定中,我國歷來的理論和司法實踐存在著對于“權(quán)益”的誤解。無論是侵權(quán)范式對于權(quán)益的過度重視,還是利益衡量范式對于權(quán)益的過度忽視,都造成了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的擴(kuò)張、反不正當(dāng)競爭規(guī)范客觀性和穩(wěn)定性的削弱。《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應(yīng)當(dāng)具備法律規(guī)范適用的基本原理,這要求其適用過程能夠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明確的行為預(yù)期,同時限制司法對于市場自由競爭的過度干預(yù)。在這種需求指向之下,應(yīng)當(dāng)賦予“權(quán)益”新的地位,既能保證適用的客觀性穩(wěn)定性,又能不偏離《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法律品性。
本文認(rèn)為,民法理論中區(qū)分權(quán)利與利益的三標(biāo)準(zhǔn)為《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中“權(quán)益”的適用提供了重要參考。它可以將市場競爭中眾多繁雜的利益類型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對于價值較高的權(quán)益類型給予高強(qiáng)度保護(hù),其余則給予中低強(qiáng)度保護(hù)。具體而言,一項權(quán)益如果同時具備了歸屬效能、排除效能和社會典型公開性,那么對其的侵害可以直接認(rèn)定違法性,而不具有三標(biāo)準(zhǔn)的權(quán)益則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具體的利益分析,只有在通過定性分析即可得出明確結(jié)論的情況下,才可以予以規(guī)制。這種分析路徑提升了司法實踐的論證效率,又將適用模式客觀化,防止了法官的主觀臆斷對市場競爭的過度妨害,應(yīng)當(dāng)成為未來《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司法適用的新趨勢。
注釋:
①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號民事判決書。
②“這種行為破壞了百度公司的商業(yè)運作模式,損害了百度公司的經(jīng)濟(jì)利益,還會導(dǎo)致上網(wǎng)用戶誤以為彈出的廣告頁面系百度公司所為,使上網(wǎng)用戶對百度公司所提供服務(wù)的評價降低,對百度公司的商業(yè)信譽(yù)產(chǎn)生一定不利影響,同時也違背了誠實信用、公平交易的市場行為準(zhǔn)則和公認(rèn)的商業(yè)道德。”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魯民三終字第5-2號民事判決書。
③上海市徐匯區(qū)人民法院(2017)滬0104民初18960號民事判決書。
④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9)京73民終3263號民事判決書。
⑤廣州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粵73民終1022號民事判決書。
⑥廣州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粵73民終1022號民事判決書。
⑦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7522號民事判決書。
⑧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終8743號民事判決書。
⑨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終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
⑩上海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滬73民終5號民事判決書。
?北京市朝陽區(qū)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70786號民事判決書,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京73民終558號民事判決書。
?上海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滬73民終420號民事判決書。
?相關(guān)案例可見北京市朝陽區(qū)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70786號民事判決書,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京73民終558號民事判決書,廣州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粵73民終1022號民事判決書。
?上海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8)滬73民終420號民事判決書。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終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