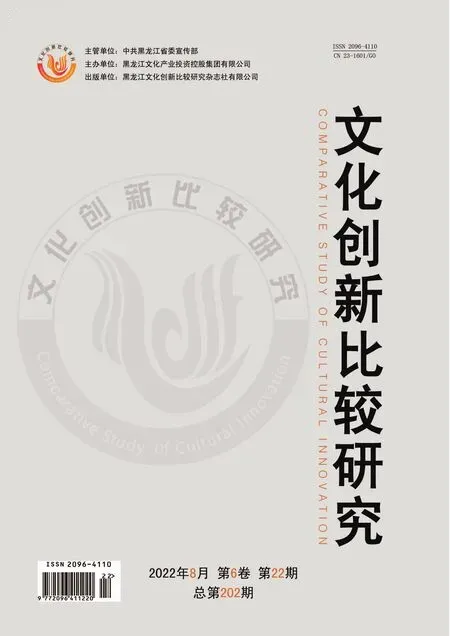芻議現代化殯葬的殯葬儀式
任俊圣
(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重慶 401331)
“現代化殯葬”是基于殯葬社會現象而構建的發展形態, 是指符合時代精神且能夠對民眾生活產生積極影響的殯葬活動, 這種殯葬活動常常是由高度組織化的、專業化的殯葬工作者發起和踐行。儀式承載了物質與精神、工作與服務、現實與希望、生與死、哀與悼、離與別等對立統一的多項范疇,殯葬儀式是現代化殯葬不可缺少且應該給予專門處理的議題。
1 殯葬現代化
“現代殯葬”是對殯葬現象的時代判定,“殯葬現代化” 是在傳統殯葬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且具有時代精神的殯葬活動變革(被時代帶動而變)和殯葬服務改革(因主體自覺而改)。 傳統殯葬執意于“死后世界”的繪制,其消極作用有:易于滑向迷信、遺落現實觀照、擾亂家庭經濟結構,有必要進行現代化變革。殯葬現代化既是殯葬服務變革的必由之路, 又是殯葬管理歷程和目標的集中表述。 傳統殯葬在傳承歷史文化的同時夾帶了消極成分, 只有推陳出新才能夠擔當起現代殯葬文化傳播者和殯葬現代化推動者的角色。
“現代化必然包括經濟上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政治上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思想文化上的世俗化與多樣化等”[1],“現代殯葬” 的表述基于對傳統殯葬的揚棄,在市場化、法治化、行業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現代殯葬應該對民眾生死觀的引導有所貢獻,而非慫恿并遵囑落后的生死觀,這是現代殯葬的現代地核心內容。 現代殯葬區別于傳統殯葬的特點包括如下內容:首先,現代殯葬是以國家意識形態為思想背景的一類社會事業,旨在加強殯葬管理,推進殯葬改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發展;其次,現代殯葬是現代先進文化的具體表現, 能夠以文明、節儉、綠色的殯葬活動建設性地在文化內涵和設施、設備外延上獲得跨越式地發展;再次,現代殯葬的自我實現不再囿于傳統、 固化的儀式活動, 而以開放包容、 兼容并蓄的胸懷使得殯葬活動的人文關懷在工作(服務)中得到自覺表述,促使現代殯葬獲得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最后,現代殯葬服務的發展指向于生者,殯葬工作者不再攀附于塑造死后世界的假象,而是對生命本身加以關注, 通過殯葬儀式等核心工作推動變革。
2 殯葬現代化進程中的殯葬儀式
2.1 儀式的一般模式及其社會功能
儀式作為一種行為程式, 可能包含特定的語言表達,這些行為和語言在現代社會中很難是自發的,也不可是隨意的,具有特定的象征內容。 儀式“向自然世界表達一些意圖、希冀、愿望或命令,所使用的表達手段是以言行事式詞語或行為, 而這些詞語或行為產生一些超越任何表達意向的意義”[2],于是,儀式過程一般都需要一個主持人的存在, 該角色使用特定語詞和行為而產生引導、示范、關系中介、傳承的作用,該引導人既可能參與其中也可能旁觀于外。在儀式行為中, 儀式的行為人通過語言和行為與特定對象產生互動,這個特定對象可能是理想自我、關鍵他人、超自然力、社會組織——均是較之個體強大的存在, 儀式過程使得儀式行為人與這個對象發生聯系并獲得虛擬的或期望的互動。儀式行為完成后,儀式行為人在心理內容上或社會關系上獲得了特定的變化,完成了特定的任務。 所以,儀式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使得現實生活中的事件莊重而有序地完成,繼而保障日常生活的穩定性、促進生活的穩步發展。
2.2 殯葬儀式的社會效用
殯葬儀式也是一種固定的行為程式, 不論表現為哪種殯葬儀式亞類。 殯葬儀式既具有將遺體(死者)送往“死后世界”的象征,也具有生者身份轉變的象征,現代殯葬儀式延存了前者、失落了后者。 殯葬儀式過程一般都有一個主持人, 該主持人的身份可能是專業殯葬工作者、風水先生、宗教教職人員、鄉紳名流、家族長者,負責對殯葬儀式的主持、引導。殯葬儀式主持人常常通過語言引導殯葬儀式行為人,現代殯葬服務中“襄儀”的角色則具有行為示范人功能。
殯葬儀式的關鍵內容是儀式行為人與實際上的抽象“死者”或期望中的“亡魂”發生互動,儀式雖表現為不同的階段和方式,但其內在的紅線為“送行”。儀式行為人的身份轉變在這種“送行”中被淡化,現代殯葬儀式僅僅保留了以“節哀順變”為表象的情感關懷,沒有集中的、明顯的對生者的關懷和祈望。 殯葬儀式的基本社會效用是使得處理遺體莊重而有序地完成、 維護日常情感生活的穩定性、 調試人際關系、轉移或者釋放情緒。對于殯葬儀式的行為人——喪屬和其他生者而言, 現代殯葬儀式具有緩沖消極變化——死亡的作用, 缺失了促進生者發生積極變化的作用。
3 現代殯葬儀式的癥狀和病因
現代殯葬儀式將自身撕裂以遷就有死性, 又企圖取信于彼岸世界。殯葬儀式將精神贈給死,將身體賣給生。現代殯葬儀式被兩股相反的力量撕碎前,需要自強、自新。 現代殯葬儀式在傳統與現代、希望與現實中尋求妥協和折中的努力被現代化的思潮和工具所顛覆,造成了自我分裂,表現出多種癥狀。
3.1 癥狀
沒有事實證明、沒有信仰支持的“死后世界”是現代殯葬儀式的“中氣”所在。 現代殯葬儀式用不能被證實的彼岸勸慰喪屬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暫時的、孱弱的,雖然可能用“彼岸亦不能證偽”來反駁,但這種反駁反而凸顯儀式的精神缺失。 精神的缺失,使得儀式的主持人和參與者,在儀式過程中沒有上升到自發的境界, 而僅僅是僵化的表演。具體表現為儀式功能的偏離,進而出現儀式創設和實施中的中氣不足。
不可否認的是,現代殯葬儀式能夠綿延而存,必然具有特定的心理效果和社會作用, 只是這種效果和作用常常停留在表層——情緒的局部宣泄和暫時轉移。 民眾因為死亡所承載的情感壓力和存在焦慮未能得到有效的釋放, 生存的根本問題——死將何往及其相關的生命意義問題,仍舊滯留于心里底層,“人在面對生活情況下建構的生活邏輯的價值旨歸,就是實現人的生存、發展和自我實現的滿足”[3]。儀式作為死亡創傷的療愈沒有發揮理想的作用, 反而使得我們疲勞不堪, 民眾在殯葬活動之后的生活仍舊以壓抑和遺忘為“醫囑”。
現代殯葬儀式在事實上沒有處理死之將來的問題, 也沒有在主觀努力中去尋求生死問題的主動作為。 現代殯葬儀式與殯葬現代化進程中的其他現象格格不入, 現代殯葬儀式暫時沒有遭到民眾的廣泛質疑,反而,民眾在其中越陷越深——不論是個案化的一宗喪事還是普遍的殯葬活動而言, 都有這種沉溺表現。 除了時間、精力和心理的投入外,最為直觀的沉溺就是物質和金錢的投入——厚葬(不僅僅在“葬”的環節)。民眾通過厚葬來表示對追逐死后世界的孱弱心境。厚葬不僅表現為物質的消費,還表現為心理的自欺,殯葬儀式讓這種消費獲得了“劇情”。現代殯葬儀式讓心理的自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行為高度,在這個行為高度上的結果:逆轉而下或者粉身碎骨,分別預示著殯葬儀式改革的兩種方向——變革、重建。
3.2 病因
3.2.1 生死彷徨的不舍:舊俗難祛
傳統殯葬儀式通過塑造死——“生”的過渡和轉換,對生存進行處理,應答死亡對生命的叩問。 這種努力和解答方式有虛構的性質,但對于拋棄了迷信、信仰的大多數個體而言, 現代殯葬沿襲了傳統生死觀并在儀式中形成類似于鴉片藥用效果的社會心理效應。 殯葬儀式是通過人對自身存在的關注和思考而應答死亡對生存的沖擊的實踐方式, 是人類在探尋生死哲學本質性問題的途中進行“善意的欺騙”的部分人的自我犧牲, 卸載死亡的重負是殯葬儀式的意義所在。 殯葬儀式以人性層面的隱忍踽踽獨行于死亡的陰影中,為多數生者“引渡”并探尋理性之光。在殯葬儀式的支持下我們送別了死者, 進而懷著對“彼岸” 的希望較為順利地完成向著死亡的生命進程。 如果殯葬儀式仍舊保留關于對“死后世界(彼岸)”的期望,現實生活在精神世界和社會心理內容上與此又格格不入,必然產生儀式理念的分裂。
3.2.2 無法突破的苦難:儀式之外
我們之所以念念不忘于“死后世界(彼岸)”,是因為終究有一個無法克服的苦難——人的有死性及其與不朽期望的矛盾, 這是殯葬儀式價值觀的心理根源。民眾傾向于將“活著”作為幸福的充分條件,將死亡視為幸福的終結,實際上,幸福的基本條件還應該包括身心健康和社會關系和諧。 身心和社會關系必然隨著衰老及其結果——個體的死亡而變化,殯葬儀式的病因可以追溯至此——民眾對幸福的奢望,漠視了幸福的前提及其變化。 由一個錯誤的、不可能的前提導出的措施——殯葬儀式, 必然具有先天不足。 當我們身心衰落、親朋遠去之時,我們很難會希望長存不亡,那時,除了病痛和孤寂難有幸福,如果你不信這種判斷, 可以去養老院問問那些老人們,或者尋機與家中的老輩深談一番。“彼岸”將此世完全搬移,對于現代殯葬儀式而言,顯然無法勝任于此。即便是比較靠譜的“多元宇宙理論”所描繪的“彼岸”那也是另一個“我”所有的,不屬于當前之我所有。 對于,無法突破的死亡苦難只有兩條路可行:態度和信仰,這是現代殯葬儀式的未來之路。
3.2.3 過度投資的失調:置身事外
現代殯葬儀式用隆重和虔敬獲得對“死后世界”的求證,其本質是用希望和可能掩飾幻想和虛無,利用了民眾賭徒心的“死不認錯”——我付出的一定是對的,這也是“渣男”被捧和受虐快感的共同病因。現代殯葬儀式慫恿民眾為幻想和虛無買單, 如果只是停留在有限的范圍和一定水平的耗費并產生了收支相當的情感作用,殯葬儀式也不用為此擔責、也不會因此詬病;關鍵問題是,殯葬儀式本是處理生死問題而演變為置身事外的推波助瀾——慫恿了民眾對死后世界的投資,殯葬活動在處理遺體的消費中,超額投資了儀式。現代殯葬儀式被買單,消費者的投資與產出比例嚴重失調。處理的方向可能是,降低投資或者改變殯葬儀式的產出量或者產出性質。
4 現代殯葬儀式的變革
現代殯葬儀式變革, 是在現有殯葬活動的社會生態基礎上,對現有儀式進行選育、改良或培育新種的自覺化社會實踐。 我們需要對現代殯葬儀式的社會生態進行考察, 結合儀式基本理論和時代精神確立殯葬儀式變革的理念和模式, 以期在殯葬實踐中循證。
4.1 關于彼岸的態度:虛構地回避到堅貞地面對
殯葬儀式是關于死者和死亡的行為表達, 傳統殯葬儀式將“彼岸” 作為處理死者和死亡的便捷之門。 “彼岸”從來沒有被證實過,當然,也從來沒有被證偽。 暫時的、局部的、特例的將“彼岸”作為歷史選擇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我們曾經不夠強大,需要虛構作為追求或榜樣。 虛構的彼岸成為抵御現實生活的替代和麻醉劑。在現代社會,獲得當下的回報是可行的,不再寄望于彼岸的心理替代和精神慰藉。 所以,我們不能持續地、普遍地將“彼岸”渡入日常,作為殯葬儀式的基本理念, 傳統殯葬儀式停留在虛構中使儀式表面化、虛假化。現代殯葬儀式獲得了現實生活的支持,有力量對虛構發出質疑,并用當下的生活代償死亡的黑暗——堅貞地面對: 縮減幻想并用現實來替代。“喪祭還以一整套復雜而嚴格的儀式促使人心懷敬畏、注重儀態,并使之慣常化”[4],儀式的這種精神影響將轉化為現實生活的行為變化, 這是心物關系在儀式理念重建中的前景。
4.2 關于生死的關系:孝之教到生之育
傳統殯葬儀式的理念構成, 除了關于彼岸的內容,更重要的就是“孝”的回報。傳統殯葬活動及其殯葬儀式以“孝”作為行為的原動力,具有直接的情感催化作用,現代殯葬活動傳承了該理念無可厚非。不論是物質的獻祭還是情感的溢出, 對于死者而言是沒有影響力的, 其影響力通過生者傳向廣闊的人際未來,“喪葬儀式主要不是人對物或者符號的運作和操弄,而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實踐、表達和確認”[5]。考慮到“孝”在人際內涵和代際外延表現上的變化,現代殯葬活動所堅持的“孝”在殯葬儀式中已經顯得力不從心而表演化。更重要的是,殯葬儀式具有巨大的承載力和作用力,我們不應該浪費其效力:僅僅是把殯葬儀式作為處理生死關系的局部——代際關系——孝。為了讓殯葬儀式產生立體化、全面化的高效力影響, 我們需要深入到儀式的精神深處——對人自身的理解和把握,不負儀式的“初心”——化育生者。 殯葬儀式須在傳承和變革中發揮其道德教化功用——不僅是關于孝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關于生的教育——這也是可行的。
4.3 關于行為的作用:虛假的隆重到真情的表達
殯葬儀式通過行為來表達生死之情感和追求生死之過渡,“死亡的儀式與信仰有著重要的心理及情感撫慰功能”[6]。 傳統殯葬儀式行為的作用凝結于表達悲痛,這是正常的,因為現實生活的普遍苦難無法排除,需要儀式以撫平未能永生的痛苦,以緩解沒有長久報恩的遺憾。于是,傳統殯葬儀式理念以悲痛為尚,進而演化為虛構,又用隆重來掩飾虛構,隆喪厚葬層層疊進而難抑。殯葬儀式行為均圍繞隆重展開,稀釋了“哀”的本質。 現代殯葬儀式的理念不反對悲痛、也不可能無視悲痛,應該表達悲痛——哀悼、應該轉化悲痛——思念、應該預備悲痛——慎終,這些內容都是真情。傳統殯葬活動以“哀”為本,傳統殯葬儀式放大了該傾向而造成其他真情的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