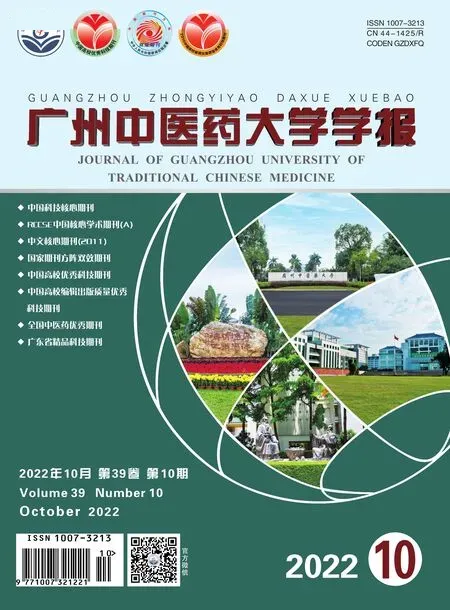《醫綱總樞》傷寒六經傳變學術思想探析
張明春,許迎,石秀琰,張濤
(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 301617)
《醫綱總樞》[1]一書,是清代醫家陳珍閣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廣東新會所著,是一本涉及中西醫理論的臨證綜合類中醫著作。《醫綱總樞》現存有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年)刻本、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年)醉經樓刻本、清刻本(殘)及1913年六經堂刻本[2]。陳珍閣生卒年不詳,據鄭洪教授的研究,認為陳珍閣當為“近代中西匯通醫家第一人陳定泰”之孫[3]。陳珍閣曾于光緒丙戌年(1886年)親赴新加坡英國皇家大醫院學習,習醫三年,獲益良多,有學者稱其為陳氏匯通世家的集大成者[4]。
傷寒六經傳變是指外感病在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六條經脈之間的傳變規律。歷代注家對傷寒六經傳變的觀點不一,陳珍閣在《醫綱總樞·卷二·外感·附辨古傳論傷寒證傳經之謬》中,專論該問題,以破解傷寒外感病傳經辨證之難。本文以《醫綱總樞》光緒十八年醉經樓刻本為研究對象,對《醫綱總樞》中有關傷寒六經傳變的內容進行梳理與探討。
1 對傷寒六經傳變的認識
1.1 對傷寒的認識中醫學中的“傷寒”向來有多層涵義,通常“傷寒”有廣義傷寒與狹義傷寒之別。廣義傷寒是一切外感熱病的總稱;狹義傷寒是外感風寒之邪,感而即發的疾病。探討《醫綱總樞》中的傷寒六經傳變問題,首先要明確陳珍閣對“傷寒”的理解。陳珍閣在“附辨古傳論傷寒證傳經之謬”篇將“傷寒”定義為“夫傷寒者,外感風寒也”;《醫綱總樞》的全書,僅《醫綱總樞·卷二·外感》的“夾色傷寒”“傷寒變實熱”及“附辨古傳論傷寒證傳經之謬”篇章中出現過“傷寒”這一名詞;陳珍閣在“傷寒變實熱”篇中指出:“感寒證,俗名傷寒;感暑證,俗名傷暑”;在“感寒”篇中,將“寒”解釋為:“寒者,天地凍冷之陰氣也,其氣純陰無熱,最能閉郁毛竅。”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陳珍閣所理解的傷寒為“外感風寒之邪,感而即發的疾病”,即為狹義傷寒的概念,而非一切外感熱病的總稱。
1.2 對治法方藥的認識陳珍閣在《醫綱總樞》中所言之“古傳論傷寒證傳經”規律為:“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證見頭項疼,腰脊強,發熱,惡寒,無汗,治用麻黃湯汗之……傷寒二日,陽明受之,證見身熱,目痛,鼻干,不臥,用葛根湯……傷寒三日,少陽受之,證見胸脅痛,口苦喜嘔,寒熱往來,用小柴胡湯。”其中的發病日期和受病之六經(傷寒起于太陽,依次傳入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以及“頭項痛,腰脊強”“身熱,目痛而鼻干,不得臥”“胸脅痛”等癥狀,與《素問·熱論》及《傷寒論·傷寒例》中相關的內容基本一致。然而“熱論”及“傷寒例”僅指出“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瀉而已”,并未給出具體的治法方藥,而陳珍閣于《醫綱總樞》中列出了“麻黃湯”“葛根湯”及“小柴胡湯”等方藥。陳珍閣提出的傷寒證治療方藥宜采用“麻黃湯”“葛根湯”及“小柴胡湯”的觀點,可能來源于明清醫家。如葛根湯治療“傷寒二日,陽明受之”這一論述,可追溯至明末清初著名醫家喻嘉言提出的“陽明經證”概念,喻嘉言將陽明證分為經證和腑證[5]。清代醫家周揚俊繼承并發揚其觀點,在《傷寒論三注》中給出了陽明經證的治療原則,即“陽明一經,有經府之分,在經者可汗,如尺寸俱長,身熱口痛鼻干不得臥是也”。乾隆年間《醫宗金鑒》出版,書中的“陽明表病脈證”歌訣及注釋中明確指出“葛根湯主治陽明表病也”[6],其后葛根湯治療陽明經表證的論述便廣為流傳,成為當時學界的主流觀點。
1.3 對傳經的認識陳珍閣在《醫綱總樞》中指出:“傷寒二日,陽明受之……以為太陽傳于陽明矣,然既外寒閉束……傷寒三日,少陽受之……以為陽明傳于少陽矣,然既加以血熱……”。對于傷寒“一日”“二日”“三日”,陳珍閣并未論述其特指六經傳變次序,故推測陳珍閣認知中的“傳經”,可能沿襲于成無己、周揚俊、黃元御等醫家的“日傳一經說”,即傷寒一日傳一經,六日傳至厥陰。
由于陳珍閣受其祖父陳定泰及在新加坡求學期間所學之解剖學理論等的影響,在《醫綱總樞·卷一·附辨十二經八脈之謬》中,記載了以手按腋下,不能感受到三脈跳動,因而否定了十二經八脈的存在。在分析“傷寒二日”出現陽明經的癥狀和“傷寒三日”出現少陽經的癥狀的原因時,否定了傳經在疾病進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2 對疾病傳變的認識
對于六經病的傳變,有的醫家從失治的角度進行闡述,如黃元御在《傷寒懸解》中言:“表邪汗解則已,未經汗解,則經熱內郁,日積日盛,明日自當傳于陽明,后日自當傳于少陽,六日六經,必然之事。”
而陳珍閣卻從誤治的角度闡釋這一過程:“傷寒二日……用麻黃湯可愈,何以今又見目痛、鼻干等熱癥乎?此必因初起有內熱癥相兼,治者只知散寒,而不清熱……今不以清熱涼血之劑,而再用葛根湯……不但病不能除,反加血熱胃燥,傳邪入大絡也。其又曰傷寒三日……治之者,須用涼血清胃生津,加辛平之品以清之,病可漸解。”
即陳珍閣認為之所以出現其他經的癥狀,是因為醫家辨證不準,未察覺“初起有內熱癥相兼”的內傷因素存在,用麻黃湯、葛根湯和小柴胡湯治療,屬于誤治。后世醫家陳亦人教授未言內傷因素,認為“目痛鼻干不得臥”為熱證,使用辛溫發汗的葛根湯治療屬張冠李戴,害人匪淺[7],其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與陳珍閣不謀而合。
陳珍閣之所以從誤治的角度思考這一問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陳氏否定經絡實質的存在,進而否定傳經對疾病進程的影響,故而另辟蹊徑,從誤治的角度進行詮釋。二是由于陳珍閣所理解的“傷寒”為狹義傷寒概念,而非一切外感病的總稱,故對“傷寒二日,陽明受之”的理解也僅停留在寒邪侵襲太陽經表,入里化熱,致使陽明經發病的層面,而忽略了其他邪氣,如熱邪直接作用于陽明,使陽明經發病的可能性。三則可能是受明清溫病學說及嶺南地域特征的影響。嶺南常年氣候炎熱,元代醫籍《嶺南衛生方》載李璆言嶺南為“炎方”[8],而清代嶺南醫家何夢瑤在《醫碥》認為嶺南“地卑土薄,土薄則陽氣易泄,人居其地,腠疏汗出,氣多上壅”[9],故而認為嶺南地區居民大多腠理不固。若患太陽傷寒,用辛溫輕劑,即可“遍身漐漐,微似有汗”。在嶺南用麻黃湯,容易過汗,傷津助熱,出現陽明經的癥狀,如宋本《傷寒論》第26條,但陳珍閣將其歸咎為“初起有熱證相兼”,總結為誤治。此外,鄭洪教授總結嶺南居民“上焦多浮熱”[10],即出現陳珍閣所言之“初起有熱證相兼”的概率較高,若醫者不察,診為傷寒,用辛溫峻劑麻黃湯治療,容易熱化,轉屬陽明,故陳珍閣言其為誤治,亦非妄言。
傷寒六經傳變問題,歷代醫家爭論不休,關鍵在于傷寒六經傳變“日傳一經”發生的概率比較小,故柯琴從傷寒幾日為見證之期,非傳經之日的角度去理解這一問題[11];方有執從傷寒幾日為傳經次序的角度進行闡述[12];張景岳從傷寒傳變不可以日數為拘,亦不可以次數為拘的角度闡釋[13];黃元御從失治的角度進行闡釋[14]。而陳珍閣從醫家忽視患者的內傷因素,用麻黃湯、葛根湯等誤治的角度詮釋這一過程,一定程度上亦增大了傷寒六經傳變“日傳一經”的可能性,使其變得更加合理,也為后世醫家思考傳經問題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3 結語
陳珍閣作為嶺南地區中西匯通的代表性醫家之一,受解剖學的沖擊,否定經絡實質的存在,雖然陳氏此說甚為激進[3],但他在此基礎上,另辟蹊徑,從誤治的角度詮釋傷寒的傳變,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治法。陳氏的論述,體現了他在特殊歷史時期下,面對西洋醫學的沖擊進行的思考與探索,具有明清的時代特征和嶺南地域氣候特點,對于臨床六經病的診治,特別是對嶺南地區六經病,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