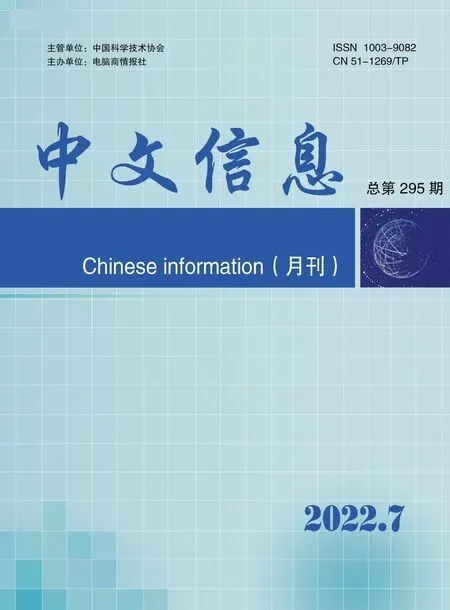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與親職壓力關系研究綜述
彭傲雪
(安慶師范大學,安徽 安慶 246133)
引言
我國特殊教育在《“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的指導下提出了到2025年初步建立高質量特殊教育體系的主要目標。2020年6月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加強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階段隨班就讀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強化家校共育。要密切與殘疾學生家長聯系與溝通,加強家庭教育工作與指導”的主張[1]。2021年12月《“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提出“切實增強殘疾兒童青少年的家庭福祉”的指導思想及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出臺,可見國家在政策層面加大對心智障礙兒童家庭教育的重視。心智障礙兒童家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高質量特殊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研究中,心智障礙兒童主要包括孤獨癥譜系障礙兒童和智力障礙兒童。2021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布的《特殊教育基本情況》數據表明,全國學前、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在校學生合計88.08 萬人,其中智力殘疾在校學生合計27.49 萬人[2]。在2019年發布的《中國自閉癥教育康復行業發展狀況報告(III)》中,孤獨癥群體數量達到1000 萬人,而2000年新生兒戶口登記為1003.5 萬人,按照1%的孤獨癥譜系障礙發生率計算,將會增加10 萬名孤獨癥兒童[3]。而龐大的心智障礙兒童群體背后是家長數量的增加,對家長的心理韌性研究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心理韌性的研究領域包括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原生家庭對心智障礙兒童身心發展產生潛移默化和深遠持久的影響,無論是特殊兒童早期干預的最佳實踐模式—家庭本位實踐,還是特殊教育生態系統的構建和利用,都離不開家長的主動參與。由于心智障礙兒童行為、情緒和人格等方面的異常,無疑會增加家長的親職壓力。因此,本文通過綜述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與心理韌性關系的中外文獻研究進展,有利于豐富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心理健康領域內容,有利于進一步充實國內在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健康領域的理論體系。
一、研究方法
我國心理韌性的研究起步于21世紀初,故文獻檢索以2004年為起始年份。本研究的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與親職壓力關系英文文獻檢索,首先,以“autism/ASD/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mental retardation/intellectual diability/mental impairment AND father/mother/caregiver/parents AND resilience/social support/coping style/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arental stress/parenting stress”為關鍵詞,英文文獻信息來源于Web of science(WOS)數據庫核心合集中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與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檢索年限為2004—2022年,文獻類別限定為Educational Research(教育學研究)和Special Education(特殊教育),文獻類型為論文。同時,在EBSCO 上以上述英文專業術語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數據庫選擇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限制文章為同行評審(peer-reviewed)期刊,語種為英語,檢索年限為2004—2022年,然后,刪除重復、無關的文獻,篩選出與本研究高度相關的文獻29 篇。最后,為了防止依靠主題進行搜索可能會導致的文獻遺漏,對29 篇研究的參考文獻進行篩選,另獲37 篇相關文獻,最終獲得有效文獻共計66 篇。本研究的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與親職壓力關系中文文獻檢索,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兩大中文數據庫,具體檢索策略以“孤獨癥/智力障礙和心理韌性/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心理健康和親職壓力和家長/主要照顧者/父母”,期刊年限為2004—2022年,最終獲得有效文獻共計24 篇。
二、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的研究
1.心理韌性的概念
國外學者對于心理韌性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我國學者對英文resilience 一詞的中文翻譯不盡相同,其中包含“復原力”“抗逆力”“心理韌性”或“心理彈性”。本研究采用“心理韌性”的譯法。心理韌性的定義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品質性定義。即心理韌性是個體身上所具有人格特質或能力,具有相對穩定性。Markstrom 將心理韌性定義為在遭遇挫折時自身形成的一種能力和品質,可以促進個體戰勝挫折且進一步得到成長。劇諾涵將心理韌性定義為面對逆境和挫折時表現出的良好適應能力[4]。第二類,結果性定義。即心理韌性是個體在經歷危機或創傷后產生適應性的積極結果。Masten 將心理韌性解釋為是個體遇到困難情境依舊能夠較好處理的一種現象。第三類,過程性定義。即心理韌性強調個體與環境之間積極的、系統的、動態的相互適應過程。Newman 將其界定為個體在各種壓力環境事件下,表現出較好地適應的動態過程。徐明津將心理韌性定義為當個體遇到重大創傷性事件時,通過各種途徑進行自我調整,減少困境帶來的消極后果的過程[5]。
2.心理韌性的測量
國外常用的心理韌性測量工具是由Oddgeir Friborg 和Odin Hjemdal 等人于2003年編制的《成人心理韌性量表》,測量的是處于壓力和危險情境時的個體對抗壓力和適應環境內部和外部保護性因子。Kathryn M.Connor 和Jonathan R.T.Davids-on 于2003年編制的《Connor-Davidson 心理韌性量表》,采用5 級計分,得分在0-100 之間,分數越高表示心理韌性水平越高,于肖楠和張建新使用該量表對來自北京和廣東地區的被試進行研究,提取出了三個因素:堅韌性、力量性和樂觀性。郁婷編制的《孤獨癥兒童家長心理韌性量表》主要包括情緒調節能力、認知調節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自我效能感、目標與未來、堅韌性六個維度,該量表能夠更全面地測量我國孤獨癥兒童家長的心理韌性水平[6]。
3.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研究現狀
有關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的研究現狀如下。第一,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的調查研究。吉彬彬和秦麗花選取湖南省四個地級市的特殊兒童康復機構的孤獨癥兒童家長為研究對象,通過心理韌性量表測量發現湖南省孤獨癥兒童家長心理韌性處于中等水平[7]。第二,對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的結構和影響因素分析。Devavrat G Harshe 通過調查孤獨癥兒童父母的心理韌性,發現心理韌性則受教養方式的影響。第三,在消極事件發生后,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心理韌性對人、環境、結果之間起作用的動態機制。Ryan Bell 對孤獨癥兒童父母進行調查研究,發現相對較低的心理韌性水平也能緩沖日常養育壓力。第四,學者們運用社會工作介入和醫學綜合干預的方法,從提升心理韌性的外部保護性因素角度出發對其進行干預研究。張奧選用準實驗研究方法,將16 名心智障礙家庭照顧者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運用《自我韌性量表》和《照顧者負擔量表》對被試進行測量,發現小組干預對心智障礙家庭照顧者的心理韌性水平具有顯著效果[8]。張明卓等通過康復訓練、志愿陪伴干預和醫學專業支持的手段使孤獨癥患兒家長心理韌性中精神支持因子有明顯提高[9]。
三、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的研究
1.親職壓力的概念
國外學者關于親職壓力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將parenting stress 翻譯為“親職壓力”“養育壓力”或“育兒壓力”,本研究采用“親職壓力”的譯法。Abidin 將親職壓力定義為家長或撫養人在履行其親職角色及親子互動過程中,因受到其個人的人格特質、子女特質、親子互動情況以及家庭情境等因素的影響,進而在教育教養中感受到的壓力。Anthony 將親職壓力簡單定義為一種在撫養孩子的需求中出現的心理壓力。蔡雅玲認為親職壓力是家長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因受到家長與孩子特質、社會與家庭環境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壓力[10]。Hayes 等將親職壓力定義為家長在育兒過程中所承擔的親職角色以及親子互動過程中所體驗到的負面情緒。
2.親職壓力的測量
國際上,《長型親職壓力量表》由Abidin 于1983年編制,該量表適用于0-12 歲兒童家長,主要分為兒童領域、父母領域和一般生活壓力三個維度,其目的在于測量親子系統中可能影響親職功能的壓力。為滿足研究者及臨床工作者的需求,Abidin 于1990年編制《短型親職壓力量表》,將原有的14 個子量表重新分類排序分為三個分量表,分別是親職愁苦、親子互動失調和苦難兒童量表。而另一常被用來評估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的工具是由Friedrich、Greenberg 與Crnic 根據Holroyed 的壓力與資源問卷改編而成的《壓力與資源簡表》,該量表的四個維度分別為由家長和家庭問題、悲觀主義、兒童特質和兒童的生理缺陷。我國學者根據中國實際情況,編制了特殊兒童家長親職壓力量表,例如,學者利翠珊編制了《身心障礙兒童家庭親職壓力量表》[11],學者李靜編制了《學前殘疾兒童家長親職壓力反應問卷》,有效地填補特殊教育領域家長親職壓力量表的空缺[12]。
3.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研究現狀
目前,有關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的研究如下。第一,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的現狀調查研究。唐月紅等調查腦癱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并發現其家長的親職壓力集中在較高的水平[13]。邵國瓊等通過調查孤獨癥兒童主要照顧者發現其親職壓力處于較高的水平[14]。第二,對其家長親職壓力的影響因素研究。一是兒童自身特質對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的影響,如馬利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探討心智障礙兒童心理健康與親職壓力的關系,發現心智障礙兒童情緒行為問題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家長親職壓力,即心智障礙兒童自身的品行問題、多動以及同伴關系不良等情緒行為問題越多,家長親職壓力越大[15]。二是家庭因素對其家長親職壓力的影響。張燕通過問卷調查和半結構化訪談,發現共同養育者之間的沖突會增強母親的壓力感受[16]。Sinha Deoraj 等采用橫斷面研究方法調查發現孤獨癥兒童父母的親職壓力水平受陪伴子女的時間的影響。三是家長自身心理健康對親職壓力的影響。倪俊偉通過調查腦癱兒童家長發現抑郁是影響親職壓力的重要預測因素[17]。李詩涵通過調查孤獨癥兒童家長發現親職壓力的心理影響因素有人格特征、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18]。Pastor-Cerezuela 等對比研究孤獨癥兒童父母和典型發育兒童父母,發現孤獨癥父母的心理韌性是親職壓力的顯著預測因子。第三,特殊教育、醫學、心理學和社會工作領域研究者對其家長進行紓解親職壓力的干預研究以及干預后身心狀態變化研究。曾晶等采用薩提亞模式對6 名親職壓力程度較高的孤獨癥兒童家長進行干預研究,發現該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孤獨癥兒童家長親職壓力水平[19]。Pamela Rosenthal Rollins 等對56 個文化和社會經濟不同的家庭進行為期12 周的孤獨癥早期干預隨機對照試驗。第四,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水平的對比研究。一是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和典型發育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對比研究,如秦秀群等調查和對比分析210 名孤獨癥兒童家長和200 名正常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水平[20],Gemma 等調查和對比分析42 名孤獨癥譜系障礙兒童與42 名典型發育兒童父母的親職壓力水平。二是不同安置方式下的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的對比研究,如左玉婷等對比36 名特殊教育機構孤獨癥兒童的家長和17 名融合教育機構孤獨癥兒童的家長的親職壓力情況[21]。三是不同障礙類型的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的對比研究,如關文軍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對比孤獨癥、智力殘疾和腦癱等五種殘疾類型兒童家長親職壓力水平并發現孤獨癥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水平最高[22]。
四、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與親職壓力關系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很多學者通過相關研究已經證實,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心理韌性與親職壓力具有相關性,且心理韌性與親職壓力呈負相關。E.D.Gerstein 和K.A.Crnic 等研究了36~60個月智障兒童的家長的日常育兒壓力軌跡以及包括心理健康、婚姻調整和積極的親子關系在內的影響育兒壓力的特定家族風險和韌性因素,研究發現母親日常育兒壓力軌跡的減少與母親和父親的幸福、感知的婚姻適應以及積極的父子關系有關。Christopher F.和Ryan Bell 通過對73 名孤獨癥譜系障礙兒童母親和35 名父親的養育經歷進行量表調查,數據的調節效應分析表明較低水平的韌性能緩沖與養育孤獨癥兒童日常壓力相聯系的焦慮和抑郁情緒。心理學學者Emma Medford 和Dougal Julian Hare 等使用《成人心理韌性量表》和《感知社會支持的多元維度問卷》對46 名苯丙酮尿癥兒童母親的心理健康進行調查,發現苯丙酮尿癥兒童母親的心理韌性的增加與心理壓力的減少有密切聯系。王天竹對425 名腦癱、孤獨癥和唐氏綜合癥兒童家長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親職壓力與心理韌性水平呈顯著負相關[23]。Elizabeth 和Shaunna 對108 名4~16 歲智障和發展性障礙兒童的母親進行調查,發現心理韌性緩和了污名對母親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并建議通過培養家庭抗逆力來幫助他們應對所經歷的污名和親職壓力。學者們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心理韌性對親職壓力減緩的保護性作用并通過提升家庭抗逆力的干預手段來提升家長的心理健康水平,進而提升家庭生活質量,改善親子關系。
五、現有研究的特點
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國內外相關研究大多數是量化調查研究,研究過程中同時采用因素分析、相關分析等方法探索二者之間的關系,較少學者注重整合式研究方法,即量表調查與質性研究的結合。而基于壓力和心理韌性框架視角下的整合式研究方法中質性研究的使用,如建構主義的扎根理論方法和結構化訪談,有利于進一步揭示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與心理韌性的變化發展過程,深度剖析育兒心路歷程,從而切實提升改善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生活現狀,改善家庭教育質量。
第二,在研究對象方面,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自閉癥譜系障礙兒童父母,只有文獻是關注智障兒童父母,在本研究中,僅有30 篇中英文文獻關注智障兒童父母。而國外學者傾向于研究臨床表現為自閉癥譜系障礙或智力障礙的具體癥狀兒童家長,如表現為智力障礙的唐氏綜合癥、脆性 X 綜合癥、苯丙酮尿癥、粘多糖 IH 型兒童家長,表現為自閉癥譜系障礙的高功能孤獨癥和Asperger 綜合癥兒童家長。而通過對不同癥狀的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心理健康進行細化研究,可以為家長心理咨詢等具體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第三,在研究工具方面,國內本土化量表缺乏,相關研究多使用修訂過的國外學者編制的量表,我國在編制專門針對心智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或心理韌性的量表的領域中存在較大發展空間。
第四,在研究領域方面,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教育、心理學、醫學、社會工作等領域,不同領域的跨專業合作,也成為心智障礙兒童家長心理韌性與親職壓力關系研究的發展頃向,如醫學干預、團體心理輔導和社會工作介入等方式,從而有利于為心智障礙兒童家長的心理健康尋求社會支持,提供全面化干預手段,也有利于提升家長在家庭教育干預過程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