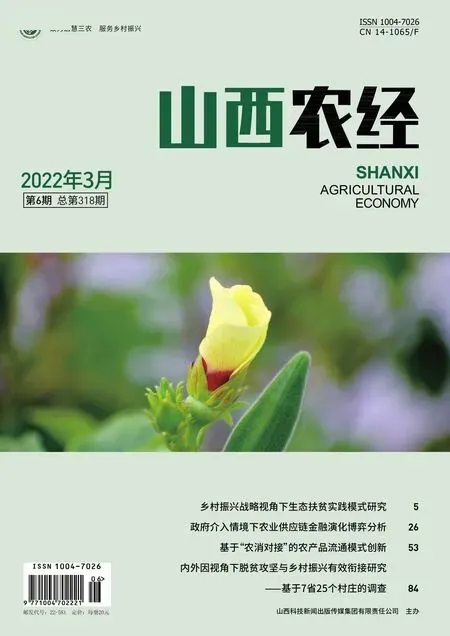江陰市濱水空間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探索
□王 洋
(江蘇金寧達房地產評估規劃測繪咨詢有限公司,江蘇 南京 210036)
1 研究背景
生態產品是良好自然生態系統以可持續的方式滿足人類生產、生活需求的物質產品和服務產品的總稱[1]。狹義上是指滿足人類需求的清新空氣、清潔水源、適宜氣候等看似對人類有形物質產品消耗沒有直接關系的無形產品。廣義上包括人類在綠色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清潔生產、循環利用、降耗減排等途徑,減少對生態資源的消耗生產出的有機食品、綠色農產品、生態工業品等有形產品。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將生態產品所蘊含的內在價值轉化為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過程。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既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也是堅持生態優先、推動綠色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要求。
2 濱水空間特征
2.1 濱水空間現狀
城市濱水空間是指城市內河沿岸、湖泊周邊的可開發土地資源。城市濱水空間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可觀賞性、資源稀缺性和歷史文化性等特征[2]。通過濱水空間生產現狀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城市濱水空間正面臨私有化傾向,其中優質濱水空間被私有化的情況并不鮮見,尤其是房地產與工業開發領域。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濱水空間的公共屬性將成為社會的共識,公共空間的大眾化和市民化將成為社會發展和城市進化的象征。
2.2 美國濱水空間啟示
西方發達國家城市濱水空間曾被大量的工廠、倉庫和碼頭所占據,水體普遍受到嚴重污染。為解決這一生態問題,美國濱水空間生產總結了一些較成功的案例。如芝加哥湖濱空間保護是政府規劃遠見的典范,以立法的形式,將密歇根湖周圍的“黃金地帶”規定為公共綠地,只能用于開發建造公共建筑;密爾沃基濱水地帶的發展規劃以旅游休憩為主,強調與周圍社區的形式與功能相協調,鼓勵土地多樣化開發和空間共享;查爾斯頓濱水區是以政府為主體,拆除老舊街區,將其開發為濱水公園。
這些成功案例均表明濱水空間會成為城市中景色優美和具有特色的場所。成功案例中的濱水空間均在水邊開辟人行道,設置開敞空間,保障親水空間的公共性和可達性,留出岸線吸引更多人來濱水區活動。此外,保護城市濱水景觀脈絡和共享性主要依賴于政府對城市水體價值的正確認識和長遠規劃管理。
2.3 濱水空間特征
江陰市總面積986.97 km2,水域面積157.31 km2,長江江陰段全長34.8 km,已被建設占用或利用的水段25.05 km,其中港口碼頭占用率50%;多年的河網建設形成13 條入江河道,輸水河道密度4.98 km/km2,運河與輸水河濕地面積為1 195.8 hm2,占江陰市濕地面積的12.03%[3],其中江陰市霞客鎮的河網分布密度較大,大部分濱河或地勢低洼的積水區形成濕地,但其開發強度較低。
3 濱水空間實現生態價值的主要做法
江陰市長江岸線過度使用、土地超強度開發等問題日益顯現,濱水空間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是破解“金色污染”困境的關鍵[4]。江陰市在濱水空間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面,開展了長江生產型岸線清退、沿江環境整治和生態修復、濱江親水工程建設,形成公園體系,通過發展生態旅游等方式促進價值外溢。
3.1 還江于民,推進濱江臨水岸線生態建設
江陰市市民長期以來臨江卻不見江、濱江卻不親水。江陰市按照長江大保護的要求,對主城區沿江區域實施了整體搬遷,沿江生產性岸線全部退還為生態岸線,臨江開展生態修復,建設濱江公園體系,長江岸線變身為美麗的“江陰外灘”。
3.2 還濕于民,提升長江岸線水環境自凈能力
窯港口區域是江陰市、無錫市以及常州市飲用水的取水口,其周邊散布有多處小型畜禽養殖場、化工作坊和小型修船廠,嚴重影響了區域生態安全和飲水安全。
按照“自然恢復為主、人工修復為輔”的原則,劃定并規劃建設窯港口生態濕地保護區,恢復天然蘆蕩和濕地灌叢岸線,提升部分生態產品供給能力。關閉、整合家庭式畜禽養殖場并異地修建環保型規模化養殖基地,新建魚類產卵場、棲息水道、長江生態緩沖林、增殖放流點野化基地和水生態修復浮島,為恢復保護區域內的生物多樣性奠定基礎。
3.3 還綠于民,提高城區綠化覆蓋率
按照“斷帶補齊、窄帶加寬、次帶提升、殘帶改造”的原則,推進沿江地區生態林建設工程。建設的環城森林公園與北部長江、中部運河共同構成江陰市城區的綠色生態屏障;結合礦山環境治理,對廢棄宕口、已破壞山體等進行生態復綠;對于連片種植空間有限的區域,做到深挖潛力、見縫插綠、宜栽盡栽,構筑更多自然景觀、濱水綠帶。
3.4 還河于民,恢復江南水鄉古城韻味
江陰市啟動了以“八公里沿江、十公里運河”為核心的生態保護與修復,在城區外新建了聯結長江和太湖兩大水系的運河,對老錫澄運河兩側實施異地搬遷,建成錫澄運河公園和應天河公園,將東部的老城區與西部的老郊區連為一體,恢復江南水鄉的古城韻味,還市民以碧波蕩漾、一步一景的古老運河。
3.5 多措并舉,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綜合運用土地儲備、片區綜合開發等措施,在生態修復及周邊區域配置合理比例的商業、住宅等經營性用地,促進生態產品的價值外溢,實現區域土地的經濟增值。
江陰市將沿江的大部分土地規劃為公共綠地等,同時儲備了部分住宅用地和商業用地,憑借土地增值所帶來的收益實現生態修復成本內部化。在生態產品供給區積極發展生態型產業,打通“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通道。依托綺山應急水源地項目,修復并建成綺山郊野公園,規劃建設集旅游、養老、居住于一體的康養居住區;引入社會資本建設玫瑰種植園,發展生態農業和旅游業。對重點生態功能區實施生態補償,促進公共性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
試件實測各特征值及變形指標見表4。表中:Py、Pu、Pm為屈服荷載、峰值荷載和破壞荷載(取峰值荷載下降至85%時對應的荷載值或未降至85%時取最大位移對應的荷載值);Δy、Δu、Δm為所對應的位移值;μ為延性系數,μ=Δm/Δy。由表可見:
4 濱水空間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困境
4.1 缺乏穩定的資金供給
生態產品開發建設工作是一項全局性、系統性、宏觀性的工作。目前,資金來源絕大部分包含在具體的工程建設費用中,對沒有列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生態產品沒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和專項預算。
對于一些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生態產品項目,如果不與舊城改造、新農村建設、國家重大項目等結合,就不能單獨立項納入預算;對于一些體量小、布局散、收益少的生態產品,由于受人工成本、建設成本與運輸成本的影響,單獨項目無法做到投入與產出的資金平衡,目前還沒有建設縱向補償和橫向交易機制。
4.2 缺乏明確的開發機制
生態產品價值包含生態調節價值、文化服務價值、物質供給價值3 個方面[5]。目前,生態產品的生態調節價值受一系列政策影響,未充分顯化。文化服務價值未得到充分挖掘,與生態旅游、生態康養的結合度不緊密。與其他產業相比,生態產品的物質供給難以達到一定規模,難以形成產業體系,產品的開發、設計、營銷、技術服務等缺乏有效支撐。
4.3 缺乏有效的利用方式
經濟發展使人們對生態環境的要求提高,對生態產品的需求增大,但由于生態產品價值沒有得到有效顯化,導致優質生態資源被個別項目低成本使用,甚至有的生態資源被破壞后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罰,最后形成企業對生態產品的過度開發與利用,增加社會治理成本。
5 濱水空間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路徑
5.1 推進生態產品供給能力提升和增值溢價
5.1.1 提升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
重點圍繞“一江三河兩地”區域,認真做好生態產品開發規劃,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資源的保護與修復,進一步提升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突出重點,著力做好入江河道整治、綺山應急備用水源地、廢棄礦山治理、濱江公園體系、霞客灣濕地、河豚漁村水產養殖6 個示范點項目生態價值實現,形成良好的示范帶頭效應。兼顧全面,以創建國家生態園林城市、林長制省級試點、河長制建設為契機,扎實開展造林綠化,改善生態面貌,不斷提升城市人居環境質量。多方借力,鼓勵引導社會資本開發生態產品,對于不適合建設的用地,做到應綠盡綠,進一步挖掘生態旅游潛力,打造更多的生態產品。
5.1.2 培育生態產品的市場需求
依托江陰市生態資源和地域文化,加快生態資源向旅游產品轉化,擴大霞客文化、江蘇學政文化、濱江要塞軍事文化品牌效應,推進農業與旅游業、休閑康養產業融合發展,建設獨具韻味的“新江南人家”。充分釋放優質生態對高端項目的吸附力,大力發展與“綠水青山”和諧相生的外源性產業,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提前布局節能環保等未來產業,持續培育壯大綠色發展新動能。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生態農業,鼓勵生態產品標識鮮明的地區,加強知名品牌培育和生態產品標準化建設,提升農產品生態溢價。
5.1.3 促進濱水空間的復合利用
根據農作物的互補性,對濱水空間及附近的土地進行集約利用。開展生物多樣性本底調查,進而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號召社會各界力量共同保護生物多樣性,如一些企業開展長江漁業資源增殖放流活動是修復長江水生生物資源、維護長江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舉措。
以霞客灣生態涵養區為中心,依托錫澄協同發展核心區的戰略區位優勢和馬鎮國家濕地公園的生態優勢,高起點規劃建設霞客灣科學城,促進生態、生產、生活有機融合,探索都市農業、濕地經濟等特色產業增長點。
5.2 因地制宜開展生態資源指標交易
5.2.1 進一步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進一步完善生態券的交易探索,厘清生態指標占補平衡目標下的生態券交易機制;編制適合于江陰市的生態產品開發利用產業發展指引、調查技術規范和價值實現過程;搭建包括政府、轉讓方、受讓方、經紀機構等主體在內的生態券交易平臺,實現生態券的交易流通。通過合理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生態券交易平臺,結合生態占補平衡機制,探索將生態券融入工程項目建設、國有建設用地配置等過程,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熱情[6]。
5.2.2 進一步構建“雙碳”協同機制
通過對各類生態產品標準化并量化為可度量、可測算、可流通的計量單位,在用地環節培育生態產品市場需求,實現占用者付費、生產者受益的生態產品供求市場,制訂不同地類生態用地保護、可循環利用能源的利用政策[7]。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以地區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導向,結合碳減排、碳捕獲任務完成情況,制定相關產業轉型政策[8]。
在城市規劃與城市建設方面,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為導向,制定綠色建筑、海綿城市、地熱、太陽能利用、城市和居住區綠化升級政策。
5.2.3 建立生態空間與城鎮空間置換機制
探索生態修復形成的園地、林地、濕地等生態空間與城鎮建設空間進行置換的可行性和實施路徑。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由政府協議收回后置換到城鎮建設空間使用。探索一些沿江地塊登記為建設用地,但現狀為園地、林地或濕地,將他們所占空間指標置換到其他城鎮建設空間使用。探索在市域建設用地不增加、耕地不減少的前提下,對現有的村級工業園區退出的農用地分類置換空間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