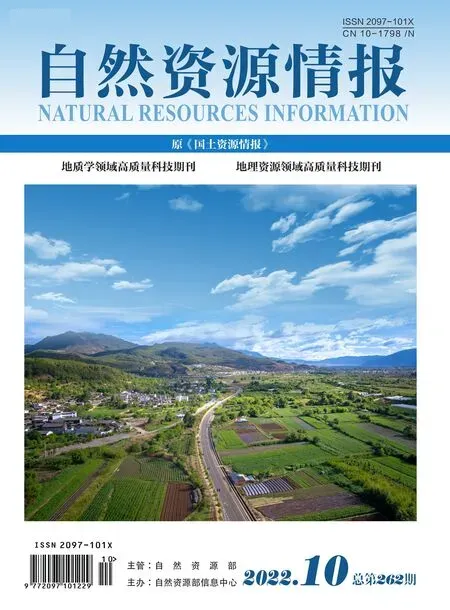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現狀與完善
黎 明,孔凡婕,梁夢茵,唐文正
(1.自然資源部國土整治中心;自然資源部土地整治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35;2. 黑龍江省自然資源生態保護修復監測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90)
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必由之路,生態文明思想不斷深入人心,生態文明建設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基礎[1]。生態修復工程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之一,可以有效保障國家生態安全。近年來,礦山生態修復、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修復工程、海島和海岸帶整治修復等一批生態修復工程先后實施,并取得顯著成效[2]。
完善的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是平衡各方利益訴求、協調各部門責任和資金來源的保障,是生態修復取得成效的基石[3],中國的生態修復相關的立法在很多方面仍有待完善[4]。現行有關生態修復的相關法律法規不斷更新,依然無法完全解決新形勢下生態修復工作面臨的問題。本文在梳理現行中國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的基礎上,挖掘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中國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思路。
1 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現狀
中國生態修復工作開展時間較短,相關部門一直在極力推進生態修復的規范化、法治化建設,相關法律法規已對生態修復工作的多方面內容做出了原則規定,但尚未形成體系。國家層面尚未頒布生態修復的專項法律,地方層面已先于國家層面探索制定了專門的生態修復法規。與生態修復相關的法律法規可以分為綜合型、要素型、區域型和污染防治型。
“生態修復”,這一特定詞語的出現相對較新,在諸多相關法律法規中可能會用相近詞語表達,或者其描述的一些整治修補措施是“生態修復”的具體體現。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中使用“整治和恢復”來表述生態修復相關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以下簡稱《礦產資源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采礦企業應對破壞的地區采取“復墾利用、植樹種草”等措施進行生態修復。
1.1 綜合型法律法規
1.1.1 國家層面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未使用“生態修復”這一特定詞語,但第二十六條規定了“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這也包含了生態修復的任務;同時“國家組織和鼓勵植樹造林,保護林木”,植樹造林也屬于生態修復的措施之一。
198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境保護法》)受到當時社會理念的影響,并未規定生態修復,但立法目中包含了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價值追求,這與生態修復目標是一致的[5]。2014年,對《環境保護法》進行了修訂,在第五條、第三十二條增加了生態修復相關內容。《環境保護法》第五條規定了環境保護堅持“綜合治理”“損害擔責”等原則,包含了生態修復的要求;第三十二條也提出了國家應“建立和完善相應的調查、監測、評估和修復制度”。《環境保護法》是對環保工作進行宏觀規范指導的法律,涉及生態修復的條款只能提出方向性的支持。
1.1.2 地方層面法規
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和一些重點生態保護地區均會制定生態環境保護條例,是生態環境保護的綜合性法規,其中均有專門的生態修復章節。例如,省級的有《貴州省生態環境保護條例》《天津市生態環境保護條例》等,市級的有《深圳經濟特區生態環境保護條例》等,針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有《陜西省秦嶺生態環境保護條例》等。
此外,一些地區已經率先探索制定專門的生態修復地方性法規,主要針對單項自然資源要素或是地區型流域。如針對自然資源要素的有《陜西省天然林保護修復條例》《黃石市礦山生態修復條例》等;針對地區型流域的有《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態修復與保護條例》《運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態修復與保護條例》和《忻州市滹沱河流域生態修復與保護條例》等。
1.2 要素型法律法規
1.2.1 國家層面要素型法律法規
自然資源管理,需要對各類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進行約束,因此按照自然資源要素分類制定了多部法律法規,其中部分內容涉及生態修復的相關工作[6],如土地資源、農業資源、植物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動物資源等(表1)。相關要素型法律主要是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進行規定,涉及生態修復的內容相對較少,并不是專門的生態修復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以下簡稱《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以下簡稱《草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以下簡稱《漁業法》)等。專門針對自然資源保護和修復的法律較少,其目的也是進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以下簡稱《水土保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生動物保護法》)等。

表1 國家層面生態修復相關的要素型法律
2019年第三次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以下簡稱《土地管理法》),為了保護與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在第十七、十八條規定土地利用規劃和國土空間規劃編制時應當堅持保護生態環境;在第四十條規定對破壞生態環境開墾的土地,需要進行退耕。《水土保持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以下簡稱《防沙治沙法》)則涉及較多生態修復內容。《水土保持法》為了預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護和合理利用水土資源,在第十六、三十、三十六條規定了在水土流失重點預防區和重點治理區、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等地區開展生態修復。《防沙治沙法》為預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地,在第四條規定應對沙化土地采取生態修復措施;第十六條規定應采取封育保護、自然修復等措施,如組織植樹種草,預防和減輕水土流失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以下簡稱《農業法》)主要為了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其中也涉及耕地的養護,禁止毀林毀草開墾,水、森林、草原和動物資源的保護及合理利用等。《漁業法》為了促進漁業生產的發展,加強漁業資源的保護、增殖和合理利用,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主體進行了規定,第三十七條規定禁止捕殺重點保護的水生野生動物。《森林法》為了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資源,同時加快國土綠化,在第三十、三十一、四十六條規定國家支持重點林區、生態脆弱地區、坡耕地、退化林地等地區實施森林資源的修復。《草原法》為了保護和合理利用草原,發展現代畜牧業,同時改善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在第三十一條規定對“退化、沙化、鹽堿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的草原”組織專項治理修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以下簡稱《水法》)為了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在第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五條規定了多種情形下的生態修復義務主體。《礦產資源法》為了發展礦業,加強礦產資源的勘查、開發利用和保護,在第二十一、三十二條規定了開采企業應當承擔生態修復義務。
相關的行政法規是對應法律內容的具體化,因此也是按照要素進行編制,主要的制定目的依然是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其中也涉及一些特定領域的生態修復具體任務。國家層面生態修復相關的要素型法規主要有《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土地復墾條例》《退耕還林條例》《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漁業法實施細則》等。
1.2.2 地方層面要素型法規
地方層面法規延續了國家層面的立法思路,針對水體、濕地、林地、耕地、草原、礦產等各類自然資源要素的保護和合理利用而制定了相應的法規,其中也涉及生態修復工作,例如,《浙江省水資源管理條例》《江西省湖泊保護條例》《陜西省森林管理條例》《內蒙古自治區草原管理條例》《福建省礦產資源條例》《無錫市濕地保護條例》等。
1.3 區域型法律法規
針對一些重點生態功能區,制定了相應法律法規,以規范生態修復,促進資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態安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國家層面的法律已經頒布的有《長江保護法》《海島保護法》;其他重點地區相關立法也在推進,《黃河保護法》(草案)已于2022年6月21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審議,青藏高原地區生態保護立法啟動編制。國家層面針對重要生態功能區的法規主要有《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條例》等。
地方層面針對重點生態功能區已經制定了較多法規,如《太湖流域管理條例》《湖南省洞庭湖保護條例》《滇池保護條例》等。
1.4 污染防治型法律法規
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主要針對水體、土壤、大氣等各類污染分別立法。國家層面的污染防治型法律主要有《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國家層面污染防治法規主要有《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防治陸源污染物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等,規定了各類環境污染的修復責任人。
地方層面污染防治法規也是針對水體、土壤、大氣、噪聲等各污染類型進行單獨制定,例如,《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條例》《廣西壯族自治區土壤污染防治條例》等。
2 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存在的問題
中國生態修復工作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一批重要生態修復工程先后實施,在重點生態功能區實施了25個生態保護修復試點工程,出臺了《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年)》;快速發展的生態修復實踐也面臨著缺少法律法規參照和約束的問題。
2.1 缺少專門性的生態修復法律
中國關于生態修復的規定分散于諸多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的法律法規中,缺少全面的制度設計。不同法律法規對生態修復的內涵、執行標準、法律責任等往往存在著不同的界定,各個法律規范間難以協調,不利于在實踐中執行。因此,有必要在國家層面制定一部系統、專門的生態修復法律,對生態修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基本制度、法律責任等重大的問題進行規定。
2.2 立法理念相對滯后
2.2.1 生態修復多著重于生態環境被破壞區域
目前相關生態修復法律法規多關注的是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地區。中國的生態修復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時間較短,主要關注的是受到污染的區域和一些重點保護區域。生態修復的內涵范圍界定不是十分清晰,導致生態修復有關法律法規適用范圍有限;對于受到威脅但是破壞程度較輕地區的關注較少,失去了及早修復的機會。例如,《土地復墾條例》第二條規定土地復墾是針對被破壞的土地進行的整治。《土地管理法》《漁業法》《礦產資源法》等資源型法律的主要立法理念是對自然資源的使用,對其生態價值和生態利益涉及較少。
2.2.2 生態修復義務主體單一
目前中國生態修復主要依靠政府。生態問題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和滯后性,當生態破壞問題暴露時,破壞者已經倒閉或轉移而無從追責,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擔修復責任[7]。比如,在采礦山的生態修復由開采企業承擔,歷史遺留礦山生態修復工作依然由政府承擔。政府財政支出是生態修復資金的最主要來源,2011—2016年,每年中央和地方財政資金占比超過99%,來自社會各方的其他資金占比一直未突破1.0%,在0.4%~0.9%徘徊[8],企業應與政府共同承擔修復責任,其他受益者也應承擔一定補足責任。
2.3 生態修復配套法規不健全
中國目前生態修復相關立法大多僅進行一些宏觀性、原則性的規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不夠完善。例如,《土地復墾條例》《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規定》缺少判定礦區修復成效和追償的規定;《森林法》規定了森林效益補償基金制度,但缺少具體實施程序的規定;缺乏全國性的《草原法》實施條例或實施細則,各地方的實施規定沒有統一標準。
2.4 法律法規監管執行機制不完善
目前對于生態修復法律的長期執行、監管得不到保障。在司法活動中,法院、檢察院等相關司法部門所具有的生態保護修復專業技術知識水平有限,在判決當事人承擔修復責任時,多選擇可以量化的承擔費用方式,對后續費用如何使用以及履行是否到位等未具體規定,如果沒有法律明確規定修復后的監管主體及相關細則,很有可能導致形式化監管。而且國家未規定生態系統修復后進行長期監管的主體,造成監管缺位。因而需要進一步細化生態修復的全生命周期監管機制,協調部門間溝通與協作。
3 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完善思路
生態修復立法體系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具體而言,首先應制定出臺具有基本法性質的生態修復法律法規,完善生態修復的實施、監管和保障體系;中期應完成構建生態修復法律法規體系框架,基本建成符合法治要求的生態修復實施體系、監管體系和保障體系,依法修復和保護生態環境成為生態修復工作推進的基本方式;遠期應建成中國特色生態修復法治體系,“全面依法”成為推進生態修復工作的根本要求和自覺行動。
3.1 制定生態修復基本法
生態修復作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重大戰略的組成部分,在國家基本法層面應當制定《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法》。考慮到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各生態要素的依存性[9],對分散在不同法律法規中生態修復有關的規定統一進行協調,對生態修復進行綜合性的系統規定,對生態修復進行法律性質界定,確定生態修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基本制度及法律責任等。在條件成熟時對憲法做必要補充,增加有關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條款。
3.2 完善生態修復的配套性法律法規
在基本法的基礎上,對《草原法》《森林法》《漁業法》等相關法律中存在差異、矛盾等的條款進行廢、改、釋;制定《國土空間規劃法》《耕地保護法》《生態稅法》《生物多樣性保護法》等有關生態保護修復的一般性法律。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法》的基本框架下,制定國家層面的生態修復法規,如《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法實施條例》;對《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法》的規定進行具體化。修改《城市綠化條例》《水土保持法實施條例》《自然保護區條例》《退耕還林條例》等相關生態保護修復的法規,制定符合各類生態要素特殊性的管理辦法。
3.3 加強對傳統立法的生態化改造
生態文明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除了加強生態修復立法外,還需要遵循生態系統管理的理念,對《行政處罰法》《刑法》等其他上位或者同位的傳統部門法進行生態化改造,不僅在條款中增加生態修復的相關內容,而且在立法理念上也需要遵循生態系統管理的基本規律,有效地保護生態利益,使所有法律形成保障生態文明的合力。
3.4 完善地方生態修復法規
中國國土面積遼闊、生態系統類型多樣、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生態修復應體現出地域的差異性。地方的立法機關應在遵循國家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結合地域自身的生態環境特點,制定符合地區特點的生態修復的地方性法規。
3.5 健全法律法規的執行與監督機制
加強行政監督、社會監督、公眾監督,形成科學有效的監督體系。為實現生態修復工作的預期目標,成立具有法律地位且相對獨立的政府或專業監管機構,通過采取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綜合手段,對生態修復涉及的相關政府單位,以及工程建設主體進行全過程管理和監督;加大生態修復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工作,不斷提高全民法治意識,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保障法律法規的有效落實;建立生態修復專項懲戒機制,明確違法行為及處罰標準,加大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和懲處力度,維護法律法規的權威性。科學合理地界定生態修復執法的權限范圍,促進執法工作的有效開展;完善現有執法管理體制,明確生態修復執法隊伍的領導部門,明晰與相關部門的權責關系,以使相關法律法規長效化落地實施。
4 結語
中國生態修復工作已經進入快車道,然而生態修復體系成型時間相對較短,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不甚完善。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可以平衡各方利益訴求,保障生態修復工作順利開展,并保證生態修復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有必要在推進生態修復工程時,加強對于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首先需要制定一部生態修復領域專門的基本法律,完善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同時對傳統立法從觀念上進行生態化改造,完善地方性的法規,健全執行與維護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