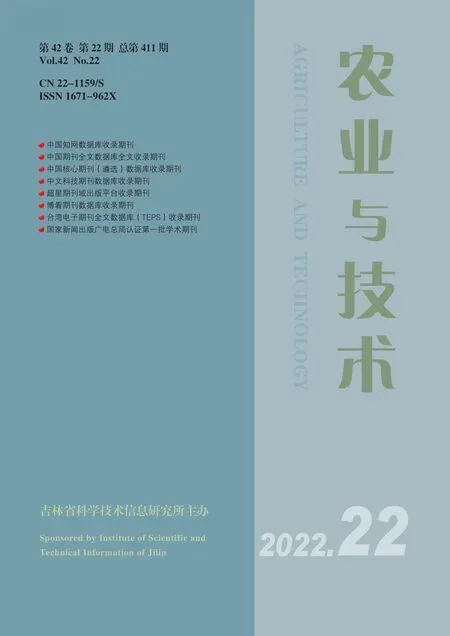貴州省土地利用轉型的生態環境質量演變及驅動因素分析
王佳佳 滕明塔 令狐雪雪
(貴州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也承載著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由于不合理的開發利用使得生態環境逐漸惡化,人類可持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生態環境質量綜合表現了生態系統要素、結構和功能等情況,能夠反映地區生態環境的優劣狀況[1]。在評價指標上,主要有RSEI遙感生態指數(Remote Sensing Based Ecological Index)[2]、RSEDI遙感生態距離指數(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distance index)[3]、EQI生態環境質量指數(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dex)[4]、EQEI生態環質量評價指數(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5]、EV生態環境質量指數(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6];其中EV指數是通過對土地利用進行生態賦值,進而計算地區生態環境質量,自李曉文構建出之后,在生態環境質量研究中的應用逐漸頻繁[7-9]。當前國內對EV指數的研究大都從土地利用轉型的生態環境質量演變[10-12]、生態環境質量的時空演變特征及驅動因素[9,13]等方面展開探討。在探究生態環境質量變化驅動因素方面,偏最小二乘回歸、地理加權回歸[9]、地理探測器[9,14]等方法成為主流;其中地理探測器中的因子探測對揭示驅動因素及機制方面具有較好解釋力,因而得到大量應用[9,14]。雖然目前對土地轉型的生態環境質量演變的研究已大量展開,但側重于關注生態環境質量演變,缺乏對驅動因素系統的探討。由此可見,基于土地利用轉型的生態環境質量演變的相關研究仍需進一步加強。
1 研究區、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圖1 貴州省區位圖
貴州位于中國地勢第2級階梯,平均海拔1100m,地形以喀斯特地貌為主且類型復雜多樣。氣候溫暖濕潤,平均氣溫為10~20℃,降水量為1100~1300mm[15]。研究區地形起伏大,山坡陡峻,土層淺薄,極易發生水土流失[16]。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土地利用遙感監測數據(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s://www.resdc.cn/),分辨率為30m。本研究參考焦露等[17]相關研究對土地進行賦值,見表1。

表1 土地利用分類及生態環境指數賦值
1.3 研究方法
1.3.1 轉移矩陣
轉移矩陣能夠定量表現土地利用的轉移方向及面積,可以較好描述土地的變化規律[18]。計算公式:
(1)
式中,i與j分別為始末的地表覆蓋類型;n為地表覆蓋類型總數;Sij為研究期內第i類向第j類轉化的總面積。
1.3.2 EV生態環境質量指數
EV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綜合考量了研究單元內各土地具有的生態環境質量及面積占比[6]。計算公式:
(2)
式中,EV為生態環境質量指數;t為時間;i為土地類型;LU為土地的面積;TA為總面積;C為生態環境質量;n為土地種類。根據貴州省實際情況,將生態環境質量分為5類,見表2。

表2 生態環境質量分級標準
1.3.3 土地利用轉型的生態貢獻率
土地利用轉型的生態貢獻率指某種土地變化并導致生態環境質量改變[10]。計算公式:
CI=(LIt+1-LIt)×LA/TA
(3)
式中,CI為生態貢獻率;LIt+1、LIt分別為末期和初期的生態環境質量;LA為轉移面積;TA為總面積。
1.3.4 空間自相關
全局空間自相關能較好描述生態環境質量空間分布及變化的空間關聯性與變異性[19]。計算公式:
(4)

局部空間自相關能很好表現縣區與相鄰縣區的生態環境質量空間分布、變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計算公式:
(5)
根據結果可將其分為高-高(H-H)、高-低(H-L)、低-高(L-H)、低-低(L-L)聚集幾種類型。
1.3.5 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驅動因素分析
參考已有研究成果[7,10]并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從地形、氣候、人口、經濟、交通、河流等方面進行指標選擇,見表3。在研究期內,由于貴州進行了行政區劃調整(涉及貴陽市花溪、觀山湖、烏當區以及遵義市紅花崗、匯川、播州區),為保證數據的完整性與統一性,以生態環境質量2000—2020年變化率作為因變量(Y)進行驅動因素分析;在選擇驅動因子方面,以2020年作為時間節點。
1.3.5.1 地理探測器
因子探測對探測因變量(X)對自變量(Y)作用力具有較好解釋力,作用力大小用q值表示[20]。計算公式:
(6)


表3 驅動因子選擇、釋義及來源
1.3.5.2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能很好探究兩要素的相關方向及相關程度[21],本文以相關分析探究不同因素對生態環境質量的正、負向作用。計算公式:
(7)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地利用轉型分析
2.1.1 土地利用動態變化
貴州土地利用類型以耕地、林地、草地為主,期間以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收縮,水體、建設用地擴張為總體演變趨勢,見表4。

表4 2000—2020年土地利用類型變化
2.1.2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貴州土地利用轉移面積呈先小后大的特征,流轉方向總體為草地、耕地、林地—建設用地、水體,草地、耕地—林地,草地—耕地,見表5。
2000—2010年有6523.83km2的土地發生轉移,2010—2020年有15300.7km2的土地發生轉移,建設用地、水體在此期間均為流入土地利用類型且主要從耕地、林地、草地流入。建設用地、水體前期共從耕地、林地、草地凈流入面積(凈流入面積=a從b流入面積-a向b流出面積)分別為274.67km2、280.33km2;后期凈流入面積分別為1540.86km2、496.91km2,后期較前期相比凈流入面積大大增加。2000—2010年耕地、林地、草地之間流轉方向:草地、耕地—林地,草地—耕地;2010—2020年流轉方向:耕地、林地—草地,后期與前期相比,耕地、林地、草地之間相互流轉的面積大大增加。

表5 2000—2020年土地利用類型轉移矩陣
2.2 土地利用轉型的生態環境質量變化
2.2.1 生態環境質量總體變化
貴州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分別為0.5043、0.5074、0.5025,期間生態環境質量呈“先升后降”的波動性減少趨勢,但生態環境質量總體保持在較好狀態,見表6。具體表現為2000—2010年生態環境質量有所提升,指數由0.5043上升到0.5074;2010—2020年生態環境質量有一定下降,指數由0.5074下降到0.5025。貴州生態環境質量總體較好主要得益于林地、草地2類生態用地面積較大,其中林地、草地面積占貴州總面積的70%以上。2000—2020年生態環境質量呈“先升后降”變化,主要是受2002年全面退耕還林影響,林地在2000—2010年大面積增長,促進了生態環境質量提高;2010年后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以及人口增長加速了土地轉型,導致生態環境質量下降。
2.2.2 土地利用轉型的生態貢獻率
研究期內貴州存在生態環境改善與惡化2種趨勢,前期以改善為主,后期以惡化為主,見表7。2000—2010年生態環境以改善為主,草地、耕地向林地、草地、水體流出促進了生態環境質量提高。草地、耕地向林地流出的生態貢獻率最大,貢獻率分別為0.00342、0.00296,兩者之和占總貢獻率的91.23%;林地、草地、耕地向耕地、草地、建設用地流出造成生態環境質量質量下降,林地向耕地、草地流出,以及草地向耕地流出的貢獻率最大,分別為-0.00207、-0.00068、-0.00055,三者之和占總貢獻率的85.15%。2010—2020年生態環境以惡化為主,林地向耕地、草地、建設用地流出造成生態環境質量下降,生態貢獻率分別為-0.00638、-0.00562、-0.00115,三者之和占總貢獻率的84.57%;耕地、草地向林地流出,以及耕地向草地流出促進了生態環境質量提升,貢獻率分別為0.00629、0.00301、0.00077,三者之和占總貢獻率的94.63%。

表6 2000—2020年貴州省生態環境質量指數

表7 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用地轉型及貢獻率
2.3 生態環境質量時空分布特征
2.3.1 生態環境質量空間分布
貴州各縣區生態環境質量以中、較高為主,整體上呈現“東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見圖2。生態環境質量較低及以下的縣區主要分布在研究區中、西部,高質量縣區多分布于貴州南、北、東部。2000年、2010年、2020年3個時期生態環境質量的空間分布格局大體保持一致。

圖2 2000—2020年貴州省生態質量空間分布
2.3.2 生態環境質量空間聚集特征
由表8可知,貴州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生態環境質量Moran’s I指數分別為0.436、0.467、0.533,并且通過0.01顯著性檢驗,說明生態環境質量在空間上具有聚集性特征。從指數變化情況來看,期間Moran’s I指數逐漸增大,由0.436上升到0.533,表明到后期階段,生態環境質量的空間集中度不斷增強。
2000—2020年研究區生態環境質量局部空間自相關聚集類型以高-高、低-低聚集為主,見圖2。生態環境質量指數高-高聚集區主要集中在紅花崗、榕江、望謨等縣區附近,低-低聚集區主要集中在云巖、納雍等縣區附近。

表8 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及其變化率Moran’s I值及參數

圖3 2000—2020年貴州省生態質量指數LISA圖
2.4 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空間異質性特征
2.4.1 空間分布特征
從生態環境質量的空間變化來看,2000—2020年貴州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總體表現為先大范圍提高、局部降低,后大范圍降低、局部提高的特征,見圖3a、圖3b。20a間生態環境質量降低縣區分布于貴州中、西部,而提高縣區多分布于貴州邊緣,見圖3c。研究發現,發展較好及發展落后的縣區多數為生態環境質量下降較快的縣區,如白云、云巖以及晴隆、普安、紫云等縣區,見圖3c。

圖4 2000—2020年貴州省生態質量指數變化率空間分布圖
2.4.2 空間聚集特征
研究區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年變化率Moran’s I指數均大于0,且通過0.01顯著性檢驗,表明生態環境質量變化在空間上具有正相關性,見表8。從Moran’s I指數值來看,2010—2020年的0.344大于2000—2010年的0.313,說明到后期階段,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空間聚集度呈加強趨勢。
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局部空間自相關高-高、高-低、低-高、低-低聚集均有分布,但分布范圍相對較小,并且隨時間流逝變化較大,見圖4。2000—2010年4種聚集類型均有分布,見圖4a,2010—2020年以高-高、高-低、低-低為主,見圖4b,期間僅云巖、觀山湖、南明區保持低-低聚集,可見貴陽市為低-低聚集分布區。
2.5 生態環境質量變化驅動因素分析
由表9可知,貴州省生態環境質量受到地形、人口、經濟、交通等一級指標影響。從q值均值來看,人口>交通>經濟>地形,說明人口是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首要因素,其次為交通、經濟、地形。
人口是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首要因素。人口密度、城鎮化率、人口總量對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作用力為0.499、0.442、0.298,相關系數分別為-0.632、-0.494、-0.378,且均在0.01水平下顯著,表明人口增長是生態環境質量降低的主導因素,其次為城鄉人口結構。
交通的飛速發展是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重要因素。公路密度對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作用力為0.409,并且相關系數為-0.575,說明交通發展造成貴州生態環境質量下降。
經濟發展是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又一因素。從q值來看,地區生產總值(0.436)>二三產業占比(0.338)>人均GDP(0.268),并且相關系數均為負值且通過0.01檢驗,說明地區經濟發展是導致生態環境質量降低的主導因素,其次為產業結構水平的提高。
地形也是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因素之一。從作用強度來看,起伏度(0.384)>坡度(0.307)>海拔(0.201);從作用方向來看,起伏度(0.358)、坡度(0.378)對生態環境質量起到正向影響,海拔(-0.266)則起到負向影響。

表9 貴州生態環境質量年變化率因子探測及相關分析結果
3 結論
貴州呈林地、草地、未利用地收縮,水體、建設用地擴張的變化趨勢;轉移面積呈先小后大的特征,轉移方向總體為草地、耕地、林地—建設用地、水體,草地、耕地—林地,草地—耕地。
生態環境質量呈“先升后降”的波動性減少趨勢,2000—2010年草地、耕地向林地流出促使生態環境質量提高,2010—2020年林地向耕地、草地、建設用地流出導致生態環境質量下降。
各縣區生態環境質量以中、較高為主,整體上呈現東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生態環境質量在空間分布上具有聚集特征,隨時間流逝空間聚集度不斷增強。
生態環境質量總體表現為先大范圍提高、局部降低,后大范圍降低、局部提高的變化特征;到后期階段,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空間聚集度不斷加強。
生態環境質量受地形、人口、經濟、交通等指標的影響,作用力大小:人口>交通>經濟>地形。人口、交通與經濟的二級指標均對生態環境質量起負向影響,地形中的海拔起負向影響,坡度、起伏度則起正向影響。
本研究在指標選取上存在一定不足,受限于數據的連續性、可獲得性、量化性等原因,未選擇其它指標,如政策等。在今后的探索中需要進一步識別不同因素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期為政策制定及評估提供一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