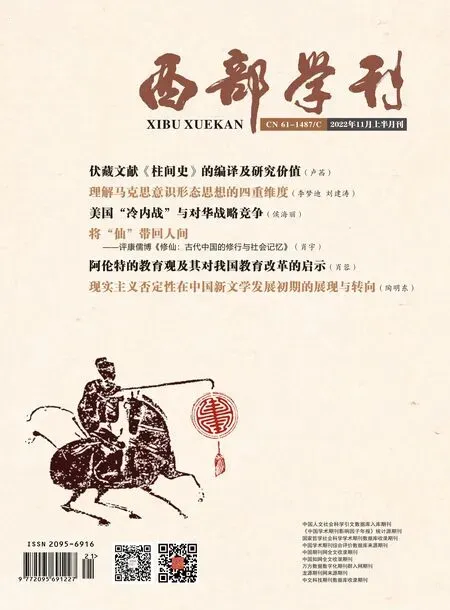理解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四重維度
李夢迪 劉建濤
一、起源維度:意識形態是現實生活過程的反射
馬克思指出:“從他們(即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引者注)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1]73可見,意識形態起源于現實生活過程,是生活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生活。但是,在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學傳統將世界劃分為兩個世界,即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他們認為真理存在于超感性的世界中,比如柏拉圖的理念論、黑格爾的自我意識哲學等均堅持此種觀點。感性世界變遷的根據在于超感性的世界,而超感性世界變遷的根據在于自身的內在邏輯。譬如黑格爾哲學認為,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根據就在于辯證邏輯,辯證法是推動事物自我否定和發展的動力。在該理論的視域下,意識形態的根源不是現實的生活,而是其內在性的邏輯發展,這就阻礙了對意識形態自身起源的追問。再譬如作為德國小資產階級的康德哲學堅持從意識形態出發去闡釋現實生活,具體而言就是從理性出發來闡釋現實生活。康德認為,人的理性不僅可以用來認識自然界,還可以用來建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前者為理論理性,后者為實踐理性。實踐理性可以把握到超感性世界的成員,比如“人格”“貨幣”“資本”“國家”等,而這些是建構社會關系和社會世界的前提和基礎。因此,以康德為起點,一直到以黑格爾為集大成者的德國古典哲學將社會關系歸結為由人的頭腦而產生出的觀念關系,還要再用人的理性思維去論證這樣的觀念。這就從根本上顛倒了意識形態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
馬克思戳破了唯心主義用意識形態觀念建構社會關系的思想,他指出“在哲學家們看來關系=觀念”[2]585。這是馬克思對唯心主義哲學家們思想建構現實觀點的直接批判,他認為在這些哲學家的視角中,現實的生活關系及其變遷成為觀念的關系及其變遷。馬克思指出,我們要以現實生活為出發點,從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出發來解釋意識形態的形成及其發展。現實生活和物質生產是在一定意識中進行的,無意識的生活和物質生產不是屬人的,是不可想象的活動。但這種與現實生活和物質生產交織在一起的意識并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實踐的意識”[2]534或“感性意識”[2]197。只有在真正的分工形成之后,即在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形成之后,意識形態才得以真正的形成。這是因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意味著從物質生產領域中會分流出一部分人專門從事意識形態的工作,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所具有的統治關系。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就意味著該階級在生產領域以及其他領域建立起了統治性的社會關系。因而,馬克思指出:“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2]534意識形態就在自發性的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分工的推動下,以精神產品的形式正式出現了。馬克思同時指出,意識形態看似有自己的發展史,擺脫了現實生活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但實際上它的感性根源仍然在于歷史性的物質生產而非自身。從事著物質生產和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然和社會的同時,也在改變著自己的意識及其產物。當然,意識形態對現實生活過程的反映有時候并不是同步的,或超前或滯后。比如德國的古典哲學和它的現實狀況并不同步,屬于較為超前的思想體系,反而更接近于法國的現實狀況,因而馬克思把德國哲學稱之為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
二、本質維度:意識形態是表達真正經驗的束縛和界限的觀念
馬克思指出:“觀念,即關于真正經驗的束縛和界限的觀念;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交往形式就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1]83由此可見,作為觀念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一種“束縛”和“界限”,這表達的是“真正經驗”運動的界限,即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運動的界限。突破這個界限,人們交往方式的性質就會發生改變。“束縛”和“界限”其實是一種限制性、否定性的表達,但現實的意識形態卻以社會的正面價值形式出現。譬如在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以正面價值的形式所表達出來的榮譽和忠誠。而事實上,封建社會是以土地私有權為基礎來建構社會關系的,農奴在貴族的莊園上勞動,比奴隸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形成的是半人身依附關系;同樣,在城市封建行會中的徒弟與師傅的關系、由層層分封而形成的封主和附庸臣屬之間的關系也都是半人身依附關系。這其實就是封建社會對人的一種界限和束縛,但是它卻得到了意識形態的正面表達,名之曰忠誠和榮譽,封建社會的物質生產和交往方式就在這樣的半人身依附的界限中運動著。但當物質生產和交往方式的運動突破了既有的界限和束縛,比如突破了封建社會半人身依附關系及其在意識形態上的表達,那么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就會被反映新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意識形態所取代,即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取代。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自由、平等,它對人來說同樣也是一種“束縛”和“界限”。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和交往是建立在價值基礎上的,這就意味著等價交換成為資本主義市場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進行交換的雙方都承認自己是商品的擁有者,以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因而雙方都是等價交換的主體。但是這種主體是建立在價值基礎上的獨立的個人,要求交換過程中的平等和自由。這種經濟領域的平等和自由反映到社會觀念和法律之中,就構成了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和交往就在獨立的個人、自由和平等的界限中運行。資產階級為了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會宣稱這樣的意識形態是天賦的。事實上,自由和平等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表層,它的深層是不平等、不自由的,獨立的個人也是彼此分離和對抗的,這本是否定性的內容,但卻以自由和平等的正面價值予以表達。
總之,從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忠誠和榮譽到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自由和平等,它們都是一定歷史階段社會交往形式的否定和限制,但這種否定和限制卻以正面的、肯定的形式表達出來。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私有制中,社會交往形式異化為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社會權力。為了掩蓋、粉飾統治階級的社會權力不得不以意識形態的形式進行正面的肯定和表達,以迷惑被統治階級,緩和階級矛盾。但我們不可忽視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較封建社會而言是一種進步,它消滅了等級壓迫,實現了政治領域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群眾基礎要比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更為廣泛。
三、階級維度: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思想的表達
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不僅占據著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分配,更是以社會思想的生產者身份實行統治,進而“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1]99。因此,精神資料的生產由統治階級嚴格掌控,生產出的精神資料以各類形式維護現有的統治秩序,并組成了滲透在社會生活領域內部的意識形態。從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階級維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在馬克思視域中,作為統治階級思想表達的意識形態具有以下四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并非完全符合階級內部成員具體的、細微的利益,它實質上是對階級根本利益的表達。這是因為勞動的分工同時也使得統治階級內部的成員發生了分化,一部分成員是脫離了社會的物質生產鏈條而作為思想生產者的“意識形態家們”,另一部分成員是“對于這些思想和幻想則采取比較消極的態度”[2]551,往往從事實際的管理,沒有時間專門去制造意識形態。這就意味著在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制造者和實際從事生產的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和分裂的可能,有時這種矛盾和分裂會使彼此達到對立和敵視的程度。但這都是表面的現象,一旦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脅時,這種“對立和敵視”就會立刻消失,統治階級內部的兩大群體就會聯合起來對抗外敵。
第二個特征,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1]98。階級究其本質來講就是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人格化表現,而最根本的社會關系是生產領域的關系,因而與統治階級相對應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對自身在社會上占統治性地位的物質生產關系的觀念表達。在階級社會中,生產關系實質上是積累的勞動對活勞動的支配,這種支配帶有對抗的性質。越是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它所具有的支配性就越強,所蘊含的對抗性也就越強烈。因此,占據社會主要物質資料生產與分配的統治階級,同時就具有了來自生產領域的強大的統治性權力。而這種統治性的權力是普照的光,它會要求自己在思想領域內也占據著統治的地位,進而為其提供存在的合法性證明。
第三個特征,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對其他階級的思想具有統攝力。在馬克思看來,不論在哪一時代,作為統治階級思想表達的意識形態,都在社會思想領域中占據統治性地位。并且由于統治性的地位,意識形態對社會的其他思想具有統攝的力量。這種思想領域的統攝力來源于三個方面:其一,其他社會成員被排除在精神資料的生產之外,物質生產的繁重壓力使他們無暇創造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體系,只能被動地選擇統治階級生產出的精神產品;其二,作為社會性的人,思想的認同是進入社會的先決條件,其他社會成員為了進入社會而不得不接受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其三,統治階級的思想充盈在社會生活之中,其他社會成員從出生開始就已在其思想教化之下,他們像漂浮的浮萍,所思所想都被“天然”地局限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框架之內。
第四個特征,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具有普遍性。由于階級利益的狹隘性,導致了統治階級自身特殊利益與社會普遍利益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矛盾。為了減弱這種來自物質生產領域的利益沖突,統治者總是將自身階級的特殊利益描繪成為全社會的普遍性利益,并將它當作一個客觀的社會事實。這就使得代表本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成為社會中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另外,在這個階級爭奪社會的統治性地位之前,為爭取社會上其他成員的支持,進而減少自身上升的阻力。階級內部的“意識形態階層”會有意識地將自身“階級意識”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鼓吹成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最起碼也要比以往的意識形態更加具有普世價值的意義。因而歷史地來看,統治階級的群眾基礎越廣泛,反映它的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也越具有普遍性。
四、功能維度:意識形態維護的是現存統治關系
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功能,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為政治上層建筑提供合法性的價值論證、為統治性的生產關系作辯護、為社會提供觀念性立法。這些功能具體來說有不同的發生、作用機制,但究其本質都是以維護社會現存統治關系為目標。
第一,意識形態為政治上層建筑提供合法性的價值論證。馬克思指出,建立在由社會生產關系總和所構成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包括兩個部分,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與“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3]。其中,由法律體系、政治制度、國家權力等圍繞社會經濟結構建立起來的,就是統治階級的政治上層建筑,這是統治階級維系自身統治的物質力量。圍繞著政治上層建筑,由哲學、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等意識形態構成的是觀念上層建筑,這是統治階級維系自身統治的精神力量。如果說政治上層建筑是以法的形式確認占統治性地位的物質生產關系,那么作為觀念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就是以價值認同的方式使社會成員接受統治階級及其建構的統治秩序。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之所以被接受,其前提就是在價值上認同了它,而論證統治秩序的價值認同恰是意識形態的核心作用。譬如資本主義制度為什么比封建制度先進,這是因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如哲學、宗教都論證了這種制度和生產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權,的確比封建社會的等級壓迫要先進。通過這種價值論證,資本主義制度就具有了合法性、合理性。因而對政治上層建筑的合法性確證,同時就是使社會成員從價值觀上的肯定與認同。
第二,意識形態為統治性生產關系做辯護。馬克思指出:“物質生產中的對立,使一個由意識形態階層構成的上層建筑成為必要。”[4]這也就是說,生產中的對立使得意識形態的辯護功能成為可能。統治階級所具有的社會權力產生于物質生產領域,這是支配整個社會生產與統治關系的權力。在封建社會,貴族主要訴諸神學,例如“君權神授”等,他們試圖證明相繼出現的統治思想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聯系”。由此,推導出在生產領域中占統治性的封建生產關系就是合法的,其他與自身對立的生產關系就是非法的存在,而非法的不能推翻或替換合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比封建社會的剝削更為隱蔽,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對其生產關系的辯護也就更加隱晦。它不再采取神學的形式,而是主要地采取人的形式,比如人的平等、自由、人權等形式。作為統治者的資產階級試圖在用資本主義生產表層的平等掩蓋其深層的不平等,用自由的市場經濟掩蓋并不自由的社會現實。同時,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把生產關系通過范疇轉化為經濟關系,這樣內在具有對抗性的生產關系就變成了非對抗的、理性的經濟關系,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就在經濟關系中被遮蔽掉了。同樣在哲學領域,以黑格爾為主要代表的哲學家們將人類歷史看成是精神的歷史,并將生產關系看成是精神在現實生活中的表達,這就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主體化運動顛倒為了精神的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論證成為了永恒的存在。
第三,意識形態為社會提供觀念性立法。在批判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時,馬克思指出“現實世界是觀念世界的產物”[2]510。這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建構出了與現實的感性社會相對應著的思想社會,思想的社會卻統治著感性的社會。意識形態以觀念的形式限制現實的人,規定其主體能動的范圍。例如,天主教是封建社會由貴族階級主導的觀念立法形式,新教是新興資產階級主導的觀念立法形式。雖然教徒們看似都信仰同一個上帝,但他們卻代表著本質不同的利益。新教摒棄了天主教的神父溝通原則,確立了自由信仰的原則,通過宗教這一意識形態的形式,表達出了以手工業者和商人為主的第三等級的感性意識。第三等級在他們的生存條件中,即動產和手藝中所產生的這種感性意識,使他們領會到了自身與封建生產關系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沖突性。因此,第三等級和封建貴族展開了長期的斗爭,這種斗爭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歐洲歷史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長達三十年的斗爭,實質上就是在爭奪宗教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觀念立法權,更是在爭奪未來社會的統治權。可見,由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思想社會是對感性社會的觀念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