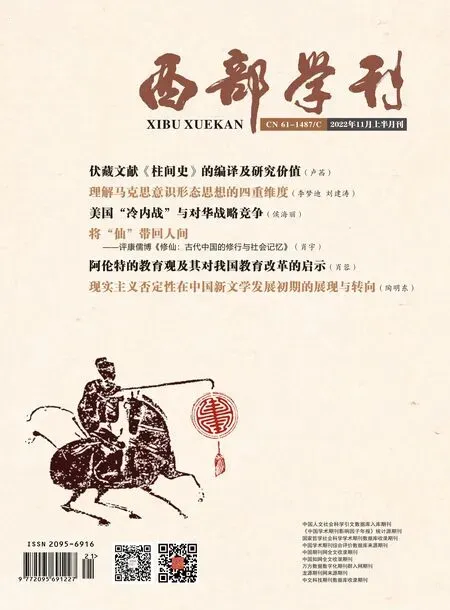清末作為社會公共空間的留園
王歡顏
位于蘇州閶門外的留園作為我國四大名園之一,是蘇州園林的典型代表,其泉石之盛、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總是引來游人如織,是蘇州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景點。學界以往對于留園的研究多集中于園林風景與造園藝術,以及盛氏家族與留園的關系[1],或從義莊與宗族角度探討留園義莊與清末社會[2]。筆者在閱讀晚清相關史料時,發現留園不僅是盛家的私家園林,更是一處重要的社會公共空間。上至官員紳士下至平民百姓無不成為留園的園中客,在其中上演著紛繁多樣的戲碼。晚清社會改良之際,借助留園的場地,旨在通過競爭促進商業發展的蘇府物產會、義振游覽會等均在此召開。本文通過梳理留園成為社會公共空間的過程,認為從太平天國戰后至清末,留園作為公共空間承載了社會改良的期冀,也成為諸多社會問題發生的場所。走向現代的晚清蘇州社會有著豐富的面向,通過對留園這一城市公共空間的考察,可以觀察蘇州在現代變遷中的經歷與矛盾。
一、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留園
留園始建于明嘉靖年間,太仆寺少卿徐泰時歸隱故鄉后,在閶門外下塘的花步里營建了疏闊淡雅的東園。徐泰時過世后其子孫經營不善,園林幾易其主。清朝嘉慶年間東園為蘇州紳士劉恕所購,經營修繕并以寒碧莊命名,時人多以主人之姓稱為“劉園”。1860年蘇州被太平軍攻破,千百年名跡盡為淹沒,無數管笙樓臺化為灰燼,而劉園因被天國諸將領喜愛,成為其各游玩之所而免遭破壞。戰亂之后,1876年,晚清重臣盛宣懷的父親常州人盛康在蘇州投資置業,花白銀五千余兩購得劉氏寒碧莊并進行修繕,使得園林面積在原徐氏東園和劉氏寒碧莊的基礎上有所增擴,園林布置“比昔盛時更增雄麗,卓然為吳下名園之冠”[3]。增擴修繕的園林面積近三十畝,園林分三部,東部以建筑為主,廳堂華麗,庭院精美;園林的中部以水域為主,山明水秀,古木蔽空;園林的西部則如置于山林之中,溪邊林下,頗富山野之趣。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學者俞樾在為此園做記時,曾問園主是否另賜嘉名。園主盛康認為“寒碧之名至今未熟于人口,然則名之易而稱之難也。吾不如從其所稱而稱之。人曰劉園,吾則曰留園,不易其音而易其字,即以其故名而為吾之新名”[4]。經歷了兵燹的蘇州滿眼荒涼,而閶門外的劉園卻得以留下,滄海桑田歷劫不磨,因此取名諧音“留園”。
留園本為盛家的私家園林,但園主并沒有讓留園孤芳自賞,而是敞開園門任蘇州城百姓游覽。留園被盛康買下修繕的第二年(公元1877年)5月,“月之初二日,開柵放人游覽,三日內不取分文。為修好街鄰之意,自初五日起每人進園收錢七十文,蓋以備日后園中修理之費也。”[5]此后,每逢春秋兩季及節日留園都會開放供游人觀覽,引得傾城士女聯袂來遊,不論男女老幼都得以欣賞留園美景。每逢春季蘭花會來此賞蘭花,秋季賞金桂,已成了蘇州城的又一習俗。晚清重要的報紙《申報》屢屢報道留園開園引來眾人游賞的新聞,“閶門外盛氏留園每逢春秋兩候,開放遊人觀覽。日來,園中桂花盛開,秋色斑斕,各處得興,寶馬畫舫歌船絡繹不絕。”[6]“距金閶不二里,有留園焉。園中樓臺昳麗,水木清華,為省垣諸園冠。以故春秋佳日,士女如云,較他處獨盛……近日秋高氣爽,涼燠適宜,遊人接踵聯裾如水趨壑。入其中者,臨矚之余,輒相對茗坐,幾無隙地。”[7]
園主慷慨大方的開園之舉使得留園成為蘇州的一個重要公共空間,不論男女老幼,紳士商賈、富戶平民均可來這方園林內游玩、賞景、品茗、宴會,日常收費為70文每人,若遇重要節日則減半收36文,“立夏佳節,蘇閶外盛氏留園特于是日減價一半,每人止收三十六文。于是遠近聞風而至者,摩肩接踵,自辰至西,蓋不下數千人云。”[8]根據1876年生于蘇州并長期生活在那里的包天笑記載,他兒時的物價相對較低,鴨蛋七文一枚,雞蛋五文一枚,鄉下人采摘的草頭2文一扎,一石米約三千文,夠小家庭的包家吃4個月,二元錢就可以請一席八個碟子(冷盆干果)、四小碗(兩湯兩炒)、五大碗(大魚大肉,全雞全鴨)的客了[9]。對于蘇城人家來說,70文約為普通百姓之家一日所費,且留園常常因為節日打折,普通人家偶爾游園完全負擔得起。由于留園初開時不收分文,故聞風而至者,無不爭先游覽,致使園內擁擠異常。甚至有一些游手好閑之人,故作擁擠以偷取財物,以致園內混亂不堪,園主特請官兵來維持秩序,并雇傭了三十余名園丁,在每日閉園后打掃以恢復園林整潔之姿[10]。
留園的日常管理由留園義莊負責,盛康在購園后即在園內設置義莊,園額即為“龍溪盛氏義莊”。留園并不單獨屬于盛康,而是整個盛氏家族的產業,包括留園在內,盛氏家族義莊的產業包括義田、祭田、祠堂、家善堂、房屋等。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盛康去世,盛家的產業由其長子盛宣懷主理,他的幕僚鄭恩照負責總理留園義莊的日常事務。為方便留園的日常管理,園內雇有賬房、管門(兼收門票)、花匠、園丁(照料花草、鳥獸)、園林各處專職看守人員、巡丁、更夫等[11]。上海圖書館館藏的盛宣懷檔案現存有近五十份留園報單,根據這些報單的記錄,留園的管家鄭恩照或其他執事每月會分三次整理留園報單寄給盛宣懷,上面詳細記載每旬每日留園售出的門票數量、轎票數量以及園票和轎票收入,到了年終歲尾還會總結年度游客數量及收入進行匯總上報盛宣懷,賬目條分縷晰、有板有眼。以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為例,該年共收園息洋五千六百五十七元,錢八百七十一千九百文[12]。在園林的經營上,除提供日常游覽玩賞之外,還可以在留園飲茶、設宴,園林也會購入名花佳卉、珍禽異獸供人參觀,并派專門的工作人員管理喂養。按現存的留園報單來看,留園的日均瀏覽人數超過一百人,每逢天氣晴好的春秋佳日,日常游覽人數則有兩三百之數。若遇到節日如清明、端午、立夏、春節后的開園日等,來園人數則會暴增至上千人。根據留園報單記錄,鄭恩照管理留園事務后,留園基本上除春節等節日外全年均對外開放。
雖說太平天國運動之后蘇州的一眾園林如怡園、獅子林、拙政園(時為八旗會館)均再次對外開放,但留園卻較他處獨盛,除了園中景色怡人外,與其位置和周邊環境是分不開的。留園位于蘇州城西北部的閶門之外,清末蘇州的六座城門中,閶門是最繁華的一處城門,“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13]雖然經歷太平天國戰亂,閶門一帶曾化為灰燼,但戰后傳統景觀逐漸回歸的同時,現代化的景觀如洋樓、電燈、馬路等也出現在閶門附近。閶門開了馬路之后,戲園堂子也紛紛搬至閶門一帶,使得這里再次成為蘇州最繁華的城門[14]。閶門外不僅商業娛樂業發達,風景更是絕佳,出閶門由山塘至虎丘是蘇州人和外地游客最喜愛的游賞路線,四季皆有佳景,總是游人如織。
1906年蘇滬鐵路通車,鐵路沿蘇州城北而建,車站就位于距閶門外不遠的地方。從前上海到蘇州乘小火輪需要12小時,鐵路通車后兩地之間的通車時間則縮短至兩小時,滬寧線附近商業更加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游客。自此蘇州上海之間的往來更加便利,來蘇州游覽之人大多會就近到訪留園游玩。1907年時,閶門與車站相連接的馬路通車,借此機會,盛家的留園義莊共捐助四千元修建了由閶門附近楊安浜至留園的馬路[15]。馬路開通以后,蘇城內外的游客通過水路、馬路、鐵路等多種交通方式均可到達留園,“車水馬龍,游者益眾。過金閶者,無不以斯園為尋優選勝之佳境矣。”[16]對外開放的留園逐漸成為蘇城內外的游客所熟知的一處公共空間,除了游覽的功能之外,在由傳統走向現代的蘇州城市,留園開始承接了一項新的功能——賽會場地。
二、賽會場地改良前沿
近代以來,傳統時期的重農抑商思想逐漸被顛覆,商戰、挽回利權、鼓勵工商、振興實業等成為常識和新的社會自覺。晚清新政以來,以物產會、勸業會、陳列會為主要形式的賽會活動成為社會各界改良人士所贊同的振興實業之舉。在賽會上各個展品優劣立現,通過獎優裁汰來鼓勵競爭、振興商業,在日趨激烈的商戰中,迎戰外國工商之沖擊,挽回國家之利權損失[17]。賽會地點的選擇則需要兼顧地理位置、交通、商業發達程度等多種因素,位于蘇州閶門外且靠近鐵路的留園成為蘇州賽會場地的首選。
1909年,為響應即將召開于南京的全國性博覽會——南洋勸業會,蘇省農工商務局會同蘇州商會共同籌辦蘇府物產會。為省去場地建設的費用,蘇府物產會監督和辦事處人員經商定決定借城外盛氏留園中大戲臺、四面廳等處為物產會陳列參觀之處。為振興工商,積極響應勸業之舉,盛宣懷同意了借園之請。留園東部以建筑為主,此處的林泉耆碩之館為典型的蘇州園林中的大型廳堂,面闊五間,四周皆可觀景并繞以圍廊,這種廳堂樣式也被稱為四面廳。林泉耆碩之館南部的天井外即為盛家的大戲臺[18],也是近代蘇州第一座室內雙層三樓大型戲廳。面積寬闊、環境優美的四面廳和大戲臺用作室內展廳,且專為參加物產會的游客可以從留園東部出入,使物產會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
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七月初一,蘇府物產會在留園盛大開幕,蘇城百姓紛紛參會,每日售出游覽券近千張,每張取小洋五分由附屬留園代收。蘇府物產會開幕后官商學界參觀者甚多,蘇州周邊各府縣人士亦慕名而來,“鎮江府承太守,常州府商會總協理暨紳商學界中人均經到會參觀。”[19]為防止男女雜處引發社會問題,特規定“初一日起至初四日止男賓參觀,初五日起至初八日止女賓參觀,初九日起至十二日止男賓參觀,十三日閉會”[20]。此次蘇府物產的展品分天產、工藝、教育、美術四大類,蘇省各地共展出了超過三千件展品[21],官紳各業代表將各種物品審查研究評出獲獎產品予以鼓勵。這些展品不僅涵蓋了蘇州傳統農副產品和織錦雕刻等手工藝,也有諸多新事物和工業產品展出。
物產會作為賽會的一種形式雖然引發了蘇城百姓的關注和討論,但畢竟是有時間限制、會期固定的展會。為擴大工業而暢銷路,各地商會和農工商局開始致力于常設性勸工廠、陳列所的創建。在官府的倡議和蘇州士紳的努力下,現代商場的雛形,固定的商品陳列所出現在了蘇州。1908年末蘇省商品陳列所正式開始籌備,在選擇地點時閶門、留園再次落入大家的眼中,“查商品陳列所宗旨原為振興實業,便利民生,而尤重在獎勵輸出物品,使外人藉此為介紹之資。故建設該所,必須繁盛之區,方有裨益。”[22]留園右側靠近留園義莊的上津橋一帶本為民房,太平天國兵燹之時街巷被毀,淪為一片荒地,后被清兵右營所占,用作練兵之地。等到戰爭結束,營房操場逐漸被廢棄,這塊位置佳又靠近留園的地方最終被選為商品陳列所附屬勸工廠的建設地址。
1911年4月15日,蘇州官員和商會士紳悉心準備了近三年商品陳列所正式開幕。在留園管家鄭恩照給盛宣懷的信中,他描述道“聞留園馬路口陳列所已于上月十六日開幕,前數日游人極盛,每人收銅元兩枚,有逛園而改游陳列所者,有游陳列所而順道游園者……然陳列各品程度尚淺,無甚足觀,是以未及匝月而游人已寥寥”[23]。1911年10月義賑游覽會再次借留園開會演劇,然而因為武昌起義,人心惶惶,且“每天上下有五六十人來園布置,喧賓奪主,蹭踏不堪,不勝其擾,游資亦受影響矣”[24]。伴隨著清朝的歷史走向落幕,這次義賑游覽會以失敗告終。
賽會這一名詞并不是舶來,而是自古有之,常與迎神一起出現,稱作迎神賽會,是承載著人民日常宗教生活的重要儀式。在吳地,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每逢重大的宗教節日,諸如城隍廟會、東岳神誕、觀音誕等,都會舉行迎神賽會,張燈演劇,百戲竟塵,游觀若狂。眾多的香客自然引來了諸多商販在此聚集,形成了獨特的賽會市集。所以蘇府物產會的曉諭才說“賽會雖系西法,說來亦甚尋常。各處趕墟趕集,意思可以比方”[25]。當西式的博覽會來到蘇州,平民百姓自然以曾經熟知的“賽會”概念來理解它,留園作為賽會的承接地,對于積極參與社會改良的士紳來說,它是推動蘇州商業進步,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權的希望之地,但對于普通的蘇州人來說,它在游觀的基礎上增加了新功能,一時間引得人們紛至沓來。但由于展出的產品品種有限,且背后缺少工業進步帶來的產品革新,借賽會以鼓勵工商振興實業對于清末的蘇州城來說任重而道遠。
三、社會問題發生之地
由于優越的地理位置,旖旎的園內景色加之園主和管家對勸業工商的支持,太平天國戰后的留園成為蘇州一處極受歡迎的公共空間。由于原則上不分性別、階級的對外開放,社會各個群體紛紛涌入園內,上演著一幕幕紛繁復雜的故事,留園也成為諸多社會問題發生之地。
在留園玩賞的眾多游客中,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夾雜其中,成了園中除花木亭臺外的又一道風景,“蘇閶外盛氏留園于月初開門,來者絡繹不絕。至清明日,則如蜂之屯如蟻之集。其中粉白黛綠拽長袖而拖輕裾者,十居其五。故是日園中比之眾香國天女散花有過之無不及也。”[26]留園的游客群體中女性游客約占一半的數量,不僅有官宦紳士人家的婦女、小姐,也有妓院青樓中的姊妹。自古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仕女每每出街必精心打扮,釵環粉黛力求時尚美觀。婦女們出現在園林中,并成為園中一景時,就不可避免地引來一群浮浪少年,引出一樁樁社會事件。
每年的春夏之際是留園風景最秀麗的時候,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的一個春天,留園“牡丹大放,滿眼芳紅。有某氏女郎約閨友兩三人緩步花磚,留連風月。不虞某氏子尾隨,雖不敢公然調戲,然輕薄之意亦可想而知。事為洪某所見,勃然大怒,謂何物狂且竟敢若此無禮,獨不謂乃公手下無情耶,驀揮拳擊落其眼鏡。某見事不妙飛步逃脫”[27]。無獨有偶,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的春天留園內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有一小家女,年可十五六,娉婷裊娜愛好天然,徒倚雕闌流連風景。少年子弟一見銷魂,品足評頭百般調笑,女赧顏微露無可奈何,正在窘迫之際,忽有白袷名流大踏步而出,怒謂何來惡少敢放肆輕狂,豈以為崔家護花旛不能拳盡游蜂浪蝶耶。于是眾始驚散,然女已粉汗蒸淫驚魂幾斷矣。”[28]浮浪少年屢屢調戲輕薄留園中游玩的閨中姊妹,幸運的是《申報》報道的這兩件花下揮拳事件,都有正義人士出手將流氓惡少趕走,閨中少女雖然頗受驚嚇但并無大的損失。
官方對此類事件是什么樣的態度,又是如何處理的?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葉姓典史之子在留園游玩,因為女色與他人動武,大打出手致人受傷,撫院黃中丞得知后,本將署滬的葉典史因此而丟官,并“榜示官廳以為不能約束子弟者”[29]。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官方頒布禁令,禁止攜妓冶游,“閶門外巡總委員乘坐官船并帶小船數支在在三塘橋轉角河口與桐橋浜兩處停泊,令差保等逢船探望。如有眷屬及妓女即行高聲喝阻,不準開付虎丘。”[30]這年五月官方再次發布憲諭“凡城廂內外各園,不準擅放婦女入內游行,并派差分往傳諭各園遵照憲諭莫不奉令,維謹標貼園門”[31]。此外,蘇府物產會和蘇省商品陳列所開設之時也專門將男賓與女賓參觀的日期分開,以防止男女混雜。官方的態度看似是非常嚴格的,甚至有官員因為沒有好好約束子弟在園林鬧事而被撤職。然而官方雖屢屢禁止設關卡查驗,游人們則選擇轉換其他道路與目的地,“獨留園一處游船反較虎丘為多,蓋多屬過卡折回顧而之他也。”雖然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春天嚴禁婦女入內的告示明確貼在了各園林門口,然而一年過后的春日,當留園錦繡天地風光無價之時,西園公子,南國佳人,扇影衣香,花光人面依然是流連其中。雖然蘇省商品陳列所標明男女分期參觀,但“十六為招待男賓之期,不意陳列所竟有女子叢集其間”[32]。
其實清朝時期婦女在公共空間的活動頻率本就不低,婦女已經成為社會上重要的消費群體,不僅在重要節日、廟會、進香等時節會出戶游觀,且每逢出游必精心裝飾,“蘇樣”“蘇州妝”甚至引領全國的時尚潮流[33]。蘇府物產會借留園開展并設定男女分期參觀,事實上留園早已男女混雜參觀,這樣的設定實屬多此一舉。在蘇省商品陳列所開展之時,各業出品人就為變通男女分期參觀之事上報蘇商總會,指出數端窒礙不便之處,物產會、陳列所等展會本就是為振興商業,爭奪利權而從西方借鑒來的一種活動形式,這種活動形式本就是男女混雜自由參觀的,然而到了中國卻要加上性別的限制,不免讓人有厚彼薄此,為外人開后門的觀感。且女性群體,尤其是上流社會婦女的消費能力是不可小覷的,她們又不習慣單獨出行,若男女分期則很有可能喪失許多消費機會,這就違背了商品陳列所開辦的本意。鑒于此等理由,農工商局的批文是“所請男女變通分期參觀一節,自可照準。維該所長隨時認真督察,務使秩序井然,至為重要。”
再則隨著清朝末年風氣漸開,婦女解放、女權、女子上學等思潮漸漸興起,在留園這方空間內,也有勇敢追求自由戀愛的舉動,“蘇垣某女士,肄業某女校有年矣。平日醉心歐風,深注意于婚姻之改良。今春往游留園,得遇某氏子,某精西文,一語通姓名,兩相愛慕,遂有指環互換之約。女母非開通者,而生家又窘于資,好事多磨,不得已于上月相攜偕遁。母知之,以為大辱,乃重金購之,如捕盜賊,現聞已合浦珠還。而癡男怨女慘離鸞,日為以淚洗面而已。”[34]晚清的留園中,不僅有浮浪少年調戲婦女的事件,也有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富家千金勇敢追求愛情的故事,雖然上述事件中的一對鴛鴦被封建觀念甚深的女方母親棒打分離,但我們也可得見在蘇州的留園,隨著時代的變遷,悲歡離合的故事屢次上演。
在普通蘇城百姓眼中,留園或是風景絕佳的玩賞之地,或是男女雜沓的問題場所,然而在商人眼中人口密集的留園卻是一處可以發財的地方。留園的管家發現了商機,向盛宣懷提議若能于園外多建房屋,開設店肆,則冷落之區將變為繁盛市廛。1906年鐵路通車之后,來留園游玩的游客日漸增多,閶門馬路的兩家番菜館,詹潤泉的普天香番菜館和仇啟臣的一品香番菜館都中意了留園的商機,意欲在園中制賣番菜。不料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七月,留園管家鄭恩照卻被一紙訴狀告到了官府,一品香菜館的仇啟辰告留園管家鄭恩照言語蠱惑其來留園開飯菜管,并向其收受五百元私費,又因費用未按數交齊,招徠唱戲人在園中另開菜館[35]。鄭恩照作為盛宣懷的幕僚,為盛家經營管理留園二十余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為何會在此時收受賄賂,自毀名聲?原來仇啟臣為壟斷留園的大菜生意惡人先告狀,幸虧留園附近同泰煙錢店與逍遙樓茶館老板作證才洗刷了對鄭恩照無端的污蔑。這一事件過后,留園并沒有重新訂立招租章程,整頓商業秩序,盛宣懷決定普天香、一品香兩家均不得在園內開設菜館。留園終究是盛家的私家園林,不是專門為了商業而經營修繕,當商業糾紛影響了園中清凈與聲譽,盛家的選擇則是干脆放棄一部分商業利益維持園林原貌。
四、結語
在蘇州,大部分的園林都為專屬于某個家族或某人的私家園林,園林多為園主社交會友的私密空間,但位于閶門外下塘花步里的留園通過收取少量游資,原則上不分身份財富的對社會上所有人開放。不像虎丘山塘街等純開放型景點,留園作為兼商兼官的盛家的私家園林,經多次修繕經營,景色清麗可人,被圍墻圍住的不僅是園內的景色,更是普通百姓對于富紳生活的好奇與向往。雖然清末時期,包括拙政園、怡園、留園在內的一眾園林均擇時對外開放,但是由于留園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園主開明的經營態度,它成為晚清時期蘇州最受歡迎的一處公共空間。
關于中國近代城市公共空間的研究已經引起了諸多城市史、城市建筑學者的興趣,并展開了廣泛討論[36-39]。嚴格上來講,城市公共空間其實是從西方舶來的一個概念,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公共空間一般被定義為由公共權力創建并保持的,供所有市民使用和享受的場所和空間[40],諸如廣場、公園等等都是常見的城市公共空間。對中國來說,這類西方語境中的公共空間其實是相當晚近的產物,在進行現代化城市改造的過程中,公園、廣場等被視為現代化城市的模板而加以效仿。對于傳統時期的中國城市來說,諸如廟宇、集市或者王笛筆下具有成都特色的茶館等都是公共空間的代表,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臘時期起以城市廣場、教堂等為代表的政治性、宗教性的公共空間,傳統中國城市公共空間是建立在市井生活之上的。
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蘇州城,轉向閶門外花步街上的留園,會發現如果按照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來界定,留園其實是一個半私密半開放的公共空間,它并不屬于市民全體,而是盛家的家族產業,留園的經營布置、招商、開放時間等都是由盛家決定的。如果僅從蘇州城市范圍內來看,留園是園林中最具“開放性”和“現代性”的公共空間,但我們也看到一旦發生了商業糾紛,留園不是處理糾紛之后重新招商,而是干脆一刀切,禁止大菜館在留園內營業。1906年,曾在上海張園進行氣球表演的洋商來到蘇州請求在留園中演放氣球,“演放氣球事照本拒絕,嗣因一再商懇,益言向在上海張園演,未鬧事。今特慕名而來,已求閶胥警察孫總辦,派梁委伯怡帶同警察到園彈壓。初意擬在園長放,后見我處不允,只求試放兩次,隨即他往,永不再來。”[41]在上海張園已經習以為常的演放氣球卻在留園中屢被拒絕。
1885年,位于上海的張叔和的張園正式對外開放,很快這里成為上海最大也最受歡迎的大型公共空間,游人們在此賞花看景品茶宴飲,除傳統的中式休閑外,還可以在此照相、觀看氣球載人表演、焰火表演,參與體育競賽,觀看展覽,來此購物。此外,張園還是上海各界集會、演出的重要場所。晚清時期,留園和張園是蘇州與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兩處城市公共空間,雖然都是屬于私人的產業,但1903年張園成立了張叔和花園公司,開始用現代的手段來經營,留園則一直歸屬于傳統的宗族產業,作為義莊的一部分由管家來打理。張園背后則是開埠之后越來越開放與西化的上海城市性格,留園背后的蘇州作為傳統城市的典范,雖然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也嘗試引進現代,但腳步是緩慢的。曾承接社會改良期冀的留園只是在傳統范圍內嘗試做出改變,正如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蘇州城,一邊沉浸于舊時的輝煌,一邊斂手束腳地邁向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