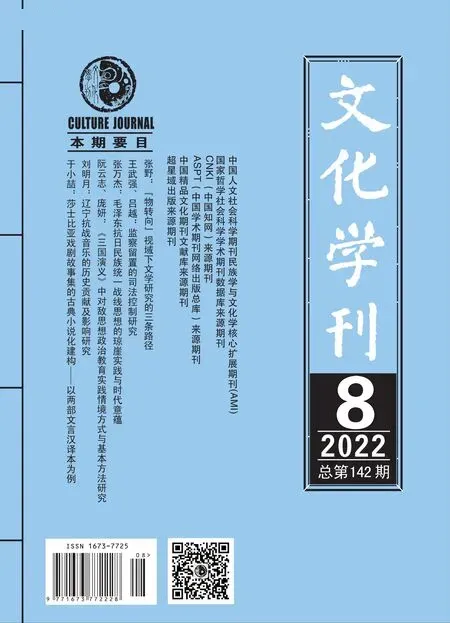十六國時期北涼政權文教政策考辯
丁瑞昌
趙向群先生在《五涼史探》一書中說到:“秦漢以后,漢族文化圈向周邊地區的迅速擴展,使一些原本地處‘戎域’的邊陲地區進入封建化的蘇醒時期,河西走廊便是這樣的地區之一[1]。”所以,河西走廊文化蘇醒的基礎來源于西漢武帝時期開始經營河西走廊并設置河西四郡,絲綢之路的開通使中外文化的交流更加頻繁,進而創造了河西地域文化繁榮的盛況。公元3至5世紀,是河西走廊文化最為繁盛的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是五涼割據政權占據河西走廊的時期,五涼割據政權采取的文化政策是這一時期文化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文教兼設,尊崇儒學
(一)北涼的文教政策
五胡十六國時期,中原地區戰亂紛爭,分裂的政局和持續的動蕩使文化典籍屢遭浩劫或散落遺失,或毀于戰亂,嚴重阻礙了文化的發展、交流和傳播以及學術成果的積累。《隋書》記載:“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余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渠閣文籍,靡有孑遺[2]。”戰亂不僅損毀了典藏古籍,也迫使大批文士尋找和平安穩的地域以躲避戰亂,學校教育荒廢殆盡,太學無弟子可教,州郡縣學更是無以為繼。而與此同時,處于河西走廊的五涼政權,文化事業卻顯得異常繁榮。究其緣由,陳寅恪先生給出了合理的解釋:
蓋張軌領涼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區。……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大亂者,略勝一籌。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猶可以蘇喘息長子孫,而士族學者自得保身傳代以延其家業也[3]30。
五涼割據政權借助于河西當地的著姓大族以及大批遷入河西的文人士子,以及他們擁有的學術文化成果使偏居一隅的河西走廊成為學術文化的繁盛之地。例如,“安車束帛征為博士祭酒”[4]2454的郭荷,其敦煌籍知名弟子郭瑀及其堪稱一代儒宗的得意門生劉昞和弟子索敞、程駿、陰興等人,對河西文教事業的發展壯大有著巨大的貢獻。五涼政權推行文教兼設的政策,不斷推進文教事業向前發展,是有重要原因的,各割據政權的統治者都擁有較深的文化素養。陳寅恪先生這樣闡述,“……沮渠之徒俱非漢族,不好讀書,然仍能欣賞漢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區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學術亦不因此淪替,宗敞之見賞于姚興……[3]30。”
漢族統治者張軌、李暠都是著姓世族,有著很深的家學淵源和很高的學術造詣。而少數民族統治者呂光、禿發氏、沮渠氏,因長期生活在漢族的文化圈,漢化程度較深,對于中原文化有著傾慕之情。特別是北涼沮渠蒙遜表現得尤為突出,身為少數民族酋豪,他卻能“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權變”[4]3189,既是一位文武雙全、運籌帷幄的統治者,也是一位對漢文化頗有研究的學者。沮渠蒙遜對于漢文化熟知,再加之前涼張氏政權推行的文教政策和漢族文士對其進一步的影響以及為鞏固北涼政權的穩定興盛,使其接受并進一步推行文教兼設的政策,推廣中原漢族文化,加強集權統治。
沮渠蒙遜掌控北涼政權后,對文化教育的推行始終沒有放松過,完全按照前涼張氏政權設置的官學推行教育。自此之后,北涼、南涼、西涼等割據政權,都在積極推行文化教育政策,籠絡廣大儒士之心,以壯大統治力量,鞏固統治基礎。對于北涼統治者沮渠蒙遜而言,對文教政策的推行更是格外看重。《十六國春秋輯補》載:“起游林堂于內苑,圖列古圣賢之像。九月,堂成,遂群臣,談論經傳[5]658。”《魏書》載:“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筑陸沉觀于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6]1275。”沮渠牧犍繼王位以后,封劉昞為自己的老師,親自致拜,命其所有屬官求學于劉延明。另沮渠蒙遜對待漢族士人也是不計前嫌,虛懷納之。平南涼、西涼后蒙遜全盤接納南涼、西涼文臣,特別是漢族文士,皆委以重用。可見從前涼開始至北涼統一河西走廊,統治者對文化教育政策的推行落實,使得河西走廊的學校教育制度、儒學興盛發展、學術文化的傳承,起到了極大的保護和推動作用,也培養了大批文士,使得“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軌以來,號有華風[6]1264。”割據政權的興旺迭變和相互間的戰亂雖讓文教政策時有間斷,但是重教之風已根植于河西走廊,學術傳承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二)尊崇儒學
河西走廊儒學發展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西漢武帝時期。陳寅恪先生曾論及:“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統之中,其由江左發展變遷輸入者之外,尚別有漢、魏、西晉之河西遺傳[3]47。”曹道衡先生在《五涼文化述論·序言》中這樣說到:“河西地區自從漢武帝建立四郡以來,許多漢族人民就不斷地移居到這里。……早在漢代,河西地區就出現了不少名傳史冊的人物。例如東漢名臣張奐及其子……張芝乃敦煌淵泉人[7]2……”趙以武先生在其著述論及這一時期河西文化事業發展時說:“在文化方面,河西置郡之前,面貌很是落后。由于軍事征伐和經濟開發的促進,河西開始接受中原文化,吸收西域、中亞文化,發展本地區的文化事業,獲得了相應的進步[7]5。”《后漢書》中記載敦煌侯瑾“覃思著述”,[9]《隋書》中也著錄有侯瑾《漢皇德紀三十卷》《侯瑾集》二卷,足見此時河西文士的文化素養及儒學底蘊已有非常深厚的積淀。魏晉以來,河西儒學繼續發展,史書記載有“敦煌五龍”之譽的索靖、泛衷、張、索、索永,以及索靖完成的《索子》《晉詩》各十二卷的著作。當時河西走廊繼承兩漢以來的儒學傳統,其文化教育、儒學推崇都已據相當的規模和一定的實力。
五胡十六國時期,河西走廊出現的五涼割據政權控制了這一區域,但是五涼政權的統治者不管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都具有推崇儒學和學術文化的共同特點。再加上這一時期河西走廊總的形勢相對于中原地區而言總體趨向穩定,成為中原避難的文士的首選地之一,也是流民遷移之地,雖然仍有割據兼并戰爭發生,但相對于中原大地而言,仍是較為穩定的區域之一。這樣的形勢下,不少中原儒學文士西遷,這使得河西地區在原有儒學傳統的基礎上,加之當地的著姓大族、遷徙而來的漢族文士,推進了河西儒學的發展和繁榮興盛的局面。在五涼割據政權中除前涼張氏和西涼李氏為代表的漢族政權外,在其余三個少數民族割據政權中,北涼沮渠蒙遜對儒學的推崇和重視尤為突出。作為一位漢文化修養較高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他具有通經博史、知曉天文的文化水平,《十六國春秋》中記載其與碩儒劉延明探討仲尼與圣人的一段對話:
蒙遜關于“圣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的說法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和屈原《漁父》中有載。可見沮渠蒙遜涉獵儒學典籍之廣并能靈活應用。其在游林堂懸掛圣人畫像、談及圣人仲尼,也顯示出蒙遜對儒學的信奉和推崇。
河西儒學的發展和興盛,離不開河隴地區世家大族和移徙河西的知名文士。北涼統一河西走廊的過程中,沮渠蒙遜接納了南涼、西涼等割據政權的大批文士,例如南涼被稱之為“中州之才令”[4]3143的張昶、郭韶,“秦隴之冠冕”[4]3149的辛晁、彭敏,“文齊楊班”[4]3149的張穆、邊憲,以及西涼劉昞、宋繇、梁中庸等。其中以碩儒劉昞為代表的“郭劉學派”[8]13-24以儒學著稱。劉昞師承東漢著名經學家郭整的六世孫郭荷。郭氏家族“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4]2454。眾弟子中,郭瑀最為出眾,“荷盡傳其業”[4]3149。而郭瑀又傳業于劉昞,劉昞因通儒博學被西涼李暠征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西涼滅亡,沮渠蒙遜封劉延明為秘書郎,專門負責書籍的注記。蒙遜卒,其子沮渠牧犍尤重儒生文士,《魏書》載:“牧犍尊(昞)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6]1275。以致劉昞助教,知名弟子索敞、程駿等皆以儒學著稱,成為河西儒學的代表人物,這對傳承和發展傳統儒學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使河西儒學達到了鼎盛。河西儒生在相對安定的環境和五涼割據政權統治者的倡導弘揚下,以面授、家族世傳、著書立說等多種方式傳承儒家文化,對中國儒學的傳承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成為儒學發展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也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興辦官學,私學興盛
(一)官學興盛
河西官學的興盛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出現在五涼政權割據河西之時,其中除了后涼外,前涼、南涼、西涼、北涼政權都曾積極興辦學校,大力培養人才,不斷提高官吏的文化素養,達到鞏固政權,維護統治的目的。以致在河西走廊出現了重視教育、獎掖文士、愛惜人才的社會風尚。前涼張軌初到涼州便開始設立學校,培養人才,同時邀請著名的學者和名儒大家講經論義,并聘為祭酒等官職,以此來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前涼官學的推廣興盛為后世其他割據政權提倡、推崇教育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后世史家學者,稱譽十六國時代的涼州“號為多士”[10]2011。西涼政權,對官學尤為重視。李暠在敦煌立國不久,便開始修建學校,推崇教育事業,為西涼統一河西走廊采取養士的策略,并組織文士積極開展靖恭堂圖贊、勒銘酒泉、曲水詩宴等文學活動。當其遷都酒泉后依然興辦官學,并加強對學生的考核,對學生考試內容及考核情況更是要親自過目審核。《吐魯番出土文書》中記述,在吐魯番哈拉和卓九十一號墓出土的西涼建初四年(408)關于秀才對策文的呈文,內容均采用臣下仰答君王詢問的口吻。現將部分出土文書移文如下(移文均按照原書中排列條目注明條目數,依次進行部分摘錄。):
(25)侯曰《風》,天子曰《雅》,以后妃之美,貫乎《風》首,王者
(41)涼州秀才糞土臣馬騭○稽首言:臣以疏陋,才非
(49)臣陟言:臣聞上古之時,人性純璞(樸),未生爭心。天
(61)臣騭言:夫日行經廿八宿,冬處虛、危,故稱北陸,夏[11]
如果說五涼政權中的兩個漢族政權對官學、教育的重視有著家族的淵源,而南涼禿發氏和北涼沮渠氏建立的少數名族政權,則在這一氛圍和環境的影響下,對官學教育的重視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北涼沮渠蒙遜先后吞并南涼、西涼,坐擁南涼“秦隴之冠冕”“武威之宿望”[4]3149等賢俊英杰、西涼一代儒宗劉昞、宋繇等大批懷珠抱玉之士。在周邊割據政權興學崇儒的基礎上和大力倡導的影響下,北涼崇學之風尤為重視,使得河西教育事業得以進一步發展。
沮渠蒙遜、牧犍父子在新建學校的同時,擢任賢才,發揮文士之專長,命其擔任侍講之職,傳道授業。《魏書》載:
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筑陸沉觀于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6]1275。
同時,委任宗欽、程駿等有學之士擔任東宮侍講,講經傳儒,主持文教事宜。《魏書》載: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仕沮渠蒙遜,為中書侍郎、世子洗馬[6]1268。
(二)私學興盛
私學發展至五涼時期,并未因割據戰亂和討伐戰爭而荒廢,反而因割據政權統治者采取的“文教兼設”政策和對傳統文化學術的重視,不斷發展壯大,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詳盡論述:“河隴一隅所以經歷……長期的亂世而能保存漢代中原之學術文化者,……公立學校之淪廢,學術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學博士之傳授變為家人父子之世業,所謂南北朝之家學者是也。又學術之傳授既移于家族[3]23……”胡三省在《資治通鑒》的注語說:“永嘉之亂,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10]2011。”所以涼州一隅在這一時期成為北方學術文化的中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世之學傳承不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晉書》中記載這一時期出現的“郭劉學派”是家學傳承的典型代表。丁宏武先生曾闡述到:“客觀地講,十六國時期河隴地區的郭劉學派,名家輩出,成果豐碩,為漢魏以來河隴文化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和歷史存在[8]13-24”。這一群體成員師徒相承,綿延近兩個世紀,“其主要傳承譜系為:郭荷—郭瑀—劉昞—索敞、程駿。從該學派形成發展的歷史看,郭荷、郭瑀兩代(前涼、前秦)均以隱居授徒為人生志趣,是聲名漸著的形成期;劉昞掌門執教的時期(后涼、西涼、北涼),該學派完成了由隱而仕、由民間向官方授學的轉變,劉昞著述等身,弟子眾多,影響甚大,堪稱一代儒宗,奠定了該學派的學術史地位,是眾望所歸的鼎盛期[8]13-24。”當北魏平定涼州次年,440年劉昞離世,其弟子被迫遷徙居住平城,雖然仍舊授徒執教,但在多元文化的沖擊和寄人籬下的境遇中,該學派也逐漸走向衰微。但郭劉學派的學術傳承對河隴文化的發展傳承和儒家學說的繼承延續做出的重要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魏書》載:“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馀人,通經業者八十余人[6]1247。”時至400年,敦煌李暠割據建立西涼,征劉昞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其學術發展有了新的機遇。《魏書》記載:“李暠私署,征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并行于世[6]1275。”雖然此時劉昞已由隱向仕,但對于郭氏家學的傳承亦未停滯,授學方式的轉變、治學范圍的擴大,促使郭劉學派走向鼎盛。420年,北涼沮渠蒙遜破酒泉,滅西涼。劉昞及其弟子仍然是北涼政權的座上賓,受到蒙遜父子的敬重,授業之職從未停歇。北涼政權積極的文教政策和寬松的環境,促使劉昞及其弟子授業延續傳承,治學范圍遠遠超越了郭氏家學初期以經學為主的藩籬,不斷推動郭劉學派的發展。雖然東遷之后,劉昞弟子仍然講經授徒,但亡國之虜的境遇,很難讓該學派再顯昔日的輝煌,但是郭劉學派此前奠定的學術地位和劉昞“河西碩儒”[6]1275的聲望已難以撼動。私學的興盛和傳承,儒學的發揚光大,在北涼時期走向鼎盛,文化實力強盛,奠定了郭劉學派在河隴學術文化發展史上的堅實地位,使其成為對河隴文化的發展傳承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文士群體。
三、結語
河西走廊文化教育傳承發展與文化興盛,與五涼割據政權占據河西走廊時期所權采取的文化政策是緊密相關的。特別是漢化程度較深和欽慕華風、傾身儒雅的北涼少數民族統治者沮渠氏對文教政策的推行更是格外看重,從而使北涼文化的整體實力達到五涼時期的高峰,使河西地區的文教事業不斷走向興盛,河隴地區也因此成為當時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