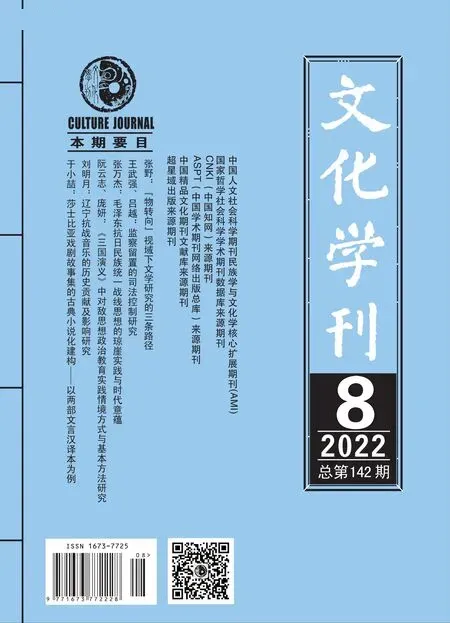山東金代碑刻整理指瑕舉例
劉賽飛
自宋代起,便有學者開始了對金石文獻的整理,如趙明誠的《金石錄》、歐陽修的《集古錄》、洪適的《隸釋》及《隸續》等。到清代時,在乾嘉考據學的興盛背景之下,學者們掀起了對金石學研究的熱潮,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以著錄為主的金石學專著。例如,王昶的《金石萃編》、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張金吾的《金文最》、羅振玉的《山左冢墓遺文》、段松苓的《益都金石記》、孫葆田的《山東通志》、吳式芬的《金石匯目分編》,等等。尤其是各省編修的地方志,不僅在《藝文志》中收錄當地碑刻,有的還設《金石》《碑碣》《墓志》等類目專門著錄。清代金石學家還注重實地考察,以原碑、拓本為依據,整理碑文時并附跋語考證,真實性高,且頗具史料價值,為后世查閱研究提供了諸多便利。現代出版的金石學專著亦數量眾多,如王新英的《金代石刻輯校》和《全金石刻文輯校》、閻鳳梧的《全遼金文》、唐圭章的《全金元詞》等。無論地方志,還是古今金石學著作,都對山東金代碑刻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民國以前各類匯集山東金代碑刻的著作中,金石學家所錄碑文多考證嚴謹,訛誤較少,方志錄文則缺乏考證,錯字、漏字較多,近年出版的金石學著作亦多不注重實地考察,常摘取另一書錄文直接整理,同樣缺乏考證,因此,常出現碑刻存地記載及文字辨識錯誤等問題,如《全金石刻文輯校》。依照原碑或拓本校對金石著作錄文可以提升碑文本準確性,同時能正方志訛誤,現以《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所收錄碑刻拓本為例,對七則山東金代碑刻錄文予以校對。
一、所選碑刻簡介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收錄多種山東金碑拓本,但有部分殘損、磨泐,而《滿庭芳詞并跋》《鄭公墓志》《塔河院碑》《天封寺記》《博州廟學記》《蒙山祈雨記碑》《興國寺碑》七種拓本尚為清晰,能夠為我們提供較準確的碑文信息。故以此為例,對碑文進行校正。《滿庭芳詞并跋》,大定二十八年(1188)立石,屬道家碑刻,現存山東濰坊,碑文見于陳垣的《道家金石略》、唐圭章的《全金元詞》、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輯校》中,具體存地玉清宮;《鄭公墓志》,大安二年(1210)立石,現存山東青州,但拓本記載此碑現存山東壽光,故碑具體存地有待實地考察,碑文見于清段松苓的《益都金石記》、清阮元的《山左金石志》、清張金吾的《金文最》、羅振玉的《山左冢墓遺文》及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輯校》中,其中,《山左金石志》未輯碑正文,《全金石刻文輯校》錄文訛闕較多;《塔河院碑》,大定二十一年(1181)立石,現存山東臨沂,碑文見于光緒《費縣志》。拓本記載:“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閏三月二十二日刻。碑在山東費縣。拓本高度為184厘米,寬度為76厘米。正書。碑兩截刻,上刻二十年十月公據,下刻記。此本為陸和九舊藏清光緒年間拓本。”[1]150碑額題“圣旨存留塔河院額”八字;《天封寺記》,大定二十四年(1184)立石,現存山東泰安,碑文見于民國《重修泰安縣志》、張金吾的《金文最》及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輯校》;《博州廟學記》,大定二十一年(1181)立石,現存山東聊城,碑文見于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宣統《聊城縣志》、清王昶的《金石萃編》、張金吾的《金文最》、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輯校》中,其中,《金文最》僅收錄碑陰,宣統《聊城縣志》不錄正文,僅存目;《蒙山祈雨記碑》,承安五年(1200)立石,現存山東臨沂,碑文見于光緒《費縣志》;《興國寺碑》,大定五年(1165)立石,現存山東滕州,碑文見于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輯校》。
二、碑刻錄文校正
(一)《滿庭芳詞并跋》
對于《滿庭芳詞并跋》現存地,各書記載有異。《道家金石略》記載碑現存山東濰縣玉清宮,《全金元詞》第390頁也注明這首詞“有石刻在濰縣玉清宮”[2]390,然而《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記載此碑現存山東濰縣昆崳山[1]190,昆崳山在今山東煙臺境內,因此,確認拓本記載有誤。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輯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記載《滿庭芳詞并跋》“在山東濰坊昆侖山”[3]312,該文據拓本錄文,所以應該和《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一樣描述錯誤。有關《滿庭芳詞并跋》錄文,唐圭章《全金元詞》引文不確,其部分原文如下:
“全性命,紫書來詔,直赴大羅宮。”[2]390
“來詔”二字,在陳垣《道家金石略》和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輯校》中皆作“詔去”,拓本作“詔去”,是。《全金元詞》引文錯誤。
(二)《鄭公墓志》
第一,正文第二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因遭宋季兵火,攜家西來”[3]499,《益都金石記》作“因遭宋季兵火,挈家西來”[4]14864,“攜”字原作“挈”,今據《益都金石記》及拓本改。
第二,正文第六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不幸夫歿守義□有二子三女”[3]499,《金文最》作“不幸夫歿守義。而有二子三女”[5]1273,闕字原作“而”,今據《金文最》及拓本補。
第三,正文第八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尚勤儉訓子”,《益都金石記》作“尚勤家訓子”,“儉”字原作“家”,今據《益都金石記》及拓本改。
第四,正文第十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爾之祖父母,我之姑舅”[3]499,《益都金石記》作“爾之祖父母,我之舅姑”[4]14864,《全金石刻文輯校》“姑舅”二字互倒,今據《益都金石記》及拓本正,《益都金石記》及拓本作“舅姑”,是。
第五,正文第十二行,按:“我祖我父率□□土未能□卜敬從母命”[5]1273。《全金石刻文輯校》作“我祖我父□□□□未□□。敬從母命”[3]499-500,《金文最》作“我祖我父率□□土未能□卜敬從母命”[5]1273,補“率”“土”“卜”三字,拓本磨泐難辨,對照其他行字數,“父”到“未”缺四字,“未”到“敬”缺三字,參照《金文最》改。
第六,正文第十三行,按:“擇其良師卜其□□□安厝之”[5]1273。《全金石刻文輯校》作“擇其良師卜□□□□□安厝之”[3]500,缺五字,《益都金石記》作“擇其良師卜□□□□安厝之”[4]14864,缺四字,《金文最》作“擇其良師卜其□□□安厝之”[5]1273,補兩字,拓本磨泐難辨,辨“擇”到“安”間缺八字,故參照《金文最》改。
第七,正文第十三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歲次庚午立□四月十有三日”[3]500,“有”字原脫,今據拓本補。
第八,正文第十四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命工刻石于靈側”[3]500,《金文最》在“石”字之后多一“□”,辨拓本疑“石”與“于”間缺兩字,亦不缺,此處難以確定。
(三)《塔河院碑》
第一,上層碑文第四行,光緒《費縣志》作“大含乎元氣下缺河院建立已來”[6]369,“院”下拓本有“者”字,當據補。
第二,上層碑文第五行,光緒《費縣志》作“天德一年”,誤,若第一年,當寫作“元年”。“天德一年”當依拓本作“天德二年(1150)”。
第三,上層碑文第六行,光緒《費縣志》作“大垂戒沙門善明上足法門嗣下缺住持以迄與今此者特奉”[6]369,“門”字拓本無,當系衍文;“嗣”下拓本疑有“行”字,當據補;“奉”字當依拓本作“遇”。
第四,上層碑文第八行,光緒《費縣志》作“圣朝崇奉真風,闡揚要道”[6]369,“揚”下拓本有“佛”字,當據補;“道”字當依拓本作“遂”。
第五,上層碑文第十一行,光緒《費縣志》作“遂使雙林之道愈光下缺廣智道”[6]369,“光”下拓本有“之流浸”三字,當據補。
第六,上層碑文第十二行,光緒《費縣志》作“時下缺一年太歲辛丑閏三月丁丑朔二十二日戊戍”[6]369,“時”下拓本疑有“大定二十”四字,當據補。且結合原碑文“大定二十年(1180)十月日給”[6]369,則大定二十一年(1181)立石應合理。
(四)《天封寺記》
第一,《全金石刻文輯校》作“承直郎、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云騎尉、賜緋魚袋黨懷英撰并書”[3]274,“書”下拓本有“篆”字,當據補。
第二,正文第九行,“落成□明年”,按:闕字當作“于”字。闕處拓本完全磨泐不能辨,《全金石刻文輯校》不錄此字,《金文最》作“于”,結合上下文,“于”字合理。
(五)《博州廟學記》
第一,關于《博州廟學記》碑刻尺寸,《山左金石志》與《金石萃編》記載差異較大,《山左金石志》云“碑高七尺七寸,廣三尺二寸”[7]14682,《金石萃編》云“碑高八尺五分,廣四尺二寸”[8]2879,因未查看原碑,故此處存疑。
第二,碑陽第二行,拓本作“乃修六經以詒后人”[1]152,《全金石刻文輯校》“詒”原作“詔”,今據拓本改。
第三,碑陽第四行,拓本作“莫不敦尚經術、開設學校為先務”[1]152,《全金石刻文輯校》“不”下原有“以”字,今據拓本及《金石萃編》刪。
第四,碑陽第十六行,“從祀畫像之廣”中“廣”字,拓本模糊,疑有四點,應為“廣”,《全金石刻文輯校》原作“院”,今據拓本改。
第五,碑陽第十九行,拓本作“歲貢士與內州等”[1]152,《全金石刻文輯校》“歲”字原脫,今據拓本補。
(六)《蒙山祈雨記碑》
第一,碑額題“蒙山祈雨記”五字,下方“白云嵓洞主白云居士皇希永撰并書篆額”[1]54十七字在光緒《費縣志》中原未收錄,今據拓本補。
第二,正文第一行,光緒《費縣志》作“巍然敦犬”,“犬”字拓本作“大”,是。
第三,正文第二行,按:闕處當作“相”字。光緒《費縣志》原作“東浮云氣(接于蓬萊”[6]372,拓本所示闕字疑為左右結構,左木右目,類“相”,將“相”字填入句中,“相接”亦合文意。
第四,正文第二、三行,按:闕處當作“南”字。光緒《費縣志》原作“東浮云氣(接于蓬萊,西根連于三宮空洞之天(隸衡岳為佐命,北重艮坎為蒙卦”[6]372,據拓本“天”字之后疑為“南”或“西”字,結合該段文字,東西南北恰缺一南,故此闕字應為“南”。
第五,正文第八行,光緒《費縣志》“千”字原作“干”,今據拓本改。但不排除此處為印刷錯誤。
第六,正文第十三行,光緒《費縣志》“燈”字原作“燭”,今據拓本改。
第七,正文第十三行,光緒《費縣志》“之上”二字原脫,今據拓本補。
第八,正文第十四行,“旱乾”二字光緒《費縣志》作“乾旱”,當據拓本。
第九,正文第十四行,光緒《費縣志》“村”字原脫,今據拓本補。
第十,正文第十四、十五行,光緒《費縣志》“眾村”二字原脫,今據拓本補。
第十一,正文第十六行,光緒《費縣志》“龜”字原作“蒙”,今據拓本改。
第十二,正文第十九行,光緒《費縣志》作“刊二銘”,“諸”字原脫,今據拓本補。
此外,光緒《費縣志》載此碑文“后有題名二行”,但未錄題名內容,茲據拓本補題名如下:
“□□村糾首楊政,妻張氏,張氏,張氏,男楊珪,新婦張氏,男鄉貢進士楊□□,新婦栢氏,男楊,新婦玉氏。維首楊震,妻趙氏,鄉貢進士楊□□,妻管氏,妻李氏,進義副尉靳□□□□□李策。蒙陽魏緒,杜真,杜成,刊。”[1]54
(七)《興國寺碑》
第一,正文第二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示生賢□之師”,拓本闕處作“智”,是。
第二,正文第三行,《全金石刻文輯校》原作“□未達真理”,按:闕處當作“縱”字。拓本闕處疑“縱”,“縱”有“縱然、縱使”之意,合句意。
第三,正文第六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在今滕邑之古二十五里”[3]125,“古”字當依拓本作“有”。
第四,正文第七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或碑志存□□□□休相□數里”[3]125,“相”下拓本有“望”字,當據補。
第五,正文第八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村之正中□□寺廟”[3]125,拓本作“村之正中□置寺廟”[1]83,今據拓本補。
第六,正文第九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因存留為大圣□”[3]125,闕處當依拓本作“院”。
第七,正文第十三行,“郡”字《全金石刻文輯校》原作“鄉”,今據拓本改。
第八,正文第十五行,“共”字《全金石刻文輯校》原作“為”,今據拓本改。
第九,正文第十五行,“修進”二字《全金石刻文輯校》作“進修”,當據拓本。
第十,正文第十七行,《全金石刻文輯校》作“□而遭遇恩詔”,拓本闕處作“既”,是。
三、結語
以上對七則山東金代碑文的校補皆以拓片為依據,基本上對有關著作錄文訛誤之處都能準確更正。此外,《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尚有許多山東金代碑刻拓本,藉此可對勘更多相關碑文。總的來說,前人已在山東金代碑刻整理及考證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這就為我們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之上繼續深入對山東金代碑刻的篇目整理和文字釋讀工作提供了方便。同時,通過對更多山東金代碑刻的整理研究,也可以繼續展開對《金史》、山東省地方志等史志及相關古籍的校補工作,深入發掘山東金代碑刻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