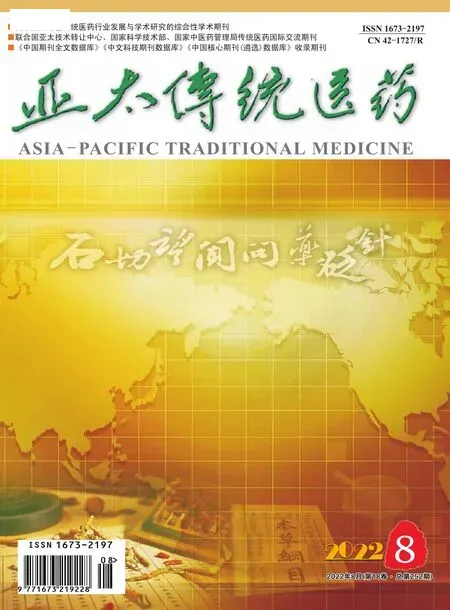基于心身醫學角度探討藏醫學取巧診斷法
卓瑪加,仁青加
(西藏藏醫藥大學,西藏 拉薩 850000)
在生物醫學領域內,醫學臨床決斷與倫理學決斷相伴相隨[1]。藏醫學取巧診斷法作為一項臨床問診技巧,其亦限定于倫理價值預設的框架內,并在心身醫學理論框架下使患者深切感受到問診過程中的人文關懷。
1 心身醫學與藏醫學取巧診斷法的關聯
“心身醫學”一詞由德國精神科醫師亨羅斯于1918年正式提出。心身醫學又被稱為心理生理醫學,是醫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學科,是研究在人類疾病的產生、診斷、發展和治療過程中,軀體與心理、社會因素之間互動關系的一門醫學[2],其理論基礎為“心身相關原理”。中醫學自先秦至今始終貫穿著心身醫學的思維方法,早在《黃帝內經》時期就注意到人的心理與生理病理密切相關。例如,《黃帝內經》理論中的“形神一體思維”強調了形與神的辯證關系、“內傷七情”對疾病的影響等,形成了內容豐富而獨特的心身醫學體系。而在藏醫學理論中雖未形成較為完整的心身醫學體系,但對于心身因素方面也有一定的思考和獨特的見解,與中醫心身醫學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藏醫學巨著《四部醫典》言:“在十方諸佛中,藥師佛特以拔除眾生一切身心疾病苦痛為本愿[3]”,此處的“本愿”正是以發心、心理預示為導向,然后趨向由“本愿”而產生現實行為活動。因此,藏醫學理論認為心理因素對事物的發展、轉變起著重大影響,如結合臨床診療,心身因素便會對疾病的診斷、發展、轉歸、愈后起到雙重性作用。《四部醫典·論述續》之診斷學專論、醫學倫理專論和《四部醫典·秘訣續》之神志病專論等章節也均有心身醫學因素體現。在《四部醫典·論述續》第二十五章診斷法中就涉及取巧診斷法,究其原文且對照各類診斷技巧不難發現,作為基礎學科與臨床學科之間的橋梁型課程,藏醫診斷學不僅包含了生理病理等醫學基礎學科,還囊括一定的心理學理論基礎。這一基礎學科在強調自身理論合理性的同時,還善于抓住廣大患者的共同心理,做到病理與心理診療有機結合,從而烘托出取巧診斷法其適用性。取巧診斷法中對于心理學法則的有關論述,雖未以現代心理學概念的方式表述、羅列,但對于強調宏觀整體性和“天人合一”等觀念的中、藏醫學來講,其診療過程、用藥規則、預期療效等方面必定以符合客觀規律作為其前提。因此,心理因素作用于診斷行為所產生的多種效應可在具體診斷過程,以及醫患間的交流和心理暗示中得以體現。在《四部醫典》原文中亦可體現出藏醫診斷法對心身醫學因素并非從未涉及,相反還有一定的考量,且在理論高度和臨床經驗方面均頗有建樹。綜上,診斷者充分掌握并利用患者在就診過程中產生的心理活動而達到診療目的,這是藏醫取巧診斷法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
2 藏醫學取巧診斷法

3 心身醫學在藏醫取巧診斷法中的應用
不同的患者群體,因其年齡不同,而在心理、生理及致病因素等多方面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性。因此,取巧診斷法以八種法則在臨床問診中分而治之。此八法分別是開宗明義法、旁推側引法、延時診療法、詢問追蹤法、因勢利導法、緘口不言法、胸有成竹法、文過飾非法,展開論述如下。
3.1 開宗明義法
此法要求醫生的理論水平達到很高水準,需全面掌握各主要疾病的特點、熟悉各病癥,還必須具備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方可有效結合臨床進行診療。由此,取巧法則之首便是對于醫者自身素質的高標準要求,并未特別闡述與診斷法則相關的論題。對此,《四部醫典大詳解:2》[4]言:“對于醫者自身素質的高標要求這一論題,本不該納入取巧診斷法這一論題之中,之所以成為眾法則之首,是寄予通過開宗明義的方法,使任何從事臨床的人從伊始就能高標準要求自己,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和運用好其余的診斷法則而造福患者。”
3.2 旁推側引法
此法主張醫生在未接觸患者前,以隱秘的方式去掌握患者的某些情況,從而獲取一些必要信息,這一點似乎與弗洛伊德的預防心理機制有關論述不謀而合。弗洛伊德在其《自我與本我》[5]中認為,心理預防機制又稱自我預防機制,是“自我”用來應付“本我”和“超我”壓力的手段,“本我”由各種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構成,“超我”則指人格結構中的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部分。因為患者的心理環境既微妙又敏感,當在公眾場合詢問其難言之隱時自然會本能地產生心理防御機制,而如果挑戰了患者“超我”精神的底線,患者就會刻意回避答詢,對問診產生抵觸情緒。《黃帝內經·靈樞》[6]中也強調醫者在診療過程中應重視社會環境對患者的影響,注意“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和于人事”,因此,此時從側面了解病情就顯得尤為必要。
3.3 延時診療法
臨床上因情緒因素導致病情加重的例子不在少數,醫生在問診時須特別注意患者在情緒上的微妙變化,例如面部表情、肢體語言等。而此法正是基于該點,極力主張醫生在問診時應耐心傾聽患者所述,更不能透露出焦躁或不耐煩的情緒。因患者的心理變化極為微妙,所以需適當延長診斷時間,以更加細致入微和謹慎的態度觀察患者的各種反應以求明診。《黃帝內經·素問》[7]言:“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即通過問診詢問病情的前因后果,從而準確了解患者的心理和精神狀態。而當醫生忽視了患者的心理狀況,且對病情無法給出準確定論時,心理預防機制之“本我”因素作用于患者,患者就會本能地產生各種猜想而產生焦慮,這對診療極為不利。
3.4 詢問追蹤法
作為問診對象的患者,是具有不同社會角色、地位和心理性格特征、文化素養及興趣愛好[8]的獨立個體,因而在問診過程中可能會產生情緒緊張、不愿配合診斷等不可抗力因素的情況。此時則會出現患者對病情描述不當及漏述、誤述的現象,導致主訴可信度不高而難以對病情進行判斷。此法針對這一現象,主張需通過詢問患者對當前疾病采取過的既往診療措施并加以判斷分析,從而初步明確疾病寒熱之屬性。詢問追蹤法的要點并不在于問診內容的多少,而在于建立在整體聯系基礎上的問診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問診技巧的優劣性。
3.5 因勢利導法
在日常診療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故意刁難醫生的患者,其通過抵制問診來驗證醫生專業水平,加之部分患者又不同程度受到鬼神觀念的影響,因勢利導法則巧妙地抓住這一心理因素,對部分受神明鬼怪觀念支配且故意刁難醫生的患者加以心理干預,使患者產生此病為鬼邪所致的假象而產生恐懼,以此促使其和盤托出病情,以利于診斷。由此可見,該診療法具有極大的巧妙性。
3.6 緘口不言法
對患者心理的把控是極其微妙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包含著醫生對患者的共情心理,即親身感受作為對患者內心的一種體驗,可由此感知患者焦慮的心理。通常情況下,絕大部分患者會不經醫生詢問而急于訴說病情,而此時醫生則要給患者一種心不在焉的假象,實則仔細傾聽。當得出初步診斷后故作深沉,告知患者無需多言,此時就會給患者一種對此疾病已了如指掌的感覺,使患者信心大增,從而達到心理層面的治療效果。這既可以使患者更好地遵循醫囑以便達到預期療效,也能使醫者在治療時心無顧及而施展醫技受利于患者。
3.7 胸有成竹法
此法實為醫生揚名之策。對確有把握醫治的疾病可在患者面前表現得胸有成竹,當診斷明確后即詳細告知患者此病之性質、治療之方法、愈后之療效等。這是有意于患者處樹立威信,使患者能感受到強烈的希望和關懷,對減輕患者心理壓力,增強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從而治愈疾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8 文過飾非法
此法實為醫生無法明確診斷結果時采取的自我補救措施。醫者用巧妙的方法掩蓋自身的不足,以含糊不清和模棱兩可的言詞回應問詢,同時又借鬼神觀念之勢對患者心理加以干擾,暗示此病是因鬼魔作祟或飲食起居不適等因素所致。若開處方,則斟酌使用對寒熱無害的衡性藥物,并對疾病和藥物冠以高大、罕見之名,給患者留下醫術高深莫測的印象。該法縱使無法準確判斷病因、癥狀及治法,但也不至于因此損害患者健康,反而給予衡性之藥物,使患者從心理上覺得醫治得當,從而起到正面心理治療作用,而醫者也得以保全自己的聲譽不受損失。
4 身心因素下取巧診斷法的臨床研究進展
基于心身因素的診斷語言普遍存在于臨床問診的全過程,這既是語言的藝術,又是獲取患者真實情況的良性法則,值得重視與深入研究。臨床上除基于道德的基本準則外,對于問診語言并無特定的規范,通常為醫患之間自然交流,以從中獲悉病患信息。在日常問診中,取巧診斷法更多是以醫生長期診療經驗作為主要依據,由于醫患數量比例兩極分化等現實問題,幾乎無法做到遵循每一位患者的心理活動軌跡去設定對應的治療計劃。基于身心醫學的取巧診斷法目前在臨床上尚未形成規范的實施體系,也并未成為研究熱點。盡管缺乏體系化,但在實際問診過程中,從不缺乏醫患間對身心醫學因素的考慮和經驗應用,其普遍存在于醫患交流過程的方方面面,醫生的診療思維中無不處處透露著對于身心醫學因素的重視和考量。這些身心醫學因素以隱形、被動的形式影響著醫生問診時的語言運用技巧,雖為隱性、被動,卻又真實存在于具體診斷語言中,且能起到指導心理診斷的作用。因此,對基于身心醫學因素的藏醫取巧診斷法的研究和應用,可在調節醫患矛盾和促進醫患關系健康發展,以及響應患者自身訴求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此外,在臨床領域對此論題研究還需做到與時俱進,多措并舉,大力宣傳普及身心醫學相關理論及其應用于臨床診斷的重要性,以此提高“身心因素對于問診細則的重要性”之論題的熱度和影響力,同時還需在具體細則方面精確劃分,規范有序,做到因人而異、因“病”制則,將對患者心理的掌控度納入健康評估的范圍內。
5 結語
綜上所述,取巧診斷法是準確獲取患者原始信息的特殊問診手段,在其診斷過程中運用了許多基于身心因素的巧妙法則。心身醫學概念體系確立于20世紀初,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其具備的醫學哲學思維特點在藏醫學理論中亦有一定程度的體現。傳統醫療體系積累千年的特色診斷法則和治病經驗[9]展現出語言學與心理活動變化的密切關系,是解決當前存在的醫療問題(醫患關系)的不二法門,值得繼承、提煉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