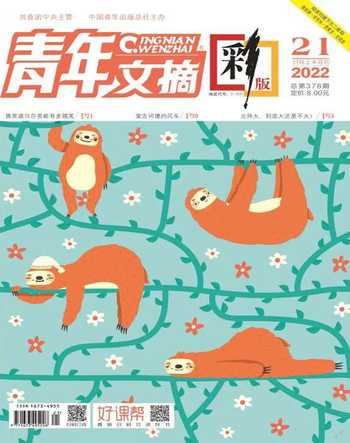Cityboy是怎么爛大街的
渣渣郡

最近的大街上,你會發現,中國街頭潮人的衣服尺碼在悄然之間數次膨脹。袖子縫合線下垂叫落肩,穿爸爸的衣服叫Oversize,這種過去被泛稱為嘻哈樣式的穿搭,現在叫Cityboy。
衣服往大了選是City boy的魂兒,夏天也得往短袖外頭套件背心是Cityboy的神,一雙腳上的白襪是Cityboy的根兒。在這一套明確公式的指導下,年輕人撿起了過去那些嘴里不夠炸的衣服,套在身上,并稱之為新時尚。
Cityboy風格除了給予人們一套穿搭之外,還搶占了P圖的陣地。端上一杯冰美式咖啡,低頭頷首大步走,做出一副看上去有大事要忙的造型,再拉個朋友一頓連拍,修圖時,只需降低照片的飽和度和亮度,再增加點顆粒感,這就出片了——“朋友圈見”。
Cityboy編織了一場單薄、刻板的審美體系,呈現出一種比工廠流水線更加公式化的樣貌。它加工著那些想要成為弄潮兒的普通人,經過掐頭去尾,把他們變成千篇一律的復制人,穿著同樣的衣服,拍著同樣的照片。
當然,有人中意Cityboy,就有人厭倦,這種厭倦并不僅僅出于無聊的時尚鄙視鏈,更有有理有據的頭頸肩關系學。
一方面,他們鄙夷這種極致Oversize的風格,把它稱之為身材破壞者——強行四六開的上下衣搭配比例,讓身高1.8米的人在這套行頭的裝扮下看上去只有1.6米。
另一方面,看上去很美的Cityboy攝影,大多數都運用了攝影巧思,拿臺階、滑板和垛口,刻意修飾了這套穿搭帶來的身材比例問題,讓氛圍感沖昏頭腦,給人帶來一種“我穿我也帥”的錯覺。
Cityboy是種理念,但很多人學的只是皮毛:姿勢限定、氛圍限定甚至帥哥限定,不考慮適合不適合自己,就直接往身上套,這種模仿非常滑稽。
Cityboy的原始概念,并不像社交平臺反映的那么刻板,中文語境下的Cityboy來自日本。
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城市化高速發展期,亞文化雜志《寶島》首先將自己稱為“C i t y b o y手冊”。隨后另一本日本雜志《POPEYE》憑借出色的制作能力接過了這一身份。
關于什么是C i t y b o y這件事,我們或許可以從《P O P E Y E》前總編木下孝浩的采訪中得到稍許啟示:“C i t y b o y的定義沒有一條清晰的界線,它該是你心目中所追求的一個理想自己的樣貌,這與穿著和住在哪無關,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所愛。”
在Cityboy概念初興的20世紀70年代,日本人覺得他們正處在漂泊狀態,只有愛上一種事物或者一項運動,才能讓人們更好地活下去。基于這個背景,滑板、沖浪、街舞愛好者寬松灑脫的穿搭最終塑造出多元自由的時尚,成為眾人追逐的目標。
當我們按照攻略復刻穿搭時,或許還該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只有一個正確答案,那么一切就都顯得了無生氣。
溫好//摘自那個NG微信公眾號,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