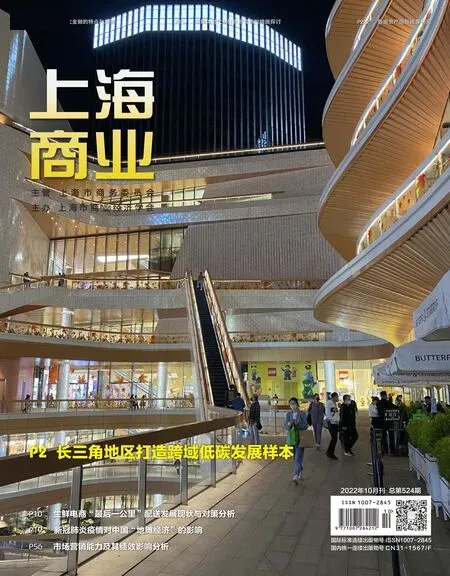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地攤經濟”的影響
劉芙蓉 冷雨恒 宿宸辰
一、引言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至今,病毒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始終揮之不去。無論是正規還是非正規領域,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被阻隔的時候,“售賣”這一環節必然受到重擊。線上交易涌起一個小浪潮——因為曾經你在上班路上、放學回家,相隔半米就可以進行的售賣被拉長為了幾千里的陣線。在小攤銷聲匿跡的那些日子里,人們重新認識了攤販,這個群體到底給社會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中國的地攤經濟來自高速的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在就業崗位沒有配套增幅的情況下,極其容易出現就業下跌、經濟低迷的情況。而通過擺攤這樣臨時性“上崗”的方式,他們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謀生手段,得以在快速發展的城市繼續生活,對快速城市化的進行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疫情之初,面對消失的攤販,百姓們的生活成本不可避免地上升,在疫情帶來的就業緊張和崗位再次配置的背景下,進一步加重了民眾的焦慮和恐慌。而因此失去經濟來源的攤販,也不知該何去何從。武漢封城76天,無法外出的攤販面臨著贍養老人、照顧子女和醫療防護等經濟開支,而收入卻長期為零。種種難題之下,政府應采取更加精細化的措施,才能探索出最合適的“后疫情時代”下,地攤經濟與病毒防控、百姓與疫情的共生之道。創造出適合地攤經濟發展的新路徑。此乃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的必由之路。
二、防疫常態化后地攤經濟復蘇與變化
地攤經濟的發展方式總是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的變遷而發生變革。2020年,“地攤經濟”被重提,給經濟帶來了新活力,也給待業的居民一份短暫的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地攤經濟發展出現了數字化、規范化等新常態。
首先,在中央的鼓勵之下,各地市紛紛推出政策,拉動居民消費激發內生動力。濟南、南寧、鄭州、南京、成都、合肥、廈門、長沙、石家莊等地紛紛明確鼓勵發展地攤經濟,其中多地已劃分外擺區域;大連市成立開展商業外展外擺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并下發了一則《關于確定我市第一批商業外展外擺地段并加強管理的通知》;四川成都推出“五允許一堅持”措施,在不影響居民、交通、不擾亂市容環境秩序的情況下,允許設置臨時攤點……對于地攤經濟來說,這樣的鼓勵和支持是前所未有的。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長期堅持了城市排斥主義,將地攤經濟視作城市的入侵者,采取取締或驅逐為主的策略。然而這也并非是對過去的否定。時隔多年,地攤經濟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對其不同的態度是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和看待攤販在社會發展的地位和作用,取決于它與政府政治經濟目標的關系。
其次,數字化商業開始與地攤經濟合作。在過去,城市中的攤販往往因為年齡和受教育水平而與網絡無緣。伴隨著年輕人工作觀念的轉變和智能化的發展,地攤經濟也開始邁向數字化。在政府的鼓勵帶動下,蘇寧在響應國家小店經濟、地攤經濟號召,推出“夜逛合伙人”政策后,計劃將提供20億夜市啟動資金、1000億本地化優質貨源解決商戶資金、商品供應鏈難題。阿里零售通將地攤加入小店經濟扶持計劃,為小店們推出免息賒購、滯銷賠等措施,提供最高10萬元的零息金融支持;京東發布“星星之火”地攤經濟扶持計劃,從保供貨、助經營、促就業三方面入手,組織超過500億的品質貨源,為每個小店提供最高10萬元無息賒購,全力支持地攤和小店經濟;拼多多宣布獨家補貼地攤經濟新晉網紅“五菱售貨車”,僅2個小時,活動頁面顯示首批補貼的100臺“擺攤神車”已經售罄……。
“云擺攤”等扶持計劃,為攤主提供幫助,支持攤主免費開店,并提供貨源和大數據分析支持。地攤與網紅帶貨合作,同時獲取線上線下流量,大大激發了零售行業被抑制了近半年的消費需求,電商平臺發揮自身優勢,從供銷兩端幫助解決地攤經濟難題,數字化技術的地攤運營正在成為新常態。
另外,地攤經濟重提之下另有整改。各地相關管理部門科學管控地攤經濟,對擺攤時間、地點、擺放范圍實施精細化管理。部分地區允許在居住集中區附近開辟臨時擺攤點,引導農戶流動攤販規范經營,鼓勵利用小區內外閑置區域設置擺攤點,有條件的地方可設置占道早市夜市擺攤。
政府根據不同時期的發展規劃來調整攤販治理政策,當前地攤經濟被重提這是疫情背景下城市治理與百姓民生相協調的產物。疫情至今政府逐步開啟一系列非臨時性政策來緩和抗疫,從中央到地方、從國企到攤販各行各業緊張的經濟態勢。縱然疫情對我們產生了一定影響,甚至2020年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下降6.8%,帶來多年以來第一次經濟負增長。但是,自2020年第二個季度起,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我國政府采取的各項措施有效地改善了經濟狀況。2020年,中國經濟交出了一份令世界矚目的答卷,翻看這份成績單,許多數據都超出預期。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初步核算,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高達1015986億元,同比增長2.3%。而在這其中,處處可見地攤經濟的身影,搞活城市攤販對維系百姓生計有著重要影響。
三、地攤經濟在經濟社會中發揮的作用
“地攤”真的那么重要嗎?他的確不重要,因為市容市貌總不允許他們任意“抹黑”城市,城管在后面追著,顧客在更后方喊著。他們總是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售賣著那三兩種玩具,或者七八種菜蔬。但在一塊塊包袱的背后卻背負了一個個家庭的生計。2010年中國“地攤經濟”總量1.14億相當于總城鎮就業的33%,創造15%GDP的產值。
任何政策的推進都離不開“保民生,穩就業”這個最終目標,為了緩解的經濟衰退,中國政府提出“六穩”+“六保”,六穩是指: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而其中最重要是穩就業。此刻,“地攤經濟”被當作保障民生的重要工具。2020年至今,中國多地出臺了促進地攤經濟發展的政策。“地攤”創業門檻低,沒有店鋪租金壓力,不需高學歷、高技能,投入成本低,具有小成本創業的優勢。這讓大量城鎮新增人口轉換成商販,獲取利潤、得以謀生。對于消費者來說,開放地攤,便捷了生活,消費者在衣食有了多種選擇,以更低廉的價格和更方便的形式獲取個人所需,節省了生活成本,可以極大地改善生活。
國家實施政策搞活地攤經濟,促進了各行各業的運作,既帶動了就業,又促進了消費。首先,緩解了就業壓力。受到疫情的影響,當前全球經濟總體形勢不容樂觀,國內企業生存困難,已經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但失業人員的生存問題也迫切得到解決。所以,允許擺地攤,提供臨時的就業崗位,解了燃眉之急。例如成都首先放開地攤經濟,解決了10萬人的就業問題。再者,允許擺地攤,可以降低百姓生活成本,方便群眾生活,緩解了衰退經濟背景下居民的生活壓力。此外,地攤經濟也能幫助廠家銷售滯銷商品,回籠流動資金,一定程度上挽救生產廠商。無法利用以往銷售渠道的商品以及生產中次品,也通過地攤的方式完成了交易。
隨著社會生活恢復正軌,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也不難發現攤販的身影。但不一樣的是,政府采取劃區管理和疏導的方式將其融入了疫情下的城市管理。越來越多的商貿市場的規劃和控制體現著城市管理的進一步升級。疫情讓政府“看見”了地攤。雖然現在各地復工復產,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還是要靠消費來拉動經濟。而地攤經濟是最能刺激市民消費的欲望。在定點隔離,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市的政策下,地攤更加貼近百姓生活,融入大街小巷,在不知不覺中激發了民間的消費需求,促進了國內經濟的增長。
四、如何看待疫情下的地攤經濟
其實,早在2019年時地攤在很多城市已經銷聲匿跡。可能如果沒有疫情,很多年后的孩子不能理解怎樣將手伸出就能交換來商品。這短短的半米之間的商品交換,伴隨著人類的產生開始發展,曾經在不同時代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為經濟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雖然它已不能滿足全部的消費需求,但商品交換這樣原始而悠久的方式并不單一,交換彼此的所有物,在價值和使用價值二者之間擇一,這樣的過程不應該只存在電腦上冰冷的文字。
地攤經濟一定程度的復歸不等于重回粗放發展的老路,而是要開辟一條既適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與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和城市發展相契合的新路。這就要求我們找準“地攤經濟”定位,推動“地攤經濟”走向提質升級,同時又要不失時機地轉變“地攤經濟”的歷史使命。
攤販的存在和此消彼長是多種類型的勞動者為了應對各自所處的不利處境而做出的主動或被動選擇的結果。這些處境與中國社會經濟重構過程產生的多種結果緊密關聯。攤販經濟的作用不僅在于帶動經濟,而且為處于生存困境的各類勞動者提供了就業機會。在未來,“攤販經濟”可能會向更加合理、更加有序的模式發展,但我們始終不能忽略他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合理化發展“攤販經濟”遠比一刀切更加符合社會期待。
原本以空間排斥為主的攤販政策在實踐中的暴力性誘發了社會沖突,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它對攤販的“零容忍”也剝奪了底層群體的生計,具有否定民生的性質。攤販爭奪空間是一種被政府管制所激發的自發的、自主的、自然的行為,奠定了空間排斥的不可持續基礎,成為攤販治理重構的一種力量。城市管理者和攤販之間的硬性對抗不僅使取締行動成為“兩敗俱傷”“沒有贏家”的政策,也使治理陷入被公眾輿論質疑的合法性危機。
擺地攤也要按照相關規定擺設,要符合市容管理者的要求:一方面,擺地攤要在規定的地方擺。城市管理者需要開辟特定區域,允許攤販在此經營。另一方面,合理規劃攤販經營時間,比如人流量較大的上下班高峰時段,禁止擺攤,以免造成交通事故。管理者必須考慮空間的可持續利用和時間上的交替使用,停車位等空間根據時段分成停車和擺攤多種利用方式可以有效緩解城市空間壓力,給予“地攤經濟”更廣闊合理的生存空間。
“地攤經濟”空間分配必須可持續、治理必然走向和諧。政府在地攤管理中采取和諧話語,以正確的方式處理好社會矛盾和沖突,能夠促進社會和諧,而不是強化沖突。且在繼續推進經濟和城市增長的同時,能夠進一步改善民生問題。各地政府需要合理的設計和規范城市流動攤販的區位控制機制,實現經營者最大利益目標和服務對象最大剩余效用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