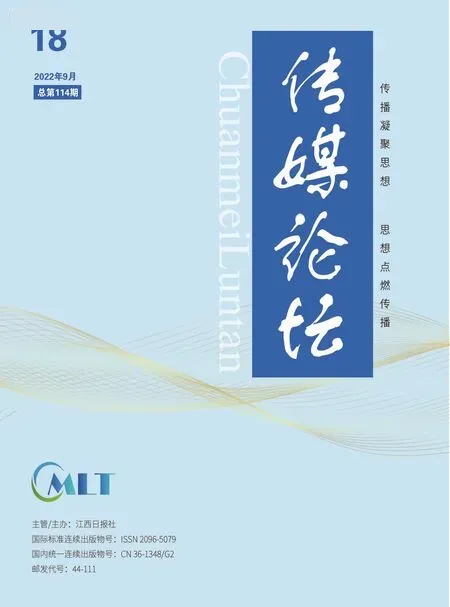文化劇情舞蹈綜藝的發展路徑探析
——以《舞千年》為例
宋玉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主張并提倡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敘述中國故事的情感道義,其中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文化類節目進行精品創作的基本規律[1]。以中央廣播電視臺和河南衛視等為代表的文化單位陸續推出了一批具有深刻文化內涵、講述中國故事的綜藝節目,如《國家寶藏》《典籍里的中國》《經典詠流傳》等。這類文化節目激起了網民們參與討論的熱情,并順勢掀起了一股“國風”熱潮,其中的作品也頻頻出圈。同時,在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文化產業年度報告(2022)》中,總結了2021年文化產業的十大關鍵詞和十大特征,其中“國風節目”當選為十大關鍵詞之一。這反映了優秀傳統文化在融入文化類節目的道路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表明“國風”與當下受眾的審美價值取向相契合。
一、《舞千年》的敘事路徑
自河南衛視于2021年春晚中推出了《唐宮夜宴》后,隨后便走上了以中國節日為切入點的創新性發展道路,并在節慶時節逐步推出了“奇妙游”系列國風節目,涵蓋“端午奇妙游”“中秋奇妙游”“元宵奇妙游”等主題,所展示的節目無一不以其獨特的美學意境吸引著受眾的關注。另一方面,嗶哩嗶哩(簡稱“B站”)作為當下年輕用戶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區和視頻平臺。與河南衛視攜手合作,以傳統文化為立足點,共同推出一檔以文化劇情舞蹈為特色的綜藝節目——《舞千年》。節目共分為八個章節,以五位薦舞官化身為歷史人物為起點,邀請了國內十三家頂級舞團進行演繹,演出舞蹈分別繼承和展現了與之對應時期文化的審美風格,生動形象地展現了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更迭的時代華章。
(一)沉浸式敘事再現歷史情境
以故事串聯舞蹈,用舞蹈講述故事。薦舞官選取當代受眾所熟知的歷史人物與事件進行實景演繹,如三國時期的曹丕和曹植爭鋒,雅宋文人撫琴、品茗、論詞等,讓故事充滿了熟悉感和新鮮感。同時,采用影視劇的拍攝手法,將影視、舞蹈和綜藝進行有機結合,有利于增強節目內容的表現力與感染力。通過渲染具體化的故事氛圍和具有層次的節奏與色彩表現來增強節目的視聽效果,幫助演出人員呈現不同舞蹈之間的情感表現。
以極具韻律感的舞蹈藝術為敘事主體,由人物情感進行支配的故事劇情為基調,層層鋪墊展現故事劇情的波瀾轉折,通過鏡頭語言的多層銜接強化演出人員的情緒傳達,并逐步推至情感高潮,進而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以高超的舞蹈表現力促使受眾處于一種“沉浸式”的觀看體驗,仿若置身其中,感受舞中所處時代人們的喜怒哀樂,體悟他們的家國情懷與民族精神,在精神上產生共鳴與共情。
(二)雙層敘事線索展示中國故事
《舞千年》在敘事層面,主要形成了明暗交織的兩條線索。一是整體節目的主線索,明線上選擇了四個時期作為演繹背景,即三國、唐朝、宋朝和20世紀80年代。五位薦舞官一同穿越時空尋找舞蹈、推薦舞蹈,兼顧了現實世界薦舞官和歷史故事人物角色的雙重身份。如第一期與第二期中薦舞的場景為銅雀臺宴會,表現的是曹丕和曹植兩大陣營通過薦舞一較高下。以倒敘的手法展現了從東漢《相和歌》到春秋戰國《孔子》,最后為舊石器時代《火》的歷史發展進程。
二是人物角色的個體敘事加強了故事的真實性與完整度,每個角色都是鮮活立體的,有著強烈的情感色彩,每人所薦之舞都與其扮演的人物性格相關聯,產生了充滿張力的劇情沖突。基于史實的藝術創作,有利于不同類型的舞蹈之間進行自然巧妙地銜接,加之適當的字幕科普使人更容易在情感共鳴中獲得沉浸式體驗。由北京舞蹈學院演繹的作品《俠骨傘影》則是講述了“天下第一劍”俠客攜心愛之人給予的紅傘,想在隱退江湖后以傘換劍,卻在雨夜中遭遇殺手追逐的故事。由北京舞蹈學院演繹的《越女凌風》借春秋女劍術家“越女”的形象,表現其以劍悟道。同時在故事表現中引用了王家衛電影的俠客風,更是與作品《俠骨傘影》產生了劇情聯動的效果。
二、《舞千年》的創作路徑
河南衛視延續之前在“奇妙游”系列節目中取得的成功經驗與路線,保留了中國節日和儀式的題材選擇,如《踏歌》等,同時融入了歷史上大眾較為熟悉的故事和人物,如《趙氏孤兒》《昭君出塞》《關公》等,具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屬性。以《舞千年》《國家寶藏·展演季》等為代表的文化類綜藝節目,滿足了年輕群體對于優質舞蹈內容的觀看需求,同時促使年輕群體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共情體驗,綜藝節目逐步成為當下年輕人了解傳統文化的新途徑。《舞千年》之所以能成功“出圈”,走進融入年輕受眾的活躍圈層,主要依賴于以下幾點要素:
(一)以中國故事為主導的內容創作
《舞千年》節目中的舞蹈和劇情編排主要依托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選擇的對象較為寬泛,對于所舉薦的舞蹈不拘泥于某一具體的時期,僅需符合敘事脈絡,則有機會入選。舞蹈本就是一種美的體現,充滿了節奏感和韻律感。在薦舞過程中,既能看到魏晉少女的婀娜舞姿《踏歌》,又能感受熾熱灼燒的現代舞劇《火》。同時,制作組十分善用歷史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故事和慶典來降低受眾的欣賞門檻,如及笄之禮《踏歌》、歷史故事《秦王點兵》《趙氏孤兒》《關公》、傳統經典《相和歌》等選題豐富的節目內容。
一舞一故事,每支舞蹈的背后都隱藏著一段歷史,如歷史上家喻戶曉的悲劇故事《趙氏孤兒》。中國歌劇舞劇院以其舞者的專業能力為觀者呈現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中國悲劇《趙氏孤兒》,制作組以忠孝家國孰輕重、一義孤行兩難全為提要,高度概括了故事內容,弘揚了忠、信、義的傳統理念。由河南省洛陽歌舞劇院演繹的作品《關公》,利用寫意化的群舞表現手法展現了關公的人生片段,再現了關公“正氣沖霄漢、大義薄云天”的藝術形象,重新解讀了“桃園結義”等讓受眾耳熟能詳的故事。
同時,敦煌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中極具特色與代表性的一種地域文化,在《舞千年》中也有著不同的演繹方式。一方面,由甘肅省歌舞劇院演繹的《絲路花雨》,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以老畫工神筆張和英娘之間的悲歡離合來反映絲綢之路和敦煌壁畫創作背后的艱辛,《絲路花雨》不僅僅是敦煌舞的開山之作,更是成為甘肅省的“文化名片”,在世界舞壇上熠熠生輝;另一方面,由中央芭蕾舞團上演的舞劇《敦煌》則讓更多的受眾看見了更多的可能性,將絲路文化與芭蕾藝術相結合,用中西合璧的方式詮釋了莫高窟的彩塑壁畫之美。
(二)以受眾心理為導向的創作方向
受眾作為信息的直接接收者,擁有高度的自主選擇權,作為接受信息的獨立個體則呈現了多樣性的特點。一是目標受眾作為社會活動的參與者,對于新信息、新事物的反應能力和由此展露出的態度必然會受到其所處時代和當下文化的影響;二是受眾作為獨立的個人有著不同的需求取向,對于以國風為主推要點的文化產品有著不同的消費觀念和審美品評標準[2]。
新時期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促使民眾對于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有了更多的認同感,開始呼吁優秀傳統文化的回歸,逐步建立起了文化自信的社會氛圍。《舞千年》在《唐宮夜宴》和“奇妙游”系列的基礎上進行升級改造,是制作組精準把握用戶心理的集中體現。接受美學理論認為受眾常用某種“期待視野”來看待某一對象。其中,受眾背景與其人生經歷必然對“期待視野”的生成產生影響[3]。“期待視野”可將其理解為是受眾對于目標事物所設定的預期心理,滿足“期待視野”實則就是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預期。
在《舞千年》中受眾所產生的共情與移情效應,往往有助于受眾深入感受優秀傳統文化魅力。“共情”一詞常用來形容作品與欣賞者之間的關系,是受眾從獲取的信息中提取出情緒體驗,將之與受眾自身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相聯系,則更容易使受眾自身代入相應的情境之中并在精神上達到趨同,從而產生共情效果。如作品《醒獅》以三元里抗英斗爭為背景,展現了人們齊心協力面對外強侵入,危難之際所展現出的善良、真誠與人性,極易引起受眾的共鳴。同時,將南拳馬步和南派舞獅融入舞蹈語言,實現了傳統文化和舞蹈藝術的完美融合,巧妙的情節架構融入了團結與正義的主題,展示了中華民族藝術的魅力和自強不息的精神。
三、《舞千年》的傳播路徑
《舞千年》選擇B站作為演播平臺,意味著年輕群體是本次節目所面向的目標受眾。文藝創作所面對的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同代人,創作者們只有通過作品各方面的不斷完善,滿足受眾的心理需求,才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受眾的共情與共鳴,從而產生傾訴、分享的欲望,受眾就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逐步完成了身份轉變,從一名接受者成為傳播者,讓更多的圈外人看到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和魅力所在[4]。從受眾群體來看,三類主體成了《舞千年》傳播的主要助推者——國風愛好者、舞蹈愛好者以及相關視頻剪輯創作者,同時他們以大量的二次創作擴大了《舞千年》節目的影響力。在字幕解說中,也有與之對應的舞蹈知識、歷史典故和人物簡介進行補充說明,更有人用二次元話語發表彈幕進行刷屏互動,這種行為充滿了B站受眾的交流特色,更是開啟了文化綜藝的“破次元”連接。同時,節目中將“采舞官”的選擇權移交于受眾,不僅提高了受眾的參與積極性,更是實現了節目與受眾的有效聯結。
《舞千年》中所設立的彼此獨立又相互連續的節目結構,有利于展開多渠道的推廣傳播。一方面,在微博平臺中各大地方博物館紛紛現身展開聯動并化身為講解員穿梭千年,借由節目中的舞劇選段進行文化推廣,如江西博物館借由《相和歌》提出舞者長袖飛舞,各類玉簪類型繁多,金珠玉珠共相顫動,盡顯女子步態輕盈之美。進而介紹到漢族女子插笄是成年的一種標志,女子年滿15歲前發式常做成丫鬟,到15歲時若已許嫁便可做成人發髻,此時便可使用發笄,并將舉行“笄禮”。而《舞千年》在《踏歌》一舞中恰好展示的便是“及笄之禮”和“上巳節”,傳統典禮與節日的有機結合,促使受眾在舞蹈中追尋中華文脈,深切體會中國傳統的文化魅力。
另一方面,眾多官方微博賬號也積極參與話題互動,如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新京報、中新視頻、光明網、南方都市報、中國青年雜志等多家媒體相繼助力發聲,宣傳節目中《昭君出塞》《書簡》《醒獅》等精彩片段。地域媒體也紛紛轉發,體現了地域文化的自豪感。部分歷史博主在線科普,文化博主解析隱藏亮點,面向微博的使用群體科普史實,通過服飾、音樂等細節挖掘歷史,展現古人的風采。二次創作的持續發酵,在視頻剪輯與美妝仿妝的圈層中得到了大量的關注美妝博主復刻唐宋的精致妝容,視頻博主通過蒙太奇的手法,以“幀”品味時代舞蹈之美。微信、抖音、今日頭條等各類圈子持續共鳴,產生長尾效應,逐步收獲了大批的真情推廣,最終產生了高度的文化認同,達到提升文化自信的良好效果[4]。
四、結語
《舞千年》作為一檔文化劇情舞蹈的綜藝節目,以影視、舞蹈與綜藝的跨界融合為特色,將舞蹈語言作為敘事主體,以主劇情的互動代替了傳統綜藝節目中綜藝主持人的位置,在劇情中以個體敘事的方式將獨立的二十四支舞蹈進行了編排與整合。一方面,靈活運用多種風格向受眾呈現一批充滿傳統文化靈韻的中國故事;另一方面,滿足了受眾對于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故事的視聽想象。《舞千年》精準把握受眾心理,巧用科技元素提升舞蹈的視聽效果,并在節目中對值得贊頌的中國故事和弘揚的民族精神進行了傳播,進一步激起了受眾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是一次將中華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良好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