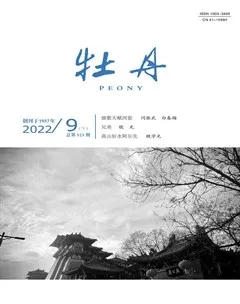人情化物,浮游鳥草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經濟驟然騰飛,巨大的經濟成就肯定了港人的聲譽地位、生存狀態和存在價值,同時卻也形成了新的“城市病”——新型城市建設改變了民眾的生活方式、生存處境、生態環境,進一步破壞了一代港人的生存記憶,“膨脹的消費主義消費造成人們精神上的苦痛、空虛和墮落”。城市文化的發展促使香港作家對香港歷史回根溯源、對香港現實記錄反省、為香港未來謀辟出路。代表作家西西以自身為橋梁,以文字為載體,以時間為經,以人物為緯,構筑香港歷史洪流中的眾生相,每個角色“帶景上場”,以人為骨,以物為皮,將豐滿的香港印象以長卷形式鋪陳在讀者面前。相較同時期的其他作家,西西在挖掘城市記憶、回溯香港歷史的過程中有意避開了宏大敘事與對關鍵歷史事件的討論,而將焦點始終聚集在市井風情,以“小人物”的生活來體現“大歷史”。馬克思評論費爾巴哈時將人界定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突出強調了“人”的地位。正如同時期作家也斯所言:“不見得寫都市文化、都市文學就一定是摩天大廈、霓虹燈、飛機火箭那種都市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活、人的體驗、人的關系的變化,以及種種對人的理解、體悟的變化。”“人”永遠是意義的制造者,對“人”的聚焦使得西西小說“城”概念的呈現中滿溢溫暖的人文關懷與寬厚的未來期許。
現有對西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土意識、敘述視角、城市書寫、童話書寫、女性意識、跨界結合、身份認同、物質異變等方面,代表性論述諸如劉慧敏等著《香港文化中的本土意識透視》和《女性意識的建構與豐富淵博的知識性敘述——論西西小說城市書寫的特質》、劉洋溪《論西西小說中都市印象的變遷》、李慧《論西西小說的城市書寫》、劉飛《淺析西西八十年代的“肥土鎮”故事》、朱孜莘《論20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小說的城市想象》、黃金《邊緣·異化·跨界——消費文化語境下的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研究》等。
一、人情化物:城市書寫的暖色調
西西鐘愛的畫家馬蒂斯曾說:“人們必須畢生能夠像孩子那樣看見世界,因為喪失這種視覺能力就意味著同時喪失每一個獨創性的表現。”作為現代主義小說家,西西早期曾效仿西方創作過不少存在主義小說,但又很快發現這些專寫“不快樂”的小說不適合自己,轉而將一雙孩童般的眼睛投向年輕人的日常,發現并訴說另一種“快樂”的存在:平凡眾生相。
眾生相的描繪始于西西20世紀創作的《我城》。在這個有著“木馬道”“公主大道”“白菜街”“胡蘿卜大廈”的明麗小鎮中,住著愛唱“烘面包烘面包味道真好”的阿果、在放假和加薪之間永遠選擇放假的麥快樂、和鬧鐘朝夕相伴的阿發、愛讀書的悠悠、相濡以沫的瑜和丈夫、鐘愛做門的阿北、跟著木匠學作詩的師弟、拿魚骨頭印版畫的阿傻、喜歡讀偵探小說的阿探、表演時總沒有節目的阿郵、喜歡航海的阿游……作者以一顆童心關照都市年輕人,而這群年輕人也繼承了作者孩童般的眼睛,發現生活瑣事中的美好與快樂:阿果在疲憊的搬家過程中驚訝地發現搬家可以減肥,“我滅了兩磅,我的家減了一千五百磅”;悠悠在霓虹燈閃爍的夜晚看見沒有顏色的窗孔,猜測“它們要點的也許是月光”;麥快樂會在鞋弄臟的地方充滿童心地畫上幾朵星云彩虹,幻想在爬上天梯、遇見巨人時將它那會生金蛋的母雞抱下來,送給大會堂的兒童圖書館。生活如一地雞毛,這群年輕人卻腳踏實地專注自我,用當下生活的積極意義來對抗現實——“他們這樣觀看世界,也教讀者這樣觀看”。
拉康的鏡像理論認為,嬰兒的主體構建依靠自身與來自鏡中的“他者”,自我的確立意味著“自我”與“他者”劃清界限。鏡中形象所呈現的形式上的完整性、整體性與協調性易致使其在形象與現實的人和物之間產生混淆和誤認,故此階段的孩童眼中,“自我”與“他者”不辨,“人”與“物”難分。而擁有孩童之眼的西西更是有意以“物”的視角觀世界,賦予“物”以新的意義與另類美感。
在西西筆下,鋼琴“必須服食鈣片”,否則“一按下去即不愿意起來”;菠蘿也會聚眾交談,生氣有同名的“菠蘿”壞了自己名譽;墻有軟硬之分,軟墻愛咬釘子,而硬墻模樣兇,招釘子害怕鞠躬;附近的海島上有很多“喜歡鬧脾氣”的巴士,一個不高興就要加倍收費。這種“觀物”,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文化移情傳統的轉化”,將主體的“人性”通過平等的視角賦予并代替客體的“物性”,從而將工業化過程中由商品拜物、資本拜物、貨幣拜物等問題形成的“物化”效應轉化為帶有東方溫柔底色的“化物”,無形之間消解了商業文明帶來的異化沖擊。
現代化的城市物欲紛擾,而西西所見的年輕人與年輕人之間、年輕人與環境之間卻流淌著某種自然的、古老的、充滿人文情懷的熨帖溫情。眾生與環境構織成覆蓋城市的大網,沿脈絡流動的溫情為西西的城市書寫披上溫暖的底色。
二、浮游鳥草:城市書寫的冷色調
西西是香港的筑夢人,她的代表作《我城》用年輕人的視角、童話的筆觸來敘述香港城市中的一切,這種“走馬觀花”式的敘述方式“將城市的光明面從沉重的城市形象中剝離出來”,塑造出一個清新明麗的童話小鎮。然而讀者不難發現,小鎮的晴空中偶爾也會掠過一絲陰霾,而這種冷暗色在其后期作品,如《浮城志異》《飛氈》《肥土鎮的故事》等之中愈發強烈,城市異化的現實背景下對于“我城”處境的擔憂不斷入侵西西筆下的理想國,使得小鎮帶有淺淡的冷色調。
西西深愛“我城”,并不吝筆墨、不厭其煩地為都市里形形色色努力生活的小人物寫下一首首明快的贊歌。但同時,作者也親眼見證“我城”中許多令人無法上揚嘴角的現實,并含蓄反映在作品中。生于上海長于香港的西西先后受到古老的中原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的洗禮,可是如今時代改變,站在處處是高樓大廈、飛機輪渡的都市,西西在為香港成就驕傲的同時,也親身感受到文化的巨大差異,目睹了港人思想觀念的異化:一代城市記憶的消逝、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冷漠、生活環境的逼仄冰冷。麥快樂接聽抱怨電話后感嘆:“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受到外界很多阻隔。”阿果看到了被塑料袋包裹起來的整個城市,而自己也面臨著刺破隔膜和被塑料袋包裹的抉擇。塑料袋的隔離暗示著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遠,阿果最后也沒能做出抉擇,問題的懸置背后隱含著作者自身對于現代城市人情困境的迷茫。“有”的意象出現得更巧妙深刻,寫著“有”的火車卡日日裝載棺木運載至郊外,直到古老的郵政局、火車站、鐘樓都被裝進火車卡時,我們才恍然大悟,這場告別過去、迎接新生的時代葬禮不僅埋葬了過去的人,也埋葬了過去的無數城市記憶。作者使用寓言化的手法,在緬懷過去時留下了一聲隱晦而綿長的嘆息,對城市異化的憂慮終于浮出水面。
在《我城》中“由得好多的臉去照個夠”的鏡子,在“浮城”中已經變得不管“轉換多少不同的方向”“反映出來的永遠是事物的背面”。看鏡子“并不能找到答案,預測未來”,向往飛行卻無法創造飛天樂伎的飄帶,只好在安靜的焦灼里繼續懸浮空中。而西西將“浮城奇跡,畢竟不是一則童話”的事實一語道破,也使得人們無法繼續自欺欺人地相信“浮城將永遠像目前這樣”。不堪忍受在時間零附近焦慮徘徊的人們選擇逃離這座“擠逼骯臟令人窒息的城市”,卻發現別處也沒有安穩的落腳點,他們“雖然是渴望飛翔的鴿子,卻是遭受壓抑囚禁的飛鳥”。至此,時刻關注小人物生存境況的西西終于引出概括了20世紀80年代香港人精神面貌的“鳥草”意象:非鳥非草,非動物也非植物,象征著城民漂泊游移、難以自洽的自我定位。對于在身份認同問題上慌亂無措的同胞的擔憂,和對于未來命運懸而未決的城市的思考,使文本稍顯壓抑與沉重,發人深省。
三、冷暖碰撞:腳踏實地,常懷期望
“沒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氣的。”《我城》的故事將盡,沒有勇氣無根而生的瑜與丈夫出城,沿途不時出現指導方向的白線。“有時,白線的末端是分叉的箭嘴,朝哪一個方向走還得由他們自己選擇。”以勇氣的白線為界,有人選擇生,有人選擇死;有人選擇進城,有人選擇逃離。選擇逃離的瑜和丈夫失去了身份證明,變得如空氣般“舒適而輕盈”。而離開“摯愛的、丑陋又美麗的城”去環游世界的阿游從侯斯頓出發,將巴西誤認為“我城”,在到達阿根廷的那一刻,獲得了生活的勇氣:“腳踏實地是一種舒服的感覺。”
“香港現代主義作家的積極精神在于腳踏實地地面對現實。”若將對一片地域的愛界定為三個層面的意思,第一層是熱愛這一方土地,如艾青“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第二層是熱愛世代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第三層是熱愛這片地域上的領導政權。前兩層含義的熱愛來自人們內心一種樸素的情感,是一種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的眷戀,和對“我”之所以區別于“他者”的文化意義上的身份認同。浮城失重地漂懸半空,而西西卻能腳踏香港實地,將愛傾注給不屈不撓、樂觀堅強的城民與養育他們的城土。愛使得西西性格、文風如趙稀方評論的那樣:“西西不像一些南來作家對社會的陰暗面感興趣,她對‘我的城市’持一種友好、理解的態度,至多只給予一種溫婉的反諷。”早期的西西描繪年輕人樂觀積極的生活狀態,使得她筆下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帶有柔和別致的底調;后期對于人的異化以及香港城市異化的書寫,又使得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印象出現冷硬混亂的色彩。在這里應當指出,這種對人的冷硬描寫表現出西西對于香港市民階層的擔憂,本質上依然是西西人本意識的體現。這種暖與冷的碰撞,最終形成西西理性而理想的人本書寫特色。
西西的香港史書寫橫亙兩個世紀,而其中對年輕一代的期望卻始終未曾斷絕。除去客觀的因素外,貫穿西西香港文本史系列的人本意識或許占據著更重要的地位。這里要明確的是:不管時代如何前進,對人性的善意、對希望的向往都是西西書寫的底色,如《浮城志異》結尾神秘卻仍在微笑的“蒙娜麗莎”,又或是給人帶來希望的飛氈,在故事最后都為未來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而這種希望來自西西對香港青年人的期待:《我城》中西西即借老師之口,表達了對如阿發般的年輕人實現“美麗新世界”的企盼,而遭到搶劫毆打后從事“警務工作”的麥快樂更可以說已經走上了實現美麗新世界的道路。在生存困惑無法得到解答時,她也樂觀地寄希望于“慧童”:“也許,一切將在他們手里迎刃
而解。”
人本意識煥發出的明亮希望,在同時期整體呈現出迷茫、失落與無盡探詢的香港文學中是一種少見的、具有撫慰性的力量。對人的書寫、對人的期盼、對人的關照,都令西西筆下各個時期的香港在人本底色的浸潤下顯得愈發柔韌頑強。當“我城”新生代青年在歷史與文化歸屬的迷失中焦慮無助時,他也許就能在西西的小說中得到安撫與啟發,就如西西最喜歡的詞:腳踏實地。踏實地、實在地活在腳下這塊土地之上,用對當下的關注來對抗歷史的虛無。從這個角度來看,西西的作品值得一個時代去閱讀。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林子涵(1999—),女,湖南長沙人,本科,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