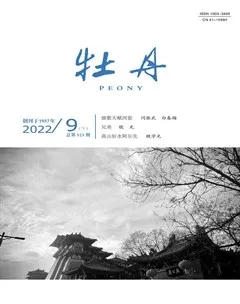巴金小說《寒夜》中的小人物形象研究
巴金作為中國現當代著名文學家,創作了許多經典名篇,他的長篇小說《寒夜》真實再現了凡人小事的悲劇,展示了小人物內心的創傷與困境。小說通過汪文宣、曾樹生、汪母等寫出了社會與時代的弊病,映射出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他以平視的視角寫出這些小人物的悲哀與反抗、掙扎與無奈,寫出了小人物的血與淚,在深切的同情與辛辣的批判中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寄托了巴金對國家、民族光明未來的憧憬之情。
這部作品可以說是巴金在小說寫作上的一座豐碑,尤其是在描繪人物心理方面,這部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巴金本人在小說的后記中曾提到,他不敢去面對“那些血淋淋的現實”,他也“只寫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小事”,是那些“不幸的患病者的血痰”、那些“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促使巴金拿起筆在寒冷的黑夜里寫下這個悲劇,而作品中他對于小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困境中的“多余人”形象:汪文宣
“老好人”汪文宣最擅長的似乎就是“為難自己,方便他人”,這種懦弱的性格使他在社會和家庭中都像一個“多余人”,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他一直在為別人著想,面對為難自己的上司、侮辱自己的同事,他只能忍氣吞聲。他只敢在心里暗罵“你哪管我們死活”,“連鼻息也極力忍住,不敢發出一點聲音”,生怕別人會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作者以沉重的筆調描寫了小人物的困境與無奈。
青年時期的汪文宣深受個性解放的影響,內心滿是理想和事業,妻子又與他志同道合,夫妻二人一心想奉獻于教育事業,想攜手創辦一所鄉村化、家庭化的學校。他和樹生沒有結婚就開始同居,勇敢地向封建禮教發出了挑戰,但是這也為日后的婆媳矛盾埋下了種子。年少時的意氣風發終于被社會所吞噬,《寒夜》是抗戰勝利前后國民黨統治區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曾經許多青年人都如文宣一樣對自己和未來充滿信心,但是戰火紛飛讓他們很快跌入了貧苦的深淵,這些善良的小知識分子只能在漆黑寒冷的社會里苦苦掙扎。
汪文宣無疑是心地善良、忠厚老實的,但更多的卻是軟弱無能。“但是誰也沒有聽見,誰也不知道他起過不平的念頭。當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歡稱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他在工作上四處碰壁,最終只能成為一名校對員,每天看著那些“似通非通的譯文”,每天完成著無聊枯燥的工作,還要仰人鼻息,忍受著“周主任的厭惡的表情、吳科長的敵視的眼光和同事們的沒有表情的面孔”,有時還要違心地為政界要員出的書寫廣告詞。他在工作中受盡屈辱,最后還染上了肺病,每天遭受疾病的困擾。回到家中,他還要夾在母親與妻子之間,在她們之間兩邊哀告,左右為難,汪文宣在家庭中孝順母親、關心妻子,但是婆媳之間的矛盾依舊是不可調和的。對于母親,汪文宣感慨她的不易,一把年紀還要照顧自己一家的起居,但是也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淪為“二等老媽子”;對于樹生,汪文宣更是感到愧疚,他一直認為自己拖累了樹生,即使樹生后來離開他并寫信表明要和他分手,他都沒有責怪她,不僅隱瞞自己的病情,還真誠希望妻子能幸福。
家庭、工作、愛情和社會各方面的壓力使汪文宣難以得到喘息的機會,他的內心變得扭曲,別人的一個眼神或是動作都會讓他懷疑是在針對自己。他身上濃縮了那些遭遇悲慘命運的小知識分子的性格特征,懦弱、膽小、苦難成了他的代名詞,他是處于困境之中的“多余人”。抗戰勝利了,但仿佛什么事都沒有變好。“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沒有上訴的心思。”在這樣悲慘的境遇中,汪文宣走向了生命的終點。汪文宣悲慘的一生,不僅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慘命運,更折射出社會的悲劇、時代的悲劇。
二、世情厄困中的“普通女性”形象:曾樹生
曾樹生是《寒夜》中最矛盾的靈魂,她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禮,大膽追求自己的幸福,憧憬自由浪漫、充滿光明的生活。曾樹生不同于傳統封建社會中那些像藤蔓一樣依附于家庭而喪失自我的守舊女性,她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與汪文宣軟弱的性格不同,她的生命力更為旺盛,她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但是丈夫的疾病與軟弱、婆婆的冷言冷語、對青春消逝的恐懼與不安使得她一直處于糾結之中。
雖然曾樹生在思想上有一定進步性,但她也只是一個普通的女性。她在大川銀行里“當花瓶”,擔負著孩子的學費和丈夫的醫藥費,挑起了家庭經濟的大梁,雖然對自己“花瓶”的身份感到不滿,認為自己“一個學教育的人到銀行里去做個小職員,讓人家欺負,也夠可憐了”。但是生活依然要繼續,她依然會每天打扮自己,希望得到他人的贊美與認同。
樹生像所有普通的妻子一樣愛自己的丈夫,也渴望得到丈夫的愛,但是丈夫的軟弱讓她一次次失望,愛意慢慢變成了憐憫,不斷折磨著她的內心,昔日的理想早已變成了奢望,曾經的恩愛最終也變成了將就。她害怕黑暗,懼怕冷清寂寞,她急切地想要脫離這個陰冷的家,可是丈夫對她的寬容又讓她陷入兩難的境地,在這冰冷的環境中,黑暗一點點吞噬掉她的熱情,孤獨侵蝕掉她所剩無幾的愛情。對于樹生來說,“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她想要追求希望與新的生活。
她也像所有普通的母親一樣希望親近自己的孩子,想要給孩子更好的生活,讓孩子擁有光明的未來,她把小宣送進私立學校,不止一次想過小宣將來不能再像如今的汪文宣一樣。她和所有慈母一樣渴望自己的孩子出人頭地,但是由于缺乏溝通,再加上婆婆的挑撥離間,小宣不僅沒有理解母親的良苦用心,反而“對她好像沒有多大的感情”。
樹生雖怨恨汪母,但她也像所有普通的兒媳一樣,渴望得到婆婆的理解與尊重。這個家庭氣氛已經讓她喘不過氣,汪母對她的厭惡與不理解,讓曾樹生無時無刻不感到煎熬。“你不要難過,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過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樣的情形。你母親那樣頑固,她看不慣我這樣的媳婦,她又不高興別人分去她兒子的愛;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氣。以后還不是照樣吵著過日子,只有使你更苦。而且生活這樣高,有我在,反而增加你的負擔。你也該想明白點,象這樣分開,我們還可以做個好朋友……”汪文宣曾經感慨:“為什么女人還不能原諒女人?”她的一切行為都會被汪母放大并且曲解,就連丈夫也在汪母的“挑撥”之下與自己疏遠,這一切都讓曾樹生覺得無法與汪母正常相處。她聽不慣汪母的冷嘲熱諷,只能一次次的晚回家到外面尋找清凈,越是這樣汪母越是看不慣她,這無疑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兩個女人之間的沖突本就非常嚴重,作為中間人的汪文宣又從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調解。“‘樹生,你不要多說。都是我不好,連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媽,’他著急地向妻央求,拉開她。他又低聲對她說:‘媽上了年紀,想不通,你讓她一點罷。’”汪文宣祈求她們二人間表面的和平,而這樣的境況無疑讓兩個女人的矛盾越積越深。
曾樹生只是一位“未完全解放”的普通女性,雖然一直急切地想要“救出自己”,想要追求幸福,但是她的一切糾結與妥協都不過是在履行千百年來男權社會中賢妻良母的義務。當時的社會現實并沒有給女性真正的覺醒獨立留出路,她離開陰冷的家飛往蘭州,等到回來時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丈夫病死,兒子和婆婆不知去向,她的眼前是一片陰暗和凄涼,直到最后也沒能在寒夜里尋找到她想要的溫暖與幸福。她得到的僅僅是經濟上的解放,沒能真正實現女性自身的價值。曾樹生是夾雜在新與舊、感性與理性中間的矛盾體,雖然是抗爭型的女性形象,但仍然存在個性解放不徹底、女性生命邏輯不完整的局限性。
三、有姓無名的“傳統母親”形象:汪母
汪母是保守封建的舊知識婦女的代表,她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只是作為汪文宣的母親活著。汪母受封建禮教侵害較深,是一位被封建文化制度化的母親。早年喪夫,將封建綱常視為準則的她毅然選擇了守寡,痛失了丈夫,兒子變成她的唯一至親,更是她的精神支柱。漫長歲月里只有兒子與她相依為命,孤獨與寂寞是她面臨的最大問題,她必然要在自己的兒子身上投入雙倍的情感,這樣才能彌補心中的孤獨與寂寞,愛得過于深,最終就形成了扭曲的戀子情結。她如所有傳統的母親一樣深愛自己的孩子,對于兒子的愛可謂無微不至。她勤苦耐勞,又慈愛堅韌,為了兒子甘心情愿做一個老媽子。即使她已經“顯得那樣衰老,背彎得那樣深”,她還要在深夜為兒子縫補衣服,因為她白天又要買菜煮飯操持家務。但是在樹生面前,她又如所有封建傳統下的“惡婆婆”一樣,她對兒子那瘋狂的母愛竟然又全部轉化成對兒媳瘋狂的恨。
對于多年守寡的她來說,她不允許“別人分去她兒子的愛”,所以當兒子的人生里有新的女性進入并將其占有時,她便會手足無措。當她發現兒子對于兒媳的愛甚至已經超越了自己時,便用“我如果是你,就登報跟她離婚”“她不會永遠跟著你吃苦”“只有你母親才不會離開你”等話語來挑撥兒子與兒媳的關系。與此同時,汪母心中殘留的舊封建舊禮教、舊觀念使得她嫉恨兒媳,她認為:“你是我的媳婦,我就有權管你!我偏要管你!”汪母對于樹生的態度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積淀上的,她一心要按照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建立自己的家庭,用傳統的家庭模式來規范樹生。汪母之所以對樹生百般挑剔和厭惡,是因為汪母試圖復辟舊有家庭模式、獲得婆婆對兒媳的權威,但是卻慘遭失敗,因而產生怨憤厭惡的情緒。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我是拿花轎接來的,’母親得意地說,她覺得自己用那兩個可怕的字傷了對方的心。”汪母同所有被封建專制迫害的婦女一樣,她們裹腳、接受傳統教育,貞潔、婦道在她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而曾樹生是受過新思潮影響的女性,她追求幸福與自由,汪母始終認為兒媳配不上自己“純潔又高尚”的兒子。在汪母的眼里,她自己才是經過明媒正娶的“汪家人”,而曾樹生并沒有與汪文宣舉行過婚禮,永遠只能是兒子的一個“姘頭”。汪母不僅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受害者的悲哀,還深為自己的“婦德”自豪,時刻以自己為榜樣來攻擊兒媳。汪母假借兒子的不幸要求世人一起殉葬,但又是她親自將兒子的幸福葬送,甚至在汪文宣患病時,她一味相信庸醫,也間接導致了病情進一步加重,加速了他的死亡。
汪母只是一個普通的母親,她又如許多不幸喪夫的寡母一樣,將自己全部的愛傾注在兒子身上,展現了高尚而偉大的母愛。但她受封建思想侵蝕極深,無法與兒媳正常相處,展現了她作為婆婆“惡毒”的一面。汪母這個小人物身上體現了她性格的復雜性,高尚與卑下、偉大與渺小、善與惡在她身上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更加凸顯了小人物的愛與悲、掙扎與無奈。
四、結語
《寒夜》以沉重的筆調書寫了渺小讀書人的生與死,寫出了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所摧毀”“被生活拖死”以至于“斷氣時已沒有力氣呼叫黎明了”的人生悲劇。處于兩難境地的汪文宣,處于矛盾糾結中的曾樹生,頗具兩面性的汪母,作品中的每個小人物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好人或壞人,作家并不是要揭發他們,而是對他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巴金通過對這些小人物復雜性格的刻畫和人物內心矛盾與沖突的描寫,寫出了小人物的愛與悲、血與淚的掙扎,《寒夜》中體現了巴金的人道主義。
(延邊大學朝漢文學院)
指導教師:郭玉玲
作者簡介:孫嘉美(1998—),女,河北承德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