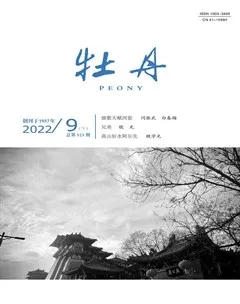敘述方式與寫作意圖:《中國套盒》帶來的啟示
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的著作《中國套盒》用書信的形式介紹了作家關于小說創作才能和寫作技巧的一些思考,展開了文學作品敘述方式與寫作意圖關系的探討,有很多獨到的見解。這部作品的另一個通行本標題為《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國套盒”與“寫給青年小說家的信”這樣看似不相關的兩個題目,就已經足以引起普通讀者的好奇心了。一打開這本書就會發現,“中國套盒”作為全書十二個章節的標題其中之一赫然在列。選擇“中國套盒”作為整部著作的統率,是隨機的偶然還是巧妙的必然,下文將著重探討。
一、偶然還是必然
趙德明先生的譯本中這樣寫道:“為了讓故事具有說服力,小說家使用的另外一個手段,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套盒’,或者‘俄羅斯套娃’。”其實只要作者愿意,這一章節也完全可以叫作“俄羅斯套娃”,那么,也許還可能會出現另一個譯本。顯然,巴爾加斯·略薩這位大師級的人物一定匠心獨運。在第二章《卡托布勒帕斯》中,作家將寫作的意義歸結于小說家的真實性或者真誠的態度,這種真誠體現在自覺自愿接納來自內心的“魔鬼”,并且跟隨這個“魔鬼”。對于作家而言,寫作本身即是一種生活方式,是為自己的內心尋找合適的發言方式,是一種生命體驗的細膩感知。一個好的作家一定是忠于內心的。作者講述的每一個細節都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中國套盒”一定不單是一個題目,而是體現著作家的某種寫作意圖。
趙德明先生認為,這是一部借書信的形式來“專門談論小說創作才能和技巧的書”。作家開篇第一封信講述了有關《絳蟲寓言》,強調“文學抱負不能僅僅解釋為自由選擇”,而是要懷著一種獻身精神。作家堅持認為文學抱負具有排他性的獻身,可以讓它的犧牲者(心甘情愿的犧牲者)變成奴隸;一個人之所以愿意投入寫作,是因為內心的絳蟲在隱隱作怪,這是一種內在的渴望;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驅使著自己去展現和表達,引導著自己以寫作的方式發言。第二章明確用“魔鬼”一詞來概括作者的題材來源。作者總是會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寫作方式和寫作素材,我手寫我心。簡而言之,作者內心的“魔鬼”也許正是作者寫作的魅力。第三章作家談到了小說的說服力,他認為小說的說服力來自作家的虛構能力。也就是說,其創作意圖即是實現其說服力。
接下來,巴爾加斯·略薩談到了小說的風格,涉及了作家的特點。風格更多的屬性就是技巧,而且不能被機械地借用或模仿。另外,風格也不能簡單等同于形式,應該有更深層的內涵。“要知道任何小說中都有一個空間視角、一個時間視角、一個現實層面視角。”由于敘事角度不同,“誰來講故事”也就不一樣,根據語法人稱的不同可以劃分為三個類別:其一為自述者,即采用第一人稱講述故事的主人公,是這個故事的核心人物,在這里,敘述者空間和敘事空間混淆在同一個視角里;其二為掌握上帝視角的敘述者,采用第三人稱講述故事,在這個過程中他是無處不在的全知者,他所占據的敘述空間與發生故事的空間是獨立的;其三為沒有確指的敘述者,這個人物默默隱藏于第二人稱的背后、語法之后、理論之后。從這個視角看來,作者的虛構和對現實的真誠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說作家越是對現實真誠、對創作真誠,就越擁有強大的虛構能力。
巴爾加斯·略薩為讀者介紹了兩種不同的創作手段——“中國套盒”和“連通管”。在兩種創作手段之中穿插講述的“隱藏的材料”意在提示讀者挖掘文本背后的深意。最后,作家談到了自己對文學評論的態度。這十二封信作為十二個章節出現,可以各自成文,而又存在內在聯系。某種程度上,這正應和了巴爾加斯·略薩所講的關于“連通管”的創作手段。“連通管”即是一種“發生在不同時間、空間和現實層面的兩個或者更多的故事情節,按照敘述者的決定統一在一個敘事整體中,目的是讓這樣的交叉或者混合限制著不同情節的發展,給每個情節不斷補充意義、氣氛、象征性等等,從而會與分開敘述的方式大不相同”。巴爾加斯·略薩以一個前輩引領一個立志成為小說家的青年人的方式,從文學抱負的初衷談起,沿著小說創作實踐的途徑,依次探討了小說家的寫作目的、風格、敘事的三個視角和講述手段。然而,正如巴爾加斯·略薩給讀者的提示,想要讓他所說的“連通管”正常運轉起來,僅有簡單排列是遠遠不行的。以這部《中國套盒》為例,若僅僅把這十二個章節作為并列關系來看待,是無法完全體會作者的良苦用心的。事實上,這些章節彼此之間有著嚴密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本身就與作家所探索的寫作初衷和創作實踐互相印證,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前提下,探討作者創作手法和寫作意圖的關系就顯得很有意義。
巴爾加斯·略薩這部作品的另一個譯本叫作《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以作家寫給一位青年小說家的信為管道,連通起文學創作初衷、創作實踐的路徑、寫作目的、敘事風格和方式等模塊,可見信件很好地承擔了作家與志同道合之人暢談文學創作的“連通管”。在他看來,去寫作對于一位作家來說不單是工作或者營生,更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全身心投入寫作或者說將寫作的行為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絲毫不考慮作品是否能產生一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效果,這正是作家對寫作保持真誠的重要表現。至此,又產生了新的疑問:這個通信的行為是否真的存在?這個青年小說家確有其人嗎?他到底是誰?這樣的問題反倒顯得無足輕重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不吝提攜后輩的作家與一位青年文學愛好者展開深入探討,集中系統地闡釋了作家自己的創作理念。這位青年可以是千千萬萬熱愛文學并立志為之獻身的青年的代表或者縮影,亦是巴爾加斯·略薩本人。即使這位通信的對象及通信的過程完全是虛構的,也絲毫不影響作家本人的表達。因為故事的人物、情節、敘事方式都是為了實現作家的表達目的服務的,即與讀到這個作品的每一位讀者交流他關于小說創作的想法。
隱匿在文學文本之中的任何細節都不容忽視,是理解作者真實寫作意圖的重要線索。在傳播學視角下,大部分情況下的傳播行為要依靠一種相對程式化的模式,即傳播者主動通過某種消息的傳遞影響受傳者。表面上看起來這本《中國套盒》是在與讀者交流寫作的技巧,實際上作家虛構了和他通信的青年小說家,巧妙地以給小說家寫信的形式闡述自己的觀點,表達自己的寫作意圖。他“清醒的意愿”具體表現在不僅為自己的“隱形”對話者塑造了形象,同時機警地將讀者同那位青年一起定位成不具備系統理論知識卻有決心為文學現身的有為青年,由自己充當向導,帶領讀者一步步探尋文本的內在肌理,甚至親臨創作實踐的現場。作品內容和表現形式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現象往往是作家自己人為造成的結果,而且通常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讀故事的內部邏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本講述寫作技巧與創作方法的著作也可以被看作一部小說。優質的評論文章已經可以脫離被評論對象,被單獨作為全新的創作來看待,其內在的價值絲毫不亞于優秀的小說或者長詩。如此看來,《中國套盒》的十二個章節正像一個疊加一個的套娃,各自成篇又互相成全。
巴爾加斯·略薩對于“中國套盒”的使用是這樣闡釋的:“如同在一組中國套盒或者俄羅斯套娃里那樣,每個故事里又包括著另一個故事,后者從屬于前者,一級、二級、三級,一級級地排下去。用這種方法,通過這些中國套盒,所有的故事連結在一個系統里,整個作品由于各部分的相加而得到充實,而每個局部——單獨的故事也由于它從屬于別的故事(或者從別的故事派生出來)而得到充實(至少受到影響)。”這種故事套故事的方法在大量古典的、現代的經典小說中并不罕見,通過文本比較不難發現,《一千零一夜》中“中國套盒”的使用很常見卻略顯機械,相較之下,《堂吉訶德》對“中國套盒”的使用顯然要隱晦復雜得多。巴爾加斯·略薩將《堂吉訶德》的結果解構成四個層面,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讀者對作品的鑒賞會受到本人的閱歷、知識結構、閱讀習慣等因素制約,由此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面貌。如前所述,不妨把《中國套盒》當作一部小說文本來看待,作家虛構了擁有豐富小說寫作和文學批評經驗的資深作家形象和有文學創作熱情的青年小說家形象,讓二人以書信方式交流,在交流過程中滲透了作家關于文學創作的一些思考。這一寫作手法應和了“中國套盒”的敘述方式,可以說作家正是以“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作為最外層的大套盒,整部作品的十二個章節就是其中的十二個小套盒,層層相套,環環相連,緊密依存。
二、敘述者與聆聽者
當然,巴爾加斯·略薩在有限的文本之內給讀者的啟示不局限于文學創作技巧這一個盒子,而是轉向了更為廣闊的視野——敘述者與聆聽者的角色定位與轉換。作家作為職業傳播者的一個代表群體,出于各種考慮,會有選擇地采集、篩選、甄別、加工、制作信息用以傳播。事實上,這就是每一個信息傳播者都經歷過的“自我傳播”過程,有時表現為沉思、自省、推理、判斷等。作家是作為敘述者和傳播者出現的,是整個傳播活動的主動發起者。同時,他還有一個身份——接受者。傳播者承擔著信息傳播的功用,也作為一個接受者提供信息反饋,完成傳播效果的實現。
在實際的信息傳播過程中,傳播者與接受者的角色往往是時時發生轉換的,在以文本為媒介的信息傳播過程中,作為敘述者的作者和作為聆聽者的讀者也可以隨時進行角色轉換。作家想要通過適當的敘述方式表達的寫作意圖,從某些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物質資源,能夠被傳播者和受傳者共同享有并且加以再創造。將《中國套盒》作為小說文本或是書信散文來閱讀,讀者將得到不同的信息傳播通道,多角度去理解、審視文本,捕捉文本信息,對于讀者全面理解作者寫作意圖無疑是更有效的途徑。在此,他以海明威為例,探討了在創作中如何熟練運用“敘述者的沉默”這一敘事技巧。海明威一向注重敘事簡潔,尤其擅長運用省略簡化的敘述和隱藏的材料,引導讀者從不同角度觀察復雜的故事整體,主動投身故事情節的加工。在《中國套盒》的閱讀中,讀者不僅能夠學習作家的創作手法,也可窺探到優秀文本的欣賞途徑。
三、結語
卒章顯志,作品最后,作家以誠摯的忠告懇請讀者朋友在閱讀和寫作過程中忘掉那些關于小說形式的闡述,杜絕在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前提下動手寫作長篇小說的念頭。作家以這樣的忠告結束全文,目的正是在于保護寫作過程中那無法言說的核心秘密,這并非作者故弄玄虛的危言聳聽之詞。這種寫作的核心秘密往往不是紙張上的筆跡,也不是暗自思忖時的自言自語,它只能是一種若隱若現的“隱語”。這樣懇切的忠告意在啟示讀者,技巧也好,章法也罷,回歸到寫作本身,應該是自覺自愿獻身其中,而閱讀經驗則是感性認知與理性過濾的結合與升華。正如巴爾加斯·略薩所說,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往往致力于模糊虛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甚至刻意混淆虛構與現實兩個世界,只為了給讀者營造一個相信敘述者“謊言”的真空時空。在這個時空里,只有虛構和幻想才是對現實最堅實、可靠的描寫。如此方可對作者的寫作意圖有較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言有盡而意無窮,巴爾加斯·略薩和他的《中國套盒》帶給讀者的啟示遠不止此。
(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作者簡介:郭斐(1988—),女,陜西安康人,碩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及外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