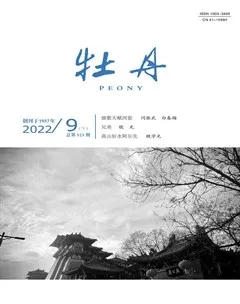“秘密狂想劇”的中斷與延續
長期以來,菲茨杰拉德的著名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被普遍地解讀為對“美國夢”傳奇幻滅與破碎的展現。而需要思考的是,在物質、金錢、都市的書寫之外,“美國夢”的幻景性質是如何被指涉的?小說第九章的一段話提供了啟示性的思路:“‘杰伊·蓋茨比’已經像玻璃一樣在湯姆的鐵硬的惡意上碰得粉碎,那出漫長的秘密狂想劇(extravaganza)也演完了。”“杰伊·蓋茨比”之于“杰姆斯·蓋茲”只是一重虛擬的角色,他與黛西的浪漫愛情故事只是被建構的一場戲。作者在此處所使用的“秘密狂想劇”一詞關聯著場景性、表演性、非現實性、狂想性等貫穿小說的核心要素,因而這一概念或許不但適用于形容蓋茨比的愛情悲劇,而且能夠成為一個具有統攝性的文本關竅。
一、“舞臺”的生成:小說的敘事場景與空間
羅納德·伯曼(Ronald Berman)曾指出,《了不起的蓋茨比》通過引入大量現代消費性景觀并模仿電影鏡頭的閃現感形成了“影像敘事”的特征。小說在敘事行進中著力于視聽感官層面的渲染,強化色彩與聲相,讀者由此得以通過閱讀想象力召喚出鮮活的文本場景。全書最勾魂攝魄的空間性景觀當屬在蓋茨比別墅里舉行的聲勢浩蕩的宴會:香檳、水果、樂隊、木筏、游艇……無數被邀請或沒被邀請的人們在蓋茨比的花園里縱情聲色,從尼克在時刻表上記錄的賓客名字來看,參加者的身份與地位參差不齊。由此可以引入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進行分析:蓋茨比的花園成為“狂歡的廣場”,在此上演著一場泯除了差異的普遍性儀式與慶典。
這一全民性的狂歡中沒有觀眾,眾人皆為演員,表演暫時成為生活本身。巴赫金所強調的源自民間詼諧文化的狂歡具有“全民性”和“儀式性”兩大外在特征與“平等性”和“顛覆性”兩大內在屬性,但在蓋茨比花園里所進行的盛宴顯然溢出了巴赫金的經典框架而呈現為“變體的狂歡”:大多數來到蓋茨比花園的人都是為了證明自己融入了這一上流社會的群體,他們只要“玩得開心就好”,不必追尋任何意義或價值。他們在完成自身“上流”形象構建的同時,充當了蓋茨比的“群演”,完成了給蓋茨比“加冕”的儀式。由此,花園狂歡的“儀式性”與“表演性”被凸顯,“平等”與“顛覆”的意味卻顯得寡淡——真正的“底層”人物,如車行里的威爾遜先生并沒有資格進入這場“盛宴”。
從“花園宴會”這一核心場景向外延伸,可以發現《了不起的蓋茨比》在敘事空間方面精心的營構,不同的地理空間常常被賦予不同的象征意義,仿佛是有意建構的“舞臺”。東卵和西卵構成首重對立,東西卵和紐約以及作為聯通的“灰谷”又構成另一重區隔,更宏觀的空間區隔則是中西部和東部的對立,而現代與傳統、發達與落后、消費狂歡與庸常無聊等相對的形容被幾近標簽化地貼在了不同的空間上。小說中的人物進入不同的場域時總是緊隨著新的故事發生,由此情節得以展開,人物形象縱深化,“場景”成為“舞臺”,文中無處不在的“凝視”加強了這一暗示:灰燼谷上空T.J.埃克爾堡大夫的眼睛長久“陰郁地俯視著這片陰沉沉的灰堆”,湯姆紐約的公寓中“一位胖老太太笑瞇瞇地俯視著屋子”,蓋茨比豪宅中象征其“被人遺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丹·科迪的相片從墻上向下面凝視,人物的活動總是被置于某種觀照之中,在其所處的場域中常常有一個超拔其上的嚴峻目光在將其審視。
此外,《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精妙之處還在于往往呈現出空間的區隔和對立之間的相互轉化,譬如曾經將“東卵”視作“彼岸”與夢想之地的尼克最終選擇的是對“中西卵”的回歸,而在東卵過著奢靡生活的湯姆一家也不得不回到中西部當一個“舊貴族”——意義和價值被驚人地扭轉與倒置,而穿梭于兩岸的人群也就在隱喻的意義上不斷往返于幻夢與理想、日常與現實之中。
二、“劇中人”:附著于人物的“表演性”
倘若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以高度純熟的場景描寫與指涉豐富的空間營構搭建起“狂想劇”的“舞臺”,那么小說中的人物則自然而然地成為“劇中人”。事實上,某種“表演”感在小說中彌散開來,幾乎成為小說中人物的日常生存狀態:“人們扮演種種角色,有時甚至在心中似乎還有腳本。”細讀文本,讀者可以見到湯姆·布坎南的表演:湯姆在文中是強硬、粗野的大男子主義形象,但卻時刻將“文明”“種族”“制度”等語詞掛在嘴邊,小說借尼克之口對其進行了幾乎露骨的反諷。讀者也能發現茉特爾·威爾遜太太的表演:從灰谷到紐約,她搖身一變,活力變成“傲慢”,“好像在煙霧彌漫的空氣中坐在一個吱吱喳喳的木軸上不停地轉動”——對物質的崇拜幾乎使她自身成為一個物件。
自然,故事的核心男女主人公蓋茨比與黛西是最成功的“演員”,作者似乎有意在二人身上注入了“表演”的兩種不同維度。黛西的表演是扭曲、變形與夸張。她的出場就極具象征意味:她和喬丹·貝克“活像浮在一個停泊在地面的大氣球上。她們倆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風中飄蕩,好像她們乘氣球繞著房子飛了一圈剛被風吹回來似的”,一位極具浮雕感的天生女主角登場了——她在蓋茨比花園中對月光下女演員場景的偏愛也流露出她對某種高貴、矜持“姿態”的向往與模仿。文本中多處細節表現出她的矯揉造作:總是有著“并不深切的憂傷”,說話時故意喃喃低語、高低起伏以引誘人側耳傾聽,抓住一切機會來表明她“屬于一個上流社會的秘密團體中的一分子”等。蓋茨比的表演則意味著遮蔽、掩蓋與隱藏。他長久地形塑自己的經歷,試圖撇開自己窮苦的出身,成就一位完美的富翁形象:
我猜,就在當時他也早已把這個名字想好了。他的父母是碌碌無為的莊稼人——他的想象力根本從來沒有真正承認他們是自己的父母。實際上長島西卵的杰伊·蓋茨比來自他對自己的柏拉圖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兒子,——這個稱號,如果有什么意義的話,就是字面的意思——因此他必須為他的天父效命,獻身于一種博大、庸俗、華而不實的美。因此他虛構的恰恰是一個十七歲的小青年很可能會虛構的那種杰伊·蓋茨比,而他始終不渝地忠于這個理想形象。
當“表演”成為人物一種生存的底色,真誠顯然就會在人際關系中缺位。“獨角戲”發展為“對手戲”的結果是小說情節中充斥了遮掩、瞞騙與不切實際的謠言:茉特爾去紐約偷情而使威爾遜以為她只是去看望妹妹;湯姆欺騙茉特爾不能離婚的原因是黛西是天主教徒;有關蓋茨比身世的謠言花樣百出,其在向尼克講述自身經歷時也常常半真半假;湯姆和黛西聯合用謊言置蓋茨比于死地……謊言的構設與撞破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也有著主旨上的暗示。有趣的是,這些瞞騙往往是不牢固的、有裂隙的——厚顏無恥的湯姆的私情幾乎人盡皆知,麻木愚鈍的威爾遜也隱隱意識到妻子的不忠,蓋茨比的身世總能被湯姆或多或少地打探到,尼克能夠推斷出造成蓋茨比厄運的幕后兇手——人物相互之間的窺視成為可能,小說中無處不在的花邊新聞記者即為這種“窺視”塑成的肉身。一個富有暗示意味的情節是茉特爾將貝克錯認為黛西,這預示著透過謊言與謊言之間縫隙所錯綜窺探出的結果極有可能是錯位的,而湯姆就是通過誘導、放大威爾遜錯位的怒火完成了挑撥。
三、“失敗的演員”:蓋茨比的悲劇
然而,蓋茨比在小說中顯然是一個“動蕩”的主體,那種純真的浪漫與理想主義使得他無法在自己捏造的人設中酣然沉睡。蓋茨比與黛西的關系挑明后,他不斷地展現出與一位億萬富翁身份明顯不符的天真與敏感,“蓋茲”的浪漫幻想火熱燃燒,不斷溢出“蓋茨比”的角色。對他來說,金錢只是夢想與浪漫的附屬品與實現途徑,財富是他建構自身的資本,其本身卻并非可以耽溺的幸福——這讓讀者想到他在其余人沉醉于花園狂歡時所保持的疏離姿態。蓋茨比被視作“美國夢”化身的緣由庶幾在此——“財富被蓋茨比用來抒情”,金錢在他眼中并非完全淫惡的象征,而是與夢想相關聯的純凈之物。在蓋茨比巨大的豪宅中,他的臥室保持著簡樸。他為了黛西而遣散賓客仆人,“由于黛西看了不贊成,這座大酒店就像紙牌搭的一樣整個坍掉了”。物質的價值全憑黛西的好惡而生成:“他一刻不停地看著黛西,因此我想他是在把房子里的每一件東西都按照那雙他所鐘愛的眼睛里的反應重新估價。”
當人人都將表演、欺瞞、窺視內化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時,蓋茨比卻逐漸卸下偽裝、表露真心。過于天真的他堅定認為可以“重溫舊夢”,他要求純粹的愛情,因而顯得過于沖動:他迫使黛西對湯姆說從來沒有愛過他,希望攜黛西一起沖破現狀。事實上,對于黛西與湯姆等人來說,金錢與利益才是終極目的。黛西并非冷酷無情、她也曾付出真心,但她顯然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夠穩定擁有富太太的“角色”——她能在一場痛徹心扉的爛醉后平靜地與湯姆踏入婚姻的殿堂。蓋茨比所要求的徹底撕破臉皮的做法沖破了人與人相互表演、逢場作戲所達成的微妙平衡,驚擾他人好夢的他注定要被驅逐出這一世界。
車禍發生后,蓋茨比在窗外幾近神圣的守望與屋內的“陰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浪漫的幻夢邏輯與冷酷的現實邏輯在此打了照面,而小說呈現出的則是后者對前者的狂野吞噬。蓋茨比可以不顧一切奔向內心的浪漫與塵世的幸福,但當現實的生活本身變成一場盛大的表演,則意味著并沒有可供前往的許諾之地,幼稚天真的蓋茨比只能以死亡的姿態終結其無限的幻夢。沃爾夫山姆“生前仗義,死后少管閑事”的“處世哲學”似乎也在宣告:一位落幕者自然是無人問津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的“終結者”威爾遜先生正是一位自始至終被排斥于這場上流社會“盛大狂歡”的“冗余物”,作者安排他來終結蓋茨比的生命并與其“同歸于盡”,在此顯得意味深長。
四、“傳奇”的失落
通過上文的分析,似乎可以勾勒出《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書中具有總括性的一種象征圖式:“人”不斷幻夢和回憶的方式進入被地理空間所標記的“舞臺”而成為“人物”,上演各自的“秘密狂想劇”,飽嘗悲歡離合,糾纏愛恨情仇。而從小說整體的敘事框架來看,蓋茨比的故事是“被講述”甚至是“被追述”的,它已然消失、只能在敘述中留存,由此又通向了小說更深一層的“幻滅感”:第一人稱敘述者尼克·卡羅威不斷使用“那個夏天”的時間標記,正是在以回溯性的視野將蓋茨比的個人際遇升華為一種已逝的時代性“傳奇”。
主人公蓋茨比被尼克賦予“了不起”(great)的主觀價值判斷,而整部小說也可以視作現時態的尼克在回憶中通過建構“超異的空間,超常的人物,超凡的舉動”來譜寫一曲黃金般爵士時代的傳奇。關聯到作家論層面,菲茨杰拉德對當時美國社會狀況的態度與情緒是復雜的,但他在蓋茨比這一人物身上至少寄寓了一種批判性向度:對純粹情感與誠摯真心的呼喚。蓋茨比幾近虔誠地向著大海伸手而顫抖擁抱的恰恰是人與人之間無處不在的附和逢迎、虛與委蛇和相互算計,被扭曲的“美國夢”不斷上演,奮力向前的姿態造成的結果可能僅僅是墮入過去。
馬里厄斯·比利(Marius Bewley)提請讀者注意:“但我們在感受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時所面臨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湯姆和黛西之類的人物會使美國變成什么樣子。”對于蓋茨比來說,他的戲份已經結束,但這場被物質與利益邏輯所支配的“狂想劇”絕不會因為他的落幕而收場。在高速突進的社會中,回眸的姿態與浪漫的幻想同樣通往虛冥之地,由此,以回溯性視角生成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小說本身也成為在反復講述中被不斷推遠的“文化神話”,成為時代洪流呼嘯中指向曾經黃金時代的一個蒼涼手勢。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