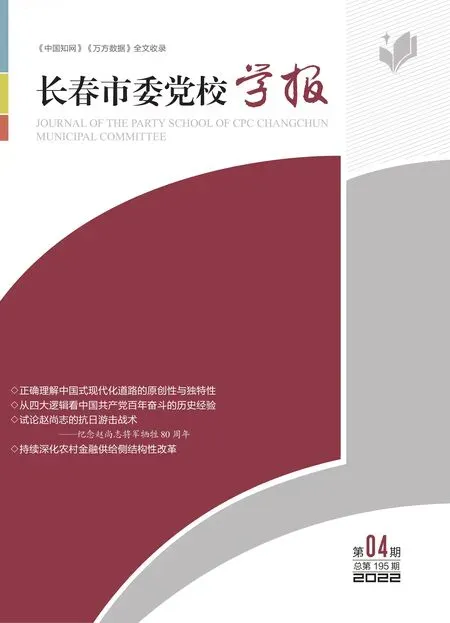青年網絡流行文化的社會心態考察與引導
——基于后現代話語理論視角
文/劉箴 劉倪
后現代話語理論通過對后現代思想叢林的巡視來證明話語理論的迫切性,主要代表人物是查爾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后現代話語理論認為,后現代是超現實的,青年群體為自身意義存在而搶占話語權形成的青年亞文化是一種后現代結構主義文化,這種后現代解構主義文化致力于消解、解構與顛覆傳統社會文化,期盼新文化逃離文化話語權力中心的控制,進而構建適合后現代的話語符號[1]。近年來,我國青年網絡流行文化以互聯網作為公共能量場,不同程度表現出了后現代思潮影響下的某些社會心態特征。對此,借助后現代話語理論的分析視角,考察當前我國青年網絡文化的社會心態,對更好引導青年網絡流行文化健康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一、青年網絡流行文化的社會心態考察
中國青年網絡流行文化的形態較為豐富,從搖滾樂、大話文藝、無厘頭電影、耽美文學到火星文及各種網絡流行語,與許多其他國家的青年亞文化一樣,雖然居于邊緣,但具有通俗化、多元化以及反權威的顛覆性,積極消解傳統符號系統的意義,形成具有自身風格標志的亞文化[2]。當前,青年網絡流行文化的主要類型:二次元文化,以“cosplay”“御宅族”“腐女”等為主要表現;粉絲文化,粉絲團體以“idol”為核心自發形成,是借助媒介手段進行創造性生產的群體,有著自身的文化空間;網絡流行語是流行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網絡流行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表情包文化是青年網絡群體日常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魔性的動圖配以犀利、戲謔的文字,給人以強大視覺沖擊;喪文化在網絡上表達或表現出自己生活中的沮喪,形成一種文化趨勢;夸噴群文化以微信或QQ群等為平臺進行“夸贊”或“諷刺”,風靡各大高校,電商服務平臺甚至推出付費夸人服務;網絡惡搞文化利用網絡對嚴肅主題、經典、權威以及某些社會現實加以解構,并建構出自身的娛樂活動方式[3]。我國青年網絡流行文化從總體上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涉及眾多領域,相對于主流文化的發展仍然處于邊緣化地位,但其內涵都具有“娛樂至上”的傾向。
文化對行為具有較強的形塑力,網絡流行文化可能存在某種獨特的感受結構,能激發或煽動網民們的集體感受和情緒共振,反映社會心態和情緒氛圍[4]。社會心態是人們對自身利益關切的自然流露和表達,它是社會現實的折射,是反映個體、個體與社會、個體與國家關系的一扇窗口[5]。網絡流行文化雖然遵循齊美爾時尚流變的邏輯,但所折射出來的社會心態卻具有相對穩定性。
網絡流行文化反映了青年群體的“張揚心態”“從眾心理”。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論及后現代主義對語言規范的破除傾向時說道:“每個群體都傾向于使用自己古怪的秘密語言,最后使每個人變成一種與他人隔絕的語言孤島。”青年群體崇尚個性,對新生事物有著獵奇心理。對亞文化的追求本質上就是青年群體“反叛”主流文化的“張揚心態”表現,而其流行更多的是“從眾心理”影響的群體效應。例如,部分青年群體對二次元文化的崇尚,不僅因為這種文化形式本身帶來視覺沖擊、獵奇感,而且更是因為它創造并催生出一個獨立又完整的世界,讓人沉浸其中,從知識儲備、思維模式、生活習慣都對青年群體產生了重要影響,與外界形成“次元壁”,造成“同代代溝”。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則是受群體影響,即使內心并不贊同,但是為了避免自己落后于“時尚”潮流,行為傾向于群體,這種從眾現象的出現在當今網絡信息爆炸的時代會更加助長這種信息的傳播速度[6]。網絡流行語的產生機制或是出于“獵奇心理”,但其傳播機制離不開“從眾心理”。
網絡流行語反映了青年群體的“戲謔心態”。網絡流行語作為網絡流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話語形式是網絡流行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更能折射出典型的社會心態。因此,以網絡流行語作為網絡流行文化研究的重要對象,更能準確把握青年群體在網絡流行文化中的社會心態。從網絡流行語來看,“戲謔心態”是青年群體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戲謔心態”主要體現為流行語的構詞結構和修辭方法(隱喻、戲仿、夸張、反諷等),例如:中英文摻雜的表述方式是當今青年在話語表達中的慣用方式,如用“我今天好high啊”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激動、愉悅和滿足;“我太南了”,以麻將中“南風”的“南”字代替“難”,體現了青年群體希望釋放壓力的心理;“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出自2019年暑期熱播的綜藝節目《中餐廳》第三季的嘉賓黃曉明之口,將不顧及其他人的意見的盲目自信及獨斷專行表現得淋漓盡致,反映了青年群體對霸道、蠻橫人格的嘲笑和反感;表現“喪文化”的網絡流行語在部分青年群體中的流行傳播,“小確喪”“每天都在用六位數的密碼保護著兩位數的存款”“條條大路通羅馬,而有些人就生在羅馬”等等,反映了部分青年對于自身處境的戲謔與無奈。
此外,一些網絡流行文化還雜糅著一些青年群體非理智的“泄憤心態”。“泄憤心態”主要體現為網民們對各種社會現象和不良事件的不滿所表現出來的消極情緒。這些消極情緒的渲染和積累會造成情緒暴力。“泄憤心態”雖然表現在對不良事件的譴責,但圍繞熱點和爭議事件的各種語言暴力現象頻頻出現在網絡空間。一些網民大放厥詞,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一些自媒體平臺紛紛“玩梗”,進行語言模仿或情景改造,對當事人往往造成傷害,也有可能誤導事件本身的發展。在網絡這個匿名的空間里,比對話更易形成的是對抗,輿論有時是壓倒性的[7]。這種“泄憤”情緒積累容易造成網絡言語暴力,輿論往往一邊倒,導致網絡暴力的產生。
二、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的后現代話語分析
青年群體由“戲謔心態”和“泄憤心態”所表現出來的內在焦慮,主要根源還是在于作為網絡主體的青年們所遭遇的身份危機和意義危機,這與后現代狀況是分不開的。后現代并不是歷史時代,而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或一種思潮觀點,影響青年群體并得以流行。青年群體是天然有活力的,有創新精神的,同時也是“反叛”的。青年網絡流行文化是青年群體對主流文化“反叛”的產物,也是青年群體為證明自身存在意義而搶占話語權的表現。從后現代狀況來看,青年網絡流行文化現象就是青年群體憑借公共網絡空間的平等性,尋求獨特而張揚個性,在亞文化的碎片中建立起某種差異化的他性特征,而這種他性的擴散也意味著社會碎片化的延續。正是互聯網的匿名性和平等性的特點,才使得青年群體傾向于在網絡空間進行互動,青年網絡亞文化也能在網絡空間中找到“忠實粉絲”——網絡流行文化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互聯網的匿名性在于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是以虛擬身份進行的。福克斯和米勒提出“虛擬社區”的概念,并稱其為“連續化團體”,是原子化個體的組合,這些原子化的個體并沒有真實社會的那種團結性,在那里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如以公共事件為焦點的豆瓣小組或微博博文等,這些都在無形中創造了一個個“虛擬社區”。青年網絡流行文化也能創造一種“虛擬社區”,例如粉絲文化,她們以“idol”為虛擬紐帶,由自發的原子化個體“團結”在一起。互聯網的平等性是建立在匿名性的基礎之上,允許有不同以往的聲音出現。互聯網有大眾化的趨勢,并沒有設置任何門檻。相對于傳統廣播媒體般的單向度獨白性交流,青年網民更喜歡在網絡平臺上發言互動,也更樂意去傾聽和接受與之相異的聲音,當然這是要冒著語言暴力的風險的。
青年網絡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網絡青年的社會情緒得到釋放和緩解,但也可能是消極情緒的累積從而形成語言暴力,造成巨大輿論壓力,甚至沖擊主流文化。青年網絡亞文化在釋放青年群體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價值危機。在后現代思潮的沖擊下,當前的中國青年亞文化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后現代主義色彩,時間被碎化為片段,語言破碎化,交往格局虛擬化,虛擬世界、小眾文化下的自我麻痹,娛樂消費主義導致的審美虛無等等。青年群體或許在這個亞文化世界取得了話語權,身份地位得到了承認,但他們現實社會中的處境和焦慮依然存在。
三、青年網絡流行文化的引導策略
通過網絡場域的意義建構和公共討論,創造清朗的網絡生態環境,引導亞文化走向正軌是我們亟需解決的時代課題。
●構建網絡話語自律機制,增強話語正當性
參與優于非參與。青年群體對信息十分敏感,通過微信微博等平臺在網絡空間自由交流信息,成為一股不可或缺的公共輿論監督力量。但是網絡輿論表達也存在著網絡謠言肆虐、網絡暴力蔓延等“病癥”[8]。依靠“人肉”搜索,或者“鍵盤俠”式的謾罵表達在網絡上筑起流量墻以尋求自我存在感,這不但會導致監督行為異化,激化矛盾,扭曲事實,甚至還會觸犯法律。因此,我們不僅需要話語,更需要正當性的話語。建立包括青年群體在內的網絡話語自律機制,既需要網絡表達個體的主觀性約束,也需要網絡監管、網絡平臺、網絡用戶等相關主體和機構建立健全價值觀引導機制。一方面要引導青年網民群體參與并建立形成網絡自律公約。青年網民要保證自身言論的真實性,做到“不信謠、不造謠、不傳謠”。有關嚴肅問題和公共難題方面的話語,需要對話者有對真誠地渴望[9]。當公共話語的場所被不真實的訴求和言論充斥時,我們探尋事物的真相將會變得越發困難。另一方面,要加強網絡輿論話題的價值引領,形成有效的價值引領機制。有實質意義貢獻的對話需要價值引領,充分發揮有影響力的公共人物和主流媒體的作用,加大對利用視覺沖擊和情緒共振而歪曲報道等網絡亂象的治理力度。
●構建清朗的公共能量場,凈化網絡生態環境
公共能量場可以打破獨白式的對話,激發人們積極主動、熱情參與的精神狀態,開展“一些人的對話”,是一個平等開放的多元化的場所。如果公共網絡空間被網絡謠言、網絡暴力所充斥和主導,就破壞了公共網絡空間作為公共能量場的初衷,形成破壞性的網絡輿論氛圍和網絡安全風險。對此,政府在構建清朗的網絡文化交流平臺時,應當積極發揮正向引導功能,盡量消除負面影響,既要保證公共網絡空間的文化交流自由,又要嚴格優秀文化的標準,保證公共網絡能量場的正能量價值主導。同時,要加強網絡環境法制規范化建設,加大對網絡謠言、網絡暴力等互聯網亂象的治理力度,緊跟網絡技術和網絡生態變化步伐,推進網絡法制建設的步伐。
●維持適度的對抗緊張關系,加強主亞文化的交流
“當信息的交流方式是獨白式的而不會公共或對話性的交流時,對抗性的緊張關系就消失了”[10],福克斯和米勒定義的“對抗緊張關系”并不是負面的,而是強調兩者之間的對話和表達的機會。青年網絡流行文化作為一種網絡亞文化,只有適度“對抗”的存在,才能實現主流文化和亞文化的互動交融。一方面,主流文化應當對青年網絡亞文化進行積極的引導,形成與青年群體的積極互動并保證價值觀引導的有效性、準確性。媒體及文化工作者應該避免頤指氣使的傳播風格,辯證地認識和運用青年群體熟悉的語言模式,讓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更為立體化、可視化、符號化和故事化,讓主流意識形態離青年群體更親近,讓青年群體愿意參與到主流文化的建設中來[9]。另一方面,青年群體在保持適度“個性”“出挑”的前提下,應當喚醒自身的文化使命,積極傳播主流文化,不斷從主流文化中汲取創意文化的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