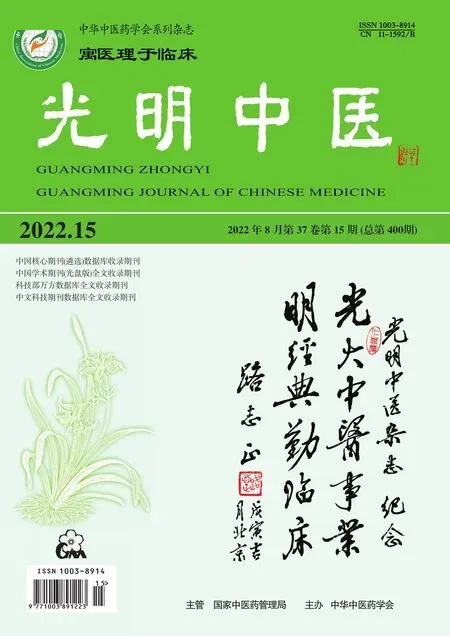劉艷驕主任醫師診治老年慢性失眠學術思想初探
許彥臣 劉艷驕
劉艷驕從事中醫診治睡眠障礙的臨床與研究工作近30年,編寫相關書籍10余部,發表各類專題論文達百篇。劉老及其睡眠研究團隊分別對老人、女性、小兒等特殊群體,高寒高原地區、地方中藥(京、冀、遼、吉、黑、內蒙、豫、魯、浙、云、貴、川等)、民族醫藥(蒙、藏、回、維吾爾)等相關中醫、民族醫睡眠文獻及臨床研究進行系統整理、歸納并做評述研究,見解獨到,論點不落窠臼。
失眠是中老年人常見的睡眠障礙。將劉老診治老年失眠(中醫稱不寐)的學術思想及臨床經驗初步探索和總結如下。
1 診斷標準
1.1 中醫診斷標準目前中醫尚無老年失眠的診斷標準,建議參考《失眠癥中醫臨床實踐指南(WHO/WPO)》[1]及中華中醫藥學會頒布的《不寐中醫診療方案》:入睡難,或睡而易醒、醒后不能再入睡,重則徹夜難眠,連續4周以上;常伴多夢、心煩易怒、頭昏、頭痛、心悸健忘、神疲乏力等癥狀[1,2]。
1.2 現代醫學診斷標準采用《國際睡眠障礙分類》(ICSD-3)標準關于成人失眠的診斷標準[2,3]:①主訴:入睡困難,或難以維持睡眠,或睡眠質量差;②此類睡眠紊亂至少每周發生3次并持續1個月以上;③日夜專注于失眠,過分擔心失眠的后果;④對睡眠質量的不滿意引起明顯苦惱或影響社會及職業功能。
專家共識的成人失眠癥診斷標準也可作為老年失眠癥的診斷標準,使老年不寐的中醫診治流程與國際同步,這有利于開展中醫循證醫學經驗總結及臨床療效評價等研究。
2 病因病機
老年失眠有生理性衰老的特征因素,也有社會因素的影響;老年人多伴隨慢性病的增多及服用多種藥物控制慢病,可能會對睡眠產生較大影響,使其睡眠障礙的發病率不斷增加,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4]。中醫對老年不寐病機認識最早源于《黃帝內經》和《難經》。《黃帝內經》:“老壯不同氣,陰陽異位……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臟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5]。
2.1 老年不寐與體質相關老年不寐與臟腑氣血衰少、衛氣耗傷有關,營衛氣血虧虛為本[6]。《難經正義》“老人血氣衰,肌肉干枯,血氣之道澀滯,故晝不精明,夜多不寐……是老人之寤而不寐,少壯之寐而不寤,系乎榮衛氣血之有余不足”[7]。表明老人不寐與榮衛氣血的不足有關外,還與其運行正常與否有關;由于衰老造成的氣血虧虛致營衛運行之力不足[4-6]。《靈樞·營衛生會》: “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行于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張志聰認為“氣至陽則臥起而目張,至陰則休止而目暝”。如果影響營衛之氣血的運行,使其不能正常入于陰則會不寐,反之,使其不能順利出于陽則引起多寐[4-6]。隨年齡增長,老人所需的睡眠時間漸少,白晝小睡的次數可能增加,常見白晝小寐、夜間不寐等睡眠顛倒現象[8]。由于老人的特殊體質類型引起的不寐,劉老強調要辨體論治。
2.2 老年不寐與藥物相關劉老非常重視老年病對睡眠的影響。老年人患原發性高血壓、糖尿病者較多,合并慢性失眠的比率也較高[9];有的降壓藥會導致失眠、嗜睡或/和夢魘。此外,一些降脂藥也可引起睡眠障礙。劉老重視藥物對人體整體的影響,如因藥毒內陷所致不寐,在治療中要兼顧他病[8];由安定或其他物質依賴引起的不寐,治要戒“毒”及解“毒”。
2.3 老年不寐與慢性病相關老年慢性病與不寐互相影響,呼吸系統如慢阻肺、哮喘、肺心病等引起夜間咳、喘、悶等;循環系統如原發性高血壓、冠心病、心律失常、慢性心衰等;消化系如炎癥、潰瘍、腫瘤等;神經系統如腦血管意外、偏頭痛、癲癇、眩暈、神經肌肉疾病等;精神障礙如焦慮、抑郁、精神分裂癥等;內分泌如甲狀腺和垂體病變、糖尿病;中老年特有慢病如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此外,有些治療急慢性病的常用藥也可引起睡眠障礙,如抗菌素(包括抗結核藥)、降壓藥、降脂藥、麻醉藥、利尿藥、抗抑郁、抗精神病、抗腫瘤、激素類等[8]。故診治不寐要考慮更多復雜的影響因素。
3 老年不寐的辨證論治
老人不寐多與情志異常、氣機失調、臟腑虛損、慢病或藥物影響相關,總體病機為陰不入陽、陰陽失交;病因多為情志、勞倦、久病傷及臟腑,精血內耗,彼此影響,日久而成;臟腑陰陽、營衛氣血不足為本,夾雜氣滯、血瘀、痰濁、氣機失調為標,多伴慢性病及安定依賴,病機復雜,治療頗為棘手[4]。劉老強調可先辨別中醫體質類型,常見9種體質中氣郁、氣虛、瘀血、陰虛、濕熱、痰濕、特稟多見睡眠障礙[10];其次要明確藥物耐受程度,在WHO/WPO失眠癥中醫辨證9種分型[1]上適當精簡證候類型,簡明扼要,以便應用時得心應手;經辨病、辨體、辨證之后劉老總結老年不寐的中醫證型多見肝郁氣滯、氣滯血瘀、氣血不足、痰熱擾心、陰虛熱擾。
3.1 肝郁氣滯 肝火擾心針對老人不寐的病機特點,劉老強調辨證多從肝、腎、脾著手,治以疏肝理氣、平肝潛陽、補腎健脾為主,選基礎方促眠方加減:柴胡、白芍、遠志、石菖蒲、生龍骨、生牡蠣、生曬參、茯苓或茯神、首烏藤、甘草[11]。該方源于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和清代陳士鐸的舒魂湯及《醫學心悟》的安神定志丸加減化裁。如伴夢多,考慮肝火擾心,加燈芯草、蓮子心等;如合并肝腎陰虛,加養陰安神的百合地黃湯、解郁安神的三花湯(白梅花、玫瑰花、合歡花)[12]。
3.2 氣滯血瘀 神不守舍由于情志失常、飲食起居不慎等因素的影響導致老人肝氣郁結日久,加上多種慢病纏身,久病多瘀,均可引起心神失養、神不守舍而不寐。劉老深得清代王清任活血化瘀治療疑難頑疾的深邃,治不寐多從郁和瘀著手,擅用癲狂夢醒湯加減治療老年慢病并不寐[13]。全方由柴胡、桃仁、赤芍、香附、姜半夏、大腹皮、陳皮、青皮、木通、桑白皮、紫蘇子、甘草12味中藥組成,共奏理氣開郁、化痰活血之功,可加化瘀安神之品,達到通達上下、醒腦安神等目的,是主治癲狂、不寐或并其他慢病的常用方,是治療氣郁痰結、瘀血內阻之名方。劉老擅用此方或血府逐瘀湯加減治老年不寐外,還用此類方治療抑郁、焦慮、更年期、癲癇、癡呆、高血壓病、糖尿病、心腦血管病、哮喘及慢阻肺等多種慢病。只要符合氣滯血瘀的基本病機,辨證準確,圓機活法,多可取效。這體現異病同治之理念[12,13]。
3.3 氣血不足 心神失養劉老認為老人常見臟腑陰陽氣血不足為本。中藥湯劑選歸脾湯合促眠方加減:黃芪、白術、人參、當歸、遠志、茯神、炒棗仁、木香、龍眼肉、柴胡、芍藥、遠志、石菖蒲、首烏藤、牡蠣、龍骨、甘草[14]。久病成瘀,對合并慢病的頑固不寐,遵朱良春國醫大師之法,加血肉有情之品,如阿膠、雞子黃、水蛭、土蟲、九香蟲、地龍等,以補益氣血的同時通絡安神[15]。
3.4 痰熱擾心 心神不寧劉老據《黃帝內經》膽為中正之官、主決斷,與肝相表里,性喜寧靜而惡煩擾等理論[5],認為久郁生火,虛火上擾則夜臥不安;肝木克脾土,則脾胃之土因木郁而不達,久則漸生痰濁,肝膽郁火生熱煉痰,擾動心神而致不寐[16]。明代張景岳《景岳全書·不寐》引:“痰火擾亂……火熾痰郁而致不眠者多”。指出不寐常見原因為痰火內擾;中醫認為“百病多由痰作祟”,氣滯多生痰涎,易壅塞經絡,經絡不通而變生諸癥。劉老認為不寐病位在心,與肝、膽、脾胃關系密切;“邪去則正安”,實證多從膽熱、痰熱、胃不和等處著手,治以燥濕化痰、清膽除煩[16],選加味溫膽湯以清膽祛怯,并心腎不交加交泰丸以交通心腎、引火下行;夢多加卷柏、燈芯草以安眠消夢[8,11];氣郁肝火者合促眠方佐梔子、牡丹皮、郁金以清肝膽之火。劉老用溫膽湯加減不但治不寐,還用于治嗜睡、鼾眠證、多夢、夜間周期性腿動等[16,17]。
劉老及睡眠研究團隊選用溫膽湯合四逆散聯合帕羅西丁治療焦慮障礙[18],中西藥結合使“肝膽之氣得升、胃氣得降”,通過調暢氣機來緩解焦慮及軀體化障礙。
3.5 陰虛熱擾 心腎不交劉老認為心主神,腎主志、藏精,神之所化,腎精充足能陰陽相交,寐寤正常。“心腎兩虛,神不守舍,則多夢紛紜,每至暮夜,溲溺且多”“心火居于上……而精輒自出,難交心腎”“腎水不足, 耳常虛鳴,寤難成寐;寤不成寐,頭目昏蒙,皆由真水不足,水不濟火”[19]。這是老人不寐及眩暈的病機之一。在中醫內科、睡眠門診臨床常見不寐和眩暈互相影響的情況。治療上劉老認為多見陰虛為本、氣郁為標,心腎不交、心神不寧。用促眠方合百合地黃湯、甘麥大棗湯;如伴盜汗、自汗、虛煩,用促眠方合酸棗仁湯、梔子豉湯[11]。
4 老年不寐的替代治療及睡眠養生
老人多伴有慢性病,每天服多種藥物,其中慢性失眠者大都有安眠藥依賴。這會增加安定與其他藥的相互作用引起不良反應的風險頻率,也會加重肝腎負擔,可能引起藥物在體內的蓄積。對于安眠藥依賴者可選替代治法[20]:首先強調醫患應了解安眠藥的分類、藥代動力學、適應證、禁忌證、不良反應、長期用藥的利弊、注意事項、常見誤區等,以免濫用和依賴[20,21];提倡結合中藥、針灸、推拿、心理治療,逐漸把安眠藥減量至停藥;同時選用抗組胺藥、維生素類等替代,并重視藥物、食物對睡眠的影響[20-22];做睡眠衛生健康教育指導也很重要,很多老人通過認知行為調整,逐漸減去安定也可坦然入睡;有關老人睡眠環境與心理調節、老人睡眠養生遵循《黃帝內經》等中醫指導,并參考現代醫學的研究成果[20];提出睡眠養生九大關鍵點:流通氣(不覆首)、選好床、用好枕、多按摩、暖好足、臥如弓、擇時睡、補足水、蓋好被[20]。
5 總結
劉艷驕主任醫師診治睡眠障礙經驗豐富。其分別對老人不寐的中醫病因、病機、臨床特征及辨證論治均有較詳細的歸納論述和拓展研究,對老年不寐的辨體論治、辨證論治與辨證論治,應用戒“毒”中藥對安眠藥物依賴的中醫替代治療及安眠藥減藥理論等均有創新突破,進一步完善了老年不寐的中醫診治方略,進一步發展了老年不寐的中醫辨治理論,進一步細化并補充了中醫睡眠醫學的理論體系。其學術思想的本質是以人為本、辨證論治、戒“毒”解“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