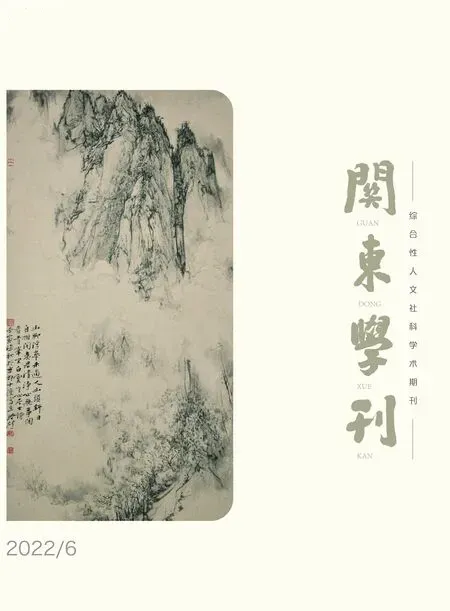智能媒體平臺的應用、倫理與規制:以重大突發事件為例
李明德 劉嬌楊
在新媒體時代,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依托的智能化媒體應運而生,以VR、AR、無人機為代表的傳媒新業態和新模式被不斷地孵化出來。智能媒體從結構上來看包括基礎層、技術層和應用層,從全球實踐看,智能技術已經滲透到媒體日常生產的全部環節,包括線索發現、內容采集、內容寫作、內容分發、效果反饋、內部協同、自動處理等。當前我國媒體融合向縱深化發展,智能化是媒體融合的重要驅動力。與此同時,“數字革命”的三大標志性事件之一即為平臺化,在互聯網這種高維媒介中,技術要素在內容生產和分發維度產生重要驅動力,平臺化也是傳媒生態進化與演變的基本路徑之一。對于平臺的研究,學界當前主要處于平臺的技術以及技術驅動下的社會新形態與新趨勢(1)蔡潤芳:《“圍墻花園”之困:論平臺媒介的“二重性”及其范式演進》,《新聞大學》2021年第7期。、融合演進的平臺(2)常江、狄豐琳:《數字新聞業的平臺化:演進邏輯與價值反思》,《編輯之友》2022年第10期。、平臺理論的語境化問題(3)姬德強:《“困在系統”之外:一個數字平臺研究的國家理論》,《編輯之友》2022年第10期。三個維度,具備智能化、平臺化特征的智能媒體平臺既是當下融媒體發展的實踐探索,也是“未來媒體”樣式的理論想象與建構。
重大突發事件是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突然發生的,能引起社會連鎖響應和嚴重后果,并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惡性危害事件。隨著烏爾里希·貝克筆下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來臨,社會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各種人為、自然的災難發生頻率增大并給社會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智能媒體平臺是重大突發事件相關信息的主要傳播渠道,同時基于智能媒體平臺形成的新的媒介生態在內容生產、分發等方面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已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間信息內容顯著地影響人們采取防護的行為傾向,體現了信息渠道在應對疫情中起到的重要作用(4)黎藜、李孟:《打破健康傳播中的“無形之墻”——宿命論信念和信息傳播對疫情中公眾防護行為傾向的影響研究》,《傳媒觀察》2021年第6期。。
智能媒體平臺既享有技術發展的紅利,也潛藏著倫理危機。“倫理”源于希臘語“ethos”,指外在的風俗、習慣以及內在的品性、品德。傳媒倫理學通常被認為是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與社會哲學密切相關。在我國,學者通過案例分析抽取新聞倫理問題域,遵循真實、客觀、隱私保護、人文關懷等倫理準則,對于諸如網絡言論失范、網絡謠言等問題,學者建議明確倫理邊界(5)曹海琴、賀金瑞:《論自媒體的倫理邊界及其保障機制建構——以微博中的網絡謠言為例》,《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形成一系列完備的理論框架和經系統分析的研究成果。國外有關傳媒倫理的系統化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倫理原則體系構建方面,例如康德的絕對命令原則、密爾等人的功利主義原則對西方研究產生一系列影響;其次在新聞業自律方面,學者傾向于制定行業規則和相關具有實操性的指標體系。在研究方法上,我國傳媒倫理多以案例分析與實證研究為主,西方多使用個案研究以及基于個案研究的道德推理。在智媒時代,媒介倫理表現出從新聞倫理到信息倫理的轉向,主要體現為機器算法價值觀運作的“黑箱化”及習得性人類偏見等方面(6)陳昌鳳:《媒介倫理新挑戰:智能化傳播中的價值觀賦予》,《新聞前哨》2018年第12期。。
綜上,我國學者已經意識到智能技術在媒介領域的應用中業已引發或可能引發的問題,而西方的研究也呈現出對智能技術可能引發“危險的錯覺”的隱憂(7)Hollis Kool,“The Ethics of Immersive Journalism:A rhetorialanalysis of news storytelling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Intersect,vol.9,no.3,2016,p.6.。伴隨著媒體的平臺化進程加快,對于平臺化社會中出現的一系列倫理問題成為傳媒倫理研究的全新課題。智能媒體平臺的演化發展、產制流程與傳媒倫理相遇產生一系列化學反應,諸如假新聞泛濫和“后真相”問題(8)史安斌、王沛楠:《作為社會抗爭的假新聞——美國大選假新聞現象的闡釋路徑與生成機制》,《新聞記者》2017年第6期。,以及算法導致的一系列倫理風險(9)楊保軍、杜輝:《智能新聞:倫理風險·倫理主體·倫理原則》,《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隨著智能媒體平臺已廣泛應用于各類媒介事件的生產與分發,網絡社會不斷深化成為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媒介生態社會,生態系統的隱喻可以成為整個社會的隱喻,媒體生態中的內容經傳導、疊加、演變、升級,使小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大的矛盾風險挑戰。因此本研究以智能化、平臺化發展趨勢下形成的智能媒體平臺為關注點,選取重大突發事件場景,基于內容生產維度和算法分發維度探討平臺媒體傳播邏輯下已經出現的倫理問題或潛藏倫理危機的問題,試圖尋找可行的平臺規制策略。
一、智能媒體平臺在內容生產維度的應用及倫理問題
(一)沉浸式內容生產與災難新聞
媒介環境學派對于技術在人類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提示音,無論是國內還是世界范圍內的各個國家,都經歷著技術給社會發展帶來的日新月異的變化。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為驅動媒體轉型升級作出戰略部署。2020年,《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指出,“要以先進技術引領驅動融合發展,用好5G、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革命成果,加強新技術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前瞻性研究和應用”(10)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體現了技術對于媒體融合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保羅·萊文森提出的媒介補償性功能的理論框架下,每一種媒介都是對先前一種媒介的變革,這種進步與革新都在不同程度上補償了其前一種媒介的不足,智能化延伸了媒體的外延,將新聞傳播推向“以人為媒”“萬物皆媒”的時代。MGC、AGC的智能化生產方式應運而生,傳統媒體行業的采寫、生產、分發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在選題策劃、采編流程、內容生產方面呈現出鮮明的智能化、平臺化特色。隨著媒體的智能化、平臺化路徑的不斷延伸,在人的媒介化過程中,數字人在“第五空間”中留下的數字痕跡和數字足跡成為基于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系統的媒體平臺收集用戶畫像和網絡行為數據的“石油”,由此在認知維度上引發由傳統媒體時代的線性邏輯思維到新媒體時代的網狀邏輯思維的轉換,再到智媒體時代的沉浸式體驗,不僅從媒介維度上得以拓展,也延伸了人的感官系統以至認知維度。例如在2015年12月,新華社記者發布VR視頻《虛擬現實|帶你“親臨”深圳深夜搜救現場》記錄與報道深圳的重大滑坡事故,全方位展示真實的救援現場,讓公眾在真實的災難場景中體驗到緊張感與悲痛感。
但是,“沉浸式”的內容生產在增強公眾對災難現場“代入感”的同時也面臨著應用困境。以重大突發事件為例,媒體通過使用VR與AR技術生產出的“沉浸式災難新聞”,可以制造出在場感,受眾獲得“身臨其境”的直觀感觸,能夠在認知層面更加深化對這一事件的理解。“VR災難新聞”的生產就是在重大突發事件的新聞報道中運用VR技術,通過360度全方位對新聞事實的采集與錄制,經過后期技術編輯呈現在平臺客戶端上,用戶采用第一視角入駐新聞現場,“直接置身”于各類新聞場景之中,使公眾產生“缺席的在場”體驗,并引發共情感受。沉浸式災難新聞的第一視角敘事邏輯將受眾從觀望者轉變成參與者,過于真實的災難場景可能引發受眾在“代入”的過程中過度地感受到災難現場的沖擊、血腥的場面,極易在放大感官刺激的同時給公眾帶來心理創傷。與此同時,由于沉浸式新聞的制作需要經歷全素材獲取、動畫制作、3D建模等流程,新聞生產時間往往較長,與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產生了一定的時間差,即使在技術層面實現了場景的疊加,還原了真實的現場,但是其仍是滯后于事件發展的,并不具備預測功能,這就會引發用戶在面對災難場景時發出“無力回天”的感嘆。
(二)媒體建構風險與輿情顯化
重大突發事件往往會引發社會經濟破壞、生產停滯和社會心態的紊亂,導致內嵌于社會生活中的固有矛盾爆發,并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呈現出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當刺激能量過度匯聚超過精神裝置的容忍度時,個體將會產生心靈創傷,而刺激在無法卸載時也將產生一系列應激反應。媒體平臺在風險傳播中報道議題和報道框架失衡、用戶表達渠道不暢通等情況都將引發放大或忽視風險的情況,同時出現反向建構風險并引發次生危機等問題,從而引發公眾的情緒反應、認知反應、行為反應和生理反應等常見的心理應激反應(psychological stress)。
媒體平臺在疏通與聯結各方觀點的同時,通過具備強粘結性和互動性的反饋機制將風險信息外顯化,在平臺化擴散中使用戶實現風險信息的多渠道接觸,平臺化的多元路徑模式將會加劇用戶的風險感知,進而引發輿情的外顯化。輿情顯性化過程的隨機性伴隨重大突發事件的突發性、緊急性等屬性被迅速激活,輿情在互動中進行相互干涉從而導致傳播效能增強(11)李明德、朱妍:《復雜輿論場景中信息內容傳播風險研究》,《情報雜志》2021年第12期。。輿情信息在不斷的生產與再生產中匯聚超負荷的情緒、意見和態度能量,基于智媒技術下的網絡傳播模式特點,個人情緒在網絡空間中病毒式傳播形成的鏈接將會刺激整體性社會情緒的生成,智媒平臺在對事件本身的渲染中脫離對事件原因的追溯和責任的厘清,也會誘發公眾負面情緒的集中爆發。
與此同時,在痛點刺激下形成行為啟動,負面情緒持續擴散并引發群體極化效應,其中,以言論表達的情緒化、表達方式的宣泄性以及現實社會行為的破壞性為主要代表。此時,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共同構成了危機生成的內源動力和外源動力,在全方位、多層次認知激活的狀態下,對用戶心理狀態在社會中的平穩運行是極為不利的,容易誘發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對家屬的侵擾以及過度的災難美學渲染等不良效應。在智能傳播時代,社交媒體在新技術加持下的傳播效能持續迸發,算法機制與平臺機制的結合充分展示了智能媒體平臺的威力,諸如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臺對“人與算法之間的關系”的重視,使得這種平臺偏向將會嚴重影響用戶在重大突發事件中對某一問題的看法及態度。
美國現代新聞之父普利策指出,新聞記者如同“船頭的瞭望者”,喻示著新聞媒體的環境監測功能,不斷進化的媒體平臺也保留著“瞭望塔”功能,具備鏈接公眾與政府的橋梁作用,是一手信息的獲取者。智能媒體平臺通過對危機進行研判并將預警結果以信息發布的形式告知公眾,這時發布的主題更多的是事實通報等警示信號類內容。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傳播總是滯后于危機傳播,雖然伴隨著大數據風險研判、人工智能即時性新聞寫作等技術正在不斷實踐中構建相對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但是,對于重大突發事件的突發性和對媒體平臺報道的專業性而言,事件的性質和問題溯源尚未定性和懸而未決之前,媒體平臺的素養缺失也會引發懸疑新聞問題的出現。
二、智能媒體平臺在分發維度的應用及倫理問題
(一)病毒式擴散與“信息疫情”
重大突發事件切實關系到每個個體的生命財產安全,與個體利益息息相關,因而具備更高水平的節點喚起和節奏連帶性。互聯網是一種高維媒體,在互聯網平臺中,原本發生并影響某一局部的事件會迅速擴散形成全局風險,與重大突發事件相關的信息內容進入傳播鏈條,并以網絡化、病毒式擴散特征不斷進入被稱作“人類生活新疆域”的互聯網空間中,公眾視野迅速從“大世界”凝聚成為“小世界”。
在平臺化時代,用戶成為媒介生態中的一個個活躍節點,在Wilson的信息需求模型作用下,個體主動搜尋信息在減少信息量熵值的同時來影響自我的風險感知,信息內容的接收、評價與個體風險感知的動態變化是保持一致的。重大突發事件的破壞性和災害性容易使公眾產生過度的風險感知,個體在該情境下處于信息渴求狀態,用戶個人因素在不斷激活中形成“以人為媒”式的網狀信息擴散結構,大量經媒體平臺進行病毒式傳播的同質化的信息支配了公眾的信息偏好和注意力,不斷吸引著公眾對于這一問題的關注度,并不斷激活個體的傳播與再傳播意愿。網絡中各種社會關系以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方式進行著波浪式的涌動,傳播結構中的自組織系統在相互嵌套、相互聯結的過程中促進了風險信息的螺旋式擴散。媒體平臺中“@”“#”等具備鏈接互動屬性的功能,也不斷構建著信息傳播矩陣,在注入新媒體互動性邏輯后也在加劇著信息的病毒式擴散。
與此同時,平臺通過智能技術諸如自然語言處理和圖像識別對新聞信息進行降維、相似計算和聚類優化等操作來整合新聞信息,受眾接收到同質化和相似性的新聞信息,反復周旋于某一類信息維度之中,容易引發信息倦怠。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信息疫情”一詞被反復提及。“信息疫情”(infodemic)一詞由信息(information)和流行病(epidemic)組合而成。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信息疫情”是指在傳染病疫情背景下,包括謠言、小道消息在內的大量信息通過手機、社交媒體、互聯網以及其他通信技術快速傳播的現象,導致人們難以發現值得信任的信息來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導,并妨礙疫情防控有效措施的施行(1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Situation Report-13,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02-sitrep-13-ncov-v3.pdf.。由于重大突發事件具有突發性、緊急性、嚴重性特征,伴生出信息內容失衡、熱點問題失焦、社會心態紊亂、網絡謠言頻發等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疫情傳播和媒體平臺的信息傳播路徑是一致的,病毒的傳播和媒介賦權下的“病毒式傳播”齊頭并進。
(二)同質化分發與用戶的非理性行為
在信息內容精準分發的智能媒體平臺運營模式下,算法的碎片化和個性化使用戶被過度地包裹在相當同質化的災難信息中,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效應層出不窮。信息繭房的出現也會加劇社會恐慌和焦慮。與此同時,智能媒體平臺中的把關人權力持續下沉,意見領袖一呼百應地將原子化的個體匯聚起來并迸發出強大的能量。其中,負面能量將產生極強的社會破壞力,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邊界逐漸模糊,當同質的網絡負面情緒大范圍傳播時,對現實社會心態也會產生不良影響。大量網民接收錯誤信息,便容易產生一系列非理性行為,如疫情中出現的“瘋狂搶購雙黃連”事件等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就是由于部分媒體平臺的不當報道而鬧的“烏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大量流調信息的公布是為了讓公眾進行更好的防疫,但是部分媒體平臺過度的隱私曝光和用戶信息不合理使用行為也引發了網絡造謠、“人肉搜索”、網絡暴力等失范行為,對當事人產生極大的精神傷害。如2021年9月21日,黑龍江新增1例新冠陽性確診患者,對此媒體公布了首例確診患者行程軌跡,并將信息精確到了該確診患者家的門牌號。隨后,相關包含大量個人信息的word文件在各大媒體平臺中瘋傳,網友給確診患者貼上“轉場皇后”“哈爾濱毒王”等帶有人格侮辱性的標簽。
智媒體平臺在這種貌似客觀的數據收集過程中也蘊含著價值觀的“黑箱”,數據表面上看似客觀,但實際上數據來源的可靠性與權威性仍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諸如水軍在智能化信息內容傳播中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傳統水軍轉向更高數量級的人工智能水軍。與此同時,社交機器人在內容發布、轉發、點贊等方面對社交媒體進行深度參與中也會進一步影響人們對事件的理性看法。例如有研究表明社交機器人會對相關議題產生操縱問題(13)師文、陳昌鳳:《分布與互動模式:社交機器人操縱Twitter上的中國議題研究》,《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5期。。而重大突發事件考驗了一國的應急能力和應急管理水平,部分西方媒體平臺在程序設定中暗含傾向性影射,在降低環境多樣性的同時包含不同價值觀的政治哲學博弈,例如部分西方媒體平臺帶有歧視、傲慢和偏見的觀點來輸出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將具體個案包裝成公共事件,企圖煽動網民的不滿情緒,社會個體逐漸被負面情緒環境所影響,不利于社會心態的平穩運行以及社會秩序的維系。
“信息疫情”的肆虐一方面對記者和專業媒體的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更好地滿足人們“關鍵性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也推動了各界對加強媒體平臺的信息治理不斷形成新共識。因此,將“規訓”算法適度地應用于重大突發事件中的信息內容生產、發布,使智能化傳播在傳媒倫理的框架下有序運行,才能不斷促進形成風清氣正的互聯網空間與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三、平臺規制:數字技術與人文關懷兼備的智媒平臺應用
“智能化+平臺化”是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的必然方向,智能媒體技術的不斷應用也成為媒體內部競相擁有的“硬實力”和全媒體建設的戰略方向。在“深度學習+應用場景”的產制模式下,應持續走兼備數字技術和人文關懷的智媒場景化應用路徑,改善智媒時代的傳媒倫理問題,推動智能媒體平臺更好地履行信息傳播職能,并不斷造福人類社會。
(一)媒體平臺:優化內容生產手段與平臺運作標準
媒體平臺采集信息、聚合信息、發布信息等行為,被看作是現代社會化解公共危機的關鍵環節。1972年,唐納德·肖(Donald Shaw)和麥克斯威爾·麥克姆斯(Maxwell McCombs)在總統大選的調查研究中證明了媒體議程設置功能的存在。媒體的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功能為互聯網居民繪制了在虛擬空間生存的“關注榜單”,在“以人為媒”的催化下鏈接線上與線下,實現時空耦合,進而生成現實社會中的熱點事項,通過向公眾提供真實、科學和有效的信息,影響公眾的感知和行為,進而降低風險對個體與社會的危害程度,達到預期的治理效果。因此良好健康的風險傳播生態需要媒體平臺提升反思性的實踐自覺,追求對事件的科學認識,在批判中更加洞察傳播環境,并在微觀上通過平衡報道等手段達成。
明確技術邊界,構建具備可評估的智媒體場景化運用與操作標準,促進智能媒體平臺在重大突發事件場景下形成行之有效、為之有益的一套運作流程。在重大突發事件場景下,智能化媒體平臺能夠幫助解決傳統新聞生產的時效性不足問題,實現新聞信息快速整合發布,在突發事件的直播和災難新聞報道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技術維度實現了公眾對于“新近”的訴求,但如何提升新聞的真實性、權威性和深度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因此,可以充分發揮不同媒體類型的長處,例如主流媒體和專業媒體以專業權威的屬性吸引公眾對重大突發事件的關注,由對“鏡像風險事實”的客觀性報道轉向“面臨風險行動指導”的解釋性報道,為公眾提供更為全面的信息圖景與評論性文章來對問題進行全面的闡釋和清晰的界定,個人媒體以相對自由的傳播方式對相關信息進行細節性補充,發揮平臺優勢,促進優勢互補。
(二)技術規制:明確智能媒體平臺的價值規范
技術發展推動了倫理學研究的熱潮,諸如機器人倫理(Robot ethics)、信息倫理(Information Ethics)、算法倫理(Algorithmic Ethics)等問題成為倫理研究的熱門領域。基于此,傳媒倫理的研究范疇也隨之由新聞工作者、新聞機構延向智媒技術和背后的技術邏輯,將智媒技術視作獨立的倫理行動者抑或是客體來判定倫理問題仍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以價值引領智媒技術的科技向善邏輯是從一而終的,構建以人為本、避免濫用的行為規則和共生繁榮的智媒應用生態是傳媒倫理理念更新的必要路徑,需建構起適應智媒時代的媒介倫理結構體系來指導智能媒體平臺的傳媒實踐。
首先,對于智能技術是否具備倫理責任主體地位的問題,牛津大學弗洛里迪(Floridi L)和桑德斯(Sanders J W)教授依據行動者的互動關系,確立了交互性、自主性和適應性三個標準(14)Floridi L,Sanders J W,“On the Morality of Artificial Agents”,Minds & Machines,vol.14,No.3,2004,pp.349-379.,目前智能媒體平臺的行為主體仍是具備主體性特征的人。隨著以算法為核心的智能媒體平臺在自適應和自主化學習能力等方面不斷提升,與學界目前探討的有關人工智能新聞的著作歸屬權、追責等問題中有關“人-機”的主客體關系之辯的難點相同,對于此,筆者認為應拋開技術邏輯本身,對于目前的發展情況而言,智媒平臺的驅動者首先是擁有技術的從業者和技術的使用者,人和智能媒體平臺是主客二元的關系。因此,與其只危言聳聽于后現代性中的技術風險,單純地強調事后追責,不如將對傳媒行業及其從業者的智媒體操作規制納入法制化、有序化的運行軌道中,落實媒體平臺的主體責任,通過將人類倫理、價值觀與社會規范納入算法模型中,來對智能技術進行糾偏。與此同時,不斷推進算法透明化,揭開算法黑箱,將平臺和用戶置于平等的位置。對于必要的數據采集行為,需將采集的目的、用途及流向告知用戶,并征求用戶同意,履行告知義務;對于非必要采集的數據,履行回避義務。
用理念與價值觀引領智媒技術發展,需要不斷探索適應人類發展的技術向善新方案。媒體平臺應充分體現價值“在場”,對于我國媒體平臺而言,媒介技術的應用邏輯需始終在科技向善的大旗下,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來驅動智媒體,摒棄利益作為內容生產的唯一價值取向,審慎對待“賽博格”時代中基于資本賦能的技術決定論調。智媒體發展不僅需要攻克技術發展難題和實現應用場景拓展,而且是實現包含體制機制、人才引進、資金投入等方面在內的智能化媒體應用的戰略部署,是對于社會制度、文化觀念、道德倫理等方面的全方位融入。對于媒體從業者而言,在堅守行業底線,使用智媒體創造收益的同時,應兼顧追求人類福祉的社會公益屬性,對于此,需要傳媒從業者不斷加強理論素養、道德素養和技術素養,不斷成長為媒體融合時代的媒體平臺全能型編輯。
(三)多元共治:形成用戶、政府、法律多元主體監管模式
在價值理性和行業規范的規約下,智媒平臺應將其新技術、高效率等優勢應用于重大突發事件的風險識別、預警、輿情監測與輿論引導的全過程中,承擔起凝聚社會共識、傳播主流價值觀的職責。媒體平臺內部在加強行業自律、完善行業規約、樹立媒體自律精神,謹防由于媒介倫理問題引發的二次危機等問題,形成媒體信息發布審核的“第一道關”的同時,還需要用戶、政府、法律形成多元主體監管的共治模式。
首先,在用戶監管層面,智能媒體平臺已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戶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使用素養來應對網絡謠言、虛假新聞等傳播亂象和良莠不齊的信息內容,對待媒體平臺中的內容要審慎思辨,杜絕偏聽偏信、罔顧事實真相的二次轉發行為,主動舉報有失范行為的媒體平臺。合理使用與謹慎對待自己的隱私數據,對待平臺不合理的數據使用行為要及時進行投訴舉報,避免隱私“裸奔”。同時,用戶也需合理地使用智能媒體平臺,避免自身成為謠言等不良信息內容的生產者與傳播者。
其次,在政府監管層面,政府治理應由事件驅動的回應型轉向需求甄別的主動型,建立起一套規范化的信息收集與發布流程,在監管部門的人才隊伍建設、業務預算支持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相關部門秉持認真負責的態度應對媒體平臺中信息內容的傳播問題,這對于營造風清氣正的互聯網空間至關重要。嚴格處理違反公序良俗、法律法規的媒體平臺,根治媒體平臺中的各種傳播亂象;建設輿情預警與防控機構,通過大數據技術獲取媒體傳播數據、探測網絡空間的輿論走向,實時監控媒體平臺的運作軌跡與行為特征,在入網許可等方面行使政府把關職能,明確部門之間的職責,做到政府監管有道、公眾投訴有門。
最后,在法制規范層面,要不斷優化既有的規制方案,并在法律層面上予以規范。技術的快速發展對于法律層面的規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應避免將互聯網視作“無法律、無管治、無國界”的“三無地帶”。目前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對此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以英國為例,英國新聞投訴委員會(The Press Complain Commission,PCC)通過制定“歐洲最嚴格的傳媒業務準則”對媒體行業內部形成嚴格約束,形成一個由16位報紙或雜志編輯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制定和修改《報業行為準則》,此后業界也相繼出臺了媒體平臺使用指南,對信息內容來源、虛擬賬號、新聞核實等業務作出明確規定。對于我國的智能媒體平臺的法制監管而言,應將營造風清氣正的互聯網空間作為法制監管的目標,在內容層面和傳播層面形成全方位的媒體平臺生態治理環境,建立健全符合智能媒體平臺產制特征、運作流程和業態模式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監管原則、清晰界定智能媒體平臺各方使用者的權利與義務,普及監管的法理解釋。最后,要加大對違規智能媒體平臺的處罰力度,并建立行業黑名單,形成對全社會的警示效應。
結語
智能媒體平臺作為社會信息系統的樞紐之一,可以在平臺優勢下提升信息傳播速率和信息到達率,在智能化技術演進下,實現信息的多樣態與立體化傳播,為媒體行業提供了新動能。但是,智能媒體平臺在傳播實踐中誘發的一系列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對于可能誘發的倫理問題也是要保持警惕的。其中,數據收集為人們保護隱私敲響了警鐘。由算法控制的信息內容推送模式不斷提示著人們陷入“信息繭房”的危機,大數據和算法更是被視為“被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媒體平臺的開放性也不斷對媒體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當今媒體平臺問題頻發的大背景下,亟需結合時代特征和技術演變特征,探討更有效的智能媒體平臺規制路徑,在當下技術與平臺社會的協同演進中,形成數字化信息技術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福祉的發展模式,這離不開學界圍繞多元治理主體進行更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