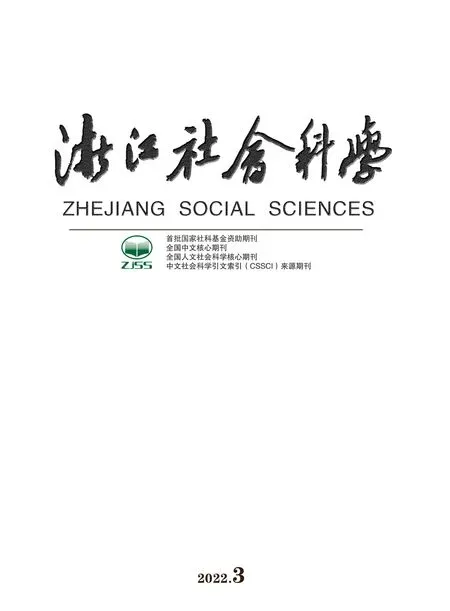王充《論衡》疾虛妄的生命思想
□ 錢志熙
內容提要 在漢代神學目的論及神鬼之說、神仙方術流行的情況下,王充《論衡》繼承道家的自然哲學生命觀,闡述其以自然元氣為基本哲學理念的生命本體論,認為人類生命是萬物的一種,生與死體現了物質發生與消亡的基本規律。秉持這種基本觀念,《論衡》在《道虛》《論死》《訂鬼》《言毒》等篇中,辯說歷史上各種有關鬼魂與神仙傳說的虛妄性,反復論證生必有死、死后無鬼、修道不能成仙這樣的觀點。為了喚回人們的常識理性、貫徹實事求是的精神,《論衡》采取繁復、周密的論述方式,并采用“荴露”即明白易懂的行文風格。這其中體現了樸素的科學實證精神。王充的生命思想,無論從其基本理論還是論證方式上來說,都達到了中國古代自然哲學生命觀的高峰。
整個漢代的政治及倫理道德領域,都彌漫著一種具有神學目的論性質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思想。同時,原始神話在漢代仍有很多遺留,各種神仙方術正處在方興未艾的狀態。可以說,漢代生命意識領域,整體上說是傾向于非理性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屬于理性范疇的自然哲學的生命觀,在漢代仍然獲得巨大的發展。自然哲學范疇的生命觀,是建立在對自然死亡的認識的基礎上的,亦即人類對生死規律的明確認識。這是先秦諸子基本的生命思想。漢代諸子之學,是春秋戰國諸子之學的繼續。漢代諸子的主流,不僅繼承春秋戰國諸子的自然哲學生命,而且也繼承了其理性思辨精神。而桓譚、王充等人在讖緯、神仙、神鬼之說盛行,并予整個政治與文化施以很大影響的時候,堅持道家原始的自然生命觀教義,以及儒家不言怪力亂神的樸素唯物的立場,并做出發展。①
王充生命思想的基本宗旨是疾虛妄。《論衡·對作》云:“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②他所說的虛妄之言,其產生的原因,除了一般的思想混亂及修辭之失實外,天人感應之說、鬼怪之說、神仙之說,都是根源于非理性的生命意識與觀念的。所以,從廣義來說,《論衡》全書都體現了王充理性的、自然哲學的生命思想。這其中對生死規律的論述,對鬼、仙之說的質疑,集中地體現了王充的生命學說。所以,在研究漢代的生命觀及其文學表現方面,《論衡》一書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價值。
一、《論衡》對生命本體的看法
《論衡》所秉持的生命觀是建立在自然哲學思想基礎上的。王充在《自然》篇申述了天地無意志的基本觀念: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為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以道家論之。(《自然篇》)③
這種觀點,與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④的觀點,當然是一源所出。他批評當時流行的那種將萬物與人類都說成是天道意志的體現的目的論觀點。所以,《論衡》的生命思想從基本傾向來看,是繼承道家的自然哲學生命觀,即他自己所說的“試以道家論之”。這從他以《自然》名篇即已可知。近世學者論王充,也多強調這一點,如鐘泰即云:“仲任之學,亦本之黃老,一出于自然”⑤。金春峰也認為:“王充哲學思想的核心或基本概念是元氣自然論。”并指出“元氣”之說,是漢代思想界提出的新概念。⑥“自然”之說,可以說是構成《論衡》一書的基本宗旨。他對一切自然現象與生命現象的認識,都貫穿著自然之說。
在對生命本體的認識方面,王充堅定地執持元氣自然之說,強調生命從本質來說,是由物質構成的,當然也體現了物質發生發展的規律。當然,這種物質,王充將其概括為一種“氣”,而氣之根本,或者說具有萬物本源、世界本體意義的氣,則是“元氣”。人的生命,即由天地元氣所生:
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稟于元氣,與物無異。(《辨祟篇》)⑦
人稟元氣于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木(埴)為簋廉(廡),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定,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論之,人命短長,可得論矣。(《無形篇》)⑧
在《論衡》中,王充提出“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觀點,就是針對學道求仙得長生之說而提出的。神仙之說,在漢代是普遍流行的,不僅存在于傳世的仙經道書之中,而且在漢代的文學藝術,如畫像石、樂府詩、辭賦中也都有突出的表現。王充認為人是天地之氣所生的一種物質,如同天地中萬物一樣,有他的形體固定性。人從生到死,只有形體外貌上的變化,生命本質并不會變化。即人不可能超越死亡的規律而變為長生不老的仙人。傳說中的神仙,都是虛妄之說。退一步,縱使有神仙人,那也是另一種奇異的物類,與我們現實中的人類不可能是同一種生物:
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于云,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原校:蛾,各本作娥,今正。)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也。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無形篇》)⑨
王充所執行的是漢儒崇尚的實事求是的實證觀點,所以對于當時尚無法實證的所謂海外毛民、羽民,他采取了闕疑的態度。按“蟬娥之類,非真正人。”蟬娥注者多作蟲類。但按照這里的語意,應該即是傳說中的“嫦娥”。但他堅定地說,縱使有“蟬娥”,那也只是一種不同于人類的異物類。又假如真有《山海經》中所記載的海外三十五國的“毛羽之民”,那也是自然生成的,并非神奇變化而成。表面上看,王充似乎是對流行的神仙之說做了一些讓步,事實上仍然在申述萬物皆自然所生的觀念。只是他從事實尚不清晰而闕疑的基本學術思想出發,承認有些事實的真相我們還不知道。王充常常采用這種看似迂繞的假設方法,來貫徹其一切求證于事實,一切符合于邏輯的學術宗旨,正是其學術精神的魅力所在。后來嵇康的《養生論》中也說:“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至也。”⑩這種觀點,明顯地受到王充的影響,但卻將王充的假設坐定為一種事實,徑直認可記載中的“神仙”的存在。雖然嵇康也以“自然”為說,但事實上他的這種思想,是對原始道家及漢代王充等自然派的自然觀的一種退步,預示著后來玄學中的玄虛生命觀,以及道教與佛教超現實、超自然生命觀流行的前兆。當然,這種神仙屬于異類的說法,與道教的神仙說還是有本質上的差別的。
王充對人類生命本體來自元氣,如同陶冶者手中的陶坯這樣的思想,是受到了《淮南子》的影響。《淮南子》對生命的基本思想,是認為天地生人,陰陽二氣化生萬物,人之精神來自天,骨骸來自地。生命結束時,精神歸于天,骨骸歸于地: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所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訓》)?
生命即為天地自然所生,所以生不為德,死亦不為酷。天地生人,亦如陶者陶坯。王充進一步發揮來自道家的這一派觀點,并運用這種“精氣”的學說對鬼神作出新的解釋: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于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神。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論死篇》)?
人的生命征象存于精氣,精氣存于血脈中,所以人的精神,本質上仍屬于物質活動的現象。人死就是這種所謂精氣的物質活動的停止,所以人死不能變為鬼。縱使人們在荒忽中見到一種鬼神形態的東西,那也不是人類的靈魂,而是自然之氣所生的別種物類。他還用漢儒常用的音訓方法,訓鬼為歸,訓神為伸,認為鬼神是陰陽二氣所生,陰氣為鬼,陽氣為神,根本不是世俗迷信者所說的具有人格性質的鬼魂與神祇。王充的思辨方法,是并不簡單地否定鬼神之說,而給鬼神以新的解釋。這是用理性來給傳統遺存的非理性的概念與觀念進行新的詮釋。這是中國古代知識者所常用的方法,但同時也使新觀念與舊觀念之間產生了復雜的糾纏。王充對鬼神的新解釋,所采用的也是這樣一種方法。宋代理學家的鬼神為二氣之說,如張載所說的“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等說,即是推演王充的觀點而成的。
《論衡》對生命本質及生死之理的闡述,也包括后面要論及的他的無鬼論、無仙論,其實帶有一種古代科學的性質,體現了科學實證的色彩。早在上世紀30年代,學者們就已經注意到《論衡》的這種科學精神。王緇塵《懷疑與迷信——讀〈論衡〉》一文,即認為王充的懷疑精神,代表了一種科學的態度。“只看《論衡》一書,對于經典舊說,社會謬見,不合事理之處,無不盡量抉斥,不遺馀力,倘有人因其說而作進一步的探究,則一切科學早發明于中國,何待數千年后,尚在掇拾西方科學家牙慧。”?他的說法雖然有些簡單化,但認為王充的懷疑精神與近代西方科學相近是有道理的。其實王充思想與科學的接近,不僅在于懷疑,更重要的是從懷疑出發,采用常識經驗及觀察物理的方法,更近于一種科學實證的方法。正是這種科學實證式方法的使用,使王充雖生于“迷信空氣最濃厚的漢代,獨能不為社會錮俗所束縛”?。當然這種科學實證的方法,是建立在自然哲學生命觀之上的。
二、《論衡》的無鬼論
在人類生命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在擺脫了原始人類生死混沌的意識狀態,對死亡事實有了明確的認識之后,就有靈魂獨立于身體而存在的觀念產生,鬼神之說即依據于此。它雖然很早就受到理性的質疑,但卻一直堅固地存在于早期人類的意識中,而且形成很龐大的歷史文獻記載。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屬于歷來被人們推崇且具有權威性的經典,如《左傳》所記載的鬼神之事。同時,鬼神觀念也不斷被一種文學性的虛構方法敘述著,成為文學的重要表現對象,其中不乏絢爛的藝術花朵。但這種在今天看來屬于文學創造的成果,有時也轉化為現實中人們的生命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們研究鬼神觀念發展史的復雜性。事實上,魏晉以后的鬼神論者,就曾利用經典甚至文學作品中的鬼神之說和鬼神形象,來證明鬼神的確實存在。王充所要解決的,不僅是現實中人們觀念里的鬼神意識,而且要面對包括經典在內的大量有關鬼神的記載。
王充用一系列的篇章來申述他的無鬼之說。他首先從論述死亡的本質出發著《論死篇》。世人認為人死為鬼,有知,能害人(當然也包括能福人)。王充從其元氣化生萬物的觀念出發,認為人與其他物類,都是物。物滅后不能為鬼,何以人死獨能為鬼?人實為精氣所生,凝成血脈、骨骸,并有精神知識行于其中。人死骸骨歸地,精神消散歸天,重新化為元氣。而人們說的鬼,居然還擁有人們生前的形狀。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骨骸精神已經回歸天地,就不可能還有一種形體化的鬼神的存在。他用粟米與囊橐的關系這樣淺顯的日常生活經驗來說明。粟米還在盛在囊橐中時,能夠看到囊橐的形狀,一旦從其中流散出來,就只見粟米,不可能再看到囊橐的形狀。人的形體也是這樣,“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接著,他又用人們的常識經驗來說明。他指出,自古以來,死者以億萬計。如果人死為鬼,則“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果真有鬼,則應該到處可見,“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而事實上,縱使我們承認文獻中記載的鬼的事情有根據,但它卻是一種極罕見的情況。所以,說人死有鬼,是無法從常識得到證明的。
王充認為人類的生命,能夠繁殖延續,但卻不能死后復生,或者變為具有生前全部形狀與性能的鬼魂。這就如天地之性,能使火滅后,重新發生火,但卻不能讓已經燃盡的死灰重新生火。還有,世俗認為人死為鬼,但人死后衣服腐爛,人能為鬼,衣物必不能為鬼。縱使有鬼,也應該是裸袒之形?何以人們傳說看到的鬼,還穿著生前的衣物呢?這也可見其虛妄。王充的這種論述方法,雖然是樸素的、經驗的,甚至有時還讓人覺得有著思想上的粗糙性。但在生命科學還不夠發達的時代,使用樸素、日常經驗的常識來破除虛妄的鬼神之說,無疑是呈現著一種思想的光彩的。更何況,王充的生命思想,是以其元氣自然的基本哲學觀念為基礎的。比如他用元氣自然的原理來論述死后無知的道理: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生,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
這種分析,是具有一種理性思辨的深度的。以未生無知來證既死也不可能有知,充分地闡述了生命的物質性。后來南朝無神論者認為人死后無神,可以說是王充思想的繼續,但在思辨性方面還沒有達到王充的深度。
死亡說到底是生命活動的一種現象,也可說是生命活動的一個過程。盡管這是個體生命活動最后的一種現象、最后的一個過程。但它的活動性質,與生命活動中的其他現象都體現了共同的規律。王充認識到這一點,他還將夢、殄(昏迷)、死三者合論,認為夢與昏迷,在現象上與死亡有共同的表現。人在夢中不能記憶醒時的狀態,昏迷時沒有知覺,死后也不可能還能延續生前的知覺與知識。雖然這種論述方法顯得有點粗糙,因為后面兩種生命活動現象,夢和昏死時候,生命活動并未結束,與死亡這一生命現象畢竟有本質的區別。所以夢中的經驗、昏迷中的經驗,無法用來證明死后的情形。但王充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能把死亡看做是生命活動現象之一。
對于文獻記載及世俗流傳的鬼魂報仇的說法,王充也同樣用一種常識經驗的方法來論證其虛妄。他說如果死后化為鬼,則為人所毆死、冤殺者,鬼魂應該報仇,或者告知親人替他報仇。但如果有鬼,那報仇被殺的仇家,也會成為鬼。其勢力應該還比先前被殺之鬼強大。又如妒夫媢妻,死后夫再娶,妻再嫁。如使有鬼,何以再娶再嫁者能得平安?他進一步從生命機理來分析,如他說言語是氣力所生,人死不再擁有氣力,所以傳說死人(鬼魂)說話是虛妄的。這一論辯中含有科學思維。總之,他從各個角度進行繁復、周密的論述,最后達到這樣的結論:“夫論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為,明矣!”?也就是說,人們所說的“鬼”,縱使存在這種事物或現象,那也不可能是人死后所化。人死后是不可能有鬼的。要破除神仙鬼怪之類的迷誤,其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人們回歸常識理性。
在《論死篇》之后,王充又寫作《死偽篇》《紀妖篇》《訂鬼篇》,對文獻典籍中記載的各種鬼魂神怪的故事進行分析,試圖給出合乎理性的解釋。
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王充的分析也是比較繁復的,也就是他自己所說“重文”的方式。他往往是先揭其無鬼之說的基本觀點,再從常識經驗以及社會倫理的一般觀念來說明。如《死偽篇》對傳記中杜伯、莊子義的鬼魂報生前之仇的故事進行分析。杜伯被其君周宣王冤殺,后當宣王出外田獵時奔起道左,射殺宣王。莊子義為其君燕簡公所殺,雖然殺得不冤,但也在道旁用彤杖擊殺外出的燕簡公。世人以此為人死為鬼,并能報仇害人之證。王充首先重申其在《論死篇》說過的“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的觀點。接著從經驗事實的立場,指出古來無辜冤死者無數,如比干、關龍逢等,都沒有聽說他們向君主報了冤。再者從道德上說,弒君是大罪,如果真有鬼,那像周宣王、燕簡公等人,也應該由比他們級別更高的鬼魂來懲罰,而不應該由其臣子以報私仇的形式來殘殺。再說假如真有鬼魂,那么這兩位君王被殺死后,他們的鬼魂難道不會再報復那兩位臣子嗎?做為君主的鬼魂,死后的勢力不是也比作為臣子的鬼魂強大嗎?所以,晉宣王、燕簡公之死,另有原因,人們見到他們生前曾殺其臣,就附會其為臣子亡魂所報。
王充總是這樣,從經驗事實與現實生活中的基本邏輯來否定這類傳說事實上的虛妄。有時候他也利用一些倫理道德規范,這其中也會顯示出他在思想上的局限,會影響他邏輯上的徹底性。如前面關于君臣關系在死后延續的說法。又比如他對著名結草銜環以報恩的故事的分析。這個故事,講的是晉國將領魏顆的故事。魏顆的父親魏武子,病未重時吩咐自己死后讓妾改嫁,但到了臨死卻又反悔,遺囑將此妾殉葬。魏顆執行父親清醒時的說法,將此妾改嫁。后來秦晉輔之戰中,魏顆遭遇秦軍中的大力士杜回,卻看到一個老人用草環絆倒杜回,從而為魏顆所獲。這一夜,魏顆夢到白天看到的這個老人來跟他說,自己就是魏顆父妾的父親,顯魂來報讓其女兒改嫁之恩。王充認為這個老人既然能報他死后善遇女兒的魏顆,當然也應該報答他生前厚待他的其他人,甚至殺掉他生前對他不善的人。何以唯獨選擇一個魏顆呢?他認為所謂老人結草,就跟黃石公教張良、白衣老人教漢光武一樣,都是妖象所結,而非人死后亡魂。
《紀妖篇》也討論了一些影響比較大的鬼神記載。如衛靈公在濮水上聽到一首新的樂曲,樂師師涓撫其音,說是徵調,是商紂時樂師師延演奏的亡國之音。后來晉平公一定要讓師涓演奏,導致晉國大旱,赤地千里,平公本人也得了癃病。王充仍然從他的人死氣散,不能再以人的形體出現,來批駁師延鬼魂在濮水演曲的可能性:
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途,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于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云吊屈原,屈原何不報??
他用屈原沒有顯靈報書,來論證師延之鬼無法出來鼓琴。這是一種同類相推的方法,看起來像是粗淺的論證,但這正是喚回人們的常識的一種有效的論證方法。他認為晉國旱、平公癃病,只是一種妖象,根本不是奏徵曲所導致的。自《禮記·樂記》有亡國之音之說,后世論樂都舉為真理。王充在這里其實是不同意這種亡國之音說法的。后來嵇康著《聲無哀樂論》認為構成音樂的要素“和聲”本身是一種自然現象,人心的感情寄之而生哀樂,聲音本無哀樂的屬性。唐太宗李世民也曾運用這種學說來質疑“亡國之音”的說法。?其淵源都可追溯到王充此論。又如記載中說趙簡子病,五日昏迷不知人。扁鵲來診,奇怪其脈象與當年秦繆公病時的脈象一樣。當年繆公病劇,魂至上帝之所,七日后醒轉。簡子可能也是這種情況。果然趙簡子在七日半后醒轉,并且自述到了上帝之所,上帝饗以鈞天廣樂,并令射死熊羆,給一翟犬。后來簡子出門,在道上被一人攔住,認出是在上帝那里看到過的一個人。他告訴簡子射死熊羆及獲得翟犬的預兆寓意。王充說:“是皆妖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也就是說有的事物因與人類樣子相似而被認為是鬼,是一種人類為了某種目的而假托鬼魂之說。
王充否定有鬼的說法,他仍然運用其元氣自然的原理,提出一種妖氣、毒氣之說。他把史傳中的種種人死為鬼顯靈或害人之事,最后總歸于妖象、妖氣、妖祥之所為:
妖之見出也,或且兇而豫見,或兇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也,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
那么,這種顯象為害的妖,究竟是什么呢?王充仍然是從“氣”的角度來加以解釋的,將其總歸為“太陽之氣”,其《訂鬼》《言毒》兩篇,有比較系統的闡述:
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為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
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他的基本說法,是說天既然能生人類之體,也能夠產生出那種類似于人類之體的形象。但徒有形象而沒有人類的骨肉精氣,所以恍惚即滅。其言下之意,是說人們所看到的鬼魂,就是這種東西。有一種評價認為王充的這種妖氣之論,“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唯心主義和有鬼論的泥坑。”“這種觀點實際上起到了為鬼神迷信辯護的作用”?,因此仍屬唯心的觀點。撇開唯心、唯物之說不論,王充的這種看法,其實是在事物不能盡知的前提下,堅持從其元氣自然的立場進行一種新的解釋。其立場與態度,與不假思索地相信鬼神之論有根本不同。這里其實體現了一種科學求索的精神。從這些論述,也可見證明“氣”的確是王充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盡管有些說法近乎神秘之說,但其基本立場是堅守著萬物皆氣生的物質主義立場的。
王充之所以對一些關于神鬼妖異的說法,不作簡單的否定的態度,而是試圖從其氣論來進行解釋。這因為他并不持有獨斷論的全知的立場,而是承認有未知的事物與現象的存在。在未知前提下,尋求一種盡量合理的解釋。雖然其結論不一定正確,有時甚至是讓我們現代人覺得粗淺可笑,但其中所體現出來的實證尋索與邏輯推演,卻近乎科學的態度。
《訂鬼篇》其實具有“原鬼”的性質,也就是從一種自然元氣的哲學立場,闡述鬼作為人們認識中的一種事物出現的原因: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則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虛見其物。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固劇身體痛,則謂鬼持擊之,若見鬼把椎鎖繩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
前面《論死篇》中,王充采用音釋的方法,解釋鬼為歸,即人死體消,作為一種物質歸于大地。這里則進一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鬼的產生。認為鬼魂是人們疾病后的恐懼心理所產生的一種虛見、妄見。他用存想生像的原理來解釋這個問題。他的這一理論闡述,可以說是新穎而深刻的,達到一種科學解釋的水準。也就是說他是從精神現象的方面來解釋鬼神問題的。戰國時期荀子已經有類似的說法,他在《荀子·解蔽》中曾云:“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此有之所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王先謙集解:“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之所疑惑之時也。”?歷史文獻記載的各種神鬼以及神仙的故事,除了一部分屬于完全有意識虛構與捏造之外,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有來由的。其產生的原因,大半可以從心理學的原理上得到解釋。王充作為一個漢代的思想家,能夠達到這一點,足見其思想力之強大。這與其堅定的元氣自然之說,以及力求征實的思考及論辨方法是分不開的。
三、《論衡》的無仙論
立足于人為天地元氣所生及生死自然之說,《論衡》不但是堅定的無鬼論者,也同樣是堅定的無仙論者。因為神仙之說理論基礎來自道家,所以求仙也被稱為求道。所謂“道”,即生命之道,從神仙家的邏輯上說,求仙是尋求一種最合理的生命之道。它的本質是原始地存在于生命之中的。得到了這種道之后,就能超越現實的生命。這正如后來佛教依據佛性來論證求涅槃成佛之可能性一樣。都是屬于宗教哲學的生命本體論。從《論衡·道虛篇》經常提到的“修道求仙”“方術仙者之業”“好道學仙之人”?,可見王充所面對的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活躍于社會各階層的神仙方術之士群體。所以,《道虛篇》在批評、辨妄的同時,也為我們留下漢代神仙道術活動的豐富史料,對于我們了解魏晉道教的前身“方仙道”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事實上,后來的道教徒如葛洪,在闡述神仙之說時,也常常運用其中的資料。當然他們是從與王充完全相反的角度來利用這些資料的。神仙方術之說,是造成“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的一大宗,王充因此專作《道虛》一篇,暢論神仙之說的虛妄,以及通過修道煉術能夠達到長生、成仙、升天等說法的不可信。
王充的無仙論和他的無鬼論一樣,邏輯的前提都是自然哲學生命觀。《道虛篇》在論黃帝、淮南王成仙之說為偽時說:
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于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
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在思想史上,莊子業已解釋清楚死亡在本質上是一種物質變化。王充對生命的物質性,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他的這個論述的精彩之處,在于講述清楚物有生,必有始,有始必有終。生與死,始與終,是一種對待相依的關系。取消了死,也等于取消了生。這是《論衡》批判神仙之說最為圓滿、自洽的一段文字。
按照一般的做法,只要對生命本質進行上述論證,就可以完成一種無仙之論。但是他跟其他無仙論者不一樣,他并不停留在這種獨斷論式的層次上。《道虛篇》仍然采取繁復重文的論述方法,對每個神仙傳說的虛妄失實的原因進行分析。其中的一種論證方法,可以說是經驗性的,甚至是“實驗性”的。
《道虛篇》舉出典籍及傳說的幾個著名神仙故事,逐一辨析其妄。這些故事分別是黃帝升天之說,淮南王修道術而舉家升天之說,方術之士盧敖游北海遇到飛行的仙人若士之說,河東項曼都學道升天而被放回人間之說,齊國方士文摯入鼎烹三日而不死之說。王充一概稱為“儒書言”。王充所說的“儒書”,泛指一般的典籍,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儒家之書。對于這一點,章太炎《原儒》篇有所解釋。?上述“儒書”所載,王充認為都是失實的,都是因為各自的現實的原因而被虛構出來的,是世人的誤會,也是方術之士的有意編造。如他認為盧敖、項曼都兩人,都是因為學道無成,難以面對他們家鄉的人,所以一個編造在北海遇仙,一個編造自己曾經去過天下,因犯事而被斥回人間。但是王充的駁論,并不停留在這個層次上,他對每個傳說,都進行詳細的辨妄。試舉其辯黃帝與淮南王之事為例。
王充先述“儒書”所記黃帝成仙的故事。黃帝采首山之銅,在荊山之下鑄鼎,鼎成之后天龍下降,垂下龍髯。黃帝接住龍髯騎到龍背,群臣、后宮也有七十余人一起登上龍背。其余小臣也想上,拉著龍髯不放。龍髯被拔斷后,還掉下了黃帝的一張弓。百姓仰望黃帝升天,抱著他的弓呼號。因此,這張弓就被叫做“烏號”,而鑄鼎地方就被叫做鼎湖。王充認為這是虛言。他首先從分析黃帝謚號入手。他說如果黃帝真是仙去,其謚號應該是 “仙”或“升”,不應該是“黃”。“《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皇),(德象天地曰帝)。‘黃(帝)’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他也考慮到黃帝時代有無謚號這件事還不能確定。但他認為無論“黃帝”這個稱呼是黃帝的群臣謚稱,還是后來人所追謚,都與仙道無關。其次,他認為龍是不升天的,只有潛淵的功能。再次,他說黃帝葬于橋山,如果真的是升天了,為什么還有墓葬?可見黃帝屬于普通的死亡,并非仙去。只有死去的人,才需要造墓埋葬。要說葬的只是黃帝的衣冠,那么群臣既然看到黃帝仙去,并沒有死,為什么還要埋葬他的衣冠呢?最后,他又迂回到倫理上去論證黃帝成仙之虛,認為治理天下與學習道術是不能兼修的兩件事。史載堯、舜這兩位圣君,都是因憂勤職事而身體干瘦如干肉、腌鳥肉一樣:“世稱堯若臘,舜若腒”。?黃帝和他們一樣,是治理天下致太平的君主,是圣,不是仙。黃帝要致太平,也必須像堯舜一樣。如果學道修仙,就會廢職事,不可能致太平。假使說致太平的同時還能成仙,那么堯、舜等圣君也應該能成仙升天了,但并無堯舜成仙的記載。從戰國燕齊之君,到秦皇漢武,以及后來的各個時代,都有帝王求長生成仙之術的奢念。《老子》一書,在講無為的治術的同時,也講后身而身存等生命思想。到了秦漢之際的黃老派,更將之改造成一套身國共治的理論。方術之士、道教徒將這種身國共治的理論與神仙方術相結合,販賣給這些耽于求仙的帝王。歷代統治者不僅因耽于求仙而疏忽國事,而且往往勞民傷財,嚴重地影響國家政治。王充的這一番論述,看似迂繞,實際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論衡》一書,不僅是在學術上辨析群書虛妄失實,而且常常飽含激情,具有深刻的現實批判性。
王充論證淮南王升天之說的虛妄,尤其能代表其運用常識理性來論證神仙學說之虛妄的方法。淮南王因為他生前愛好道術,聚集方士八公等人。所以死后有淮南王舉家升天的傳說,并且說其家的雞犬,因為吃了多余的仙藥,也隨之升天。王充說:“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歷史的事實,是淮南劉安的父親劉長因罪遷蜀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八公之儔,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儔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應該說,王充這一理性的分析,已經切中要害,也有助于我們認識同類傳說產生的原因。但這是一般的無仙論者都容易做出的結論。王充的貢獻,或者說他的獨特的、具有科學實證精神的無仙論,是從人類生命的物質性出發,對學道修仙者的飛升之說展開一種實驗科學式的辯論。他用一種繁復的解說常識的方式,來論證人非鳥類不能飛行的道理:
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形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
闡述了這個基本常識之后,王充還覺未盡。因為方士們還有所謂變化之說,所以王充繼續展開辯論: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筆者按,這是指對方的觀點)。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蟆化為鶉,雀入水化為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筆者按,這也是指對方的觀點)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不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
盡管從當時思想界甚至一般人已有的常識理性來說,神仙之說的虛妄是顯然可見的。但由于人們執著于一種永生的迷思,而方術之士又造作種種的修仙方法及成仙之說,固結于世俗的人心中。所以王充分析鳥類飛翔及事物變化的原理,來破除其說的虛妄。
王充的許多論證,在前提確定后,又采取假設的方法,來證明對方說法不能成立: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昆侖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徙昆侖,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徙之昆侖,又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
在我們今天看來,王充這樣的論述未免顯得繁瑣。但是,如果我們了解漢代社會神仙之說的流行,人們對生命的幻想之深,尤其是方術之說盅惑或說誘惑力之大,就能明白王充的用意。《論衡》對于他認為虛妄的傳說與學說,多是采用這種繁復論證方法的。在《自紀篇》中他交代這樣做的理由。因為這些他稱為“偽書俗文”的虛妄記載固結于人心:“通人觀覽,不能釘(訂)銓(詮)。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為古昔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辨爭,浮華虛偽之言,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化,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總之,要反復論證才能澄清事實,反歸淳樸之風。他的這種學術精神,和喜歡抗言論辨的孟子有些相似。其次他因疾俗情之迷誤而作《譏俗》《論衡》等書,面向的是大眾。所以必須訴諸常識,并且為應付世俗的種種疑問而做出解釋。他說自己做“《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這就是他所說的“《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即用一種很直觀的常識事實,進行反復、多層面、多角度的分析,并且不故作典雅隱曲之文,而是用“荴露”即明白易懂的行文風格。他不僅鮮明地申述了自己無鬼非仙的理性的觀點,同時也以近乎實錄的筆墨呈現了漢代鬼怪及神仙之說流行,以及對人們的思想與生活的深刻影響。這樣一種實證的方法,正是王充不同于獨斷論的地方,也是《論衡》與其他子書論述與行文風格很不一樣的地方。
神仙家的修道學仙的一些理論,來自道家。但在將道家合理的養生說改變為長生成仙學說的過程中,形成一種道教的神學生命哲學。如世人認為老子之道,恬淡無欲能致長久。神仙家就此發展出養精愛氣、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的說法。這種觀點,也是神仙家的主要說教之一。對于這些成仙之說,王充仍然運用常識理性來破除。王充辯論說,要是恬淡少欲、無思慮、無情欲就能永生,那么鳥獸、草木就是這樣的,但鳥獸的生存期比人還短,草木也是春生冬死。何以它們無情欲,反而比有情欲的人生命要短呢?可見恬淡無欲就能不死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又如術士常說辟谷能長生。王充說:“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于天,何能得久壽。”?古人常說人是“噍類”,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從人體的構成來論,今天看來雖然膚淺,但不失為實證科學式的觀察。他接著說,人們所說的王子喬那些辟谷不食之人能成仙,除非他不像普通人一樣長著口齒、孔竅,否則就不能不吃不喝而能長生。所謂“真人食氣,以氣為食”也是一樣的謬說。氣是什么呢?如是陰陽之氣,不能飽人,“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猛烈,胸中憒毒,不能飽人。”從經驗事實來說,彭祖倒是行過“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但最后還是死了。?又有如導氣養性之說,“道家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則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這就是熊經鳥伸、打通經絡、運動周天之類的說法。王充認為“此又虛也”。他說“夫血脈之藏于身,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久生乎?”至于“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但要“延年度世,世無其效。”藥只能除病,使身體復原,“安能延年至于度世?”?
養生可以延年,本身是符合生命規律的。王充本人也曾從事養生之術。他晚年因老病貧窮,“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但他深知這只是一種庶幾有效的養生延年之術。所以很清醒地認識到“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可見其終生堅持著人只是一種生物的說法,堅定地否定永生之說。
總之,王充的無仙論和他的無鬼論一樣,都是在認識了生死的自然規律之后,運用經驗事實和物質規律、生命活動的原理相結合的辦法,在幾乎難以展開正常辨論的神鬼有無、神仙有無的領域,主動地與唯鬼、唯仙論者尋求對話的途徑。在今天看來,他的論述過程雖然不一定很嚴密,而多流于經驗之論,缺乏深刻的思辨。而且在不少地方,采用先向對方讓步的方式,然后再尋找最終將其駁倒的方式。甚至以另一種看似唯心的說法,如用妖氣說、毒氣說代替有鬼說。對流行的非理性生命意識與觀念做了相當大的讓步。但是他自始堅持著人死不為鬼,人學道不能成仙,人是天地元氣所生,是萬物的一種,遵循著萬物的生滅、終始的規律,卻是那個時代自然哲學生命最輝煌的成就,甚至在整個中國古代,理性生命觀在對生命本體的認識上面,也一直沒有超過王充的思想。其對漢魏晉的疾虛妄、無神論、無鬼論、無仙論這一派,更是起了思想上的奠定作用。
余 論
王充的《論衡》,整體上表現了一種廓清各種虛妄的生命意識的力量。其對后來魏晉諸子,有直接的啟引作用。在中國古代理性與非理性生命意識及思想的發展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論衡》疾虛妄的生命思想,代表了中國古代秉持自然哲學生命觀這一派的思想高度。后來如南朝的無神論者,以及宋明理學家,都繼承以王充為代表的先秦漢魏的自然哲學生命觀,卻沒有繼承王充的近于科學實證的學術精神與方法。晚清學者宋恕詩云:“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此言完全可以用來評價王充在生命思想上的建樹。
從另一方面來看,《論衡》不僅是表述理性生命觀一派的經典,同時也保存了上古到漢代非理性生命觀的重要史料。這是因為《論衡》的寫作,以疾虛妄為宗旨,并且采用繁征博引的“重文”的風格。不僅征引前人正面的觀點和事實,而且對反面觀點的事實也大量征引。所謂眾書的“虛妄”失實之言,就是人們在針對自然界及人類社會方面產生的種種虛幻、錯誤的認識與傳聞,其中有一些是屬于原始以來生命意識與生命觀念的反映。所以《論衡》一書,從文獻資料的角度來說,其實也可視為原始以來的各種神話故事、神仙傳說以及鬼神傳說的淵藪。所以,就理性與非理性兩端來說,《論衡》一書,都具有集成的意義,是研究從上古到秦漢生命意識與生命思想的重要文獻。至于《論衡》中有關仙、鬼、神怪之說的一些敘述,常被后來的道教徒所征引,走向王充疾虛妄生命思想的反面,則是王充所意想不到。這也反映了古代生命思想發展中的一種曲折性與復雜性,以及人類理性進展之艱難。
最后,我們要補充的是,“生命思想”是一個廣義的范疇,包括對生命本體的認識,也包括對生命價值的看法。另外,對于生命個體的遭逢與命運的認識,也屬于生命思想的范疇。《論衡》的生命思想,也是在上述豐富而廣闊的界域中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論衡》一書整體地體現了王充對生命的豐富的、多層面的思考。其基本的立場,則是一種自然哲學的生命觀。但在對具體問題的論述上,有時也存在著矛盾。如《論衡》最前面的《逢遇》《累害》《命祿》《氣壽》《幸偶》《命義》《無形》《率性》《吉驗》《偶會》《骨相》《本性》等篇,主要是圍繞時命與性命等問題展開的,其基本立場仍然是一種自然論尤其是對傳統的天道福善禍淫的質疑。但在命運的問題上,王充是接受先天決定的命定論的。這其中的原因很復雜,我們可以理解為王充對于人生遭遇陷入困境時尋求的一種解釋,也與漢代士大夫階層流行的時命觀、士不遇論相關。這些都是屬于生命思想的范疇,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注釋:
①以上參看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三章“先秦道家的自然哲學生命”、第七章“宇宙自然大生命觀的形成”、第九章“漢代文學中的神仙主題”等章的論述。
②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卷29,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028頁。
③《論衡校釋》卷18,第676頁。
④《老子道德經》,載《諸子集成》,上海書店1986年版,影印本第3 冊,第3頁。
⑤鐘泰:《中國哲學史》,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頁。
⑥金春峰:《漢代思想史》,中國社會出版社1987年版,第478頁。
⑦《論衡校釋》卷24,第882頁。
⑧《論衡校釋》卷2,第91頁。
⑨《論衡校釋》卷2,第57頁。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小組在《論衡注釋》中作“娥蛾”,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0頁。
⑩嚴可均校輯:《全上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四十八,第2 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234頁。
?《淮南子》卷七,載《諸子集成》,影印本第7 冊,第99頁。
???????《論衡校釋》卷20,第761、762、762、764、770、1042、1042頁。
?張載:《正蒙·太和篇第一》,載《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9頁。
??王緇塵:《懷疑與科學——讀〈論衡〉》,載《諸子集成》,影印本第7 冊,《論衡》卷首,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1、3頁。
?《論衡校釋》卷21,第796頁。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28,第4 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40頁。
??????《論衡校釋》卷22,第800、807、827、823、827、814頁。
?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小組:《論衡注釋·訂鬼篇》解題,第3 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72頁。
?《荀子集解》卷15,載《諸子集成》,影印本第2 冊,第276頁。
?《論衡校釋》卷7,第274、275、276頁。
????????????《論衡校釋》卷7,第276、295、273、275、276、278、276、276、277、292、293、293~294頁。
?章太炎:《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49頁。
????《論衡校釋》卷30,第1043、1045、1055、1055頁。
?胡珠生編:《宋恕集》卷九,中華書局1993年版。